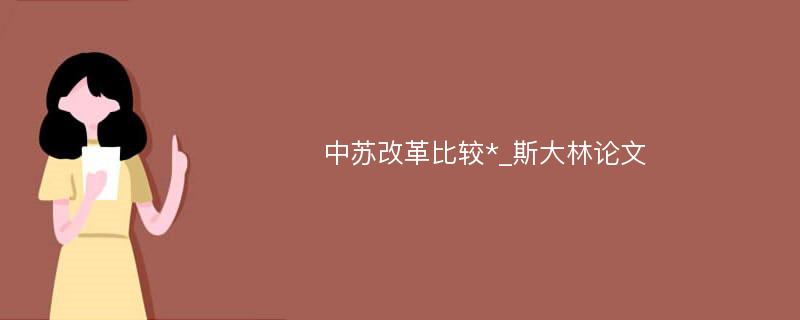
中国与苏联改革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扩展到欧亚十几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对旧模式、旧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是互相影响的。到1989至1990年,东欧八国和苏联的改革先后都以共产党的失败和下台而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的后果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着重谈对苏东剧变深层原因的看法,把我个人的研究心得和盘托出。
一、苏联东欧变化对我们党较大的三次影响
第一次影响是在1956至1957年。开始毛泽东是想从苏东变化中吸取教训,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重、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等十大关系要作较大变化。党的八大也指出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但是到1957年时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波匈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欧国家没有抓阶级斗争。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抓阶级斗争,造成了反右派的扩大化以及1958年后的“大跃进”。总之,第一次苏东变化,开始我们是想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但是很快就变了。变的结果,是1957年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左”,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深重灾难。
第二次影响是因为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闹事、罢工,波兰实行了军管。1980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端正路线的关键时期,特别是1980年8月18 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个人看法,应把这篇讲话视为整个改革的纲。可是这篇讲话发表后,发生了波兰事件。中央一些领导人据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一搞就会乱。
到1986至1987年,邓小平又一次感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因此他又一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已经收进《邓小平文选》的8.18讲话,又重在198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全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带动全面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又专门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第三次影响是由于1989年至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彻底剧变。16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柬埔寨在1979年最早垮了, 1989 年以后一下子又垮了10 国。 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如何吸取苏东教训的问题。 但是1990 至1991年,国内“左”的思潮明显上升,一些人不是正确地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教训,而是认为苏东剧变是胡乱改革开放造成的,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对西方开放,加快了和平演变。一时间出现了很多奇谈怪论。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了南方谈话,批判了国内上升的“左”的思潮,指出要从正面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南方谈话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而且强调“左”是根深蒂固地存在,所以着重是要反“左”。
总之,苏东变化对我们党产生了三次重要影响,前两次我们没有能全面地、准确地吸取苏东剧变的真正教训,“左”倾思潮有所上升,以至走了弯路。第三次也有“左”倾思潮上升的趋势,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这股风刹了下去。但是,“左”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二、关于苏东改革与中国改革比较研究的几点看法
能不能正确吸取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苏东改革和中国改革的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苏东改革失败了,导致三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导致三兴:兴党、兴国、兴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我们党大约只有3600万党员,现在发展到5800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实力大为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苏东改革为什么改了40多年,最后导致了三亡呢?对此理论界流行三种观点,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东改革失败,关键在于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改革,从赫鲁晓夫起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长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因此葬送了苏联。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苏联的变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三和”(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把苏联搞亡了。有人认为,苏联改革失败,“第一位掘墓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最后的埋葬者。中国改革成功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个看法是对的。但反过来说,赫鲁晓夫的作法应该怎么看?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揭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并不公正,确实一度引起思想混乱。但从其基本经济政策来看,赫鲁晓夫主义仍然是“左”,不是右。这个有关是非的认识问题不解决的话,就不能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实际上赫鲁晓夫路线是形右实“左”,少右多“左”。赫鲁晓夫不是苏联的第一个掘墓人,而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的第一个改革家,如果要说是“改革家”的话,他是一个蹩脚的、不高明的、不成功的改革家。斯大林“左”的东西,他并没有改掉,只作了局部修补。正因为斯大林“左”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改正,才导致了苏联后期的右。从赫鲁晓夫到1987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一直是“左”。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半以后,到1987年11月他的《新思维》一书出来后,才开始转向右的方面。
第二种观点:把苏联剧变仅仅归结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人认为苏联是被党内外三种资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搞垮的。一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二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即所谓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不忘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好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一些倾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撤换下来了。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警惕右,又防止“左”,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国根深蒂固的还是“左”。说苏联是资产阶级联合搞垮的,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苏联在1936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长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1991年剧变以前,苏联并不存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不能说苏联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靠戈尔巴乔夫等一两个领导人就能够把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2 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悄悄搞垮吗?这不能让人信服。说西方对苏联、东欧搞和平演变,不错。西方也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得逞,在苏联、东欧却能得逞?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还要分析更加深层的内部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失败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中国成功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应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慢半拍、浅三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个观点带有很大的误解。苏联失败,不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方向。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弊病的根子在政治体制,按理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全面发展,取得成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正是因为从三中全会起,首先改革政治体制。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三中全会打破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个人集权,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能端正路线吗?中国的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而三中全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随后,1980年开始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分开,党的主席不再兼政府总理。近20年来,中国的改革,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腐败越来越加剧,老百姓反映极为强烈,有的地方“怨声载道”。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不能说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在大的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没有关系。在有的方面确有进展,如公务员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基层民主等,这都是必要的,应当充分肯定,也需要坚持下去。但是在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马上转向搞市场经济,钱权交易现象必然加重,腐败必然加剧。
苏联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单一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合力论来解释。从1991年起,我就这一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我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有12个原因: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大的决策有错误;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为主,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浅因与深因,深因为主。浅因,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深因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不发达国家的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应该正确处理四个“主义”,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这四个主义大体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封建主义糟粕比发达国家多,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比发达国家少。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掌握好它的特殊规律,应该着重铲除封建主义糟粕,适当利用资本主义成果,不能急于建成“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都犯了错误。从根子上说,苏联共产党受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在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发达国家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简单地搬到苏联来。封建主义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封建君主专制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很深。长期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难以改正,到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从盛到衰?我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谈到过。我认为,11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都是被“左”葬送的。最先是柬埔寨。柬埔寨共产党推行一套极左的路线,致使众叛亲离。从1989年的东欧6国、1990年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到1991年的苏联、 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其失败的原因,毫无例外地都是长期推行“左”的路线。苏联后期的右倾大约持续4年,从1987年底到1991年12月。 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是在后期搞右,长期也是“左”。有没有一“左”到底的?有。罗马尼亚就是一“左”到底,但败得更惨。不仅亡党、亡国,甚至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被押上军事法庭就地枪决,亡身丧命。长期的“左”,促使后期转向右的极端,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如果只看到了后期的右,而无视或忽视长期主要的错误是“左”,那就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病象、病变,回避了病根、病源。苏东剧变的病根、病源是“左”的东西,病象、病变是后期右的东西。如果还不能真正从苏联、东欧剧变中吸取教训,痛下决心,大力铲除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如果还以为苏联东欧这些国家是由于个别领导人最后右倾才丧失了社会主义,而无视或轻视长期根深蒂固的“左”倾顽症的祸害;如果在改革开放当中不能有效地防止外来的和平演变,并且根治内部的腐败,听任腐败系统化、制度化,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免还会出现新的动荡,甚至还会发生剧变。对于剩下的5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并不是不存在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的可能性。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不可掉以轻心。
三、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导致“三个危机”和“三个灭亡”
苏联剧变,从长期来考察,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深层的矛盾,而苏共长期无视这些矛盾,也无力、无法解决这些矛盾,最后引起三种危机,苏共急剧转向右,导致前面所说的三个灭亡。在1936年以前的过渡时期,苏联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过渡时期结束后,苏联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出现了新的矛盾。到80年代,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些新矛盾。苏联社会存在哪三大矛盾呢?
第一个矛盾:过“左”的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高速健康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
1、过“左”的路线。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 从政治路线和某些重大政策方面看,大约有半个世纪都是推行“左”的路线,大约有9 年(1921—1929)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路线也基本正确,最后4年转向推行右的路线。
前9年正确路线时期,执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逐步改造小农经济。邓小平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时,唯一肯定的也就是新经济政策。1930年,斯大林急剧地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 并不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1939年斯大林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的整个指导思想是急于求成,对农民(特别是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都采取了过“左”的政策。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于1946年又提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在国际上,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急于实现世界革命。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不是搞右的呢?不完全是。在某些问题上,这也需要拨乱反正。因为从1956年起,我们党和赫鲁晓夫有分歧。1963至1964年中苏两党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中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观点的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错误,给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赫鲁晓夫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总代表、右倾机会主义总代表的深刻印象。实际上,赫鲁晓夫搞的“三和”、“两全”也有“左”的一面,只是因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在某些方面比赫鲁晓夫更“左”,所以认为赫鲁晓夫是右。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缓兵之计,还是想“埋葬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我们认为他放弃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要暴力革命,是右。实际上,当时还看不出暴力革命爆发的形势。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势。
那时,我们认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否认了党和国家的阶级性,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讲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是右。实际上,赫鲁晓夫之所以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其中一个重要想法是急于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从超越历史阶段这个角度看,还不能不说又有“左”的一面。
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左”的错误没有克服掉,只是稍微作了点变动。赫鲁晓夫时期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到苏联在20年内还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在60、70年代,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安德罗波夫对“发达社会主义”又作了修补,他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还是要逐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他认为苏联还没有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又接近了些实际。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加速战略,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并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转向搞市场经济。到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党才猛醒过来,意识到再坚持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行了,在1990年才改变提法,急于要在500天之内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 这样就进一步把苏联的经济搞乱了。
总之,苏共在总体上长期推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左”的路线(在某些方面也有右的政策和制度相伴随),难以改正,致使广大人民和党员对党的领导和改革失望了,于是社会上和党内右的思想必然滋长,想从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找出路。这就促使苏共领导人从1987年底以后逐步转向右的方面。
2、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
过“左”路线如果仅仅是路线问题,那还不难解决。通过实践检验以后,可以改变认识。但是由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使得苏联过“左”的路线长期难以纠正。现在人们谈论到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可是对他最大的错误,我们长期认识不清楚。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涉及苏联体制问题,但只是擦边而过,没有深入探讨。我们党当时看到了苏联制度存在一些问题,还说斯大林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但斯大林推行的是什么制?没有说。现在来看,当时对斯大林错误的认识是不够的,没有看到他搞的制度或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到1980年邓小平8.18讲话,对斯大林的错误才有了深刻的认识,看到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问题。1982年以后,才改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提法,以示具体的体制和根本的制度还是有区别的。
不少人认为,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肃反扩大化,我认为那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斯大林最大的失误是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形成了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请注意,我在这里用“过度集权”,而不用“高度集权”,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必要时要有高度集权,但过度集权,就过头了),给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长期的、广泛的危害。
(1)在国家领导体制上,斯大林搞了个人集权制、 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按照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与君主专制国有三点区别:前者国家领导人应该实行权力制约制、限任制和选举制;后者则实行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指定继承人制。自古以来这两种政体的区别截然分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怎样实现民主共和制?马克思还只有巴黎公社72天的经验,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6年, 在民主共和国方面作出了表率。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行集体领导。他作为政府总理、党的政治局委员,与其他委员一样,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而且列宁常常处于少数。在领导人限任制问题上,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托洛茨基说,我们夺取政权后,准备55岁就退下来。可是1924年列宁54岁时病故。列宁不指定接班人。列宁遗嘱中对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优缺点作了评价,没有暗示谁接班。
但是,后来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既是党的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又是全军武装部队总司令、最高统帅。斯大林还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斯大林的三制,带有封建君主专制的色彩,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原则,对苏联有长远的影响。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始终没有触及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只在某些政策方面作了调整。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专门作出规定,党内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三届,但德高望重者可以例外。这实际上为赫鲁晓夫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开了绿灯。勃列日涅夫上台时58岁,任期18年,76岁病故。安德罗波夫1982年68岁接班,70岁病故。契尔年科74岁接班,75岁病故。苏联在1982至1985年的两年4 个月内,党和国家三易其首,这是老人政治、终身制的贻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地受苏联体制的影响。东欧1989年剧变时,东欧国家的第一把手大部分是70多岁的老人。
斯大林体制对中国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毛泽东在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三个方面都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建国之初,毛泽东集党、政、军、政协等多个职务于一身,而斯大林在1941年才完成了党、政、军三权的统一。斯大林搞终身制到73岁,毛泽东到83岁。斯大林指定接班人一次到位,毛泽东先后指定了几个。从国家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毛泽东执行了斯大林体制,而且在高度集权的某些方面超过了斯大林。我们国家“左”的错误长期难以纠正,跟这种体制密切相关。邓小平8.18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总结。他总结斯大林、毛泽东晚年的教训,认为应该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我们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
从一般政治学来看,斯大林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三制,从社会主义政治学来看,斯大林还加强了、加深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高干特权制。前三制加后三制,这六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发生了在实践中很大的变形。
(2)在党的领导体制上,斯大林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 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外,还实行了一些具体制度,这也有很多弊端。
第一,关于政治局的权力。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党的政治局从何而来,政治局在党内是什么性质的机关,总书记何时才有,他在党内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在广大党员心目中,大都认为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根据马列建党学说并非如此。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1847年6月马克思、 恩格斯参与建立的,那时的党中央根本没有政治局,也没有总书记,中央设有中央委员会,由5人组成, 有主席, 主席主要是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俄国党于1898年建立,没有设过主席,只是在1903年至1904年设过总委员会主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没有主席,也没有总书记。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也不多,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人,实行集体领导,并没有设政治局。政治局从何而来?苏共中央正式建立政治局,是在1919年的苏共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政治局并不是党的权力中心,而是和中央组织局并列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执行机关。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从1847年马克思建党以来,在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中央还有一个机构即书记处,也是1919年才正式建立的,是日常办事机构。最初没有设总书记,只有三五个书记。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因书记处处理的事务繁多,在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之后,才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作为书记处的首脑。 在俄文中,总书记为秘书长之意。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担任了总书记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才是俄国党公认的领袖,但他的党内职务只是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后来明确地说,在苏联,中央全会决定一切,政治局决定一切,把政治局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变为党的权力中心。30年代之后,政治局会议经常不召开,由总书记独揽大权。
根据马列建党学说,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权力中心,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都主张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度。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领导6年,召开了6次党代表大会。1925年以后,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以至13年之久。斯大林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代表大会转移到政治局,使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他在党政领导体制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后来长期也难以改正。1952年苏共党的十九大党章规定党代会至少每4 年召开一次,1971年的二十四大又改为每5年召开一次。
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也不是一建党就有政治局。政治局成立于1927年6月1日第三次修改党章后。党中央原来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7年6月后才改称中央委员会。1925年四大以后,中共才设总书记, 陈独秀最初称委员长。1943年后我们党才设主席,1956年八大后增设副主席,总书记的位置就更低一些。从大革命后期起,设中央秘书长,后又撤消,以后几经变化,到1954年中央的秘书长改由邓小平担任,1956年后秘书长改称总书记。当时邓小平表示还是当秘书长,不要当总书记,毛主席很风趣地说:总书记就是秘书长嘛。
第二、关于监察机关。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为了有效地对中央进行监督,列宁继承国际共运好的经验(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于1919年提出,从1921年起,苏共中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任务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1923年,列宁在临终前写下《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主张国家的监察机关与党的监察机关合并,合并以后的机构专门监督中央领导人,包括总书记在内。1934年苏共十七大修改党章,斯大林把原由党代表大会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其任务是监督地方党委是否执行中央的决议。从此中央监委的性质完全改变。从1934年以后,没有任何机构能监督苏共中央领导人。我们党的中央监察机构,也不能不受苏联党的影响,一直是属中央委员会领导的。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政见。
党内在决策问题上、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不同意见应该自由、平等地展开讨论、争鸣。不能求得共识时,以少数服从多数来进行决策。决策错了,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纠正。列宁领导的6年,党内有很多派别。 列宁反对派别活动,但是赞成党内民主自由,从来没有把谁打成反党集团。从斯大林开始,把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党集团,人为地加深、加剧了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又一个大的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健康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要求。苏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如布哈林、沃兹涅先斯基等都看到了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意见。但由于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也与当时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有关,他们都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集团、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枪毙。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变种,是资产阶级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并对苏共党内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人,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
第二个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与劳动大众的矛盾
过度集权的体制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根据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巴黎公社开创了两个原则,一是主要领导干部选举产生;二是领导干部和工人工资平等,工资待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而斯大林搞的是等级授职制和高薪特权制,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苏联在斯大林中期(1935至1936年)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托洛茨基曾提出过,苏联出现了一个工人官僚阶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成《新阶级》一书,也认为南斯拉夫出现了新阶级。这些说法,未必准确,有争议。我琢磨了很久,可以不用“阶层”、“阶级”这些词,而用“官僚特权集团”较为合适。
苏联出现的官僚特权集团,显然是受封建等级制度影响的产物。苏联在分配方面,对群众实行“左”的平均主义,对领导干部实行右的封建主义等级制。这个官僚特权集团从计划经济体制内获得了很多好处,害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风险,害怕失去他们的利益,所以就以马列主义为招牌,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维护自己的特权,成为反对改革的阻力。如果苏联这些党政领导干部知道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可以不伴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去搞市场经济体制后,从权钱交易中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那样他们可能也会赞成市场经济的。
第三个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
苏联民族结构与中国不同,在120多个大小民族中, 俄罗斯民族不占绝对多数。十月革命时,俄罗斯民族只占人口的42%。1989年俄罗斯民族也才占50.8%,刚过半数。苏联革命胜利后,列宁以各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采取联邦制的形式组成多民族的国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联邦。但是,长期以来,大俄罗斯主义严重,实际上是过度中央集权。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长期以来,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把俄罗斯族往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推行俄语,甚至搞民族大迁徙,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在宗教、文化、语言问题上歧视少数民族。
总之,这三个矛盾长期不能很好解决,导致了苏联经济、社会政治、民族三大危机。
经济危机:苏联在战后的50年代,经济增长接近10%,60年代降至8%,70年代是5%,80年代经济增长2%—3%,1990年经济负增长2 %,1991年达到-12%,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不足,通货膨胀严重。
社会政治危机:党的威信下降,很多人对党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满,要求实行多党制。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工人罢工、怠工增多。
民族危机:民族要求独立、分离。苏联的解体从1940年被兼并的波罗地海沿岸3国开始。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 民主化,不让历史留下空白,公布了1939年9 月苏德秘密签订的将波罗地海沿岸划归苏联势力范围的协定文件。由于处理不当,引发了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于1990年3月至5月率先独立。到1991年8.19事件后,各民族害怕又回到过度集权的旧体制中去,到12月21日,11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这样苏联就完全解体了。
于是,上述“三个危机”导致了苏联的“三个死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制度)。
四、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的“和平演变”?
波兰出现团结工会闹事、罢工,实际上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长期不民主,漠视工人福利、意见和要求有很大的关系。波兰军管结束后,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议会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 原来与统一工人党合作的民主党和统一农民党也与统一工人党分手,但是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认为它们是附庸党,缺少独立性。然而我们只从“左”的方面总结了波兰的教训。有人由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也不能给民主党派过大的权力,否则容易出乱子。可是,我们应该看到,用压制民主、限制自由的办法一时可以奏效,但不是长远之计,最终将会把矛盾激化。西方多党制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影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不充分。东欧的波兰、捷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这四国也实行多党制,但民主党派长期都是共产党的附庸,不能真正对共产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在群众中也没有威信。当东欧剧变时,民主党派大都作鸟兽散。有一点值得注意,东欧新执政的党都不是原来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党。
西方的和平演变,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二靠市场经济,三靠多党制,四靠文化自由。因此,对付西方的和平演变,我们要有正确的对策。靠什么?一要把科技搞上去。二要自觉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对党的高层领导人能实行有效的监督,充分发挥党的最高监察机关的有效作用,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充分发挥其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四要坚持文化“双百”方针,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对民主自由的属性要全面地看。民主自由固然有其阶级性,但也有它本身质的规定性。不符合这个质的规定性,那种民主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例如选举,应该是自下而上提名、有差额的选举,有竞争的机制。我们的民主需要完善,要逐步创造条件扩大差额选举的使用范围,既要发挥协商制的长处,也要重视差额选举制的优点,要把两点的长处结合好,形成更大的政治优势。
当然,中苏两党两国的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苏联改革导致三个灭亡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作为借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该从苏共、苏联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在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样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的胜利。
此文是作者1998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研讨会上的讲话。
标签:斯大林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巴乔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