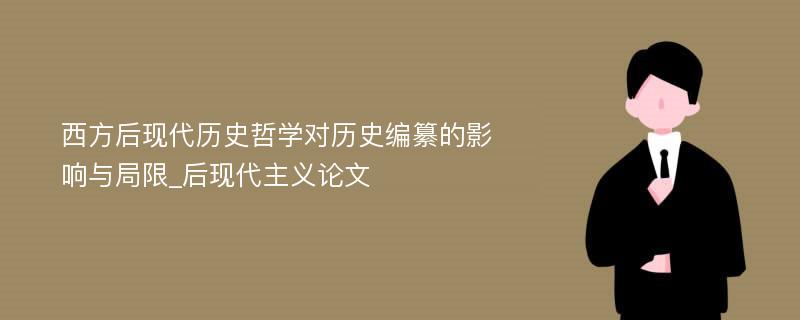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01
一、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编纂的影响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不少历史学家持抵触态度,因为它与他们自己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和体验相去甚远。美国历史学家贝林(Bernard Bailyn)比较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态度。他说:“对过去实在之再现的精确和适当,对所撰写的事实的逼真和接近,这些仍然是衡量优秀历史著作的标准。”①英国历史学家布伦特(A.Brunt)也宣称:“历史学家的目的无疑是发现‘事物实际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也意识到,他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成功。”②哈斯克尔(Thomas L.Haskell)则坚决捍卫历史的客观性,反对从历史学中剔除“合理性”、“逻辑性”和“真实性”等字眼。③
即使是在对后现代主义表示同情的历史学家中,大部分人也没有放弃实在论的观点,他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任务是认识那消逝的过去,并尽力去重建过去。法国学者罗歇·沙尔捷(Roger Chartier)坚持认为,历史学是一门有关过去实在的“可确定的和可证实的”知识,只有在“批判实在论”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才能有效地抵制“对历史学的扭曲”以及“对过去的神话重建”。④他还指出,许多史学实践与话语策略没有相似之处,因而反对把经验还原为话语。⑤
客观地说,后现代主义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并未占据显要位置。大部分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理论无动于衷,仍然遵循着某些传统的史学研究原则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同时希望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久将会烟消云散。美国中世纪学者帕特纳(Nancy F.Partner)在1995年撰文指出,“以语言为基础的批评模式在史学界造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动荡,但它并没有对学术实践产生实际的影响。”⑥提厄内(Brian Tierney)说:“元史学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迷人的主题,它被看做是语言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与实际历史学家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⑦
但是,从历史学家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各种历史著述的现状来看,当今历史学的确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并发生了一些变化。后现代历史学不仅拓展了历史撰述的范围,而且还给一些陈旧乏味的主题注入了活力。一般来说,后现代历史学拒斥作为现代历史学核心的理性和进步观念,转而关注特异、犯罪、神秘等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它抛弃实在而注重象征。它拒绝构建某种核心的宏大叙事而将其他叙事推向边缘,因此,许多以前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主题都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后现代主义者大都相信,最有趣味的动植物往往隐匿在路边和沟渠中,而不是招摇在康庄大道上。
后现代历史哲学带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我们看来是社会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和历程,现在正在日益被看做是文化和语言的产物。这种对语言的强调已经渗入到当今西方很大一部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在这些领域,不少学者已经接受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和话语观。譬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就较为成功地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到了对女性主义政治的研究中。在其《历史的性别与政治》(1988)一书中,斯科特对语言的看法甚至比任何一位后结构主义者都更为激进。同德里达一样,她也认为,传统的语言设置了一套等级秩序,它导致妇女长期处于屈从地位。⑧她论证说,性别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并不是由自然所规定的,而是由语言所“形成的”。针对别人对她“毫无批判地接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指责,她辩解说:“我的论证并不是说现实‘仅只是’一个文本,而不如说是现实只可能通过语言而获得。所以社会政治的结构并未被否定,而不如说是它们必须通过它们的语言学上的发音才能加以研究。而德里达对这种研究则是非常之有用的……”⑨
后现代历史哲学通常把历史看做是一种文学形式,这一做法使得叙事性较强的历史著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著作曾一度充斥着令普通读者望而生厌的社会科学术语。8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采用文学策略来撰写历史作品,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沙玛(Simon Schama)的《公民:法国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和费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1891~1921年的俄国革命》(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1)。虽然这两位历史学家所处理的都是重大的传统主题,但是他们独出心裁,把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和大人物或小人物的个人经历编织成一个宏阔的叙事。他们拒绝宣称自己是确定无疑的权威,相反,他们都承认,在对书中的次情节和人物经历的选择上都是主观任意的。这也就等于说,同一个故事可以存在多种多样但同样有效的讲述方式,这显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在后现代历史著作中,有两部作品不可不提。一部是N.Z.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基尔回家》(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另一部是达顿(Robert Darnton)的《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同前两部历史作品一样,这两部著作也都是引人入胜的叙事作品。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它们的题材并不是伟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卑微的日常琐事。两部著作都把这些日常琐事编织成故事,将它们作为更大事件的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线索来加以分析。通过这种方式,作者让读者去感受过去人们的精神世界,去触摸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是难以想象的。
戴维斯在该书前言中坦言,书中的有些内容是她虚构的。她试图为“大概”或“可能”留出地盘。许多批评家都对戴维斯的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认为这纯属主观臆测。在他们看来,任何臆测都必须在资料和文献的法庭前接受审判,无论这种臆测是出于直觉还是基于某些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概念,历史学家不应该让过去的人们说出或作出一些违背文献的事情。但是,戴维斯指出,类似这种间接的推论过程甚至在最为传统的历史著作中也并不少见,尤其在缺少第一手史料的情形下。
达顿关于“猫的大屠杀”的叙事则源自于1762年某个人写的一份只有三页纸的文献,而作者要描写的这个故事则在此3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作者所谈论的这些学徒工们曾经屠杀过猫这件事,也没有任何理由断定,这次猫的大屠杀象征性地预示着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屠杀。猫的大屠杀的象征意义指向的是老板和老板娘,而不是那些在法国革命中成为民众泄愤对象的贵族或乡村诸侯。批评者们认为,达顿的这个叙事漏洞百出,从头到尾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这种批评也许是非常有道理的,但仍然不应该太过苛刻。至少,达顿故事的想象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国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象。⑩
另外,后现代主义还促使历史学家更仔细地考察文献,更认真地对待表面现象,重新思考文本和叙事问题。它已经帮助历史学家开辟了许多新的主题和研究领域,并使很多似乎已经山穷水尽的问题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境界。它迫使历史学家去反省某些长期以来想当然的方法和步骤,从而使它们更严密和更有效。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对于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这反而更有利于读者对历史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在它的倡导下,历史著述的重心已经从社会科学方面转移到了文学策略上,从而导致大量可读性较强的历史作品的出现。后现代主义把被科学历史学冷落的人类个体重新安置在历史中。
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后现代历史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把后现代主义的原则应用于其自身,它就必然会陷入悖论。如果真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所有的理论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只相信后现代主义理论而排斥其他理论。
某些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把自己列入政治左派阵营。他们认为,一旦把历史从客观事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会使它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宽容。在美国,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相伴而行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社会中不同的文化群体(包括弱势文化群体)有关历史真相的观点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因而各个群体应该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但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观点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和宽容,也不一定有利于政治弱势群体,它也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泛滥。
保罗·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不少反犹太人的言论。他于战后到了美国,在学术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文学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只字不提。德曼提倡所谓的解构主义,强调文本和作者各自的独立性,强调文本中能指的无限游戏,这实际上是暗中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言论作辩解。德曼于1983年去世,1987年便有学者披露了德曼的反犹太主义倾向。随后,罗蒂、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开始为德曼辩护。但是,他们在辩护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策略,是同他们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立场相矛盾的。
在美国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不再坚持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确定性,转而认为意义是由读者本人强加给文本的,因而可以存在多种意义的阐释方式。一时间,抨击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在这种气氛的熏染下,已经没有什么学术禁区可言,人们可以随意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提出质疑。这种后现代主义给历史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正像利普斯塔特(Lipstadt)所描述的那样,后现代思想情绪“培育了解构主义的历史学。没有哪个事实、哪个事件或哪个历史方面具有某种固定的意义或内容,没有什么真相不可以重新讲述,没有什么事实不可以重新改写,没有什么终极的历史实在”。利普斯塔特提醒人们说:“否认大屠杀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它并非是对某个特殊群体历史的攻击。虽然否认大屠杀可能是对灭绝犹太人历史的一种攻击,但是,实质上,它对所有那些相信知识和记忆是我们文明的基石的人们来说……对于所有那些相信理性的根本力量的人们来说,都构成了一种威胁。”(11)
这样,极端相对主义为极右历史学家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像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所说的那样,这些历史学家随心所欲地阐释和操纵证据,掩饰重要事实,从而制造了大量虚假的舆论。(12)海登·怀特的确承认,在个别事实的层面上存在历史真相,因而反对修正主义者对大屠杀的否认。(13)但是,一旦提升到他所谓的历史实在层面上,怀特就会承认,对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解释和其他解释都具有合法性。极端相对主义使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否证法西斯历史观的标准。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相对主义盛行的美国,出现了不少有关大屠杀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公然宣称,从来就没有发生过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这样的事件,奥斯威辛集中营只不过是战后那些反德国、亲犹太分子的伪造。否认大屠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与后现代主义泛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虽然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并篡改教科书的行径与后现代历史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泛滥也极有可能会助长他们的罪恶意图。因此,我们应该对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醒。
注释:
①B.Bailyn,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4,p.8.
②A.Brunt,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508.
③T.L.Haskell,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8 ~9.
④R.Chartier,History between Narrative and Knowledge,in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History,Language,and Practic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26~27.
⑤同上,pp.19~20。
⑥N.F.Partner,Historicity in an Age of Reality Fictions,in F.Ankersmit &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Reaktion Press,1995,p.22.
⑦B.Tierney,Religion,Law,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1150~16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vii~viii.
⑧J.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 ~ 11.
⑨[德]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10)R.J.Evans,In Defence of History,London:Branta Books,1997,pp.244~248.
(11)D.E.Lipstadt,Denying the Holocaust: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New York:Penguin,1993,pp.19~20.
(12)C.Norris,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p.16.
(13)H.White,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7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