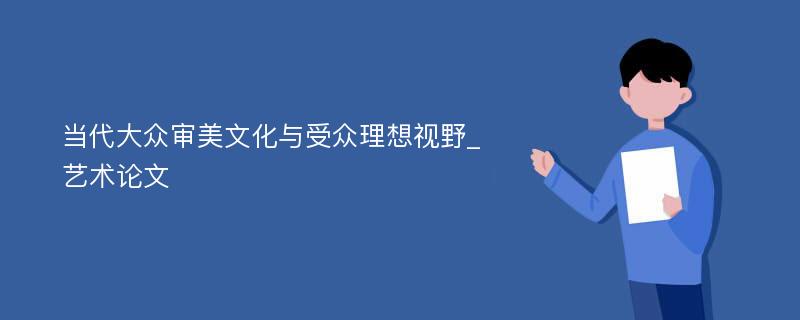
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与受众的理想幻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景论文,大众论文,受众论文,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成分,它是以通俗文学、流行艺术等文艺形式为中坚,另辅有大众文化消费方式,诸如卡拉OK、时尚装饰、休闲旅游等在内的活动系列。它是当代文化工业的产物。
作为大众文化的成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有着大众文化的一般特性,即笔者所指认的它的大众性与伪大众性。它的大众性看来是理所当然,不待多说的。它的伪在众性在于,它是由一定生活条件下,大众被安排的一种文化,而不是大众真正理想的对象,如对多数人来说,自己演唱有乐队伴奏更好,求之不得,以卡拉OK的录像伴奏来替代;自己能够游历世界各处的名胜景点是很好,但苦于缺乏经费,也难以挤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参观许多城市都建有的“世界风光”公园,也就聊作替代。这种大众文化的兴盛在于,它是大众可以用于实际的日常生活消费,从而也就可以使相关投资者获利的范畴,由于它具有商业盈利的潜质和批量化生产的特性,也就可称为文化工业。
大众文化是体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而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则是在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审美经验的文化,由于审美是感官经验的行为,因此它是属于文化工业中感觉消费的领域,在这方面又同艺术有着相通之处。
一般的文艺学家、美学家在谈及艺术时,多从艺术的美娱功能上着眼,当然,要明确艺术在人类活动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这也确实是有必要的。但当艺术处在专门家的研究视野中时,已成为了一种缺乏实际生命力的标本,而真正生活中的艺术显然在性质上更为复杂,至少,当艺术处在大众文化立场中时是如此。
我们知道,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身份的标志,这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制度建立起来后,各种专门活动都有某种从业者来专司其职,在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个人都只需干而且在后来也几乎是只能干他所熟悉的那一部分工作。在此背景下,艺术家的工作不是生产食品、衣服等实用品,他们是以创造审美对象乃至新的审美经验作为首务,但是从社会制约的背景来看,艺术家就并不是简单地创造美的问题,他还被要求表达出一定阶层、阶级的愿望,将他们对于生活的理想加以诗意化的表现。普列汉诺夫指出,狩猎民族的艺术题材都是对动物的描写,农耕民族的艺术则主要是对植物花蕊和果实的礼赞,这是无意识中进行选择的结果,而它底层的原因完全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定性,但社会发展到经济关系对于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意义时,社会就分化出对立的阶级,并且文艺也就因而具有了阶级性。就是说,艺术家个人很可能自我感觉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缪斯的信徒,但实际上也是受着人间烟火制约的,这里,艺术家常对艺术存有幻觉。
与此同时,在公众的艺术观念中也存在着对于艺术的幻觉。自从社会分工导致知识分化以来,每种学问实际上都有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来负责研究,但公众中的大多数人不识字或即使识字却无广泛知识的情况下,艺术也就兼有了他们生活中的百科全书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曾论及原始文化中知识的整一性问题,然后他还进一步指出:
艺术和知识也是极相近的东西。一方面在写实的艺术中,常含有许多正确的观察和研究周围环境的动机,另一方面,艺术的象征和科学的图解,也是常联合在一起的。审美的动机在不同的文化水准上,都会使知识统一化和完整化。格言、谜语、故事以及历史的叙述,不论在原始或发达的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其实,对这段表述的意思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在原始文化阶段,艺术和知识是综合为一的,但在后来的文化中,应该说二者就有区别,只不过在对各种专门知识知之不多的情况下,大众关于生活的总体认识就来源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体验,艺术则成为对生活经验和体验的延长,他们就仍将艺术看作是知识的来源。与此同时,大众的生活理想也就在艺术的描写中寻求表达。
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从社会分工制确立以来,那些秉受了较多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实际上就已把艺术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实际追求区别开来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的理想是哲学理想,是对于智慧、学识的追求;新教改革家路德的理想是宗教理想,希望在信仰上建立平等观念,反对神职人员高人一等的特权;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学说中表达的是一种人文大同的政治理想,他是冀图以西方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复兴中国;罗素在篇什浩繁的著作中表达的是一种科学理想,在认识论中以实证的逻辑的原则为认识活动的主导,在情感领域则以互谅互惠的态度与他人交往,而两者的结合造成社会的和平昌盛。这些堪称为思想界巨子的理想同自己工作的目标是有联系的。但恰恰作为文艺家的那部分人则未曾以文艺作为自己理想的展示和实施的领域。
托尔斯泰是以小说来表达基督教理想,托马斯·莫尔是以小说来表达乌托邦社会理想,毕加索是以涂鸦式的绝大手笔来反抗既有文化压抑人的心灵自由空间的个人理想,贝多芬是以音乐来对抗失聪的痛苦,表现的是精神超越肉体束缚的人生理想。这些艺术大师们确实在艺术中表达了自己的某种理想,但它们都不是关于艺术的理想。至于19世纪盛行的唯美主义艺术,也并不是艺术家关于艺术的理想,它实际上是一部分激进青年艺术家由这一艺术运动,去反拨各种利用艺术来从事政治等其它活动的口实,在没有更强有力的口号之前,他们只能以“唯艺术”作为号召,其目的只是以艺术作为个人主义、个性表达——而不是将这扭曲到基于集体意识的宗教、政治思想的表达物。王尔德曾说:“一切坏的艺术的根源,都在于要回到生活和自然,并提高它们成为理想。”(注:伍蠡甫、蒋孔阳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16页。)在这里就明确否定了艺术作为理想表达的领域。退一步说,即使那些艺术家在艺术中描写出理想的话,也是同现实中应该追求实现的价值目标作出了一定区别的。
民众中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没有深入到一定学科领域中去施展自己理想的可能,他们不会冀望哲学家的国度(柏拉图的社会理想)比现实世界更好,他们也不能想到自己从出生时就浸润于其中的宗教教义还可能加以改造(路德的宗教理想),这一想法本身就让人惊骇,显得大逆不道了。另外,孙中山、罗素、托尔斯泰等人的那些理想也因需要个人的学识、经历和一定的特殊技能才可能加以实施,所以也与一般民众无涉。民众的理想就是一种朴素的人生理想,是关于一个人出生之后如何显得具有价值,如何觅得幸福的理想,而这一理想是以大众文化的价值观为衡量尺度的,它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角色错位的人生理想。这实际上也是原始艺术就已开始表达的内容。它的具体内涵是指艺术中的角色与大众的社会角色呈现出巨大反差的状况,象神话中的神仙、史诗中的英雄,乃至童话中的精灵、传奇中的好汉之类,他们是作为作品中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角色出现的,反之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则位卑职低,处于社会的下层,他们的生活经历是一部遭受痛苦与失败的历史,他们就从错位了的艺术人生中寻求个人幸福的短暂安慰。
其次,则是角色虚位的人生理想。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艺术中的笔触转到了下层人民身上,但在描写和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他们实际上是被虚构的,在现实生活逻辑中难以实现的角色,如饱受欺凌的白雪公主遇上了白马王子,牧羊女受到国王垂青,牛郎娶上了下凡的仙女,穷书生时来运转平步青云当上附马,等等。这一类型比之前一种来说,体现了较多的平民性色彩,将大众的文化价值观多少溶入到了艺术描写中,作品对他们是充满同情和肯定的,但在这种描写中也仍是将他们的生活价值向大众之上的统治精英看齐。是要过上了精英们的生活才实现了人生价值,而这一点是很难在现实中实现的,因而它只是角色虚位的理想。
其三,则有角色本位的人生理想在艺术中的表现。它的产生是在前二者对大众人生的感召力下降之后,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或新的社会秩序刚建立的一段时期,这时,旧有的人生理想图式遭到破坏,新的人生价值观则尚未成形或缺乏权威性,它表现出一种萌动中的大众情绪。我们以侠义小说作为一种个案类型来说,它在唐代即有了雏形,连李白、王维有些诗都表现了一种侠气。但侠义小说的兴盛在清代,侠客多是书剑并举、智勇双全的英雄,但无一例外地他们又都是落魄江湖的英雄,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实则是平民形象的化身。他们虽可能有满腹经纶,但真正成就事业的工具却是具有原始气息的刀剑拳脚,它体现出的矛盾心理就在于,在潜意识中他们是对社会既有秩序表达了愤懑:只有侠客才能除暴安良;但另一种潜意识又要求其行为的价值依据仍以诗书中的教义为根本。说到底,它在当时是反映了民众对满族统治者武力灭明后的一种价值观的失落:悠久的华夏文明是中华帝国一直引以为傲的,但恰恰就是这一文明败在了一向被视为夷狄的清帝国的文明中,因此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用他们惯用的刀剑之力才能将其制服,而这种制服又只能建立在回复华夏文明的理想上,侠客们的书卷之气就正是它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侠客们的各种礼仪和行为规范也反映了清代反清地下组织的礼法制度和秩序。
同样,欧洲出现的所谓“流浪汉小说”也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即是:
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下层阶级出身的新主人公登场,所谓“恶棍小说”就产生并发达起来。通常,主人公是恶棍,对财产不大有兴味,不断更换工作,经过长久的辛苦之后,而获得世俗的幸福。以各社会层广泛的情景为背景,描写着这主人公的事件。(注:维拉格诺多夫:《新文学教程》,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46-147页。)
在这类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中,主人公并不追逐名利,而终于获得的“世俗的幸福”只是不期然而然的偶然得之,它表达了一种认识,即贵族阶级的所谓“高贵”只不过是财产继承权使其具有了财富、地位,而真正人的价值则还应在对工作事业的不懈追求中才可觅得,而凭着这一价值,则世俗的幸福也同样可以获得。这就表达出一种人生价值的悖论:即不热爱财产而热爱去冒险的公式可以说是“钱财如粪土,冒险值千金”,钱财是被贬黜的,但它所标榜的冒险生活的最终衡量尺度仍是钱财,即世俗生活幸福的内容。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则将矛头对准上流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也包括其实并不是上流社会的人士,如小老板、爱虚荣的职员,等等。在其作品中塑造的正面形象很可能就是社会用世俗标准来衡量时处在罹难窘况的人物,是不会引人去效法他们生活的人。应该说,表达出角色本位理想的艺术是最接近于平民意识的艺术,它表明了平民在艺术意识上的觉醒,即要创立自己的艺术和人生价值尺度,而不是简单地向非平民的艺术看齐。但是在这种艺术中也表现出否定其他美学传统的较为激进的倾向。
作为对这种美学偏激的补救,那么就还有一种应运而生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角色同位的艺术,它以“后现代”的流行艺术作为最突出的代表。这种艺术不是要大众艺术向精英艺术看齐,也不是要退缩到反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面,而是将所有可能成为它的欣赏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内去,各种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够认同的方面,欣赏者扮演的什么社会角色,那么它就同这一角色有着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作为“人”的本性,即潜意识进行的沟通。这就如同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赛,啦啦队中可能有绅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为自己球队助威这一点上他们都处在同一营垒,并且在助威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参与感。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虚渺的远离现实人生理想而只以艺术为美的家园,只以艺术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艺术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图创立不同于经典艺术的大众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支点。这种艺术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理想的内容,同时也具备了经典艺术那种代表人类艺术文化创造的胸襟。可以说正是这点才使流行艺术在20世纪大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发达国家的平均学历已接近本科毕业水平时,能获得广泛认同的主要原因。这种角色同位的艺术实际上表现的东西是“空框”,无非是如同每一个人走到镜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显得可以容纳很多人,其实待人走开后它里面是空无一人。而这一点若作形而上的终极追询,也许更近于艺术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