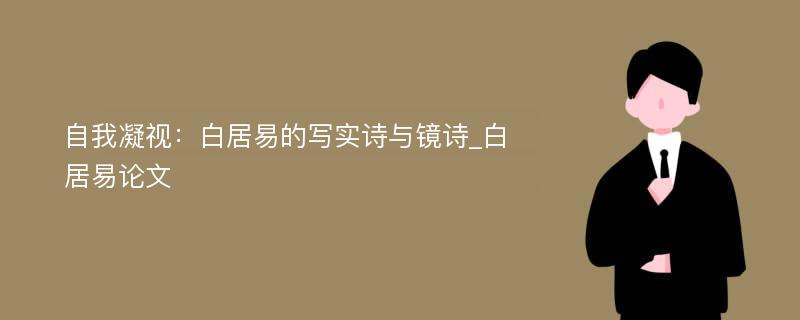
自我的凝视:白居易的写真诗与对镜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居易论文,写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6—0051—07
一、前言:看见自我
本文探讨的是作者书写“看见自我”的视觉经验及其反思。写作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它指向作者对于自身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的认知。自我意识的形成固然历经个人的学习积累,与社会环境、文化体系的互动,本文谈的是较为直观的侧面,也就是透过“看见自我”而表述的“自我形象”及其内涵。
所谓“自我形象”(self image),简而言之,即人如何看自己,如何定位自己。“自我形象”一般有三重层面:真实的自我形象(real self image)、理想的自我形象(ideal self Image)以及他人心目中的自我形象(other self image)。如果我们把“形象”的概念说得更具体而狭义,认识“真实的自我形象”不假外求,即从看见自己的身体外形样貌而来。吊诡的是,人生双目,却无法如前言所云的“不假外求”地看见自己整体的身体外形样貌——人无法不凭借外物看见自己的面容。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自我必须靠着“客体”的他者(the other)而看见、认识自己。这个“客体的他者”的首要前提,便是能够“如实再现或复制”自我的形象,基于普遍的共识,人们使用的工具是镜子,观看的对象是图画。
在唐代诗人中,题咏自己的肖像画、书写揽镜自照心情者,以白居易(772~846)的作品最多。对白居易而言,照镜和观写真具有“自相形骨”的共通性。在他四十五岁写给妻子之从兄杨虞卿的信中,说自己:“又常照镜或观写真,自相形骨,非富贵者必矣,以此自决,益不复疑。故宠辱之来,不至惊怪。亦足下素所知也。”[1](卷44,与杨虞卿书,P2769) 本文便以白居易为例,试论诗人如何经由看画与照镜而“看见自我”,以至认知自我、体会人生。
二、看画与对镜:时光之流
白居易以个人“写真”(肖像画)① 及镜子为题材的诗篇,依其生命历程排序,作品见下表②。
序号标题写作时间 年龄 写作地点
官职
1自题写真
元和五年(810)39长安翰林学士
2题旧写真图 元和十二年(817) 46江州江州司马
3赠写真者
元和十三年(818) 47江州江州司马
4感旧写真
大和三年(829)58长安刑部侍郎
5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 会昌二年(842)71洛阳刑部尚书致仕
序号 标题
写作时间
年龄
写作地点官职
1
新磨镜 元和五年(810) 39长安 翰林学士
2
照镜
元和六年(811)至元和十年(815)之间
40~44
下邽
3
以镜赠别
元和七年(812)至元和八年(813)之间
41~42
下邽
4
感镜
元和七年(812)至元和八年(813)之间
41~42
下邽
5
对镜吟(闲看明镜坐清晨) 元和十四年(819)
48洛阳江州至忠州途中,忠州刺史。
6
镜换杯 大和二年(828) 57长安刑部侍郎
7
对镜吟(白头老人照镜时) 大和三年(829)至大和五年(831)之间
58~60
洛阳太子宾客分司
8
对镜
大和三年(829) 58洛阳太子宾客分司
9
览镜喜老
大和九年(835) 64洛阳太子宾客分司
10 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
开成四年(839) 68洛阳太子少傅分司
大约在三十六岁到三十七岁之际,白居易拥有了第一张自己的肖像画。《题旧写真图》云:“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③《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则说道:“元和五年,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时年三十七。”[1](卷36,P2490) 元和五年白居易三十九岁,该年五月,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白居易除左拾遗是在元和三年四月,时年三十七岁。因此“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之事应该在元和三年。
白居易缘何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并不清楚,集贤殿御书院设置于开元十三年,本名丽正修书院,其中设有画直,为宫廷画家,负责朝廷绘艺之事[2](卷43,P1851~1852)[3](卷47,P1212)。白居易于元和二年十一月为翰林学士,次年除左拾遗,左拾遗属门下省,职掌供奉讽谏。《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所说的“奉诏写真”可能和他任左拾遗有关,为他画像的画家则为御书院之画直。门下省左拾遗有两位,“奉诏写真”在当时不会仅为白居易一人举行,很可能是某种例行之公事④,白居易特地记下,可见对于个人肖像之重视⑤。
这幅在集贤殿御书院画的肖像是否归白居易收藏,吾人不得而知,白居易三十九岁和五十八岁时写的《自题写真》与《感旧写真》诗,提到他观看和收藏的肖像是李放所绘。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里,记载了一位妙于写真的画家李仿[4](P18b~19a),或许便是李放。而李放是否即在集贤殿为白居易画像的同一人亦不详。
总之,白居易题写真诗所涉及的肖像画至少有三幅⑥:一是画于三十七岁,于集贤殿御书院;一是李放所绘,白居易个人收藏,并且多次题咏;最后是七十一岁时,“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第2490页),当时已经致仕。
我们之所以能够整理出白居易写真诗的写作脉络,与其诗歌本身清晰而强烈的时间感有关。白居易记录了肖像画的作者、作画的时间、地点以及几次观画的时间、地点与个人的情况,可以说,白居易将写真诗与他的人生经历结合,每次观看题写自己的肖像画,便是回顾或展望自己的人生。且看几首作品: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自题写真》,第311页)
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顇卧江城。岂比十年老,曾与众苦并。一照旧图画,无复昔仪形。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题旧写真图》,第403页)
李放写我真,写来二十栽。莫问真何如,画亦销光彩。朱颜与玄鬓,日夜改复改。无嗟貌遽非,且喜身犹在。(《感旧写真》,第1491页)
第一首和第三首诗,看的是同一幅画,第二首虽然没有标明画家的名字,从诗题看来,应该就是第一首的续篇,对照前列的写作时间可知,这三首诗正好显示大约每过几年,诗人借着观看自己的肖像画所表达的自我认知与期许。这种具有“纪年”意味的表现倾向,在写作当下的时间点上联系与肖像画的互动情景:三十九岁时的白居易想到自己任职于朝廷已经五年,希冀早日罢官归乡。四十六岁时为江州司马,容貌与心境随着仕途之颠踬而颓萎,憾恨未能功成名就。迈入五十八岁时,珍视生命重于嗟叹衰老。
到了七十一岁,白居易再看自己在香山寺的画像,不免深有所感:“前后相望,殆将三纪,观今照昔,慨然自叹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几变。”作诗道:
昔作少学士,图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寄香山。鹤毳变玄发,鸡肤换朱颜。前形与后貌,相去三十年。勿叹韶华子,俄成皤叟仙。请看东海水,亦变作桑田。(《香山居士写真诗》,第2490页)
天地间无物不受时间之摧残,即使是沧海也会变作桑田,何况是血肉之躯。
与看画相似而更为直接且即刻的,是从镜中反映的个人形貌变化意识到时光之匆匆。前文提到白居易的自题写真诗具有“纪年”的意味,事实上,他的“纪年”诗便是从对镜的经验开始。墟见邦彦教授研究指出:白居易的“纪年”诗有如日记般规律地记述日常事物,自三十二岁开始有纪年诗,三十四岁和三十六岁时两年一首,三十七岁到七十二岁(七十二岁除外),每年都作“纪年”诗⑦。白居易三十二岁时作的《秋思》诗为:
病眠夜少梦,闲立秋多思。寂寞余雨睛,萧条早寒至。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何况镜中年,又过三十二。
白居易三十四岁时作的《感时》诗里,也有从镜中感悟时间的想法:
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将至。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
肖像与镜中所显现,最能代表岁月痕迹的,莫过于白发与鹤颜,《香山居士写真诗》有“鹤毳变玄发,鸡肤换朱颜”之句。
白居易的对镜诗里,更是经常注意头发与容貌的变化:
衰容常晚栉,秋镜偶新磨。一与清光对,方知白发多。(《新磨镜》,第814页)
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岂复更藏年,实年君不信。(《照镜》,第507页)
我惭貌丑老,绕鬓斑斑雪。(《以镜赠别》,第527页)
今朝一拂拭,自照顦顇容。(《感镜》,第534页)
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对镜吟》,第1138页)
三分鬓发二分丝,晓镜秋容相对时。(《对镜》,第1897页)
从三十四岁作《感时》,白居易便开始忧心“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到了三十六至三十七岁,果然生出了白发,而且预想未来将逐渐布满:“白发生一茎,朝来明镜里。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⑧ (《初见白发》,第472页)不但有白发的困扰,而且还担心落发的问题:“夜沐早梳头,窗明秋镜晓。飒然握中发,一沐知一少。”⑨(《早梳头》,第477页)“渐少不满把,渐短不盈尺。况兹短少中,日夜落复白。”(《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之二》,第566页)
四十岁的白居易,抒发了叹老之声:晨兴照青镜,形影两寂寞。少年辞我去,白发随梳落。万化成于渐,渐衰看不觉。但恐镜中颜,今朝老于昨。……(《叹老三首之一》,第517页)
这些老态,都是从镜中得见:“早世身如风里烛,暮年发似镜中丝。”(《夭老》,第1956页)“镜里老来无避处,尊前愁至有消时。”(《镜换杯》,第1803页)多愁善感的诗人在“白发逐梳落,朱颜辞镜去”(《渐老》,第557页)的伤怀中一再地沈吟“雪发随梳落,霜毛绕鬓垂。加添老气味,改变旧容仪”(《白发》,第1342页),眼看“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沈吟吟旧诗。二十年前一茎白,如今变作满头丝”(《对镜吟》,第1454页)。
直到六十岁之后,白居易已然满头雪白,六十四岁时作的《览镜喜老》诗,依然带有纪年的意味,心态却已经改变,由嗟老叹衰转为喜老惜生:
今朝览明镜,须鬓尽成丝。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赢。亲属惜我老,相顾兴叹咨。而我独微笑,此意何人知。笑罢仍命酒,掩镜捋白髭。尔辈且安坐,从容听我词。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
白居易早就明了“万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叹老三首之一》,第517页),在亲属喟然年老体衰之余,诗人反其道而行,认为衰老总比早岁夭折好,能够活到接近古稀,已为庆幸,不必羡慕寿高九十余岁的荣启期,只要泰然处之。这种从叹老到喜老的转化⑩,酝酿于白居易五十多岁时。五十三岁时作的《自咏》诗云:
夜镜隐白发,朝酒发红颜。可怜假年少,自笑须臾间。朱砂贱如土,不解烧为丹。玄鬓化为雪,未闻休得官。咄哉个丈夫,心性何堕顽。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高声发一吟,似得诗中仙。……
对于安静闲适的希求更胜于哀怜形体的萎老。在五十八岁时作的《对镜》诗里,白居易认为“静中得味何须道,稳处安身更莫疑”。五十八岁至六十岁作的《对镜吟》中,白发是长寿与高位的象征:“我今幸得见头白,禄俸不薄官不卑。眼前有酒心无苦,只合欢娱不合悲。”(11) 他并与好友刘禹锡(772~842)共勉安度老境: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咏老赠梦得》,第2236页)
既然视力减退,不必勉强阅读;反正懒得梳理头发,干脆不照镜。偶尔照了镜子,也不对镜中形影有所惊怪:“闲来对镜自思量,年貌衰残分所当。白发万茎何所怪,丹砂一粒不曾尝。”(《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第2405页)如同《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所云:“请看东海水,亦变作桑田”,万物皆战败于时间,诗人念兹在兹,凭借赏画与对镜产生的自我观照,最终都可以由“看见”到“不看”了。
三、凝视:再现与反射
笔者曾经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或译拉冈,Jacques Lacan,1901~1981)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关于观看行为之一的“凝视”(gaze)概念,分析唐宋的题画文学(12)。本文希望再从看画与对镜的共通点、绘画与镜子的不同物质形式及其感官特性,谈谈诗人如何凝视自我,认知自我。
白居易的写真诗与对镜诗所凝视的对象(或对象的原主)始终是自己,因此“凝视”论述中所含括的权力、性别与暴力性问题(13) 在此姑且不谈,仅集中于自我意识的层面(14)。
康德(Kant,1724~1804)认为“一切认识起源于感觉”,黑格尔(Hegel,1770~1831)也指出,自我意识是“从感性的和知觉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5],因此,自我意识的形构过程与人的“感觉”、“知觉”有关,也就是经由感觉的认识活动“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总体把握”[6](P49)。拉康认为康德和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局限于认识活动,局限于精神本体,主张回到弗罗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认识活动与心理活动二者结合,才有了现代文化层次中的自我意识[6](P49)。
拉康观察六个月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认出镜中自己形象的经验过程,提出了所谓“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的看法。在镜像阶段中,婴儿起初视镜中的影像为实存的事物,接着认为那是他人的影像,最后辨识出那正是自己的影像。人的自我认知经历,便是以自我映像(imago)为认识对象,从镜子中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的映像,拉康称之为“假自我”(false self)。这个视觉的形象与自我感觉合为一个结构,发现自我(ego)的完形(gestalt),逐渐摆脱了其“支离破碎的身体”的处境,而得到初步的自我认知(15)。
回到白居易的诗作中来看,丰富的对镜诗显示他长期以镜子鉴照自己的形象,一直渴望从镜中的“我”认知真实的“我”,从镜中呈现的自我的视觉映像得知主体的存在情况。所以当他凝视镜中的影像,特别留意的是头发变白,容貌变老,感知这些身体上反应的年华流逝迹象,是自我意识之来源。虽然其间未见如婴儿一般似非而是的辨认过程,白居易从未怀疑或迷惘镜中之像是否为幻觉,但是他也明白镜中见到的是“影”,他说“晨兴照青镜,形影两寂寞”(《叹老三首之一》,第517页),“形”与“影”是个别独立的个体,“影”的寂寞映射了“形”的寂寞,而“形”——身体,最直接体现“我”的样态(16)。
白居易为何特别关注镜中影像的生理变化呢?他不断地焦虑衰老,继而用“喜老”试图淡化或消解“老”所伴随的疾病、所暗示的死亡,不只是由于爱惜生命,希冀停滞青春,而是耽恋“审美自我”(aesthetic self)的完好形象。拉康提出婴儿对于观看镜中的自己流露的强烈兴趣,可视为人生初期的自恋。反观白居易,照镜是一种刻意的“制造镜像”的举动,自我产生了镜像,镜像完成了自我。婴儿满足于认定自己正是镜像的完形;白居易则在“制造镜像”时,表现不满于被镜像完成的自我,情绪不安:“欲照先叹息”(《叹老三首之二》,第517页)、“照罢重惆怅”(《感镜》,第534)。叹息与惆怅的原因,便是“我惭貌丑老”(《以镜赠别》,第527页)。
相较于照镜,画肖像的刻意“制造”意味更为浓厚,白居易写给画家的诗说道:
子骋丹青日,予当丑老时。无劳役神思,更画病容仪。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第1085页)
白居易非常介意自己的“丑老”之貌,“丑老”无药可救,破坏“审美自我”的形象。
前文谈过“自我形象”的三重层面,其中“理想的自我形象”包括“审美自我”,即具体生物的身体以及精神心灵的境界。白居易经常并举“身”与“心”,对照或互补,说自己身如“蒲柳”:“蒲柳质易朽”(《自题写真》,第311页)、“蒲柳之年”(《病中诗十五首并序》,第2386页)、“一枝蒲柳衰残身”(《感旧》,第2493页)。心如“麋鹿”:“麇鹿心难驯”(《自题写真》,第311)、“病对词头惭彩笔,老看镜面愧华簪。自嫌野物将何用,土木形骸麇鹿心。”(《中书寓直》,第1266页)难驯的麋鹿之心其实还是有着自我的期许,那就是立功于朝廷。像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画霍光、苏武等武功于麒麟阁[7](卷57,P2468),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表彰长孙无忌等廿四功臣,阎立本(约600~673)奉帝命图绘画像于凌烟阁。白居易一生的功业,也的确无所辜负,以致于寻求身心的安闲自适[8](P10~30)。
看画与对镜的凝视经验有共通之处,但从媒介物的性质而言,又有所差异。前文谈到白居易明白镜中所见的是“影”——“晨兴照青镜,形影两寂寞”。观看自己的肖像画,同样是“影”,却是“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题旧写真图》,第403页),画上的“影”和现实中的自我有着时间点上的落差。照镜时,物理的流动时间在镜中镜外是并行同步的;观画时,画上的“我”永远比现实中与之相对的“我”年轻,即使是画家即席完成的肖像,所再现的仍然是主体被图绘当时的形态,画中的时间是停止于彼时彼刻的时间。因此,写真诗的先天条件便被赋予了“回忆”的特性,每一次观画,便是一次对过去的自我的巡礼。于是白居易会写道:“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顇卧江城。”(《题旧写真图》,第403页)回想画像初次绘成的情景,对比如今的人生境遇。在《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中,清楚交代一生肖像画的前后因缘:
元和五年,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时年三十七。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时年七十一。前后相望,殆将三纪,观今照昔,慨然自叹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几变。……
白居易说实际的“我”与画上的“我”如同兄弟,真的是“我看我,我亦非我”。只要我还存活,镜中的“我”“回映”(reflected back)的始终是当前此刻的我。绘画则未必。白居易说“莫问真何如,画亦销光彩”(《感旧写真》,第1491页),画上的“我”可能在年久坏损之后,甚至比实际的“我”还早殒灭。相反的,也可能在保存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比实际的“我”延长寿命。绘画毕竟是一种具体的物质,画上的“我”在被画家创造出来后,便是与实际的“我”分别存在于世间。比起镜中的“我”,画上的“我”的陌生感更强更深,因为那是经由人为手段再现的形象,可以说其实是他人眼中、他人笔下的自我形象。
白居易写的第一首写真诗说道:“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自题写真》,第311页)仔细想来,“我貌不自识”是很牵强,甚而不合实理的。在此(三十六到三十七岁)之前,至少在三十二岁的《秋思》和三十四岁的《感时》诗里,白居易已经谈过照镜得见自己的形象,既然照过镜子,怎会“不自识”?这“不自识”并非自己不知自己的长相,而是不知别人如何看自己,必须经由画家的再现,具体留存形象。所以他才会接着说“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借着认可被画家描摹出的外在容貌,表达个人的人生意向。他人心目中的“我”的自我形象,成为取决“自识”的根据。这又令人联想起拉康的理论,拉康提醒我们:左右错置的镜中之像其实是幻觉,是想像,甚至是异化或误认的自我。亦即,个体对于自我存在的认证所产生的自我认同的一致性是一种想像关系,自我主体始终是分裂的,是一个他人(17)。绘画的“他者”感受——“如弟对老兄”,非但更甚于镜像,也更具有想像与幻觉的成份了。
四、结语
本文以白居易观看自己的肖像画以及照镜题材的诗作为例,分析诗人从凝视自我的视觉体验中感知的自我意识。诗人透过再现或反射的媒介,得知自我的形象——真实自我的幻影、他人眼中的“我”以及理想之“我”的期许,这三重层次的“自我形象”,都不敌时光所导致的“变”与“坏”。
现代诗人余光中有一首诗,名为“与永恒拔河”,界河这方是“我”,彼端是谁也未见过的对手。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竞争游戏,每一次惊觉的败绩,都累计在我们凝视的画幅上、镜像中。
本文之部分内容,曾经由森冈缘博士翻译为《自己へのまなをざし——白居易の写真诗と对镜诗》,刊登于日本《白居易研究年报》第7号(东京:勉诚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36页);之后补充修订,于第五届东方诗话学会国际学术大会“东亚诗学传统与文化特性之再探”(seoul:东方诗话学会,韩国外国语大学校BK21新韩中文化战略事业团等共同主办,2007年7月3~6日)中宣读;会后再次修订,依《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规范删节而成。
注释:
① 白居易题写真诗的研究参看丸山茂:《自照文学としての“白氏文集”——白居易の“写真”(肖像画)》,《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通号34,1987年),第59~73页。泽崎久和:《白居易の写真诗老をめぐって》,《福井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1部(通号39,1991年),第1~29页。
② 根据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京都:世界思想社1971年版)。花房英树:《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74年版)。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罗联添:《白乐天年谱》(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并参考泽崎久和:《白居易の写真诗をめぐって》,泽崎教授的大作承蒙森冈缘博士赐知,谨此致谢。又,白居易还有《百炼镜·辨皇王鉴也》诗也和镜子有关,但是重点在“以人为镜”的规鉴比喻,非实质之镜,故不列于表中。至于诗题未言明对镜,诗中抒发对镜感怀的作品虽未列入表中,本文仍加以探讨。
③ 见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后引白诗皆据此本。
④ 例如任命官职的委派令“告身”中,有时也会绘画当事人的肖像,北宋司马光的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现存的例子。
⑤ 白居易在《画竹歌并引》里自称“天予好事”,喜爱绘画。关于白居易与绘画,参看泽崎久和:《白居易と绘画》,《福井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1部(通号40,1991年),第1~21页。西村富关子:《中唐期に於ける弓绘画と文学——白居易と绘画》,《东海学园大学研究纪要》(10,2005年3月),第104~189页。
⑥ 朱金城和汪立民《白香山年谱》皆认为《题旧写真图》所说的“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此三十六岁时的写真非李放所绘,见卷6,第312页。岑仲勉先生则认为未必别有一图,见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罗联添:《白乐天年谱》,第109~110页。仅就白居易的诗意,未详是否果真如此,故而笔者认为至少有三幅。
⑦ 墟见邦彦:《白居易“纪年”诗考》,内藤干治编:《中国的人生观·世界观》(东京:东方书店1994年版),第287~302页。关于白居易诗的日常性特点,参看川合康三:《ことばの过剩——唐代文学の中の白居易》,《终南山の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东京:研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17页。
⑧ 又,白居易二十八岁时作的《生离别》诗有谓“未年三十生白发”,可能当时白发虽生出,尚不明显。
⑨ 白居易还有《嗟发落》诗,见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22,第1509页。
⑩ 韩学宏:《白居易诗中的“老境”》,《华梵学报》4卷1期(1997年5月),第1~17页。王红丽:《白居易诗中衰老主题的文化阐释》,《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69~71+97页。黎活仁:《从叹老到喜老:(诗经)、(楚辞)到白居易的演变》(“第四届先秦两汉学术国际研讨会——上下求索:《楚辞》的文学艺术与文化观照”,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第303~330页。
(11) 埋田重夫教授研究白居易的白发诗,归纳出十项内容要点:“悲秋”,“惜春”,“失意、落魄,不遇”,“左迁、流谪、望乡、客愁”,“伴随具体声音所带来的形象”,“吟咏病与死”,“白发为长寿之象征”,“白发为显官荣达之象征”,“致仕、退老、隐栖”,“白的颜色印象”。在同样具有时间意识的自题写真诗和对镜诗里,也有类似的面向。详见埋田重夫:《白居易の白发表现に關する—考察》,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刊行会编:《中国古典学论集: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版),第517~539页。中译《白居易白发诗歌表现考》,增野弘幸等著,李寅生译:《日本学者论中国古典文学: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集》(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32—256页。
(12) 衣若芬:《观看、叙述、审美——中国题画文学研究方法论之建构》,《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版),第2~29页。
(13) 参看Norman Bryson,“The Gaze and the Glance”in Vision and Painting:The Logic of the Gaz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88~131.Lynette Finch,The Classing Gaze:Sexuality,Class and Surveillance(Australia:Allen & Unwin,1993).Norman Bryson,Michael Ann Holly,and Keith Moxey ed.,Visual Culture: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Hanover,NH: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fo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4).[英]Peter Brooker(彼得·布鲁克)著,王志弘、李根芳译:《文化理论词汇》(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64~167页。孙萌:《凝视》,《文化研究》第5期。
(14) 又可参看林明珠:《试论白居易诗中表现自我的艺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5(1996年6月),第81~110页。
(15) Jacques Lacan著,李家沂译:《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形塑“我”之功能的镜像阶段》,《中外文学》27卷2期(1998年7月),第34~42页。Darian Leader著,龚卓军译:《拉冈》(台北:立绪出版公司1998年版)。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96页。
(16) 白居易对举“形”与“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陶渊明的《形影神》诗以及中国的形神论传统。陶渊明的《形影神》,逯钦立认为乃针对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见《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8年1月),第211~228页。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则以“新自然观”理解陶渊明有别于嵇康的“旧自然观”,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张亨教授《读陶渊明的形影神》总汇诸说,标举陶诗融合儒道的见解,见《现代文学》第33期(1967年12月),第50~60页。无论采取何种阐释的角度,陶渊明在《形影神》序文指出的“惜生”观点,均可与白居易诗中的生命意识基本相通。不过,陶渊明所写的“影”,如《影答形》所云“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是指日照于物之影,与白居易对镜之影有别,故而白居易云“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白居易对于陶渊明《形影神》的继承,其实表现于拟《形影神》所作的《自戏三绝句》诗《心问身》、《身报心》、《心重答身》,也就是将传统“形神”、“形影神”的课题转为“身”与“心”的相应。关于此问题,笔者拟日后再作专论详述,本文暂不赘言。
(17) 杜声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27~132页。拉康著,汪民安译:《镜像期:精神分析实践中所揭示的“我”的功能构成》,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9页。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译:《拉康:镜像阶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黄作:《是我还是他?——论拉康的自我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7~22页。周小仪:《拉康早期思想及其“镜像理论”》,《国外文学季刊》1996年第3期,第20~25+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