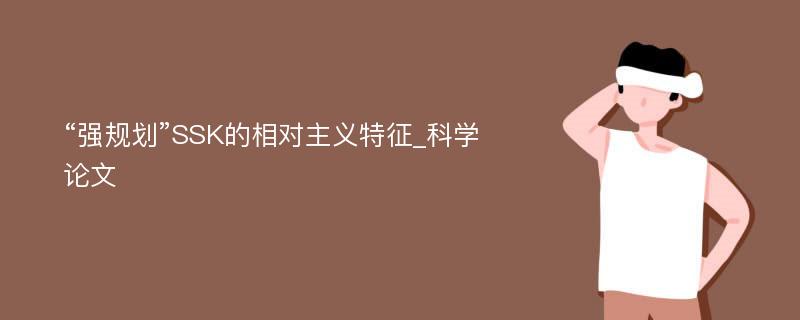
“强纲领”SSK的相对主义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纲领论文,特征论文,SSK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强纲领”SSK,即“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社会建构主义。其基本特征是:第一,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的反映,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谈判和妥协的结果,自然在确定科学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二,主张科学知识和事实本质上必须是一种社会建构,特别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
一般来说,“强纲领”SSK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倾向。他们提出①无偏见性原则:“应该毫无偏见地对待真理与虚假、合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种二分法的双方都应该得到解释”;②对称性原则:“上述解释是对称的。同类型的原因既能解释正确的信念,也能解释错误的信念”[1]。按照这种观点,有关自然秩序的一般观念,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原始人的宇宙观还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同样都是虚假的,或者同样都是真实的。
正是借助于这种相对主义原则,强纲领SSK对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解构。
1 对实在的解构
逻辑实证主义没能把实在论处理为科学家活动的一种社会特征。通过研究科学家的集体活动,“强纲领”SSK把社会学引入实在论研究,这是一种进步。但由于这种研究抽掉了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把科学对象看作是一种纯粹社会建构的产物,结果走向极端相对主义。
安德鲁·皮克林在1984年发表了一本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的书《建造夸克》,这本书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早期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把科学理论看作是科学家之间社会协调的特殊文化产物。在这本详细讨论高能物理学历史的书中,皮克林一开始就批评把“实验看作是理论的至高无上权威”的实在论观点。他说:“当科学家通过对自然进行研究而做出科学判断时,我却试图理解他们做出这种科学判断时的文化内涵。”[2]70年代早期,“味道”模型与“颜色”模型被认为是对夸克的不同解释。到70年代后期,大多数不同物理学家团体都发现“味模型”更适合他们的特殊兴趣和实用目的,结果“味模型”就成为整个物理学共同体的制度化程序与实践的一部分。正如皮克林所说的那样:“味夸克被保护在高能理论物理学的几种亚文化的实践中,并且在这一保护过程中,它变为了实在。”[3]
巴恩斯等人总结到:“科学有其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论策略不是研究电子,而是‘电子’与‘其’电荷。这种策略已经被制度化为物理学的一部分,以致于物理学家已经忘记了电子是一个理论实体,把它视为一种通常的客观客体:把电子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这种理论实体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相互之间协调的产物……原子、电子与夸克等和热素与燃素具有相等地位。就这种对象的存在方式,就对维持这种存在状态的实在论模式所采用的技术与设计来说,它们在所有文化中,是人类典型的创造物。”[4]
2 对归纳法的解构
在上述本体论解构的基础上,“强纲领”SSK进一步对科学方法论进行了解构。最著名的工作就是柯林斯的所谓“归纳问题的社会学解决”。在其著名的《改变秩序》一书中,柯林斯讨论了韦伯对引力波的探测实验。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都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这就是“实验循环。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困扰任何实验者。在实践中,这种循环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打破的,并且这种谈判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认识基础。按照柯林斯的观点,科学家是借助于科学共同体中现存的公认信念来打破这种循环:在这里,某一传统中的科学家坚信在某种现象中,他们具备探测到这种现象的实验能力,而不相信这种现象能否证这种实验。只要在这种信念下,科学家就能够证实其所渴望的结果。用柯林斯的话来说就是:“在泛心理学(parapsychology)中,用一种替代现象来打破这种无穷的实验循环。”[5]结果是“科学家个人联系着较广泛社会中某种制度框架,并且能够证明这种框架就包含着实验室研究的选择和工作结果”[6]。根据这一点,那些在1970年不相信引力辐射存在的人可以认为其信念已经被“有资格”的实验所证实,而那些对立的观点也可以声称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在归纳上的支持。按照柯林斯的观点,对引力现象中的事先相信与事先不相信是不同生活形式与传统的特征。因此,当争论发生在不同生活形式的争论者之间时,它们往往是最激烈的和最顽强的,这不是其对手在任何实验技术上无能或失误,而是不同生活形式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争论。维持信念的不同共同体沿着不同的道路引导着自己的归纳,使归纳法分别适合于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并认为这种适合只能由自己所生活的传统所证实。在自然中被感觉到的规则,不是从自然的经验中产生,而是从描述自然的共同体中公认规则中产生。这就是柯林斯所谓“归纳现象的社会学的解决”[7]。
3 对实验的解构
就实验问题而言,“强纲领”SSK认为它们总是在一个特殊研究框架中出现,在其中传统能够区分出哪些能被观察到和哪些不能够被观察到,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并且这种发现纯粹是一种“机遇”。
巴恩斯等人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密立根的著名油滴实验。这种分析的结果是:密立根没有在其实验中真实地观察到电子,而是在“本质上”看到一个电子,词“本质上”暗含着科学中实际看到的是对一个原子的真实捕捉过程,这一捕捉过程主要是依赖于科学有家处的科学传统,而不是实验。“密立根对他的结果的处理将允许我们进一步地观察到作为文化的麦克斯韦这种特殊传统是怎样被采用的。当然这并不是这样做的惟一道路,但的确是一条道路。因此,就我们对这段历史插曲最好的认识而言,它被接受为一种没有理性的偶然事件。”[8]“对于科学家来说,世界是研究对象,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科学家研究的世界是研究对象,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就应该避免指出:密立根理论的正确性不是来源于其研究对象,而是来源于其对事实真理性的反映。”[9]这样,在“强纲领”SSK看来,不同的解释传统就会产生出不同的真理,密立根只是很偶然地采用了麦克斯韦这一解释传统,如果采用另外一种解释传统,就会发现不同的真理,也许就是电子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自然事实”。结论是:“正如如果我们是用水桶从井中打水,那么水就自然是应该以水桶的大小为单位而存在。同样电子应该依靠这种推理而存在”。“这是作为具有资格机制的实验的问题所在。所有这些内容,其标准是靠这样的制度来保证:不是在人、实验仪器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是人类文化的因素,它们是解释的规范。”[10]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家的精神是我们的客观世界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交汇点,科学家的解释总处于自然与文化合作,客观与主观的相互作用之中。
4 对理论的解构
“强纲领”SSK是通过人种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来达到对科学的逻辑结构的解构的。
人种学方法论的经典著作是哈罗德·伽菲肯(Harold Garfinkel)的《人种学方法论研究》。伽菲肯把文献学方法描述为寻求一种隐藏在大量完全不同意义表象下的同源模式(Homologous Pattern)。伽菲肯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其中的主人翁叫安吉斯,她本质上是一个女性,但不具有女性的明显解剖特征,包括发育完好的生殖器,结果使她不得不带有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外表活动。这里强调的是安吉斯的女性本质是体现在这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女性的外表活动中(文献记录中),而不是其生理特征中。这种方法现在已经成为“强纲领”SSK的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这种方法,“强纲领”SSK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观察受理论污染,那么理论也受观察污染。对以社会学术语去理解理论来说,这一点是关键的。”[11]相对于奎因的理论来说,这应该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强纲领”SSK目的不是在这里,而是想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实现后现代的解释学转向。巴恩斯等人强调:理论是由观察报告(文献记录)来证明的,随着理论的记录、观察报告的增加,理论就将显示出其本性(类似于安吉斯的女性),理论将被理解。“这就要求把理论看作是一个比喻。……因此我们能够抛弃理论在逻辑上强制用法,强迫科学家采用逻辑程序进行思考的做法。当再一次认识到科学家是用相似与类比的直觉来进行思考时,他们倾向于一种特殊形式的比喻性描述。……这样的重新描述必须根据有关科学家的偶然性判断来理解,不是作为其理论‘真实地演绎出来’的必然结论。”[12]
5 知识的政治学
在宏观上,“强纲领”SSK的目标是描述行动中的科学,考察科学家在实际中是怎样“制造”知识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政治与权利这类社会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拉脱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他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13],这是对整个科学活动的一种社会学描述,在其中,他认为科学家是范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科学家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政治利益与观点之间的斗争。“演员网络理论”,现在已经被科学社会学家广泛认可和采用。这方面,夏平与斯恰夫的《利维塔与空气泵:波义尔、霍布斯与实验生活》一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什么是“理论符合实验与观察”?夏平与斯恰夫通过对科学史上的第一场大论战,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波义尔——哲学家霍布斯之争的分析,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社会学的回答。这是公认的“强纲领”SSK最出色的案例分析。在本书中,两位作者试图表明的是:与把实验看作是一种认识论标准不同的是,他们所揭示的新事实和新思想发现:近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封闭、对自身特权持高度警惕和对缺乏资格的门外汉持敌意态度的团体。更进一步说,自我任命的科学贵族在组织上是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其方法与观点反映着当时的政治要求。反过来,科学的权威、地位与认识论上的垄断是由它所服务的国家的权力与社会组织来保证的。
在夏平与斯恰夫看来,首先,实验检验只能够代表一个像波义尔这样绅士的证词。这种检验是让少数具有特权阶层的人在实验室中制造一个事实,然后在皇家学会上宣读,让其成员相信这是事实,结果达到一致。反过来。这一共同体就成为这一事实的口头证明人。没有这种一致,事实就不可能被认定。这些人的话,一般被认为是可信赖的,因为,皇家学会强调其成员“绝大多数具有绅士风度,自由的与没有私利的”[14]。因此,所谓实验检验就意味着皇家学会少数特权阶层决定了“科学事实”的存在。
其次,金钱成为一种认识权威的基础。书中的水泵,不是一个简单的装置,这是17世纪非常昂贵的仪器,有金钱与地位的人才可能利用这种仪器进行气体的重量与压力研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进入皇家学会。失去这种机会的人不是其智力上的问题,而是没有地位与金钱。波义尔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就能成为科学精英。
因此,在夏平与斯恰夫看来,作为划界标准的所谓实验活动,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科学家全神贯注于谁将被视为科学权威、在科学争论中谁的判断将值得尊重,谁的证据被视为可信的,谁的认识方法是可靠的,而这一切都和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参与实验的学术讨论是和名利、财富、政治和宗教信仰,和查理二世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新生的皇家学会,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与社会观点的产物与代表。“强纲领”SSK的这种科学图像是令人沮丧的:科学被描述为一场永不停息的残酷斗争,在范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借助于财富、地位和斗士的狡诈,笼络了大量亲信为其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地位服务。并且,“强纲领”SSK已经广泛运用这一过程来解释天体力学、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的诞生。在其中经验证据并不代表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被视为一种恐吓,一种疯狂权力的代表。
夏平与斯恰夫从他们的特殊案例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是获取自然真理的认识方法。“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知识形式的约定与人为的状态时,我们就把我们置于这样一种地位:认识到科学是我们自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对我们认识负责的实在。知识,就像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15]
6 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强纲领”SSK的思想根源于利奥塔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因此,西方学术界认为“强纲领”SSK是后现代科学的主要代表。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是一本在西方学术界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他所谓的“后现代”是指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态,这种知识状态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作为语言游戏的科学及其方法论上开放的多元性;第二、像福柯一样,科学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认识。
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神话的破灭。这些“元叙事”指的是支撑人类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真理。利奥塔认为这种“元叙事”的破灭意味着科学应该归属为不同的生活形式,这种“元叙事”方法已经被大量的“语言游戏”所代替,每一游戏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游戏规则。这样,科学认识论价值(真理、理性,观察等),其优先权在后现代社会中已经让位于“叙事”的策略。根据这种策略,科学不再是一种知识,而只是一个故事,与文学、诗歌类似的在范式中叙述感情的故事,一种说服人的诡辩术,从而实现了所谓后现代的解释学的转向。在后现代社会中,衡量科学的真理性,已经不是根据方法论规则来判断,而是表现为其赢得相关科学共同体成员一致的默契程度。“每一特别品类的知识都有其专门的特定法则。除非偶然,否则,各科领域中,自有其评定步法、行动恰当与否的标准,不可混同其他领域的评定标准……这就引发了两项值得关注的科学知识特质:其一是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上的多样性,亦即科学语言的多样性;其二是科学注重语用有效性的特质……而新的‘步法’的产生,是根据科学研究者们之间的民主意识和默契程度而被决定的。”[16]
显然,所有这一切是以完全放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标准与思维的严格性为代价的。后现代的世界被分割成为许多孤独的世界,它是一个拼图,一幅在地域性叙事中的各种各样元素随意组成的拼图,根本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图案。科学不过是众多叙事中的一种。其次,科学自身也没有统一的图案,存在着不同的科学叙事,各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有自己的事实与理性的标准。这实际上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走向了相对主义。再其次,在众多叙事中,利奥塔特别注意到了权力叙事,他把科学与政治、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关系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认为科学在后现代社会中已经丧失了其认识论功能,而仅仅变为一种权力,一种服务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后现代与现代“主要的差别不再在于知识与无知之间,而是像资金一样,存在着‘有偿性知识’与‘投资性知识’区别”[17],“在我们这个电脑的时代,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是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18]。
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一书中讨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明确提出:“政治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错误、幻觉或反常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自身。”[19]
由于原子物理学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原子核能威胁到整个人类与世界的命运,因此原子物理学家的话就代表着整个世界的声音。“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不是作为法理学家或高贵的人,而是作为被雇用者或专家。我这里所说的是原子物理学家开始进入历史前台”[20]。这种权力是与科学的普遍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声称对普遍真理的把握,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形象便在二战后形成。“在这种功能与威望中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真正的作家’,而是作为‘绝对的奴仆’、不再担负着所有的价值,反对非正义的统治和他的部长,甚至他们的反响超越了这种统治的声音……他不再写这一永恒世界的赞美诗,而是生与死的战略家。”[21]
总之“真理之争”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与利益的政治斗争,联系着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利奥塔和福柯有意识地解构各种各样的判断(认识的、评价的、伦理的和美学的等)的区别,然后再颠倒其原有的秩序,其目的是要放弃近代科学方法以及探索真理的研究模式。科学被视为一种话语的类,一种含糊的语言游戏,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规则,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的哲学家,如罗悌、奎因这样的后分析哲学家,海德格尔后的解释学家、与利奥塔和福柯这类后现代思想家之间,能够结成广泛的联盟。
“强纲领”SSK的泛滥,不仅威胁到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迷信与邪教势力的泛滥。这正是“科学大战”爆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众多科学家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投身于保卫科学,保卫理性,反对相对主义,反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中去原因。
收稿日期:2001-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