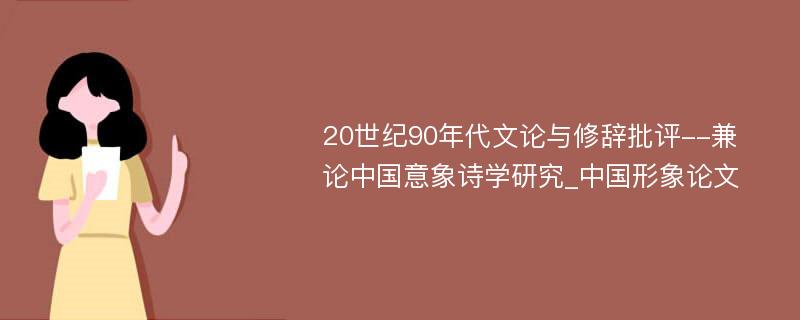
九十年代文论状况及修辞论批评——兼谈中国形象诗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文论论文,修辞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不少人有种感觉:文学理论在当前失去了80年代曾有过的那种魅力,变得不吸引人了,好多作家和读者也都不大看理论书籍了。你是做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理论研究的,你怎么看?
□:你说的这种“感觉”有一定道理,不过,并不全面,我还要说的是,有些东西可能被这种看似有理的“感觉”弄迷糊了,让人看不清楚了。这是需要加以辨别的。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理论在80年代的状况,然后再加以对比性说明。理论在80年代确实辉煌过,而且是一种“超常的辉煌”,这当然不是就其成果而言,而是就其声势和吸引力来说的。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需要“拨乱反正”,理论自然就被寄予厚望,成了“拨乱反正”的主导,扮演起文学界的“先锋”角色。人们要寻求文学创作的突破,或对新突破加以合理化阐释,都需要求助于理论的突破,或者与理论的突破一道前进。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不少作家、诗人都大量“消耗”新理论书,尤其是新译介的外国理论书。所以,在80年代文学界,人们是“格外”崇高理论的,尤其相信理论的超常魅力。但是,到了90年代,原来那么具有魅力的理论为什么突然间变得不那么吸引人、甚至那么不吸引人了?
△:你的意思是理论一度被抬举得高了?
□:是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作用,都难免对理论作了不切实际的想象、构想和理解。可以从这两方面看:一是犯有“理论至上”或“理论万能”的偏颇,即简单地割裂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这与“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关),片面相信理论先于并高于批评,总是要用理论去指导创作和批评,而现在看来,真正的理论应来自批评、与批评难以分割:二是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倾向,这就是相信本质先于现象,本质是理论思考的起点和中心,只要本质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构想文学理论体系总是先论证文学的本质再谈内容与形式、主题与题材等,而现在看来这是过于绝对化了。正是人们心中固有的“理论至上”和“本质主义”信仰为理论穿上一件神奇的外衣,使得它显得比自身更有魅力,从而制造了一种“理论神话”。我用“理论神话”的意思是说,理论被我们自己打扮得太神奇、太有权威了,以致超出了它本身可能具有的能力范围、或忘记了为它的能力划定某种界限。这个教训是必须认真反省的。我这样说不是要整个儿否定八十年代理论。其实那时的“理论神话”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并确实产生过有益的作用,而且人们的理论激情也是十分宝贵和令人怀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需要做的,不是热烈的缅怀而是冷静的反省,这对继续发展理论是必要的。
△:你这样说好像有道理,但我想知道,如果说80年代的理论确实出现了你所说的“神话”式谬误,那么我更关心的是,90年代的理论到底怎么了?
□:90年代的理论可以说是处在一种解构和重构同时交织进行的状态。对“理论神话”的解构是理论界已经和正在努力做的。这种解构状况的主要标志在于,人们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八十年代那种“理论至上”和“本质主义”信仰(当然还有少数人仍不愿改变,但其影响已日渐衰微了),转而从事别的工作。这不妨概括为“三化”:一是理论的史化,大量学者由于认为目前在基本原理上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也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论转向”的影响有关),就干脆转向中外理论史研究,对既往理论得失加以总结,取得了许多成果;二是理论的批评化,人们感到抽象的理论构想已经丧失了灵性,不如走向具体批评,在批评中重振旗鼓,这显示了新的理论活力;三是理论的专题化,人们不再热衷于构想普遍适用的“堂皇理论”或“大理论”,而是专注于追究专门而细致的理论问题,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
△:听了你的描述,我算明白理论工作者们在做什么了,我想别的朋友也会由此对理论界现状有了一种新“感觉”。但是,我想知道:这样的理论现状还能使理论重新具有吸引力吗?
□:如果你同意上述三方面说明,那么,你想必会承认,理论并没有像人们感觉的那样轻易退场,或者那样满足于自我解构,而是正在从事解构中的重构工作。也就是说,现在破灭的主要是理论的“神话”般幻觉,而不是理论本身。我认为,虽然“理论神话”破灭了,但理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你所批评的当前理论缺乏吸引力的状况,诚然有道理,但应当看到,这一方面与理论界自身的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应与创作界的理论素质关联起来,因为理论的发展并不只是理论界自己的事情,创作界也负有一份责任。我的意思是,不应当仅仅反思理论界,也应当同时反省创作界。
△:你这样说有点新鲜,不过,仔细想来,又确有道理。那么,创作界该怎样参与理论建设呢?
□:我觉得,一是要给理论界以时间,不能指望它一下子就能拿出新的且富有征服力的东西来;二是创作界的朋友本身也应当清理自己内心的“理论神话”残余,破除对理论的不适当的过分崇信,转而冷静地对待理论,重新认识它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而建构新的理论。我说的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因为文学史告诉我们,很多新的理论其实往往来自于充满活力与个性的创造性作家,而不是那些故作高深的理论家。我说一句可能不大中听的话:不能只指责理论脱离创作,也应当看到创作疏远理论的情形。当理论已经脱尽“神话”外衣时,我们的一些作家却还在那里静待它的“神话”风采重新降临,以便由此获取创作灵感:当整个文学创作潮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或转向时,一些人还在那里死抱住旧有信条写作,这些岂非咄咄怪事?当然,好在有的作家已经和正在那里积极地思考新的理论问题,并以他们的新作实际地证明了新的理论方向,或为新的理论的创生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激励理论家们去创造。因此,我乐观地相信,90年代理论界失去80年代那种吸引力固然令人遗憾,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其正常的和积极的方面,看到宁静表面下隐伏的理论潜流。很可能,理论丧失的只是其“神话”般超常威力,而得到的却是新的活力。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作家和诗人朋友能一道来关心理论重构,甚至成为理论重构的先锋或主力。
△:这一点我赞同,衷心祝愿你关于理论界和创作界联手创造新理论的想法成为现实,并且获得成功。那么,你近年来在做什么理论研究?能否介绍介绍?
□:90年代以来,理论界的分化已成了必然,路子多样化了,各说各的,杂语喧哗嘛,这很正常,谁也不能说自己就是正宗而别人是异端。至于我个人做的,实在算不了什么,这几年的工作或许都可以统括在“修辞论美学”或“修辞论批评”这名称之内。从80年代末以来,我对“理论神话”状况、尤其对其中的“理论至上”和“本质主义”不满意,希望有所变化。经过反省,我找到了自己的新起点:从纯理论转向批评性理论,在批评中重构理论。我发现,进入90年代以来,理论界现有的认识论美学、体验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已经丧失了往日的灵性及整体风貌,被肢解为碎片,但并不能说它们就都“寿终正寝”了,而是仍有其特殊价值,需要透过表面迷雾而加以分析和抢救。我认识到,应当突破以往认识论美学的内容阐释、体验论美学的个人体验还原和语言论美学的模式分析等各自的单一视界,转而寻求把它们以新的方式重新聚合起来。这样就有了“修辞论批评”,就是把理论置放在批评之中,与批评紧密结合,以对文艺本文的修辞论分析为中心,着重考察本文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修辞性“互赖”关系,再由此深探更为深层的历史,为此我对自己提出了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语言的历史化和理论的批评化等具体要求。
△:你的“修辞论批评”有点新鲜,我感兴趣,因为我也希望有人做一点新的突破性工作。但同时,我更怀疑:你的主张真的有什么新东西吗?这些年打着新招牌炒旧货的不少,人们要的不是“招牌”,而是“实货”,你能否先拿点出来给我们看看?例如,你在著述中是怎样使你的新主张落到实处的?
□:你的警觉有道理,我很赞同,我对自己的尝试结果怎样确实不敢自夸,但我欢迎你检验甚至挑剔,这我感谢还来不及呢!简单说吧:我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年)里作了最初的尝试,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正面中心英雄形象——“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作了修辞论阐释,其中尤其注意运用语言学或符号学模型去分析典型人物,如用“符号矩阵”分析陈天华《狮子吼》、鲁讯《祝福》和柳青《创业史》等,以“三角结构”分析《冲出云围的月亮》等:接着我在论文集《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艺》(1997年)中除了从理论上明确梳理“修辞论美学”主张之外,还把修辞论阐释视野从文学扩大到其它艺术,如分析“张艺谋神话”及90年代审美文化:最近,我刚出了一本书《中国形象诗学》(1998),同样是顺着这个路子走的,研究近十年文学新潮中的中国形象。
△:你这样说我算是对你的工作有了一个大体了解。我感觉你用新路子重点分析的还是文学与某种外在的原因的联系,即你所说的文学本文与“文化语境”的联系,当然你加进了自己的新东西,如把语言学模型统合到修辞论阐释中,我感觉这在目前理论和批评界是有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你是否考虑到,文学首先和直接地是审美的?你在那样做时把“审美”放到了何处?而如果不讲“审美”,那文学是否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还有,我对你最近的“中国形象”研究有兴趣,能否告诉我:怎么想到研究这个问题的?
□:你这是搞贴身紧逼啊!这两个问题可以并到一起回答,它们在我实在是同一个问题。你说的有点道理,我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中确实主要是从文学的文化阐释角度去分析典型形象的,在那样做时,为了特别突出我所见出的文化意义,我不得不暂时忽略或淡化审美方面。写完后我自己也感到了一种不满足,回头作了认真的自我反省,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应当把文学的文化阐释同我过去曾十分投入的审美(体验)阐释结合起来,即探索一种对于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文化阐释结合的双向阐释之路。这就需要找到那么一个合适的形象概念或问题以便实现这种双重阐释,于是,“中国形象”问题就逐渐“跳”了出来,给我以极大的诱惑。我感到,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中国形象正集中凝聚了20世纪中国的审美与文化危机及其化解策略,可以说是这种危机的一种尤其富有感召力的象征性解决方式,具有审美与文化双重意味,值得一做,而这在1985年以来的文学新潮中有丰富的展现。
△:能否谈谈中国形象问题研究现状?你的研究与这有什么关系?
□:近年国内涌动着一种“中国文化”或“中国形象”热。一是出版由国内或国外学者撰写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类著述,如《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美国的“显学”——中国学》、《世界的中国观》、《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费正清看中国》、《外国政治家眼中的中国》等,这些主要是谈论外国人“看”到的“中国”,让我们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二是重版一些旧作,如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的《中国人》等,重温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这显然表明当前学术界的“中国”热正在持续升温。我认为这一热潮颇有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迫切的反省渴望、憧憬及探究兴趣。我的研究无疑与这热潮有关,但我感到其中存在一个缺憾:大多是从文学以外或外国文学角度去谈论中国的,却没有充分体现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学界的“声音”,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造的丰富的中国形象,至今还缺乏集中有效的阐明。所以,我希望自己这本不大成熟的东西,能权且补缺,以待成功的后来者。
△:你的“中国形象”的内涵是什么?它是怎么包含你所说的审美与文化双重意味的?
□:简单说来,“中国形象”是指有关“中国”的艺术形象,即艺术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中国形象所含有的审美与文化双重意味,可以首先从“中国”一词的原初的形象性见出。这个词语在最初和长时期里,原是用来形容或比拟中国文化的权威地位的象征性或形象性词语。只是由于后来沿用已久,尤其在现代,其原初的形象(象征)意味才渐渐地被淡化甚至遗忘了。“中国”,作为形象性词语,原初地意味着“天下”之“中央”。“天下”一词代表的不是后来的“全球民族国家”,而是指世界文化或文化世界。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表述,“中国”就大致相当于“世界文化的中心”。正由于如此,作为古代文化帝国的中国在长时期里一直不需要和不曾想到民族国家的国体名称,而只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这一总体象征性形象。不过,中国的这种文化象征意义又是与特殊的审美魅力分不开的——“中国”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某种深厚的审美内涵。不如说,在“中国”这个词语中,文化象征意义往往需要通过审美意义显现出来,并且始终不离开这种审美作用。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的总体象征,“中国”代表的是同时富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审美魅力的文化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本身就是在审美魅力中凝聚着丰富文化想象的形象,或者说,是洋溢着审美魅力的文化形象。“中国”同时蕴涵着审美意味和文化象征意味,即具有双重意味。“中国”如此,整个中国形象亦然,即具有审美与文化双重意味。不过,在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审美意义总是直接的,而文化意义则是间接的,后者通过前者、并始终不离前者而显现。如果不坚持这一点,就可能把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它领域的“中国”观混为一谈。
△:你刚才说的多是“中国”的古时含义,能谈谈它在现代又发生怎样的变化了吗?
□: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作为国体名称的“中国”要直到作为文化象征或艺术形象的古典“中国”走向衰亡时才出现,换言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诞生恰好成了古典文化“中国”衰亡的墓志铭!这一事实固然令人极度痛惜,但更应看到,也正是由于这种衰亡,现代中国人才可能更加清晰地重新唤起对于“中国”一词的丰富的文化想象和审美缅怀;同样,作为文化象征的“中国”,也才能如此深刻地植根在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以致只要这个字眼一出现,就会激起似乎无穷的中国文化想象。因此,对20世纪中国人来说,“中国”形成了不同于古代的特殊蕴涵:它在审美“平台”上把古代文化主义含义与现代民族国家含义交织在一起,即远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体术语,而往往是一个寄托着有关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主权的丰富想象力和审美体验的总体象征符号。
我这里只要提到闻一多写于1925年的诗《一句话》就清楚了:“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这里的“中国”,被视为是一个集聚了五千年文化想象和审美内涵的具有强大魔力的字眼,它只要一说出而无需解释,就能如“青天霹雳”或“火山”爆发地产生巨大作用:唤起民众、震慑敌胆、激发新的文化创造勇气。“中国”正是一个被赋予如此深厚的文化象征和审美意味的艺术形象。
△:你这样说的话,那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还有不少这样的本文呢。艾青的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7)就描绘了古老“中国”的沉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的路/是如此崎岖/是如此泥泞的呀。/……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漫长呀!/……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这里的“中国”同样显示了文化象征与审美意味。“朦胧诗”人梁小斌也有《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80)的急切呼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对!在这两首诗里,一方面,“中国”作为被描写对象出现,分别表明“雪”落的范围和“钥匙”的适用范围。但“雪”在这里已不只是普通的影响人们生活的自然现象,而主要被想象成危及中国文化生命的文化现象:同样,“钥匙”也不只是用于打开普通家门的钥匙,而成了开启整个民族的封闭已久的文化之门的钥匙,从而这两个词语都体现出丰富的文化象征意味。另一方面,“中国”还被拟人化地充当了抒情人“我”的倾诉对象。“中国”如果单单作为“国家”术语,怎么足以成为个人的抒情性倾诉对象呢?这里显然也是在运用它的文化象征意味。不过,需要看到,正像这些作品所体现的那样,在文学中,文化象征意味总是从直接的审美意味中透露出来的。
△:你提出了“中国形象诗学”这一新概念,您能否谈谈它的具体内涵?
□:“中国形象诗学”其实不是标明一种诗学原理建构,而只是表示一种诗学阐释,即对中国形象在诸种文学潮流中的状况加以阐释。另外,它与“中国”的联系,本身就决定了它同时也是牵涉面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因此,这项研究也必然要在美学或诗学视野中体现文化视野,带有“文化诗学”或“文化研究”的某些特点,而这正是我的“修辞论美学”主张的具体体现。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像什么?或,中国人想象之中国怎样?这正是令人既兴奋又焦虑的中国形象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浪潮迭起,中国形象是怎样在其中展开的呢?
□:在世纪初民族危机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就把有关民族自我的文化想象倾注到“中国”上,“新中国”、“混沌国”、“民权村”、“晨曦”和“天空”等形象表明了理想的与现实的树立,展示了中国的眼前的衰败和即将到来的美妙前景。其后,伴随着“五四”文化启蒙高潮,中国形象层出不穷,形成多元化局面:胡适眼中的东方“睡美人”美丽柔弱,需要由西方武士来吻醒:鲁迅笔下的“吃人”梦魇、“铁屋”等成了病态中国的隐喻:郭沫若则满怀浪漫激情把中国想象为一位“年轻女郎”。到了20年代后期至30、40年代,对中国现实的深重失望和对它的美好过去及未来的诗意体验,使得中国形象出现彼此对立的两极,这以闻一多的“死水”与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新中国的成立使有关现代中国的想象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凝聚点,“铁路”、“矿井”等形象显示了有关公有化和工业化中国的统一而单一的浪漫形象模式。可以看出,中国形象的创造已成为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只是在“文革”一度断裂。
△:从你的追溯中不难看出中国形象问题实际上是处于现代进程中的中国如何“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这种认识仅仅是“自我”确认吗?
□:完整的中国形象,应既包括自我形象,也包括“他者”形象,他者犹如镜子映照出自我的形象,“中国”只能在与周围他者的形象对比中认识自己的形象。简略地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中国形象呈现为前后两幅不同图景:古典性形象,自我与他者之间属我强他弱关系,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的荣耀:现代性形象,由于西方的强势介入,关系被颠倒:我弱他强。当古典性中国形象在西方他者冲击下急剧破灭,重构新的现代性中国形象就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一方面,在西方大他者的映照下,中国自我究竟已经呈现为何种现象?另一方面,凭借新的“现代性工程”,中国自我未来可能呈现为何种形象?因此,中国形象问题在20世纪出现,实在是首先出于急迫的文化复兴需要。对中国形象的反复寻找、呈现或重构,竟演变成了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性”传统。
△:你上面谈到的这个寻找中国形象的传统曾一度断裂,那么80年代以来文学新潮与中国形象的关联又如何呢?
□:我们已经知道,在80年代之前,本世纪中国形象创造已出现过四次浪潮:世纪初、“五四”时期、20-30年代和50-60年代,而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新潮显然可以称为中国形象创造第五次浪潮。分析这时期的中国形象可以抽出如下要素: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和市民形象。语言形象即为直接而具体的语言组织和语言特色,多种向度的文学语言探索留下了立体语言、白描式语言、间离语言等多种语言形象;表征形象是指那种在典范意义上表征“中国”文化独特风貌的形象,如“后朦胧诗”所创造的“黄河”、“大海”和“大雁塔”等形象;神话形象表达了当代人对中国文化根基的认同,是“寻根文学”的努力所在,如《爸爸爸》、《小鲍庄》等;家族形象是能体现历来重视家族统治的中国的独特形象,在这方面《红高粱》、《浮躁》和《古船》是值得分析的本文;市民形象是那些代表中国当代城市生活由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转变的新型市民人物,这是“新写实”小说对中国形象的一个特殊贡献。这几方面的中国形象涉及到了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各个层面,为我们留下可供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
△:在80年代后期以后文学新潮中,上述中国形象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其文化内涵如何?
□: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内语言形象体现为以新兴的奇语喧哗去消解主流化语言和精英独白,表征形象呈现出非正统形象对正统典型形象的瓦解趋势,神话形象表明文化的原始根基已经离散,家族形象显示正统家族权威受到了挑战,市民形象则披露出神圣的政治国家为世俗的市民社会取代的初始信息。总之,这些中国形象的共同特征是奇异或新奇性。从审美上看,当唯一神圣、庄重的正体中国支配乃至束缚了人们的审美想象力时,奇体中国的出场正是要打破正体一统天下的格局,为想象力的解放制造良机:从文化层面来考察,“现代性工程”所生产的富有新的中心权威和魅力的伟大中国在此遭到质疑。
△:“中国形象”的这种变化是否暗示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自我确认的一个新阶段?
□:不完全如此。从现代中国形象在本世纪的演进看,80年代后期至今具有特殊的新旧交替位置。20世纪现代中国形象内部总是交织着两组话语冲突:中心与边缘、崇高与卑琐等。面对这冲突,现代性形象总是竭力突出和证明着前者而掩饰和淡化后者,从而构造出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中国。这大体上属于现代性第一期,由于把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的伟大文化的持续生命力置于首要地位,所以主要地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现代性。而到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现代性第一期逐渐耗竭其能量而显示出衰败、解体迹象,80年代后期文学新潮创造的奇体中国正是一个明证。它不代表一个新的独立发展阶段,而是介于旧的解体和新的孕育之间。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处在“全球化”世界文化格局内,估计中国的民族国家问题不再会那么突出和紧迫,取而代之的首要地是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这要求它着重从文化角度重新确立自己的新形象——而这则是需要从现代性第二期去考虑的了。我想时间关系,咱们下回再聊吧。我的修辞论批评不过是众多批评之路之一,请随时批评。
标签:中国形象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神话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学论文; 文学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他者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