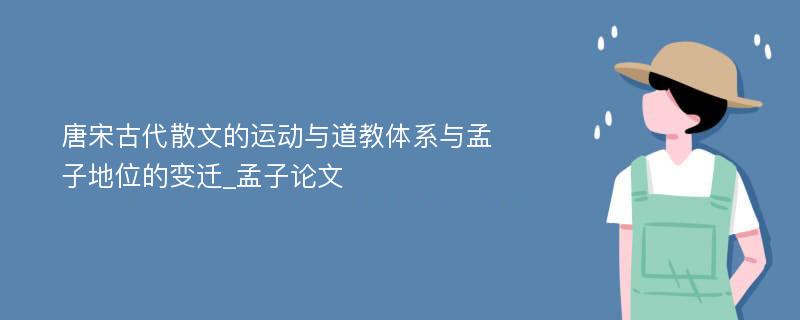
唐宋古文運動及道統說與孟子地位的變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唐宋论文,古文论文,地位论文,道統說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宋孟子地位升格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孟子在“道統論”中地位的確立與鞏固。一般認爲,“道統論的正式提出是在唐代韓愈,基本確立是在北宋程顥、程頤,完全確立和集大成是在南宋朱熹”。①韓愈及二程均將孟子視爲道統失傳前的最後一位關鍵人物,並都有唯己能接續道統之意。學術文化史上,二程與韓愈分屬兩種不同的群體,前者通常被稱爲道學家或理學家,向爲哲學史、思想史研究所重視;而韓愈則以文聞名,和柳宗元及與二程並世或略早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三蘇等人,被統稱爲“唐宋八大家”,是文學史研究的中心人物。事實上,不僅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三蘇等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尊孟傾向。如不局限于道學家式的道統論視角,不將韓愈至二程視爲單綫發展之必然,則對韓柳至歐蘇等所謂“文學家”思想的考察,也應是唐至北宋孟學研究的題中之義。
從中唐以至北宋後期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蘇等人爲中堅的古文運動,學界將其統稱爲“唐宋古文運動”。②古文運動,顧名思義,是針對駢文展開的一場文體、文風革新運動。但古文運動的涵義遠不止于此。如學者所指出的,“古文並非僅僅是人們尋求更宜于言志的文學方式的産物…而是尋找與文風的選擇相聯繫的價值觀”③。在這個意義上,古文運動可以說是一場“思想運動”,它力圖通過轉變人們的寫作方式來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爲方式。④古文運動不僅要在形式上“復古”,在內容上也同樣要“復古”,即恢復古代的聖賢之道,振興儒學,因此,古文運動不能視爲單純的文學運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與儒學的復古思潮緊密結合在一起。⑤有關“文”、“道”(儒家之“道”)關聯性的討論,以及對儒家道統說或文統說的申說,貫穿了唐宋古文運動的始終。諸家文/道統人物譜系多有分歧,但大體來看,孟子的地位在這一時期的論說中逐漸凸顯:中唐韓愈首倡道統說,孟子被尊爲孔子之後儒道的唯一嫡傳,其地位由此而極大提升;韓愈的道統說爲北宋古文家所繼承、改造,最終理學家又在此基礎上了重新確立了孔孟道統論,並以接續孟子之後的道統而自居,孟子作爲道統中樞的重要地位得以穩固和延續。
一、唐代古文運動前驅的文道說與孟子觀
唐代古文運動盛于韓柳,却非始于韓柳。大曆時古文家梁肅這樣概括初盛唐文的演變:“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⑥初唐以來肇端的文體革新之風發展至天寶年間出現一個高潮,延至貞元、元和間韓柳主盟之前,已有一批文士著手進行文體、文風之改革,發表文章復古之言論。他們被稱爲古文運動之前驅。
中唐古文家獨孤及曾概括天寶間文章之發展狀况,云:“帝唐以文德旉祐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向方。天寶中,公(李華)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于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⑦之所以在安史之亂前後出現了一個古文革新的高潮,實與當時唐代由盛世走向中衰的政治社會狀况息息相關。此期的古文運動不僅是針對駢儷之文的文體、文風方面的革新,而且與儒學復興的思潮緊密結合起來。中唐古文家所期許實現的就是恢復先秦古文的文學創作傳統,藉此重振儒家的王政和道德觀念,所謂“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希圖由此來恢復唐王朝的統治秩序。古文家們大都繼承了儒家傳統的詩教觀,認爲文章應宗經明道,承擔教化之功,提倡道德與文章的統一。他們主張恢復先秦兩漢儒家的文學傳統,將文學溯源至六經、子史,以儒家典籍爲文學創作之源泉。如阮元所云,“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⑧六經之外,孟子與荀子、賈誼等儒家子學的文章正是他們這種文藝觀念的體現,因而備受古文家的關注和推崇。《孟子》佐經的地位也因此而逐漸凸顯出來。
最早致力于扭轉人們的寫作方式和思想觀念,提出宗經明道主張的是開元、天寶年間以文並稱的蕭穎士和李華。他們痛心于當世之文人徒務于寫作淫麗浮華之文,空洞虛誕而無益于王化政教,且文人多浮薄無行,“詞人材碩者衆”而“體道者寡”⑨,使德行和文章常處于衝突的境地,因而感嘆“夫子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無人兼之。雖德尊于藝,亦難乎備也”⑩,“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于古歟”(11),主張實現德行與文章的統一,使文章有益于治道。蕭、李認爲必須將文章寫作奠定在儒家典籍的基礎上;儒家的經史之作,而不是純文學著作,纔是文之典範。李華云:“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昏明。”(12)蕭穎士自稱“僕有識以來,寡于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13)因此他們以經籍爲其思想、創作之源泉,所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14)李華所推崇、效法的對象即是儒家之經籍。“愚以爲將求致理,始于學習經史”,五經之外,“《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15),也在學習之列。“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遁矣。”(16)孟子之文章,文德一貫,尚能體現六經之志,可視作“六經之遺”,而其後之屈、宋則已使儒道不彰了。在李華看來,孔門四科中“文學”之道的傳承統緒是孔子—子游(偃)、子夏(商)—子思(孔伋)—孟軻。孟子意味著文道的最後體現者,其在古文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可以想見。李華與蕭穎士等古文家互相推重,成爲天寶末年文壇之主流,其文學主張在當世和身後均有很大影響。(17)
安史之亂後,梁肅、柳冕、權德輿等古文家繼承了蕭、李宗經明道之說,其中尤爲突出的是柳冕。他完全以正統儒家的觀點立論,明確提出了文道一貫的主張,而這個道即是儒家的教化之道。“君子學文,所以行道”。(18)“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19)真正能實現文道合一的就是君子之儒。所謂“君子之儒”,是與只明章句注疏的“小人之儒”相對而言的通經明道之士。先秦君子之儒的代表就是荀孟等人。柳冕在其文中一再稱頌《荀》《孟》等文是真正明道的“君子之文”。他指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繫于《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20)“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21)“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22)可見柳冕的文道觀以明道爲本,文章爲末,完全是以儒道教化爲主旨,以道之高下論文之高下,極大地取消了文學的獨立價值,近似于儒學復古之論,而幾無涉于文學。(23)柳冕以堯、舜、周、孔、荀、孟等爲文道正統,既有上中下層級之分,也有明顯的時間排序;所論雖是“文”之正統,因此特別點出孔子學生中專長“文學”的子游、子夏的位置,但既以道之高下論文之高下,則“文”之正統毋寧更是“道”之正統。這種“文道合一”的隱約的“文/道統”觀以及其對儒道的重視,在其後韓愈等人的道統說及其古文理論中得到了繼承。(24)在柳冕譜系中,荀孟因爲其文章宗經明道,文教合一,而處于較爲關鍵的中樞地位。
對荀孟之文的推崇幾乎成爲貞元、元和間古文家之共識。儘管同時代也有一些古文家對荀孟頗有微辭,如獨孤及曾批評“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25),但可以看出這種批評主要是針對荀孟之文的文學性,而無關乎文道之旨。李華以《孟子》爲佐經之作和荀孟之後文道陵夷的觀點被稍晚之學者多所承襲。如權德輿指出:“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况、孟軻,修道著書,本于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26)又,裴度《寄李翱書》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27)柳宗元則直接將《孟子》視同于經:“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28)雖然此時仍然是荀孟並提,荀子重要性甚至在孟子之上,對《孟子》之思想也缺乏真正深入的探討,但經由古文家對孔孟之文的推崇和關注,孟子其人其書的重要性無疑更加凸顯了。從這裏已經可以看到韓愈不遺餘力推重孟子的端倪,韓愈能够提出以孟子繼承孔聖道統的說法絶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廣的社會文化背景。
二、韓愈、李翱的道統論及孟子觀
公元8世紀末至9世紀初,韓愈、柳宗元在繼承前期古文家學說的基礎上,又對文道觀進行了更爲深刻全面的闡發,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大力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其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韓愈首倡道統說,推尊孟子爲孔子之後儒道的唯一嫡傳,極大地抬高了孟子在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李翱、皮日休等人又繼承韓愈的衣鉢,對道統說進行了調整和推揚。古文運動中道統理論的提出爲宋代孔孟道統的確立及孟子地位的升格奠定了基礎。
中晚唐儒學復興運動和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韓愈,出生于儒學世家,其父仲卿、叔父雲卿、兄韓會皆能爲古文,崇儒重道。受家學熏陶,韓愈自幼即讀聖賢之書,“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29),“少而樂觀”《孟子》(30),致力于闡揚儒道。爲了同佛道相抗衡,重振儒學之權威,韓愈提出了著名的“道統說”,構造了一個聖賢迭相遞緒、承接的儒道傳承譜系。
韓愈在《原道》中明確指出:“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31)韓愈構造了一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迭相遞緒傳承的儒道系統,認爲這纔是華夏文化的正統。
雖然“道統”一詞並非韓愈所提出(32),但對于儒家“道統說”的明確闡述和大力倡導却始于韓愈,在此之前尚無有關“道統說”之明確表述。關于其淵源,學界有受禪宗傳法世系啓發(33),受唐代孔廟祭祀系統啓發(34)等多種說法,但一般都承認韓愈道統譜系深受《孟子》卒章的影響,其內容實質多承繼孟子之說。
韓愈道統論所論“道”的核心內容是“仁義”:“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35)仁、義是孔孟以來儒家道德學說的核心,尤其是孟子在孔子之後進一步突出了“仁義”的地位,使“仁義”成爲儒家倫理思想的代稱。(36)“道”的具體表現是:“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37)“道”無所不包,舉凡儒家之典章制度、社會階層、倫理秩序、社會禮俗皆在其內,可見韓愈所謂的“道”實則是囊括了“整個儒家文化—社會秩序”(38),這同宋代理學家所講道統之“道”實有很大不同。
錢穆先生曾論及漢唐之儒與宋代理學家之分野,云:“漢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學家興,則志在爲真儒。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爲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軻。”(39)二者之別實即一偏于事功,一偏于心性,前者重外王,後者重內聖。而韓愈爲“自孔子下究之孟軻”的唐儒,其思想恰爲二者前後相承之過渡,其志在求善治,而又于心性修養有所措意,重新樹立了儒家以“仁義”爲核心的內聖外王之道。(40)
在內聖一面,孟子將仁視爲人的內在本性,認爲“人皆可以爲堯舜”(41),把“內聖”亦即成就君子之理想人格作爲個體的內在自覺要求,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42),君子修身之要即在于必反求諸己,從本心上反思。韓愈在心性修養觀上承孟子之說,强調道德自律。《原毁》篇指出“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43),並借用《孟子·滕文公上》及《離婁下》求爲舜之語(44),認爲君子應“求其所以爲舜”,“所以爲周公”,以成聖成德來要求自己。又,《省試顔子不貳過論》云:“所謂過者,非謂發于行,彰于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于未形,不貳之于言行也。”(45)强調道德的自覺、自主意識。此外,韓愈亦對孟子所說的“踐形”、“反身而誠”進行了深刻的詮解。(46)
韓愈雖然在如何成就內聖之心性修養上有取于孟子,但對于其性善說却並不認同。在佛教精深的心性理論刺激下,中唐的儒者開始致力于重建儒家的心性系統。爲反對當時“雜佛老”而言性之風尚,韓愈在《原性》中提出了“性三品”說。孟子之性善論、荀子之性惡說及揚雄之善惡混在韓愈看來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47),都是片面的。“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善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48)韓愈認爲性是人先天即具有的,由仁、義、禮、智、信五常構成,不同的人之性因其所具備的五常程度之不同而分爲上、中、下三種不同的品級。中品可以導而爲善爲惡,而上、下品是不變的。韓愈此說吸收、綜合了前代諸儒的說法,一方面承繼孟子的性善論,以仁爲本然之性,認爲五常“與生俱生”,是人內在固有的,近于道德先驗論。一方面又認爲性分爲善、惡、可善可惡三品。韓愈之所以有如此前後矛盾的理論,大概由于他一方面要對抗佛老“絶仁弃義”的心性觀,故而倡言孟子之道德心性論,一方面又念念不忘反復强調外在的社會等級秩序、禮法刑政的重要作用,要爲之尋找人性論的依據,因而不能接受孟子人皆性善之觀點,認爲性有“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49)之別。
內聖必以外王爲目的,是韓愈思想的基本主張。集中反映韓愈此種取向的就是其在《原道》篇中引用了《大學》那段著名的修齊治平之論。《大學》本是《禮記》中的篇章,漢唐間一直湮没無聞,少有關注者。其“明明德”之首段以“正心”“誠意”爲修身之要,以內在道德心性的修養爲治國平天下之始基,實則近于孟子存心養性,擴充仁心以推至家、國、天下的內聖外王思想。(50)韓愈將此段抽出,針對佛教只講治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違背儒家之倫常綱紀的情况,重新闡揚儒家內聖外王之道,指出“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批評不求“有爲”而專在“治心”的取向,强調正心誠意(“內聖”)必須以服務于政教倫理(“外王”)爲目的。
要之,韓愈的道統論無論是具體譜系還是對“道”內涵的闡發,均深受孟子影響。在其道統譜系中,韓愈賦予孟子以關鍵性的位置,指定孟子是先秦諸子中周孔之道的唯一傳人,並且這個道統孟子之後就失傳了。這一定位,與古文前驅如柳冕諸人所論之文道觀呈現出重要差异。一是“道”不同,李華、柳冕等人多是從孔門四科之一的“文學”論孟子所承襲之“道”,而韓愈則强調孟子傳承的是完整的孔子之道。二是“統”不同,前期古文家的譜系中,得傳孔子者前有游夏之徒,後有荀子等人,而韓愈則是獨顯孟子,大大抬高了孟子在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在《送王秀才序》中,韓愈詳細論述了孟子的師承:“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51)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在此明確勾勒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傳的學術譜系,但他同時也指出包括曾子、子思等人在內的諸多門人弟子對孔子之道並“不能遍觀而盡識”,即完整地傳承孔子之道,而唯有孟子能“得其宗”。因此,韓愈極力闡發“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的觀點,一再强調“始吾讀孟軻之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52),“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53)
韓愈道統論需要分說的還有傳道的方式問題。他認爲著書、“修辭”都是不得已的傳承道統的重要手段,“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54),“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55),“君子則不然…用則施諸人,捨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56)韓愈本人就是以“文學”爲業而志在傳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57),“愈也少從事于文學”(58),“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潜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59),“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60)换言之,文學與傳道在韓愈本是二而一的事業,創作古文即是傳道。
因爲主張“修其辭以明道”,所以韓愈一方面强調文學創作必須以“道”爲依歸,在古文創作理論與實踐上深受儒家觀念尤其是孟子的極大影響,如將孟子養氣工夫與爲文結合起來,論述“氣”之重要性等等;(61)另一方面,韓愈也很重視文辭本身的價值及重要性,認爲“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而文辭之“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也”,特別强調爲文需獨樹一幟的重要性,即便是師法古代聖賢,也應當“師其意,不師其辭”,文辭上不能因循守舊。(62)在《送孟東野序》中,韓愈集中表彰了包括孟子在內的歷代擅長文辭的代表性人物,“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63)有學者認爲這表明韓愈已有“文統”譜系的設計。(64)不過韓愈既未强調這些“善鳴者”有前後相承的統緒,更未指明他們對“文”有較爲一致的認識,所謂“文統”之說似難成立。即便視之爲一種“文統”,這一“文統”也只是純從“文”的立場而論,不能與囊括了“整個儒家文化—社會秩序”傳承的“道統”等量齊觀。從“文統”論,孟子與他奮力“辟之”的楊、墨等人並列,而從“道統”言,孟子獨出諸子之上,二者顯然也不可同日而語。
韓愈的文學觀及推尊孔孟道統的思想觀念對其門生友人多有影響。如李翱和韓愈一樣,都認爲著書是道不得于時的選擇,“凡賢聖得位于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當兹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65)李翱也認爲文學自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强調義、理、詞三者的統一,“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66)義理的傳布有賴于文,孔孟也不例外,“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67)李翱積極肯定先秦兩漢諸子的文學價值,“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御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子、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68)他一方面認爲諸子百家“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但另一方面又强調文章應是“仁義之辭”(69),要以教化爲根基,“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70)這與韓愈“修辭以明道”的文學觀一脉相承。
在“道”的一面,李翱也繼承了韓愈尊孟的思想,高度贊揚孟子辟异端之功,“自仲尼既歿,异學塞途,孟子辭而辟之,然後廓如也”。(71)在李翱看來,不同于諸子只是有得于“文”,孟子是既能文,又能傳道。李翱還將韓愈譽爲孔孟道統的繼承者,“孟子既没,亦不見有過于斯者”。(72)在爲韓愈撰寫的祭文中肯定韓愈辟佛老、昌明孔道之功,“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异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明”。(73)
但李翱所說的孔孟之道的傳承統緒及內涵與韓愈存在一定差异。李翱認爲儒家本有一套以《中庸》這一“性命之書”爲傳授核心的心性傳統,但漢唐間湮滅已久,學者莫能明之,凡講心性便“皆入于莊、列、釋、老”,而誤以爲“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他在《復性書》中明確指出孔子之道即是“性命之道”,孔子弟子中,顔淵最接近孔子,其餘升堂者如子路、曾子也程度不同地傳承了性命之道;此外,李翱特別指出孔子—子思—孟子—公孫丑、萬章這一授受序列:“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與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廢缺。”(74)李翱這一道統序列與韓愈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序列相比,共同點是將子思、孟子的思想相銜接,並都認爲孟子傳承孔子之道,但二者的區別也很顯著。韓愈指出,“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認爲孟子超越孔門諸弟子,是孔子之後唯一傳承其道之人;李翱則特別强調子思對傳承孔子之道的重要性,指出孔子之道完整地體現于子思所撰《中庸》一書中,而孟子僅是對子思的承襲。在“道”的內涵上,李翱也不同于韓愈。陳來先生指出李翱以“不動心”爲道統之傳,提出了一個有別于韓愈“博愛之謂仁”的道統說。(75)此誠確論。這個“不動心”就是李翱所一再言之的“動静皆離,寂然不動”的“至誠”之道。概而言之,韓愈的道統涵蓋了治統與學統,代表了“整個儒家文化—社會秩序”(76),其意在于恢復儒家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入世傳統,重新確立其在政治倫理上的統治地位。而李翱的道統則主要偏重于學統,通過發揮《中庸》、《易傳》、《孟子》中的心性論,以構建儒家的心性體系。二者同樣都以孟子爲道統之傳人,但著眼點却不盡相同。宋程朱理學的道統論尤重思孟《中庸》一系的心性傳統,實則更接近于李翱所標榜的傳道系統。
除李翱外,韓門中張籍、皇甫湜等也都普遍繼承了韓愈尊孟之說,但在理論上都少有建樹。
晚唐時有皮日休尊韓,依仿韓愈《原道》等篇而作《原化》諸文。受韓愈尊孟之影響,皮日休認爲《孟子》之文“粲若經傳”,“繼乎六藝,光乎百世”。(77)肯定了《孟子》之文符合經旨,並奏請將《孟子》列入科舉選目。他繼承韓愈之道統說,並在韓愈所言孔孟道統之後又增入荀子、王通以及韓愈。(78)其對韓愈道統體系的改造,得到了宋初古文家的認同,影響深遠。(79)又有唐昭宗末進士沈顔痛心于其時文章浮靡,撰寫《聱書》十卷,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80)不但接受韓愈以孟子爲道統中樞的觀念,而且儼然以道統自任。
五代喪亂,隨著時局之動蕩和社會之衰敗,古文運動也走向衰落。其間亦有個別學者繼承了韓愈的古文觀念,肯定文章之旨應倡明孔孟之道。如後蜀牛希濟感嘆當世之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艷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絶。賴韓吏部獨正之于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建言朝廷“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夑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于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81)又如晚唐孫郃,字希韓,“好荀卿、揚雄、孟氏之書,慕韓愈”。(82)
從唐代中期興起的古文革新運動,其明“道”主張推動了儒學的復興。在古文家的推闡下,孟子的地位逐漸從諸子中凸顯出來。以《孟子》爲直承周孔的佐經之作,實已開《孟子》升經之先聲。韓愈倡言孔孟道統,其道統說以孟子爲道統中樞,大大提升了孟子的學術地位。韓愈的道統說在北宋中前期産生了深遠影響,爲衆多學者廣泛接受。雖然道統序列歷經幾次調整,但最終宋代孟子道統地位的確立離不開韓愈的引領。可以說,韓愈的道統說開啓了唐宋間孟子地位升格的路途。
三、由尊韓而尊孟:北宋中前期古文家對韓愈道統說的發展
宋初文風主要沿襲五代,四六文盛行。柳開、穆修、王禹偁、石介等人不滿于其巧麗卑弱之風,倡爲古文,發揚古道。仁宗嘉祐前後又有歐陽修等人矯“太學體”之流弊,確立了古文簡易暢達之風。唐代古文運動文以明道的主張被北宋中前期古文家所繼承。
較之唐代古文家,北宋中前期柳開、孫復、石介等人的復古傾向、衛道意識更爲强烈,在他們看來,不僅要文、道並重,甚至道的重要性更超過文。在韓愈那裏,尚有承認文章獨立價值的一面(83),而柳開、石介等古文家則大多將文攝于道之下,復興古文的目的即是要復興儒家孔孟之道。正如郭紹虞先生所論,“宋初論文的風氣偏主于道,而論到道又最易有‘統’的觀念”。(84)倡言道統成爲宋代前期古文家的風氣。他們繼承韓愈的道統說並加以推衍,雖道統譜系略有差异,但大致都認可“孔、孟、荀、揚、王、韓”的道統序列,一再闡明要回復孔孟之道。如柳開倡導“文道合一”,又如石介對西昆體大力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排擊佛老,維護儒家的道統,恢復其正統地位。古文革新完全成爲儒道復興的一種手段。他們既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也是北宋儒學革新的先驅者。其中孫復、石介以及胡瑗更被理學家尊爲宋初“三先生”,視爲理學“發源之自”。(85)至嘉祐年間歐陽修主盟文壇後,古文運動則逐漸由道重于文轉向文道並重。因歐陽修對韓愈的大力提倡,又出現了孟韓並提的道統序列。
雖然對于具體如何承繼唐代古文運動,北宋中前期的古文家各有其主張,但他們大都推尊、慕法韓愈,認可韓愈對古文運動及儒學復興的倡導之功,繼承了韓愈提出的孔孟道統說,並加以推闡發揚,同時韓愈也被尊爲儒家道統的繼承者。黄進興先生曾指出:“退之是北宋孟學興復的催化劑。宋初的儒者實透過韓氏著作的導引,以重新認領孟子,且賦予孟子在儒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樞紐地位。正由于此,使得韓愈成爲孟子榮登孔庭的原動力。”(86)北宋中前期的古文家正是由“尊韓”進而“尊孟”,韓愈提出的以孟子爲傳道中樞的孔孟道統說經由他們的推闡和發揮,成爲當時學術界的共識和流行論調,並最終爲官方所認定,也爲後來理學家確立其道統說奠定了基礎。
范仲淹曾謂:“唐貞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已降,寖及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87)柳開,字仲塗,號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他提倡復古,在宋初首先樹立起道統說的旗幟,是北宋古文運動以及儒學復興的先驅。在韓愈道統說的基礎上,柳開宣揚文道合一的道統說,以孟子爲孔子之道的繼承者,所謂“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88)並以道統傳人自居,謂:“自韓愈氏没,無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89)如果說唐代的古文家大多文道並重,那麽發展到柳開這裏,儒道的重要性則完全超過了文學性:“文章爲道之筌也…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90)柳開認爲文章僅僅是道的工具,是否闡發孔、孟、揚、韓之道纔是衡量文章優劣的標準,寫作古文與弘揚古道成爲二而一的事情,提倡古文,其意即在恢復“古道”。柳開一生都以恢復、發揚儒家聖賢之道爲職志。自稱“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91),“惟談孔、孟、荀、揚、王、韓以爲企迹”。(92)柳開的弟子張景對其師的評價即是“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柳開對孟子的推崇主要體現在對孟子衛道之功的肯定:“楊墨交亂,聖人之道復將墜矣…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辟之,聖人之道復存焉。”(93)在《答臧丙第一書》裏柳開構建了由孔子至孟子,再至揚雄、王通、韓愈的道統傳承系列,對此做了詳細描述,同時聲稱自己就是這個道統序列的繼承者。在韓愈那裏,儒家道統至孟子就斷絶無傳,並不及荀子及漢代以下揚雄、王通諸儒,柳開既然尊韓,緣何道統觀不遵韓說而增入荀子、揚雄、王通等人?關于此點,前人已有辨說。因韓愈《讀荀》等文對荀、揚亦不無肯定,且重視揚雄猶在荀子之上,因此將荀、揚列入道統不能說完全違背了韓旨。而在道統序列中列入王通,或爲受皮日休之影響。(94)
柳開對韓愈的態度及其學術志向前後期也有所變化。原名肩愈,後來又改名爲開,字仲塗,其名、字的先後改變即體現了他文道觀的轉變。柳開的改名之由在其《答梁拾遺改名書》中有詳盡解釋:“幼之時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韓之文,故欲肩矣。今長而成,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是以《補亡先生傳》曰:“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志,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將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95)早年他熱心于取法韓文,對韓愈極力推崇,故名肩愈,後來則“所著文章與韓漸异,取六經以爲式”。(96)柳開後來已不滿足于僅是創作古文,而是要補經籍之亡闕,探六經之旨,要“包括揚、孟”,學習王通補續六經,開聖賢之道而達于孔子。其紹繼孔孟道統的志願較之早年更爲明確和强烈,其論調已更接近于後來的理學家。柳開的文道觀對其門生師友也有一定影響。如高弁曾師從種放,學古文于柳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97)
與柳開同時,還有一位隱逸之士種放,亦是北宋古文運動與儒學革新的先驅。據其自撰《退士傳》記述,種放年少時曾學時文,後不滿所學,盡弃時文轉而從事古文創作,“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于道者恣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98)種放推尊孟子,撰有《述孟志》上、下篇,篇首序云:“余讀孟軻書,然後知聖賢之道千古若符契而不違也。蓋孔子之道,非軻則不明;軻之書,非尊孔子之道則不傳。”(99)對孟子倡明孔子之道的肯定,近于韓愈之論,當是受韓愈的影響。他推崇孟子和韓愈,也提出了孔子、孟子、揚雄、王通、韓愈的傳道序列:“後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軻…廣軻之道,則揚雄…嗣雄之旨,則曰王通…如通之學者,則曰韓愈,愈尊夫子道,以爲迨禹弗及…嗚呼,愈死,未有卓然明其學、顯其道者。”(100)其中認爲揚雄發揚孟子之道的提法大概也是受了韓愈的啓發,因爲韓愈曾指出“因雄書而孟氏益尊”。(101)
王禹偁與柳開同時,其古文主張與柳開有較大差异(102),但他也主張文道合一(103),且認同孔、孟、揚、王、韓的道統觀。其《投宋拾遺書》云“書契以來,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又云“孟軻氏没,揚雄氏作…揚雄氏喪,文中子生…文中子滅,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在該文中贊宋白“履孔、孟、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104)又有《送譚堯叟序》,謂譚氏“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105)
真、仁之際,又有孫復、石介諸人也極力主張文道合一和孔孟道統觀。孫復明確指出:“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106)石介稱頌孫復之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107)孫復自稱是“學孔而希孟者”(108),又謂:“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109)在《信道堂記》這篇數百字的短文中,該道統序列就反復出現了六次。仁宗時,孔道輔在家鄉兗州夫子廟構築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祠,孫復在給孔道輔的書信中大力稱揚此事:“自夫子歿,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于夫子者也…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堂像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110)可見孫復也沿襲了韓愈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子”的儒家道統系列,但在孟子之後又增加了荀子、董仲舒(111)、揚雄、王通、韓愈諸人,與柳開近似。景祐年間孔道輔在鄒縣建孟子廟,延請孫復撰寫記文。孫復在文中極力贊揚孟子辟楊墨之功:“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钜。”(112)韓愈曾稱揚孟子的衛道之功“不在禹下”,孫復對韓愈此說表示贊同,認爲在護衛孔子道統的鏈條中,孟子之功當居首位。孫復的道統說在其門生當中亦有影響。如祖無擇在爲李覯文集撰寫的序文中寫道:“孔子没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异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旴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113)其道統序列與孫復相近,惟去韓愈而增一賈誼。
孫復的另一位門生或說是同道——石介對于倡導古文、推闡道統則更是不遺餘力,較之前人有過之而無不極。石介主張,“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爲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114),認爲作文應以傳道爲目的,而不必取其文辭。景德以後,楊億等人開創的西昆體詩文盛行,對古文形成衝擊。石介極力反對西昆體浮靡之文風,以辟佛老、斥時文、崇道復古自任。在其《怪說》上中下三篇中,石介斥時文、佛、老爲三怪,認爲這三者破壞了儒家之道的傳續:“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115)職是之故,對于辟楊墨的孟子和排佛老的韓愈,石介都極尊崇。他極力宣揚孔孟道統說,肯定孟子辟楊墨,有衛道之功。《上趙先生書》中引用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116)的聖賢更迭觀,進一步闡發了孔孟以來遞相授受的道統觀:“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楊子,楊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117)同柳開近似,石介的道統序列也是孔、孟、揚、王、韓。有時亦會列入荀子,如《與君貺學士書》云:“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柳開)而已。”(118)孔子之前,石介還經常往上追溯至傳說中的古聖先王,如伏羲、神農、黄帝等。對此道統觀的宣揚,石介可謂不遺餘力。如歐陽修所論,“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于口”;(119)“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120)在石介文集中這個道統序列屢屢出現,如卷五《怪說》、卷七《尊韓》、卷十二《上張兵部書》、卷十三《上蔡副樞書》《上孔中丞書》《上范思遠書》、卷十五《上孫少傅書》《答歐陽永叔書》《與祖擇之書》等,皆可見類似申述。有時石介的道統名單則在孔子之後只開列孟子和韓愈,如《是非辨》曰:“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121)《尊韓》曰:“孔子後,道屢塞,闢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122)可見石介亦認可韓愈將孟子置于傳道中樞地位的道統觀。但總體上看,石介對揚雄、王通等人亦極推重,孟子只是這幾位“賢人”中的一位,而且其尊韓更過于尊孟。如石介專門撰寫《尊韓》篇,其文云:“孟軻氏、荀况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而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123)將韓愈尊爲孟、荀等五賢人之首。
古文家的崇韓明道之風也影響到釋門學者。據記載,太宗、真宗時期佛門中已有爲文師法韓愈及尊儒的風氣。(124)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智圓,自號中庸子,學問淵博,擅詩文,喜好儒家經典。自稱“好讀周、孔、揚、孟書,往往學古文,以宗其道”(125),“爲文宗孔孟,開談黜莊老”。(126)所謂古文,智圓認爲就是以儒家仁義五常之道爲宗旨撰寫的古文:“夫所謂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也。古道者何?聖師仲尼所行之道也。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經大備。要其所歸,無越仁義五常也,仁義五常謂之古道也…老莊楊墨弃仁義,廢禮樂,非吾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古道也。故爲文入于老莊者謂之雜,宗于周孔者謂之純。馬遷、班固之書,先黄老,後六經,抑忠臣,飾主缺,先儒文之雜也。孟軻、揚雄之書排楊墨,罪霸戰,黜浮僞,尚仁義,先儒文之純也。”(127)智圓不但以孔孟之道爲撰作古文的宗旨,而且他開列的道統譜系也同古文家的名單一致:“仲尼既没,千百年間,能嗣仲尼之道者,惟孟軻、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柳子厚而已。”(128)其道統序列和柳開等人的認識近似,或即受古文家之影響。(129)智圓尊崇孟子,自稱“宗儒述孟軻”。(130)孟子辟楊墨的行爲在韓愈、孫復等儒家學者眼裏不僅是捍衛儒家道統的象徵,更是引領他們自身排佛老的旗幟,而作爲佛門弟子的智圓,竟然也肯定孟子辟异端之功,認可孔孟道統,表面上看似乎匪夷所思,實則反映了宋初儒佛融會互動的狀况以及古文運動宗儒明道觀念的影響之深。
孫復、石介等人反對時文而倡言儒道,但因一味張揚道統,好務高言,在古文實踐中矯枉過正,“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131),形成了所謂險怪奇澀的“太學體”文風。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對“太學體”進行排抑,使文風轉向平易暢達,爲古文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新途。一般認爲,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宋代文風的轉變,歐陽修作用最大。(132)元代脫脫等撰《宋史》即肯定了古文運動成于歐陽修及其門下:“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合之,宋文日趨于古矣。”(133)可見歐陽修在宋代古文運動中實居樞紐地位。自歐陽修始,不但宋代古文之文風爲之一變,道統論和文道關係也漸次發生了轉變。
柳開、孫復、石介等人都繼承了韓愈的道統說,由尊韓而尊孟,並在孟、韓之間添列了荀子、揚雄、王通等大儒。至嘉祐年間歐陽修主盟文壇時,這種尊韓的傾向更是達到了頂點。歐陽修謂其時“學者非韓不學”,“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134),韓愈其文其道得到了極大的推廣。由宋祁和歐陽修撰寫的《新唐書·韓愈傳》給予韓愈極高的評價:“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135)“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36)認爲韓愈衛道之功過于荀子、揚雄,而直承孟子。對于孟子傳道的中樞地位,歐陽修仍然給予肯定:“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137)“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138)而對于揚雄和王通,歐陽修則認爲他們體道不足,只是勉强模仿而爲文:“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139)因此,歐陽修的道統序列是將韓愈置于荀、揚等人之前,直接將孟韓並提。如其慶曆八年《青松贈林子》詩云:“青松生且直,繩墨易爲功…于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140)將韓愈置于揚雄、王通之前,徑稱“孟韓”,且不提王通,正可見其獨特的道統觀念。對歐陽修習作古文有指點作用的尹洙也推崇韓愈爲孟子之後唯一的道統繼承人:“自孟而下千載,能尊孟氏者,唯唐韓文公。”(141)
如前所述,經由柳開、孫復、石介等人的推闡,孔、孟、揚、王、韓的道統序列成爲北宋中前期很多儒家甚至釋門學者的共識,即便是古文觀念與柳開差別較大的王禹偁也認同這一道統觀。儘管柳開、石介等人也大力尊韓,但並未明確提出孟韓並稱的道統體系。而從歐陽修開始,則出現了孟韓並稱的道統說,較之前柳開、石介等人提倡的道統序列有所不同。歐陽修大力提拔、獎掖後進,其門生友人如三蘇、曾鞏、王安石等受其影響,在道統觀念上亦遠祧孔孟,近宗韓愈,大多將孟韓並提,並且將歐陽修上接韓愈,以歐陽修爲道統承繼者,從而形成了孔、孟、韓、歐這一道統序列。
最典型者,如蘇軾在爲歐陽修文集所撰序文中說:“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晋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142)蘇軾不但認可韓愈所提出的孔孟道統,而且直接以韓愈上接孟子,又以歐陽修直承韓愈。
其次又如曾鞏,其《上歐陽學士第一書》云:“仲尼既没,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捨是醨矣!退之既没,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143)贊揚歐陽修之文章“其深純温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蹖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韓退之没,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144)其道統名單雖然從表面上看同柳開、石介等人相似,但實質上更推重孟、韓、歐三人在傳承儒家之道中的重要作用。
相較而言,蘇洵的道統序列則較難理清。(145)如其《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將孟子、韓愈及歐陽修三人之文並提;(146)《上歐陽內翰第二書》則云,“自孔子没,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于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147)又將荀、揚置于序列之中,但其主要的看法仍是孔、孟、韓、歐這一序列。
蘇轍對于孔子以來的文道之傳承,亦有其認識。如《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孔子既没,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仿佛…自漢以來,更魏晋,歷南北,文弊極矣…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閼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復無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148)這段文字主要論列孔子之後儒家載道之文的傳承。蘇轍于孔子之後,儘管開列了一長串的名單,孟子亦位列其中,但其中最推重的當屬所謂“二人”,即韓愈和歐陽修。
王安石早年亦認同孟韓並稱的道統觀,如其慶曆二年(1042)《送孫正之序》云:“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贊揚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能以孟、韓之心爲心”,勉勵其至“孟、韓之道”。(149)又,王安石早年爲文著力于模仿孟子和韓愈,歐陽修曾對王安石模仿孟韓爲文提出建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150)亦可見王氏當時所受“孟韓”道統譜系之影響。“孟、韓、歐三人,正是理學没有取得主流地位之前,宋代一般學者心目中道統之所繫”(151),楊國安先生的這個論斷,大概可以說明歐陽修主盟文壇時學者的一般看法。
四、弃韓而尊孟:北宋中後期孟子道統中樞地位的穩固與强化
韓愈所提出的道統觀得到北宋中前期古文家的大力推闡,孔、孟、揚、王、韓這一道統序列成爲當時思想界普遍認同的觀念。從歐陽修開始,這一道統序列發生微妙的變化,逐漸不同于之前柳開、石介等人的道統說,孟子之後的荀子、揚雄、王通等人被弱化或徑直弃而不論,韓愈的地位更加得以凸顯,超軼荀、揚、王通諸人而直承孟子,孟韓並稱成爲當時較爲普遍的看法。但與此同時,大概從仁宗末年開始,對韓愈儒道理論及其修身實踐等方面的批評開始萌生發展,韓愈的地位由此從鼎盛的輝煌轉向低谷。(152)學者接受了韓愈提出的孔孟相傳的道統,但却拋弃了韓愈以及漢唐之間的其他儒者,最後在理學家手中,道統觀似乎又回歸到韓愈所提出的孟子之後漢唐“不得其傳焉”的狀態。但這種回歸絶非重新回到歷史的起點,其意義在于孟子地位的强化和新的儒學體系的建立。
仁宗慶曆之際,“學統四起”(153),理學思潮初興。在孫復、石介等人倡言“孔、孟、荀、揚、王、韓”道統譜系的同時,對荀子、揚雄、韓愈等人道統地位的質疑聲音也開始出現。最顯著的即爲王開祖,永嘉人,皇祐五年(1053)進士。講學鄉里,學者尊之爲儒志先生。其著作多湮没不傳,有《儒志編》一卷傳世。《儒志編》末章王開祖闡明了其宗孟的道統觀,云:“或曰:荀揚之學何如?曰:奚以問歟!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我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論者以爲王開祖倡言道學,早在二程之先。(154)黜荀子、揚雄,而獨以孟子爲道統之傳,其道統觀可謂導夫先路。
又有賈同,青州臨淄人。石介稱其“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録》數萬言”(155),可見其極尊孟子。他撰寫《責荀》一文,批評荀子的非孟之說,並反對將孟子與荀、揚並列:“今以荀之書比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楊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156)
再如章望之,浦城人。《宋史》本傳稱其“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157)雖然尚没有文獻證明章望之明確排斥荀、揚、韓諸人的道統地位,但通過他對三人心性理論的批駁和對孟子的尊崇,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其大致的道統傾向。
王安石早年受知于歐陽修,也有孟韓並稱的言論,但後來隨著其對文道認識的改變,對韓愈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如他指出:“韓子嘗語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矣。”(158)認爲韓愈只講究文辭技巧,不知作文之目的。他認同孟子所說的“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雖然所說的是君子的道德修養,但“亦可托以爲作文之本意”。(159)又有評論韓愈的詩句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160)明確批評韓愈不識“道真”,于弘揚儒道徒勞無功。嘉祐元年歐陽修有《贈王介甫》詩,曰“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161),以李白和韓愈的文學成就勉勵王安石,但王安石並不以爲然,答詩曰:“欲傳道義心猶在,强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162)王安石的夙願是要傳續儒家道統,直承孟子,“傳道義”而非“學文章”,而韓愈在安石心目中只是一個文學家,故他並不以韓愈爲期。在另外一首《秋懷》詩中,王安石亦表達了同樣的情懷:“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有來還不拒。”(163)可見此時的王安石眼中,韓愈只是一介文人,不足取法,故而將韓愈剔除出儒家道統序列,而要直接上承孟子。對于孟子,王安石一直是推崇備至。孟子在北宋地位的提升,王安石功不可没。在此限于篇幅,暫不展開論述。之前柳開、石介、歐陽修等先賢將孟、韓並尊,孟子僅位列“賢人”,王安石則尊孟子爲“聖人”,並特別說明聖人與賢人之別。(164)對于荀子,王安石也認爲其學不能與孟子相配,“後世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165)余英時先生指出,越過韓愈,直承孟子,在這一點上,王安石實開理學家風氣之先。(166)此論誠然。
王安石的莫逆之交王令亦尊崇孟子。王令一方面肯定韓愈對孟子地位的倡導之功(167),另一方面又指摘韓愈的理論與踐行都與孟子相差甚遠。其《說孟子序》云:“至于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而愈之與孟子异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168)認爲韓愈在性命之學以及出處之道上與孟子差距甚遠。對荀子、王通、韓愈均提出批評,只肯定了揚雄。
儘管蘇門以詩文著稱,但對于性命之學亦有其獨得之見,形成了以“蜀學”著稱的學術派別。秦觀評價蘇軾的學術成就時稱:“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169)可見蘇軾及其門人皆自認爲在性理之學上造詣最高,而文章乃是其“至粗者”。因此儘管蘇門認可孟、韓、歐的傳授序列,肯定韓愈在文學上的成就,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韓愈之道的批評。這一認識也說明了文道二分的現實。(170)蘇軾雖然認可韓愈在道統中的地位,但對于韓愈的儒學理論仍表示出不滿,批評“韓愈之于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171)他對韓愈的性三品說亦有詳細的批駁。(172)蘇轍也批評韓愈不知“形而上”之道:“愈之學,朝夕從事于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道哉?”(173)對于荀子,蘇軾亦嚴厲批評其性惡論,認爲李斯之禍實荀子“高談异論有以激之”。(174)對于揚雄,則譏諷其“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175)儘管蘇軾並不認同孟子的性善論,認爲其說引起了荀子、揚雄等人性論的紛争(176),但對孟子仍大體持肯定態度,稱贊“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177)另,蘇軾撰有《論語說》,其中“與孟子辯者八”。之所以與孟子辯論,其目的是“以孟子爲近于孔子也”,“故必與孟子辯,辯而勝,則達于孔子矣”。(178)蘇軾認爲孔孟相近,故而與孟子辯論,以求上達于孔子。可見蘇軾雖然表面上批駁了孟子的一些說法,但總體而言還是肯定孟子的。比較而言,蘇轍較其兄對孟子更爲推尊。他嘗自附于孟子,明確指明“其學出于孟子”。(179)蘇轍認可孔孟相傳的道統觀,主張以孟子爲準的而觀道:“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180)可見蘇軾、蘇轍兄弟都認同孔孟之道,皆主張由孟子上達于孔子,同時也對韓愈等漢唐儒者的儒道理論表露出不滿的傾向,
再如“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詩文兼長,在蘇門中文學成就頗高,但其爲學又極重儒道。他一方面認可韓愈“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其說”(181),另一方面又指摘“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並對韓愈的道論提出質疑:“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捨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异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182)張耒認同的是《中庸》的性道之說,對韓愈以仁義爲“道”的內容不以爲然,甚至譏諷其不知“道”爲何物。
王門和蘇門學人對于“道”的認識已不同于以往的古文家。他們批評韓愈不明“道”之真諦,要越過韓愈直承孟子,這一傾向在張載、二程等理學家那裏被進一步加以深化。張載認爲揚雄、王通皆不見道,韓愈“只尚閑言語”。(183)又曰:“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184)張載指出“道”是所謂“天理”,依靠“心傳”,而孔孟之後,荀子、揚雄皆不能得聖人之傳,道因此而斷絶。程頤早年的道統觀念尚受古文家的影響,如皇祐二年(1050)程頤在《上仁宗皇帝書》中還自稱所學之道爲孟子、董仲舒、王通三子之道。但他後來對于孟子以下的漢唐諸儒則持明確的否定態度。如對于荀子、揚雄,程頤不認同韓愈“大醇而小疵”的評價,認爲二子是“大駁”。(185)“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186)對于王通,則譏諷其“聚道”之說(187),指責其所作《續經》“甚謬”。(188)程頤贊同韓愈對孟子“醇乎醇”的評價(189),亦認可韓愈提出的儒家道統在孟子之後失傳的說法:“‘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190)對于韓愈本人,則批評其作文害道,由學文至修德是“倒學”:“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191)認爲其道粗淺:“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192)因此程頤在爲其兄程顥撰寫的《明道先生墓表》中稱“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193),直接以程顥上承孟子,排除了荀、揚,也排除了韓愈在道統中的地位,漢唐諸儒悉被拋弃。二程以直承孔孟道統而自命,“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194),這應當都是夫子自道。程頤肯定孟子的道統地位,主要是著眼于孟子能明“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195)因此程子的道統譜系是以天道性命之學的傳承爲核心,他接受了韓愈“軻之死不得其傳”的道統說,在孟子之前又增入了曾子和子思,“孔子没,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196)這個道統名單表面上同于韓愈在《送王秀才書》中所說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這一傳授序列,但內涵上則更接近于李翱基于思孟心性傳授世系所提出的道統說。程頤認爲子思所作的《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197),其道統論更著意表章思孟一系的心性傳統。范祖禹評價程顥的學術宗旨時說:“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198)獨獨標舉“《中庸》之學”,恰好可以證明這一點。另外,在二程的道統譜系中,孟子之後一千多年没有人接續,不像石介等人的道統譜系中因包括韓愈等漢唐儒者而“代有傳人”,更爲連貫,因而二程强調“心傳”的道統授受方式,爲其“超越漢唐,直承孔孟提供了理論依據”。(199)程頤提出的這一道統譜系隨著理學的發展,尤其是經由朱熹的表章,被此後的理學家所廣泛接受。上接孟子,克紹道統成爲理學各學術宗派的一致追求。朱熹還明確指出《大學》爲曾子所作,這樣孔、曾、思、孟的道統譜系與理學家表章的“四書”體系——《學》、《庸》、《論》、《孟》相對應,二者互爲依托,而孟子傳道中樞的重要地位更加彰顯。孔孟並稱、孔孟之道成爲習說,孟子的地位大大提升,不再混同于荀子以及揚雄、韓愈等漢唐儒者。
爲什麽北宋中後期會出現弃韓尊孟的道統論思潮?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歐陽修之後古文運動文道理念的改變以及由此引發的道統和文統之分裂。對于文道關係的認識,歐陽修與柳開、石介等人的觀點不同。在柳、石等人眼中,道遠重于文,文只是表現道的工具,而歐陽修則是文道並重。如歐陽修曾云:“君子之于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200)可見歐陽修認爲文章須是道的體現,周公、孔、孟之道是爲學的目的,也是爲文的基礎。但歐陽修也同樣肯定辭章文采的重要性,“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後世”。(201)因此歐陽修並不如石介諸人反對楊、劉時文,反而認爲“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202)歐陽修本人對文辭的重視,其影響所及就是使得此後的古文運動文漸重于道,到三蘇諸人手上,則是“爲文而文”,又雜以莊、釋之道,于是儒道“僅成門面裝點而已”。(203)如上文所引蘇洵的《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韓愈、歐陽修的評論主要著眼于文風。他自述其年少時的學文經歷,“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204),只論文而不言道,關注點集中在文辭方面,“只是學其文而不是學其道”。(205)又有《上田樞密書》曰“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206),將孟韓並舉,但僅論其文風。故而蘇洵等人的統緒說與其說是道統,不如稱之爲文統。這與柳開、石介等人以道爲本位的道統觀相去甚遠。黄啓方先生曾指出,“宋代古文之發展,似可視爲二支,其一由柳開而石介,重在道,爲道學之古文論者…其二即王禹偁而歐陽修而蘇軾,蓋文人之古文論者”。(207)柳開、石介等人代表了北宋古文運動中道重于文的一派,而王禹偁、歐陽修、蘇軾等人則被視爲是文道並重或者重文的一派。歐陽修及之前的古文家所云之“統”是道統涵蓋文統;歐陽修之後,則所指僅限于文統。古文運動由是不再負載振興儒道的功能,傳道的意味進一步淡化。道統與文統逐漸分離,道與文裂爲二途。理學之先驅周敦頤曾提出“文所以載道”的觀點(208),從表面上看近于古文家所說的文以明道的主張,但實際上周敦頤僅將文視作載道的形式之一,他反對以崇尚文辭爲能事。“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209)他指出,道的實現從根本上說端賴于修身踐履,而非文辭。這實際已開文道二分之先河。發展至張載、二程,則甚至有“作文害道”之說,將爲文等同于玩物喪志。(210)程頤謂:“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于訓詁,三惑于异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歸于道矣。”(211)將文章等同于异端,不但歧文與道爲二,且認爲學文妨礙了學道。南宋學者對北宋中後期出現的文道二分的狀况已有所見。如吳子良指出:“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212)吳汝一又提出“周程、歐蘇之裂”的說法(213),所概括的皆是此種歷史境况。這種情勢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宗經重道的儒家學者對原有的古文諸家所倡導的道統說及文道關係提出質疑,最終將古文家所倡導的道統序列中孟子之後的漢唐諸儒一概剔除,而自居道統,直承孟子而上接孔子。因此可以說,北宋前期的道統說主要是沿襲韓愈的道統說,由尊韓而尊孟,後期則是弃韓而尊孟,直承孟子而自續道統。
再者,弃韓而尊孟這一道統論傾向的形成也受到了熙寧年間科舉制變革的影響。熙寧初年王安石主持變法,科舉考試廢除唐代以來的詩賦試,而改爲以經義取士。從當時的文獻記載可以發現,這一制度變革對士風的影響之一便是士人以講經論道爲高,鄙薄辭章及文士,形成了“文與經家分黨”的局面,由是也引發了批評韓愈不知“道”的言論。呂南公《灌園集》卷一《與汪秘校論文書》云:“今之學士,抑又鼓倡争言韓柳未及知道,不足以與明,不如康成、王肅諸人稍近議論…當今文與經家分黨之際,未知秘校所取何等之文耳?”南宋汪藻也指出:“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214)而熙寧變法將《孟子》列入科舉考試科目,與《論語》並列爲“兼經”,這一舉措無疑也促進了士人對《孟子》的研習,並强化了孔孟道統說的確立。
弃韓而尊孟的又一原因是,對道統之“道”的內涵,仁宗、神宗之際的學者與之前的古文家有著不同的理解。宋代前期的柳開、石介諸人,他們所說的道統主要立足于仁義、王政之道,不離治道、政教之準的,在這一點上與韓愈以仁義爲道之內涵正相近。如穆修嘗謂:“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215)直接指明仁義即謂之“道”,認同韓愈對“道”之內涵的闡釋。石介論道也主要根于仁政治道,如他推崇柳開爲當世道統的承繼者,稱贊其“著書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216)歐陽修更是提出“性非學者所急”的論斷,他認爲“道”必切于政教人事。(217)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論,宋初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其“注意力還没有貫注在‘道德性命’之類的‘內聖’問題上面”。(218)而後起的王安石等“新學”派以及張載、二程等理學家不滿于漢唐儒學體系的粗疏,受佛教心性論的刺激和影響,更關注儒家內聖心性體系的建立和形上學基礎的建構,故而以道德性命之學爲立足點而確立道統。他們對古文家所闡發的道統內涵提出質疑,進而也對古文家所增續的孟子以下的道統譜系中的人選加以否定,認爲荀、揚、王、韓諸人皆不明儒道。韓愈儘管有其理論建樹,但在他們看來則是粗疏不周,甚至並未觸及“道”之本質。尤其是對于荀子、揚雄以及韓愈的人性論,學者批駁甚多。蘇軾、蘇轍等蘇門學者儘管肯定韓愈的古文成就,但對韓愈之道也有所質疑。對荀子及漢唐儒者否定的結果,就是孟子地位的凸顯及“孔孟之道”的確立。
唐宋之際的古文運動與儒家的復古思潮緊密結合,對儒家道統說或文統說的申說,貫穿了唐宋古文運動的始終。自中唐以來,孟子之後文道不彰和對孟子之文的推崇成爲古文家的共識,《孟子》被視爲佐經之作,其人其書的重要性愈加凸顯。韓愈首倡道統說,孟子被視爲孔子之後儒道的唯一嫡傳,居于道統中樞的重要地位。這一道統說極大地提升了孟子在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李翱繼承了韓愈尊孟的思想,又將子思、孟子的思想相銜接,以《中庸》的心性傳統爲核心,提出來一個有別于韓愈的傳道系統。韓、李的道統說對北宋中前期學者有深遠影響,尤其是韓愈的道統說,開啓了孟子地位升格的路途,爲宋代孟子道統地位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
韓愈的道統說在北宋經歷了數次的變革和改造,雖有李覯、司馬光等人的“非孟”之聲,但總的來看,孔孟道統已成爲當時思想界普遍認同的觀念,孟子道統中樞的地位亦越來越凸顯。北宋中前期的古文家大多尊韓,經由尊韓而尊孟。他們倡言韓愈的道統說,並在其基礎上形成“孔、孟、荀、揚、王、韓”的道統序列。在這個道統序列中孟子與荀、揚等諸子並列,其地位並不是那麽突出,有時甚至不及韓愈更受推崇。但孟子辟楊墨的衛道之功得到了古文家的一致肯定,孔孟道統說經古文家反復推揚,幾乎成爲當時學術界和朝野的共識。這啓迪了之後理學家新道統觀的確立。嘉祐年間歐陽修主盟文壇後,又提出“孟韓”並稱的道統觀,孟子和韓愈的地位更加凸顯。但嘉祐以後古文運動漸朝著重文的傾向發展,“道”的因素逐漸减弱,最終文、道二分。後起的王安石“新學”以及張載、二程等理學家不滿于古文家所建立的道統譜系及對“道”之內涵的定義,他們以道德性命之學爲立足點而重新確立道統,越過韓愈,直承孟子。孟子之後的韓愈等漢唐諸儒皆因駁雜不純而被剔除出道統序列,孟子在道統中的關鍵地位得到進一步的突出和强化。
然而終北宋之世,程頤提出的孔、曾、思、孟的新的道統譜系一直未得到官方認可。元豐七年,朝廷下詔以孟子配食孔子,同時荀子、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並封伯爵。(219)孔廟從祀的這一舉措是道統說制度化的體現,說明官方認可的仍是北宋中前期古文家所倡導的“孔孟荀 揚韓”的道統譜系。(220)不過配享孔子的孟子,其地位顯然高過從祀的荀、揚、韓諸人。北宋紹聖間進士、永嘉學者劉安上嘗謂:“韓愈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今七篇具存,學者服膺而讀之…學者同是堯舜,同尊孔孟,雖五尺之童知之也。”(221)可見孔孟並稱、同尊孔孟在北宋末年已是婦孺皆知,孟子傳道地位的特殊性在此時已然是毫無疑問了。南宋中期以後,由于朱熹的倡導,伊洛之學始占據儒學的主流地位,理學家的道統觀方因理學之發展而擴大其影響。但無論所提具體道統譜系爲何,對于孟子是道統中樞的關鍵地位一般都不再有异議。
注释:
①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44。
②據羅聯添先生研究,“古文運動”這一名稱的最早使用見于1928年出版的胡適《白話文學史》,後來被各種文學史著作援用而慢慢固定下來。“古文運動”是近代人受時風潮流的影響而産生的一個名詞。見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唐代文學論集》(上),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頁16。日本學者東英壽援引羅說,對“古文運動”這一名稱提出質疑,認爲所謂“運動”是由團體計劃並從事的各種活動,而在唐宋時期是不存在這種運動的。他不主張盲目搬用“古文運動”一詞來考察文學史,而是用“古文復興”一詞替代之。見東英壽:《歐陽修的科舉改革與古文復興》,《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0~111。東英壽說有其客觀合理性,但鑒于學界對于“古文運動”的使用已相當普遍,本文姑且仍使用這一名稱。又,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9年,頁212~215)對“古文運動”之名有所辯護,可以參看。
③[美]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7。
④《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頁29~30。
⑤錢穆先生指出:“韓愈之‘古文運動’,其實乃是將儒學與散體文學之合一化…若明白闡述,即是把文學與儒學挽歸一途。”見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70~71。陳弱水先生認爲:“就思想史而言,古文運動是中唐儒家復興的中堅力量,對于中古思想局面的結束、宋學的形成,起了開端的推動作用。”見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頁212。
⑥《全唐文》卷五一八《補闕李君前集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261。
⑦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頁3946。
⑧阮元:《揅經室二集》卷二《揚州隋文選樓記》,《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388~389。
⑨李華:《楊騎曹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頁3198。
⑩同上,頁3198。
(11)李華:《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頁3196。
(12)《全唐文》卷三一六《著作郎廳壁記》,頁3204。
(13)蕭穎士:《贈韋司業書》,《全唐文》卷三二三,頁3277。
(14)《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15)《全唐文》卷三一七《質文論》。
(16)《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17)獨孤及在爲李華文集所作序中評論其在天寶文壇中的作用時說:“于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荂》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頁3946。)
(18)《全唐文》卷五二七《答楊中丞論文書》,頁5359。
(19)同上,卷五二七《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頁5359。
(20)同上,卷五二七《與徐給事論文書》,頁5356~5357。
(21)同上,卷五二七《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頁5354。
(22)同上,卷五二七《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頁5358。
(23)一般文學史都將柳冕視爲古文運動的健將,而陳弱水則認爲,“無論就社會角色或發言立場來說,他(柳冕)恐怕都不能算是文人”,不能計入古文家之列。參見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頁223。
(24)韋政通認爲柳冕提出堯、舜、周、孔爲文學的正統,已暗示了以道統爲主的文學觀。韓愈的道統論極可能有來自這方面的影響。參見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657。當然,柳冕的文道觀猶將孟子與游、夏、荀子及漢代賈、董並提,這與韓愈獨獨推尊孟子,孟子之後道統斷絶,荀子、漢儒皆不與焉的道統觀顯然是有差別的。有學者認爲這反映了古文運動先驅者和韓、柳諸人對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前者重禮而後者重仁。參見唐曉敏:《中唐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9~56。
(25)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引,《全唐文》卷五一八,頁5261。
(26)《全唐文》卷四八九《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頁4997~4998。
(27)同上,卷五三八,頁5461。
(28)《柳宗元集》卷三四《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80。
(29)《全唐詩》卷三三六《赴江陵途中寄贈王十二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3768。
(30)《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王秀才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61。
(31)《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頁18。
(32)清代學者錢大昕考證曰:“道統二字,始見于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于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十駕齋養新録》卷十八“道統”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86。)高明士先生則指出,在李元綱之前,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紹興六年(1136)條已使用“道統”一語。參見高明士:《隋唐廟學制度的成立與道統的關係》,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頁361。
(33)陳寅恪《論韓愈》云:“退之自述其道統傳授淵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啓發,亦從新禪宗所自稱者摹襲得來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86。)唐長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指出,“唐代中葉禪宗業已盛行,所謂六祖傳授衣鉢已是人所周知,韓愈生當其時,熟聞其學,受此啓發而創立聖聖相傳的儒家傳統,無待詳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67)。
(34)參見郭畑:《試論唐代孔廟祭祀系統對韓愈道統思想的影響》,《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5)《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頁13。
(36)張岱年先生指出:“‘仁’是孔子所宣揚的最高道德原則,而孟子道德學說的核心是‘仁義’。”見其《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61。又據楊澤波先生統計,《孟子》中“義”字凡108見,而“仁義”這個複合詞出現特別多,有27次。見楊澤波:《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26~229。
(37)《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頁18。
(38)陳來:《宋明理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22。
(39)錢穆:《周程朱子學脉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頁199。
(40)黄俊杰先生認爲從韓愈開始,儒者所關心的大問題開始從政治轉變爲道德,亦即從“位”轉向“德”。見其《內聖與外王——儒家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劉岱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天道與人道》,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頁270。筆者以爲,雖然從韓愈開始,儒者已開始著手關注道德問題,此後“德”“位”之關係逐漸發生轉變,但僅就韓愈而言,其所關心的重心仍然歸于政治而非道德。至少,“德”的地位還未超于“位”之上。
(41)《孟子·告子下》,《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大字本。
(42)《孟子·離婁上》。
(43)《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頁23。
(44)《孟子·滕文公上》:“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離婁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45)《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頁124。又,“顔子之過此類也”,“類”,《韓昌黎文集校注》誤作“顔”,今據《四部叢刊》影元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改。
(46)參見拙著:《漢唐孟子學述論》,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頁278~280。
(47)《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性》,頁21。
(48)同上,頁20。
(49)同上,頁22。
(50)關于《大學》之來源問題,馮友蘭先生認爲《大學》所說大學之道,當用荀子觀點解釋之。參見馮友蘭:《〈大學〉爲荀學說》,《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80—186。而徐復觀先生則認爲《大學》就其主要內容而論,受孟子思想系統之影響遠過于荀子。《大學》以正心、誠意爲修身之要,是順著孔子“修己以敬”及孟子的“存心養性”發展下來的。雖然修身爲儒家之通義,但荀子以“由禮”、“得師”、“一好”爲修身之要,而未嘗徑以正心誠意爲修身之要。《大學》乃屬于孟子以心爲主宰的系統,而非屬于荀子以法數爲主的系統。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頁240—246。馮、徐皆以爲《大學》晚出。20世紀90年代郭店楚簡的出土使學者對《禮記》諸篇的年代有了新認識,現一般認爲《大學》、《中庸》皆是早于孟荀的戰國文獻。但徐氏所云《大學》思想性格屬于孟學系統,則是大體不誤的。學者認爲,“《大學》的思想雖具有二元的傾向,對以後孟子、荀子均有所影響,但就其思想的主要性格而言,似與思孟一派關係更近,將其看作思孟學派的一個環節可能更爲合適”(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637)。
(51)《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王秀才序》,頁261~262。
(52)同上,卷一《讀荀》,頁36。
(53)同上,卷三《與孟尚書書》,頁214。
(54)同上,卷二《争臣論》,頁112~113。
(55)同上,卷二《重答張籍書》,頁136。
(56)同上,卷三《答李翊書》,頁171。
(57)同上,卷三《答陳生書》,頁176。
(58)同上,卷二《上李尚書書》,頁141。
(59)同上,卷二《上兵部李侍郎書》,頁143。
(60)同上,卷三《上宰相書》,頁155。
(61)參見《漢唐孟子學述論》第四章第三節,頁283~286。
(62)《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劉正夫書》,頁207。
(63)同上,卷四《送孟東野序》,頁233~235。
(64)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19。
(65)《全唐文》卷六三五《答皇甫湜書》,頁6410。
(66)同上,卷六三五《答朱載言書》,頁6412。
(67)同上,卷六三六《寄從弟正辭書》,頁6422。
(68)同上,卷六三五《答朱載言書》,頁6412。
(69)同上,卷六三六《寄從弟正辭書》,頁6422。
(70)同上,卷六三七《雜說》上,頁6427~6428。
(71)同上,卷六三四《再請停率修寺觀錢狀》,頁6405。
(72)同上,卷六三五《與陸傪書》,頁6415。
(73)同上,卷六四〇《祭吏部韓侍郎文》,頁6466。
(74)《全唐文》卷六三七《復性書上》,頁6434。
(75)陳來:《宋明理學》,頁30~31。
(76)同上,頁22。
(77)《皮子文藪》卷九《請孟子爲學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89。
(78)同上,卷九《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頁88。
(79)參見後文北宋古文家道統說的論述。關于對皮日休道統說的分析,可參看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2~23。
(80)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937。
(81)《全唐文》卷八四五《文章論》,頁8877~8878。
(82)《郡齋讀書志校證》,頁933。
(83)參見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頁282。
(84)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282。
(85)《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黄百家案引黄震語,沈善洪主編:《黄宗羲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08。
(86)黄進興:《聖賢與聖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4。
(87)《范文正公集》卷六《尹師魯河南集序》,《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刊本。
(88)《河東集》卷一《應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9)同上,卷六《答臧丙第一書》。
(90)同上,卷五《上王學士第三書》。
(91)《河東集》卷六《上符興州書》。
(92)同上,卷二《東郊野夫傳》。
(93)同上,卷六《答臧丙第一書》。
(94)參見何寄澎:《北宋古文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83~84。
(95)《河東集》卷五。
(96)同上,卷二《東郊野夫傳》。
(97)《宋史》卷二六九《高弁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250。
(98)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文》卷二○六,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第5册,頁564。
(99)同上,卷二○六,第5册,頁559。
(100)同上,卷二〇六《辯學》,第5册,頁562~563。
(101)《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讀荀》,頁36。
(102)參見馮志弘:《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4~95。
(103)《小畜集》卷十八《答張扶書》云:“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四部叢刊》影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配吕無黨鈔本。)
(104)見《宋文選》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5)《小畜集》卷十九。
(106)《孫明復小集·答張洞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7)《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九《泰山書院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24。
(108)《孫明復小集·兗州鄒縣建孟廟記》。
(109)《孫明復小集·信道堂記》。
(110)《孫明復小集·上孔給事書》。
(111)據《孫明復小集·董仲舒論》,孫復的道統觀尤爲推重董仲舒,這是其道統觀特殊之處。
(112)《孫明復小集·兗州鄒縣建孟廟記》。
(113)《直講李先生文集序》,《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
(115)《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二十《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頁241。
(115)同上,卷五《怪說下》,頁63。
(116)《孟子·公孫丑下》。
(117)《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二《上趙先生書》,頁138。
(118)同上,卷十五,頁180。
(119)《居士集》卷三四《徂徠石先生墓志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97。
(120)同上,卷三《讀徂徠集》,《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69。
(121)《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六,頁69。
(122)同上,卷七,頁79。
(123)同上,卷七《尊韓》,頁79。
(124)智圓:《師韓議》,《全宋文》卷三一二,第8册,頁255。
(125)智圓:《閑居編自序》,《全宋文》卷三〇八,第8册,頁188。
(126)智圓:《暮秋書齋述懷寄守能師》,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卷一四〇,第3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505。
(127)智圓:《送庶幾序》,《全宋文》卷三〇八,第8册,頁184~185。
(128)智圓:《叙傳神》,《全宋文》卷三一二,第8册,頁253。《對友人問》所言道統序列與此相近,見《全宋文》卷三一一,第8册,頁231~232。
(129)余英時先生認爲,智圓與柳開“南北懸隔”,“是否曾直接受到柳開的影響,今不可知”。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上),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84。此說不確。智圓文中確曾提及柳開,如其《廣皮日休法言後序》云:“近世柳仲塗復申明《美新》之理,詞亦不出于文過矣”(《全宋文》卷三一〇,第8册,頁223),可見智圓應讀過柳文。
(130)智圓:《潜夫咏》,《全宋詩》卷一四〇,第3册,頁1558。
(131)《蘇軾文集》卷四九《謝歐陽內翰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423。
(132)參見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86~387。
(133)《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一》,頁12997。
(134)《居士外集》卷二三《記舊本韓文後》,《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927、1928。
(135)《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265。
(136)同上,頁5269。
(137)《居士集外集》卷十六《與張秀才第二書》,《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760。
(138)《居士集》卷五十《祭丁學士文》,《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248~1249。
(139)同上,卷四七《答吳充秀才書》,《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177。
(140)同上,卷四,《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15。
(141)《河南先生文集》卷五《送李侍禁序》,《四部叢刊》影印春岑閣舊鈔本。
(142)《蘇軾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頁316。
(143)《曾鞏集》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31。
(144)同上,卷十五,頁232。
(145)對于蘇洵文統觀之分析,可參看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頁90~92。
(146)《嘉祐集箋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28~329。
(147)同上,卷十二,頁334。
(148)《欒城後集》卷二三,《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36。
(149)《王文公文集》卷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433~434。
(150)《曾鞏集》卷十六《與王介甫第一書》,頁255。
(151)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頁285。
(152)參見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第一章第四節“儒學分進時期對韓愈學術的評價”,頁38~45。
(153)《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黄宗羲全集》第3册,頁316。
(154)參見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57。
(155)《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九《賢李》,頁97。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録》卷一云其“以著書扶道爲己任,著《山東野録》七篇,頗類《孟子》”(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同樣記載又見宋江少虞《宋事實類苑》卷十六“忠言讜論”,日本元和七年活字印本。
(156)《宋文鑒》卷一二五《責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750。
(157)《宋史》卷四四三《文苑傳五》,頁13098。
(158)《王文公文集》卷三《上人書》,頁45。據王水照先生考證,此書簡當作于慶曆六年。見《王安石的散文理論與寫作實踐》,《王水照自選集》,頁514。
(159)《王文公文集》卷三《上人書》,頁45。
(160)同上,卷七三《韓子》,頁776。
(161)《居士集》外集卷七,《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475。
(162)《奉酬永叔見贈》,《全宋詩》卷五七七,第10册,頁6643。
(163)《王文公文集》卷五一,頁574。
(164)同上,卷七《答龔深父書》,頁86。
(165)同上,卷二六《周公》,頁303。
(166)《朱熹的歷史世界》(上),頁40。
(167)王令《讀孟子》曰:漢代賈誼、劉向輩“于孟氏之學,不切切深造,則漢儒之學可語哉?自唐韓愈前倡之後,天下日知所向,至今則孔、孟之學盈門矣”。見《王令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45。
(168)《王令集》卷十四,頁266。
(169)《淮海集箋注》卷三十《答傅彬老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981。
(170)劉真倫:《從明道到載道——論唐宋文道關係理論的變遷》指出:“對韓‘文’的高度評價和對韓‘道’的輕視,正是以‘道術分裂’爲基礎。蘇門人士對韓愈文道兩端截然不同的評價,透露出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真實的文道觀:文道之間並没有實質性的聯繫,道術的不足,不影響文章的超卓。”《文學遺産》2005年第5期,頁67。
(171)《蘇軾文集》卷四《韓愈論》,頁114。
(172)參見《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頁110~111。
(173)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末注引,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4)《蘇軾文集》卷四《荀卿論》,頁101。
(175)同上,卷四九《與謝民師推官書》,頁1418。
(176)同上,卷三《子思論》,頁94~95。
(177)同上,卷三《孟子論》,頁97。
(178)余允文:《尊孟續辨》卷下引,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9)《欒城集》卷二二《上兩制諸公書》,《蘇轍集》,頁389。
(180)同上,卷二二《上兩制諸公書》,《蘇轍集》,頁388。
(181)《張耒集》卷五六《上曾子固龍圖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845。
(182)同上,卷四一《韓愈論》,頁677~678。
(183)《經學理窟·自道》,《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291。
(184)《經學理窟·義理》,《張載集》,頁273。
(185)《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31。
(186)同上,卷十九,《二程集》,頁262。
(187)同上,卷十七,《二程集》,頁179。
(188)同上,卷十九,《二程集》,頁262。
(189)同上,卷十九,《二程集》,頁262。
(190)同上,卷十八,《二程集》,頁232。
(191)同上,卷十八,《二程集》,頁232。
(192)同上,卷六,《二程集》,頁88。
(193)《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頁640。
(194)同上,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狀》,《二程集》,頁638。
(195)同上,卷十八,《二程集》,頁204。
(196)《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五,《二程集》,頁327。
(197)《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二程集》,頁411。
(198)《門人朋友叙述並序》,《河南程氏遺書·附録》,《二程集》,頁334。
(199)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頁269、336。
(200)《居士集外集》卷十六《與張秀才第二書》,《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759。
(201)同上,卷十七《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777。
(202)同上,卷二三《論尹師魯墓志》,《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917。
(203)參見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頁170~171。
(204)《嘉祐集箋注》卷十二《上歐陽內翰第一書》,頁329。
(205)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302。
(206)《嘉祐集箋注》卷十一《上田樞密書》,頁319。
(207)黄啓方:《王禹偁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頁65。
(208)《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通書·文辭第二十八》,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頁66。
(209)同上,卷四《通書·陋第三十四》,頁69。
(210)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頁239。
(211)同上,卷十八,《二程集》,頁187。
(212)《筼窗集續集序》,《筼窗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3)見劉塤:《隱居通議》卷二“合周程歐蘇之裂”條,《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7。朱剛認爲,此處所謂“裂”只能指道學與古文之“裂”。見朱剛:《從“周程、歐蘇之裂”說起》,《思想史研究》第四輯《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01。
(214)汪藻:《浮溪集》卷十七《鮑吏部集序》,《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本。
(215)《河南穆公集》卷二《答喬適書》,《四部叢刊》影印述古堂影宋抄本。
(216)《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八《送劉先之序》,頁217。但蔡方鹿先生指出,石介所謂道已表現出向本體範疇過渡的趨勢。見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頁276。
(217)《居士集》卷四七《答李詡第二書》,《歐陽修詩文集校箋》,頁1169。
(218)《朱熹的歷史世界》(上),頁39。
(219)《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五,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8291。
(220)南宋中期仍有學者認同此道統觀。如南宋孝宗、寧宗時人王稱在《東都事略》卷七二《歐陽修傳》末論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嘗輕以畀人。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得其正傳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没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揚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修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秘而息邪說,立化本而振儒風,邃然以所學入,發爲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于物者,蓋天之所畀也。”(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稱的這一道統論與北宋中前期古文家之論極其相似,這足以說明古文家們鼓吹的道統觀影響之深遠。
(221)劉安上:《給事集》卷四《策問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