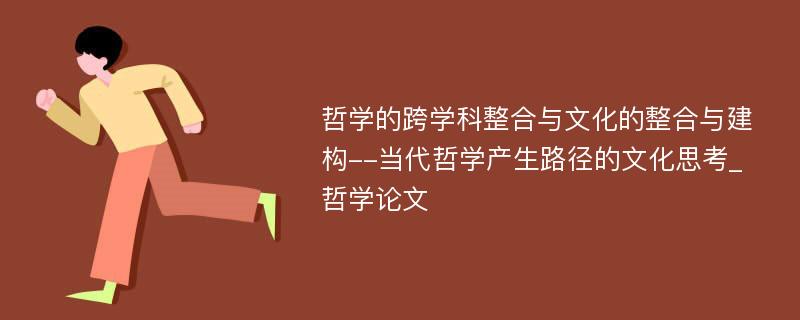
哲学的科际整合与文化的合和建构——当代哲学出场路径问题的文化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路径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078—06
学界关于当代哲学分化与整合之动势问题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深入了,且大致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主张:其一,有人认为,当代哲学通过科际合作与界外阅读对生活和文化所实现的多边切入,正在全面铺开。这虽然使之作为形上之思的旧日风光和智思之流的崇高形象大打折扣,然而它在现代人文精神和日常生活中却早已深入人心,使现代文化的一切形态都别无选择地处在哲学之光的照耀之下,哲学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内在构成要素,不仅在经验事实上而且在心智生活中都极大改变了现代世界。可见,当代哲学对生活、文化、科学的发散性影响,不仅照亮了自己前进的航标,开辟了许多自我生成之域,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外联手与并驾齐驱提供了公共的逻辑之桥,而且还张扬出了一种指向未来、多元融通的实践性姿态,使哲学在大文化语境下赢得了全面性的胜利。其二,有人主张,哲学若通过非哲学化而回归现实生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它的“纯思”取向,也有利于防止它通往神秘主义的危险境地,但如果把它的研究旨趣滞留于生活的直接性事实里,对之进行所谓精妙绝伦的体认和情真意切的回味,它极有可能只附着于生活的表层,从而从思想论坛中渐渐淡出,丧失自性,魂不附体。因而,在大文化语境中所广泛展开的科际合作,决不能精神失控和意义放任,而必须对它的文化边界和理性领地进行必要的限定,否则,其核心理念和话语元素就会淹没在具体的生活细节、文化泡沫中,哲学对人的形而上的感召力、再造力和提升力,将会无情地被消解。若真的那样,哲学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不仅被边缘化、被异己化了,而且终将自我埋葬。其三,有人强调,现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不是如何回归生活的问题,而是怎样从生活中实现超越的问题,即如何使哲学重新活在当代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哲学对生活、对科学、对文化多边切入的根本旨趣不在于放弃自己的形上诉求,而只进行所谓“平民化的对话”。恰恰相反,当代哲学的跨文化、跨学科合作旨在通过内在超越而实现自我深化,使之以变化了的新姿态重新呈现在历史理性的逻辑运动中,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永恒的形式,从而升华为一种世界历史理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时下,在“和谐文化建构”这一大哲学、大文化语境中,伴随着当代哲学大分化、大整合的整体推进,如何对其科际整合作出切当的边界限定,并为之提供学科对话和交流的文化出口,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不避浅拙愿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谈些浅见,以征询于学界同仁。
一些学者曾再三指认,当代哲学研究,面对学习和接受主体多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应自觉超越长期以来由于内部研究分工过细而形成的学科划界和思想藩篱,在构建和谐文化所倡导的“大哲学”层面实现多元化生、内在融通,“以一种真正哲学的方式”[1] 开展哲学内外跨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促进哲学与生活、与时代、与其他科学的良性互动,将自己的研究触角伸向多学科领地,通过界外阅读以打通各种研究视域,实现哲学跨学科的整体性的合和建构,从而消解哲学研究传统中的学术壁垒及其所造成的专业缺憾。应该说,这早已成为学界多数同仁心照不宣的共识与锲而不舍的追求。
事实上,哲学学科的专门化、专业化,由来已久,这对于加强其内部研究,提升其学科层次,唤醒其操持者的学科意识、学术良知,固然理所应当,原本无可非议。然而,这种研究格调所导致的学科分割、专业疏离、学术芥蒂,使其整体性的哲学“大智慧”长期处于破缺状态,使其“成人教化”功能(哲学实质上是在思想中引人上路、在反思中成全人的学问)处于晦暗之中。在传统研究格局中,哲学的守望者大多囿于固定的精神资源及其人文背景,长时段地接受呆板而苛刻的专业规训,以致养成了只对少数几个极具玄学意义的哲学难题进行偏执性操作的坏习性,病态地固恋于自己的特殊兴趣和切问方式,将自己定位并接纳于特定哲学社区的褊狭胡同中,定格为只知摆弄哲学碎片的“单面人”。这种人所沉吟出的俱乐部性质的专业行话或黑话,只能在少数同等弱智的所谓“士人”中秘传,岂能将其智慧的理性能量释放于哲学之外?对此,人们有理由质问:以这种怪癖的方式所操作出来的可以算作是“坏文学”的东西,究竟对人、人的生活有何用?其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乎?
在传统的研究框架内,哲学的优越性、自足性、至上性常常得以不适当的宣示,根本不能同等地看待其他学科的文化价值,一味片面追求十分狭隘且过度专业化的内在性研究,这种忘掉外在世界,刻意把哲学当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学科进行构建的努力,哲学史已再三证明并不是一种成功的方案。“纯思”的确是哲学守护“思的事业”的最高成就,但同时也是一种完全的文化灾难;它的确使哲学实现了纯净如水般的保洁,但惜乎又在纯洁中走向了堕落。因为,那种完全离群索居式的哲学研究,自我铲除了由于对日常生活广泛接触而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丧失了在混合文化中生存的多点支撑,不能对哲学之外的新颖的文化刺激和极具精神性意义的重大事变积极地予以回应,并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深刻洞察力,而是变成了被形上理性过分缠绕而走向窒息的“木乃伊”。在此尴尬的境遇下,不要说学科渗透、文化对流根本无从展开,即使在哲学界内部,不同背景下的哲学人也很少能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商榷,偶尔为之,也往往由于连最起码的公共商谈的学术前提都不具备,表面上讨论激烈,相互质疑,骨子里却貌合神离,尖锐对立。因而,总是有争论而无结论、多意气而少共识,不欢而散乃至侮及人身,都是常有的事,更遑论竭力参与实践、对时代课题积极表态、思入生活并引领时代前进了。铲断了与生活、科学和文化一切价值关联的旧哲学,被人们遗忘、抛弃甚至唾弃,都像呼吸一样自然。现代人没有谁会因为缺乏了这种玄思之学而感到给生活带来了什么不方便,因而将之作为一种无疗效的药而丢在了生活的阴沟里。
哲学高度的致思性、抽象性以及操持者对它的病态执著,辩证而历史地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必要,但却也往往是一种局限。因为,形上致思理路使哲学发展的健康肌体和生命机理遭到破损不说,还使它的接受者离哲学的真精神、真智慧越来越远,使自己演变成悖反性的文化怪物。哲学对人的思想启蒙和对时代的解蔽,最终都在理性的牢笼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思想进一步启蒙的阻碍和时代发展的精神枷锁。显然,这是由于形上理性的自我缠绕使之丧失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多元文化的滋养所致,由于日益小化、细化和窄化,既烂掉了自己的根又迷失了自己的魂。鉴于此,学界同仁普遍感到,当代哲学研究只有以特殊的超越性把握方式,与日常生活世界保持亲密的对话态势,才能使之不断地获得时代性跃迁,多渠道、多层面展示出“大哲学观”所特有的魅力与风采,同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升人的生命质量、生存境界和做人的根本,使之理智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哲学般地活着,并活出自己特有的风格和胸襟来。而当代哲学人也只有伫立时代潮头,以真正的哲学方式积极反思和回应重大的时代性课题,积极有效地参与当代社会变革所作出的一切重大安排,踊跃地对各种生活谋划献言献策、概括总结、及时范导,才能在历史与当代、理性与实践、哲理与生活的全新高度、全新意义上激活时代精神的多元智慧因子,使自己的哲学见解成为革新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时代、与人民、与实践均保持内生性的文化价值关联,从而真正赢得时代、人民、社会的青睐。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在谈及“哲学应在混合文化中求生长”这一观点时,也认为“所有原创性的哲学都是对发生于哲学之外的事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艺术的、科学的或者文学上的创新——的一种回应。哲学是,也应该是一种反应性的事业,它不应以自主性为指归,也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确立为一种准科学。”[2] 从当代哲学发展的未来取向上看,罗蒂之见,确属见道之言。
而当哲学真的打破了学科界限而建构出一种合和性的“大哲学观”,[3] 那么它就呈现为一种混合型的和谐文化。的确,当代哲学变得异常敏锐,在思想文化界获得了非常特殊的优势地位。因为它通过向相邻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向其他文化门类的弥漫与扩散,早已逾越了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的专业屏障,成为了一种深受人民大众广泛关注的公共话语、一种“出文入史”、科际合作的“拥有完全知识理想”的“通观”和“大略”,从而获得了多种学科的支撑、混合文化的滋养,涵盖了人文理性、价值理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包容了社会实践中的各种智慧,并且在其专业领域之外也发现了自己的接受群体。一方面,哲学自身固有的合和性的意义系统,使之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容量,的确将多元文化的智慧因子(内源的和外源的)有效组织起来并使之按哲学的方式整体而统一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本体论上的终极指向性,作为文化交流、学科对话的“经纬线”,更是将整个文化门类融会贯通并系统地整合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母体,从而使哲学的文化特色和文学意义更显著,成为一种具有整体性、全息性、普适性、广谱性的合和哲学或者和谐文化。
也有人担心,若哲学依凭多元文化的面具出场,借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这种公共形象的自我设计,能为之无边拓展自我生成之域吗?笔者在与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中曾指认,这种担心是多余的。[4] 68哲学人原本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国士”,而非精于一技的“某种人”、“单面人”。古代贤哲曾倡导,“君子不器”、“学不厌杂”;而“外博内精”、“兼容并包”则向来是当代哲学同仁的治学准则。他们热心公益事业,尽可能利用一切文化样式以创造公共出场的机会,借以宣示自己公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念,为自己塑造和确立公共性姿态和实验性立场,而不愿躲进高楼深院或栖止于书斋讲坛,只独白自己的私人情感,要么发思古之幽情,要么兴无端之慨叹;相反,而是勇于直接思入现实生活,真切感受和把捉因时代变迁所释放出的文化意义,而不甘心蜗居象牙塔中,一味把玩思辨概念这种高级精神奢侈品,说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且有一定技巧的废话,严重拒绝大众理解。哲学在混合文化中的生长,不仅拭亮了自己的公共形象,编织了多维的和谐文化网络,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也在学理内部发现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出口和路径,注入了新的语言元素、生命活力和文化之魂。它对其他文化样式的多边切入,使之在当代文化体系中占据了首要地位,甚至全面垄断了文化总体,使之从原来站在文化之外只做袖手旁观的“外行人”,变成了立足于多元文化内部进行腾挪的“内当家”。它的科际交叉和界外联手,不仅促进了它与科学、与文化的多元互补、重叠共识、交往互惠与和谐共进,而且开掘了科学和文化获得向高层跃迁的理性基础和价值范式,为其参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当代战略进行谋划,为之在核心层面代表并引领当代中国跨越性的发展,搭建公共的理性平台。哲学从各种理性教条和单一模式中奋力挣脱,将自己的智慧尽可能占满现代生活的广阔空间,以更加富有弹性和宽容的心态回应时代的挑战,以“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精神沐浴“和谐社会建设”这一新生活的阳光,定将绽放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那种更加绚丽多彩的智慧之花。
诚然,笔者也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哲学不是社会之学、生活之学,更不是纯然的科学之思、文化之思。哲学脚下自有路,何必步步随人家。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领地、切问方式和发展规律,它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文化和生活,不能随随便便地将一些非哲学的东西拿来进行哲学操作,更不宜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旁置和泛化,将自己的研究中心无端地外移和扩散,否则就会使自己沉陷或淹没于生活的直接性事实中,使自己的内在性、纯品性、同一性瓦解,使之与科学、文化的固定界限模糊,在日渐边缘化、碎片化、空壳化中魂不附体,精神委顿,并在自残自虐中走向他者化、异化。这表明,哲学在科际整合中,适当地为之进行学科划界是多么的必要,否则若忽视领地划分,对自己根上的东西遗忘得太久而只对无关宏旨的枝节突发议论,它也同样会在喧嚣与骚动中自我放逐,日益淡出,泯灭自性。须知,哲学在混合文化中的生长,换来的不是哲学自身的泛化和异化,而是自我的凸显和张扬。
但是,笔者本文更想强调的是,不能为了固守哲学的自性而对其进行硬性分割,使哲学回到昔日那种只在文本中找题目、只在单一的原理框架中讨生活、只在政治语录中找灵感的旧模式中,哲学不能只是哲学人的心灵独白或文字游戏,而应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社会变革的先导。为此必须倡导哲学的科际合作和跨文化思考。有人主张,哲学若放下自己正常角色而对其他学科进行“病态移位”,放弃自己的“本质之思”而试图界外阅读,这简直就是一种“乌托邦奢望”,它不仅会冲淡自己的担当意识,而且还会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一场致命伤。当代西方思想怪杰——齐泽克甚至说,压根就不能相信哲学能成为“混合在一起的事物”,“最傲慢自大的立场就是明显的多学科式谦虚”[5] 47。在他看来,哲学家都是疯子,都有自己的某个深刻的见解(“哲学地图”),他们之间只有误解和互相被压制的真理,哪有真诚的对话与交流?因而,若将哲学视为“一种跨学科的计划,这根本就是一场噩梦”[5] 43。他关于哲学应恪守自己的“纯思”本色的主张,其实在国内也不乏其人。不是有人曾依据哲学的至上品性而横加质疑另类文化人的切近资格吗?的确,哲学不能只附着于生活的表面,更不能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如果我们因不满意于形上之思的纯粹建构,从而不允许哲学有任何超越性指向和独立性的思考,那它就只能让思想依附于现实生活的表面,这哪里还谈得上“抓住事物的根本”!而如果让哲学之思完全放弃抽象性的追问,从而也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向生活示好,那学术研究还有什么深刻性、前瞻性可言?[6] 但,若一味看重自己的致极性特征,忙于为特殊的语言进行理性营造,甚至不惜以邻为壑、自设藩篱,最终也只能走上精神自杀的道路,岂能全面验证自己思想的当代意义!而缺乏跨文化运作和界外探索,又怎样实现哲学的多元化生、视域整合。[7] 那么该如何调适哲学的科际合作与领地划分之间的张力呢?或许,和谐文化建构所倡导的“大哲学”观及其“合和取向”,能为之提供一个和谐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文化出口。
就西方哲学的“合和取向”来看,除了后现代少数几位思想者竭力主张全面颠覆哲学之外,对哲学作非哲学理解的哲学流派,实在不胜枚举。实现哲学的合和建构与文化的和谐共进,一直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最持久性的文化特征。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哲学和科学、道德、审美等一样,也是一种文化因素,而且是文化因素中属于中心位置的因素。它关切的是人生经验中的生存悖论和矛盾,是对人如何通过“在”的活动而不断提升和拔高人的生存境界和生命质量问题的深切追问和反思。可见,哲学本质上是人学,是对人安身立命的人生切要问题的总体性把握、终极性关怀。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始,就形成了一种以致思形上本质为根本旨趣的研究理路,这种研究理路和格调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到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才达到了“纯思”精神的造极期。应该说,这条理路只切问了人类原始智慧中所蕴含的“逻各斯精神”(形而上的理性精神)这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奴斯精神”(诗性的生存)的另一个方面。因而,总的看来,黑格尔以前的西方哲学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空场,成了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自我繁殖、自我建构的历史,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语言自我生成和如何“使概念运动起来”的历史。当然,对这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垄断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并非到了现代才开始着手。其实从亚里士多德之存在论哲学开始,哲学这一智慧仙女就萌动了走出象牙塔而染指红尘的凡心了。它对感性经验的重视和对超验东西的质疑,就已亮出了自己反形而上学的立场。近代大哲学家笛卡尔、休谟,更将这一反形而上学的精神凸现为显学。对此,康德走得更远,它甚至彻底铲断了形而上学的科学基础。当然,康德没有经受住“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最终在实践理性层面仍保留了它的道德基础和信仰地盘。而步入现代的西方人文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一道,都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回归人的现实世界的口号。但,在科学主义发展过程中,他们不仅终结不了形而上学,而且最后都无奈地与之妥协,这体现了哲学必须与科学进行内在关联、合和建构才能一道发展的铁的规律。与之相反,现代人文主义的发展史,则可谓是完整意义上的反形而上学的历史。自尼采以降,中间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尔,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各位大师们,对形而上学都作了决不妥协的批判,使哲学真正成为一种切问人生真谛的人文精神,使哲学敞开了一种试图破除传统形上理性严重弊病的新的境域,将在场的东西(有限的具体物及其同样有限性的本质)与不在场而同样现实的东西(无限的然而却是现实的)综合为一,从而使哲学真正能够从历史的大视域出发对人获得整体性的把握,“以道观物”而非以理性(本质)观物,大大拓展了人生视域和生存境界。[8] 哲学真正回到了人自身,回到了诗意的“在”的世界中,彻底摒弃了只关怀在者(具体的在者或者永恒的在者)而遗忘了“在”的理性史。而现代哲学对生存意义的张扬表明,哲学不断地非形而上学化了,不断地与纯理性之思告别了,成了真正属人的智慧。它离开了形而上学的理性基地,似乎“无家可归”了,然而却正好可以“四海为家”,正好能在其他非哲学的文化活动中,如语言、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实现自我发展的通道,不仅拓展了自我生成之域,精神地图的新边疆不断获得刷新,而且能实现界外阅读和科际交叉与合作,使哲学能在混合语言元素、混合文化滋养中获得茁壮成长。西方哲学发展史表明,哲学作为人文精神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它压根不能离开其他一切文化元素而存在,相反,而必须对它作出一种深度的理性反思,使之为当代而存活,使之在人学平台上获得深层融通,并构建出一种以彰显人的真、善、美合一为旨趣的和谐文化。为此,当代哲学必须超越“思”而不能“让度出‘思’”(海德格尔语),必须将一切看似非哲学而实际上最哲学的东西拿来进行拷问,以实现其精神状态和思维状态的转换和再生。
当代哲学对生活的还原和对文化的多元渗透,恰恰意味着它在双重意义上否定了形上之思,既否定了理论理性对本质的先验诉求,又否定了实践理性对虚幻幸福承诺的超验追问,使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一体化的哲学模式普遍失效:使之丧失了指向终极可能性的智力反应和精神力量,其试图重写或重建形上之思的任何努力及其在词句包装上的任何谋略,都因不能有效地组织和表述思想而成了一道多余的手续,其原有的对外部世界的超越能力和对人的精神的“提升”能力皆处于委顿之中,再也不能以一种准强制性的规训作用把“世界的人”和“人的世界”聚集在它的周围,并在各种宏伟叙事中完成大写的“人”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吞噬。这种情况极易给人造成错觉,仿佛哲学已让度出“思”了,已放弃思想或不再思想了,似乎哲学已离我们远去,不再影响和触及当下现实生活和文化生命了。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哲学对生活的回归并试图活在多元文化中,并没有因泛化而消散,更不可能消解或变相消解它固有的对现实生活和文化的感召力、生命力和再造力,而是使哲学的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使之全面而彻底地得到贯彻和展现,使世界成为理性化的“合和世界”,并使理性成为世界性的“和谐理性”,哲学与世界真的融合为一了。这表明了当代哲学在多元文化内在融通中对生活世界的最后生成,也张扬出一种指向未来、指向“和谐共进”和内在沟通的实践性姿态。可见,这种貌似泛哲学的时代,恰恰又是最哲学的时代,是哲学精神和“思”的事业再度繁荣并步入辉煌发展的时代,是哲学在内在超越中所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和谐文化建构”的文化革命。当然,也要看到,哲学对生活的渗透和扩张、与多元文化的公共商谈、哲学的科际合作和界外阅读,的确彰显了哲学的非哲学化取向,但这种“非哲学化”方向无论如何却没有导致文化和生活的反理性、反哲学局面的产生。因为,这一切都是以哲学的把握方式进行的,是在仍旧取得了“准形上之思”的高位和深度基础上展开的,从而避免了哲学自我发展中所可能导致的精神失控和意义放任,避免了因理性腾挪的毫无节制和漂浮不定而最终走向自我埋葬的厄运。
其实,一方面,哲学是最自由的精神,它的所有概念都是辩证性极强的精神活体,它绝不会停留于、满足于某一点,它的意义不会终结于产生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而总是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智谋活在自身之外,活在其他文化样式中,活在大众性的日常生活中,借生活、文化、科学之光以照亮自己,使自己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形式出场。这表明,哲学原本与生活、与文化、与科学具有极强的可兼容性、可相通性。当然,这是一种内在融通,是一种理性之间的高端互访、极处会通、深层互动。它们越是在深层,可通约性越强,合和建构的可能性就越大。哲学就是在“出入”“尽究”各种文化思想之后才获得向高层跃进的,哲学史上的几次“学术造极期”以及思想史上的“文化轴心期”,无一例外都是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对流中形成的。当代和谐文化构建的伟大实践,自然也不能例外。因为,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主文化可以取代一切,相反,而要在多种思想和文化的合和建构中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域也是开放性的,它不可能固定不变,它总是处在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多元文化的融通而进行意义的自我澄明和自我呈现之中,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的发展永远“在途中”,永远处在生生不息的理性反思和文化交流的路途中,这是哲学不断获得新生和再生的历史必由之路。在当代建构和谐文化的新文明时代,社会变革的深层推动必然引发哲学问题域及其把捉方式的重大调整。如果当代哲学不能因应变化,实现自我革命,仍然用旧框架及其话语元素去面对因社会重大变革所引发的科学和文化的大分化、大整合的新态势,那它就会日益衰竭和委顿,只徒然留下一个“创新”的文化外观,实质上不可能激发出思想创新的原有能量,只能使之在纯思中绕圈子,看起来很学术,其实恰恰是“思想悲剧的诞生”。[9] 因而,只有通过科际合作和界外阅读,才能打破旧范式的思想牢笼,出入尽究并斡旋于一切文化样态中,在不断地批判人类业已形成的文化构造、科学构造(包括自身业已形成的各种体系和固有成见)中,不断捕捉、预见和引导新文明时代合和精神的生成;只有通过合理的学术定位、领地划分和学科限制,当代哲学才能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清醒的自我意识,才能通过不断的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和谐构建提供科学的智力支持,也为自身的科学发展确立切当的文化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