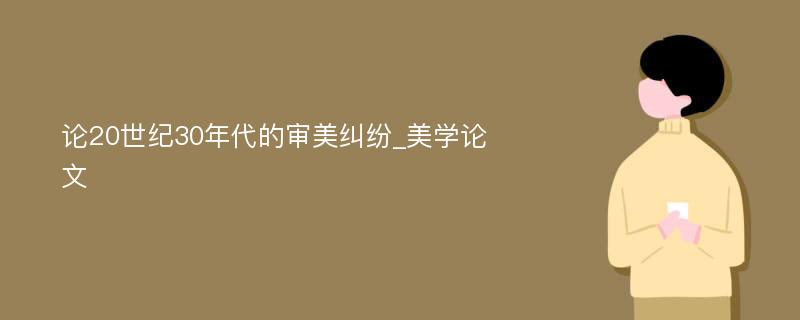
评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美学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美学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2-026-06
20世纪的20-30年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相继被介绍到中国,各种美学思潮也随之在中国理论界粉墨登场。20年代初,吕澄的《美学浅说》、《美学概论》、《现代美学思潮》,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以及稍后蔡仪的《新艺术论》等著作,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专著,与中国前一时期的有关论著相比,这些著作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大大开拓和深化了,虽然其中不少论著与文艺理论临界不清,但总体上看已经有明显的美学学科特征。这些论著对开拓和发展中国的美学研究,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它们大多带着明显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烙印,因此遭到了左翼理论家们的抵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分析审美问题,成为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出现了一场新旧美学的论争。
一、梁实秋与朱光潜的论争
1937年,梁实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文学的美》一文。有感于当时理论界有文学批评与哲学批评的边界不清的趋势,梁实秋在文章开头就写道:“……文学批评与哲学只是有关联,二者不能合而为一。即以文学批评对哲学的关联而论,其对伦理学较对艺术学尤为重要。艺术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其对象是‘美’。艺术学史即是‘美’的哲学史。”[1](P303)他在文中重复了自己10年前的一个看法:一个艺术家要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分“快乐”的种类,但在文学批评家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文学应该不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这“应该”两个字,是艺术学所不过问,而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以“生活的批评”为文学的定义,那么文学批评实在是生活的批评的批评,而伦理学亦即人生的哲学。所以说,文学批评与哲学之关系,以对伦理学最为密切。这是梁实秋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至于美学,他认为:“美学是哲学的一部门,它起来是很晚,现在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因为派别分歧所以内容很宠杂,因为唯心主义的色彩太浓所以结论往往是很抽象空虚。”“但是一般人总以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而美学正是一般艺术原理的学问,所以美学的原理应该可以应用在文学上面。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所谓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这原是很古老的说法,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莱辛,有不少的批评家根据不同的原则给艺术划分为若干类型,给文学也留一个相当的位置。文学与图画音乐雕刻建筑等等不能说没有关系,亦不能说没有类似之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各个类型间的异点,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到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同上)梁实秋举例指出,看一幅成功的山水画,几棵枯树,一抹远山,只能说“气韵生动”“章法严肃”一类的赞美话,总而言之曰“美”。看一部成功的小说戏剧或诗,就不能拿“文笔犀利”“词藻丰瞻”这一类的话来塞责,不能只说“美”,还得说“好”。因此他提出两个设问:
(一)假如我们还退一步承认美学的原则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那么我们要问——文学的美究竟是什么?或者我们用较正确的术语来问,从文学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美感的经验”?
(二)文学给了我们以“美感的经验”,是否就算是尽了他的能事?换言之,美在文学里占什么样的地位?(同上)
他通过对西方近代美学的分析,提出“我们要讲文学的美,我们只能从‘文字’上去找具体的例证。因为离开了文字,便没有文学。文字不是文学,文字是文学的形体,离开了形体文学便不能存在”。(同上)
梁实秋虽然也承认文学里有美,因为有美,所以文学才能算是一种艺术,文学也才能与别的艺术息息相通;但他又认为美在文学里只占次要地位,因为文学虽是艺术,又不纯粹是艺术。“文学里面两项重要的成分是思想与情感。文学的题材,严格的讲,是人的活动(man in action),其处置题材的方法是具体的描写,不是描象的分析,所以文学异于社会科学,是想象的安排,不是各别的记载,所以文学异于历史。”(同上)他指出文学作者对于人世必须先有新感悟,然后才能发而为文,所以文学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体系,因此文学作品与道德关系密切。“若是读文学作品而停留在美感经验的阶段,不去探讨其道德的意义,虽然像是很‘雅’,其实是‘探龙颔而遗骊珠’。”梁实秋强调文学是道德的,但又不注重宣传道德。在分析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之后,梁实秋指出:“文学与人生既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批评文学的人就不能专门躲在美学的象牙之塔里,就需要自己先尽量认识人生,然后才能有资格批评文学。”(同上)
20世纪30年代,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为代表的观念论美学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在文中,梁实秋虽然对以观念论为核心的美学极为不满,指出这种唯心论的美学极度浪漫,在逻辑上虽然能自圆其说,却不切实际,把艺术看成是一刹那间的稍纵即逝的心理活动,这只是一种浪漫的玄谈而已。但他并没有真正看出以观念论为核心的旧美学的要害问题。离开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内容,一切关于美的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梁实秋发表《文学的美》后,朱光潜于同年2月22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梁实秋的公开信——《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在这封公开信里,朱光潜对梁实秋《文学的美》一文的几个核心观点逐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美学的功用时,朱光潜指出:“……美学的功用除你所说‘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别快乐的种类’之外还要分析创造欣赏的活动,研究情感意象和传达媒介的关系,以及讨论一种作品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用‘美’字形容:而这些工作也是文艺所常关心的。每一个重要的批评家——从希腊时代到现代——都可以为例证。”[2](P507)针对梁实秋将美学归之于“自然科学”,而将文学批评归之于“规范科学”的观点,朱光潜提出美学与文学批评的不同并不在此,而在于一个是“纯粹科学”(美学),一个是“应用科学”(文艺批评)。针对梁实秋所言“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
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的观点,朱光潜通过对“文学的美”的具体分析指出:“……你只承认声音和图画可以美,而情感经验,人生社会现象,道德意识等则‘与美无关’。这样看来,你似乎在无心之中采用上述第二种解法,至少,你的‘文学的美只能从文字上着眼’一句话,如果说得明白一点,应该是‘文学的美只能在文字所给的一部分东西上——音乐和图画——出现’”[2](P509)朱光潜反驳梁实秋,并设问:“何以情感经验,人生社会现象,以至于道德意识不能成为美感经验的对象呢?”朱光潜还指出了梁实秋文中的“图象”概念不明:“它可以指(一)画家的作品(picture),可以指(二)心中的视觉意象(visual image),可以指(三)心中的一切意象(mental image),包含视听嗅味能运动诸器官所生的印象在内,也可以指(四)心中一切观照的对象(object of contemplation),即一般人所说‘意境’,文学的‘图像’究竟是指哪一种呢?”(同上)朱光潜指出了梁实秋最大的问题是视人生社会现象和道德意识与美无关。他认为社会现象和道德意识确实不能成为“图画”,不能成为“视觉图象”,但它们可能成为“观照对象”,或“意境”,而可以成为“观照对象”的事物都有令人觉到“美”的可能。
朱光潜同意梁实秋“文学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的体系,因此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无关”的基本观点,但他又指出:“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我们不能说其他艺术家也有同样的需要吗?想一想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全部,想一想贝多芬的乐曲,想一想中国所流行的文人画,我们可以说这些和文学不同在它们‘与道德无关’吗?在它们的作者‘没有人生观和思想的体系’吗?”[2](P511)朱光潜认为,文艺是否有关道德是一个问题,应否有意宣传道德是另一个问题。读任何文艺作品都必须“探讨其道德的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作者既不必“宣传道德”,读者又何以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探讨其道德的意义”呢?他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指出,我们可以在无形中读他的作品而得到道德的影响,但是不能在他的任何作品里都找出一个可以明白叙述的“道德的意义”。与梁实秋不同,朱光潜认为道德是一切艺术的共同点,它在文学中可以成为美感观照的对象,“美”在文学中的重要不亚于在其他艺术中。
二、周扬对唯物主义新美学的呼唤
梁实秋与朱光潜的美学讨论也引起了左翼理论界的关注。1937年6月15日,周扬在《认识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他在肯定梁实秋有关文学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批评文学的人不应专门躲在美学的象牙之塔里,而需要自己先尽量认识人生,然后才有资格批评文学的观点,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见解后,又指出:“可惜的是,梁先生虽不满于美学之唯心主义的色彩,却并没有对那唯心主义进行根本的批判。他的批判可以说是非常不彻底的。”[3](P212)他尖锐地指出,观念论的美学自鲍姆嘉通到克罗齐可以说走到了头。“现代美学的主观化,形式化,神秘化,和那完全失去了进步性的资产者层的文化全体的没落和颓废相照应,显示了它已不能再往前发展”。“新美学的建立,只有在和旧美学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上)这里,周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新美学”的口号,还分析了梁实秋理论的局限,指出他没有把从来美学的原则和实际的文艺作品的分离看成可以而且必须克服的困难,倒把这个分离合理化了。针对梁实秋视道德重于美,以为道德是内容,美不过是形式,因此在文学的关系上,美学还不及伦理学重要,周扬指出这是梁氏的理论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薄弱的一面,虽然也在反对观念论的美学,但不自觉地又与之同流了。周扬强调:“我们要批判他们,就正要指明:美并不只是在形式上;离开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内容,一切关于美的议论都是空谈。美不能形式主义地去理解,道德也不能看成抽象的概念,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借形象而具体化的内容。”很显然,周扬在这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美的问题,来理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周扬还指出,梁实秋对于艺术中的美学和道德性的二元的看法,是他的理论上的最大的缺陷和弱点。这个弱点的产生是在于他一方面正确地主张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能够完全克服旧美学的观点。朱光潜虽然也看到了梁实秋理论中的这一缺陷,并给予了批判,但是朱光潜从观念论美学之辩护出发而进行的批判,与问题的正当解决正好走了两条相反的道路。周扬还认为旧美学之所以只是少数资产者层文人占有物的原因,就在于它与现实的作品和批评的分离。这种“分离”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周扬对观念论美学的批判也是准确的,这样的美学显然是需要改造的。但周扬在这里提出要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堪称科学的文艺学”的观点,又显得过于激进了。且不说他所说的“文艺学”是否就是后来作为学科名称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ПИЕ”(注:俄语“文艺学”,文艺学这一名称就是从俄语中来的。作者注。)即就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也远不止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艺术性和思想性等问题,显然不能把美学简单地等同于艺术理论,尽管二者的研究领域会有交叉,但毕竟是不同的学科。
针对朱光潜的将艺术作为心理现象来看待的美学观,周扬批评道:
我们承认美的感情,美的欲望的事实(没有它们,艺术活动便不存在),却不承认它们是先于社会的发展,生物学地内在的。无论是客观的艺术品,或是主观的审美力,都不是本来有的,而是从人类的实践的过程中所产生。这就是我们和一切观念论美学者分别的基础。[3](P217)
周扬引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关只有音乐才唤起人的音乐的感情,在非音乐的耳朵的人,最优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因为在他,这不成其为对象的论述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的正确。周扬认为:“美的感情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发展被决定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这是颠扑不破的法则。永远不变的绝对的美的规范决不存在。各个时代各种社会层的美的概念是极其不同的,甚至于常常相反。”[3](P217-218)这里周扬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美的情感问题,尽管这种解释今天看来还相当简单,但他却尖锐地指出了朱光潜、梁实秋无视道德意识和美的概念一同变化的那个历史的条件。
为了克服旧美学的种种缺陷,周扬提出必须努力于新的美学理论的建立。他认为新的美学应当根据已有的理论成果全面地从根底上批判旧的美学。不但要否定它的观念论的内容,连那个名称也该改变。“因为'Aesthetics'这个字原含着感性学或直观学的意义,确如甘粓石介所说,是一个适合于观念论美学者的名称。所以新的美学的正当的名称应当是‘艺术学’”。[3](P224)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这里又使用了一个“艺术学”的概念。他虽然不再如前那样把美学与文艺学相提并论,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极不情愿使用“美学”这一旧名称的。周扬特别强调新的美学首先要克服美学和现实的分离,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和斗争是新的美学的基础。同时新美学并不把自己和过去一切美学、一切艺术理论分离,新美学要继承它们的“正当的部分”,把使它们往前发展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新的美学已不是研究抽象的美的学问,它应当指出美的要求不是艺术作品的最后根源,它本身,就和艺术作品一样,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这是新美学和旧美学的根本不同,也就是前者和后者诀别的起点。”[3](P225)他还认为新美学要从客观的现实的作品出发,来具体研究艺术的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的根源,它的本质和特性,它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创作批评和实际活动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协助文学艺术实践,是新美学的最大的特色。尽管周扬在这里并没有详细论述新美学的特质,也没有为新美学建构起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与范畴体系,在文章结尾处,还很不自觉地把美学与文艺学、文学批评相提并论,但他的这篇文章在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因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应对旧美学的论战性文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实践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30年代共产党人有关马克思主义美学专论的不多的文献之一。
三、蔡仪对“新美学”理论的建构
3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真正探讨美学基本问题的论著还十分有限,在这些论著中,绝大多数是介绍和转述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潮或美学家的观点、学说和著述的。由于当时受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所限,对近代唯心主义美学的译介尤为集中,特别是柏格森、立普斯、克罗齐等人的观点、学说在当时十分盛行。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代表作。梁实秋、朱光潜讨论“文学的美”之际,也是蔡仪开始自己的新美学思考之时。蔡仪并没有像周扬那样立即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或主张,而是着力于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称之为艺术认识论体系的原理,以纠正唯心主义观念论与艺术直觉说的谬误。不过这项工作的展开在30年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美学界乃至整个自由主义的学术营垒还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一统天下。
朱光潜虽不同于梁实秋将文学排斥在审美之外,但他主要是将“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我们知道,这还是典型的西方心理学派的思路,沿着这一思路轨道,我们也很容易找到它在哲学观上的位置。朱光潜善于从审美实际出发讨论美学问题,因此他较重视来自审美体验的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和立普斯的“移情说”。作为对“移情说”的一种补充,谷鲁斯、浮龙·李的内模仿思想也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朱光潜及其同时代的不少美学家们都主张在审美的过程中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或实现人的某种“价值”。受这种理论的驱使,人的表现及其主观精神又成了他关注的主要问题。他没有也不可能“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他在肯定上述学说真理性的同时,几乎与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缺少对这些学说的批判精神。这也就是左翼理论家称之的“旧美学”。
蔡仪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开始他的“新美学”建构的艰难历程的。他所要建构的“新美学”并不只是要狭隘的批判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观念论美学,而是这位初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整个西方思想的冲击。在蔡仪建构“新美学”之时,马恩经典作家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已经在中国传播,马恩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有关论述以及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先后介绍到了中国。苏联美学和艺术社会学对中国左翼文坛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等也相继被译成了中文。中国的左翼理论家们开始尝试用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待、分析社会和艺术,这也是蔡仪建构“新美学”的理论基础。
蔡仪最初撰写《新艺术论》是试图以自己在留学日本期间所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阐发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美学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作一次知识性的系统整理。正如作者在《新艺术论》1949年再版时所写的小跋中说的:“这本小书是1942年下半年在一种愤郁的心情下写成的。当时只觉得应当做点什么,应当写点什么,借以刺破那压下来的黑色帷幕让自己透一口气。此外还说有点什么意图,也不过是想整理荒疏已久的关于艺术的一点知识罢了。”[4](P10)因此,《新艺术论》着力于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称为艺术认识论体系的原理,纠正“旧美学”观念论与艺术直觉说的谬误。他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态度批判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谬误,既包括西方近代美学传统中的理论缺陷,也包括了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美学观念,甚至还包括对苏联当红的文艺理论家的批评。对长期以来中国左翼理论界强调文艺的宣传效能而忽视了艺术表现特征,忽视了艺术的特殊认识的本性,也同样给予了直率的批评。《新艺术论》的最后一章,作者论证艺术美即具体形象的直观,亦即艺术的典型时,发现具象真理即艺术典型的立论,有可能为“新美学”确立一个可以延伸、可以发展的核心概念。他也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创见,最终发起了对“旧美学”的全盘批判和改造,他要用“新美学”认识论的反映论来代替“旧美学”的主观或客观的观念论,他也是在这个基点上阐发自己的一系列美学观念的。蔡仪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较好地论证了美、美感、美的创造与认识的关系。他从这一方法论原理出发,指出美学研究客观现实的美,要根据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美的认识及美的事物能给予人们美的感受和感动,也就是通过认识的关系。如果认识论问题不能恰当地解决,那么美感论和艺术论也难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现实美论、美感论和艺术论都须有认识论的基础。
客观地说,40年代问世的《新美学》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系统地讨论美学体系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比起30年代周扬发表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来,无论是体系的创建,还是具体的问题的阐释上都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重要的成果。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接受蔡仪对新美学的界说,学界普遍承认《新美学》有它的体系与方法,它一方面冲击了旧的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揭露了旧美学的痼疾,较系统地批判了旧美学的根本弱点;另一方面建立了崭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美学研究的新途径,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来考察美学上的根本问题,以崭新的方法论来建构唯物主义的新美学体系。但是无论蔡仪还是周扬,在他们提出“新美学”设想的架构的同时,也为后来我国的美学建设留下了隐患,一味强调“唯物”和“唯心”的对立,强调“斗争”,忽视“融合”、“对话”,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美学理论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这种倾向也影响了后人对前代美学家的评价。
今天,我们也可以客观地说,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在当时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介绍了几乎所有在近代有重大影响并对建构中国美学界产生了现实影响的西方各种美学思想及其美学家,这项工作在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开创意义,因此得到了学界的普遍称道。今天我们客观地看待《文艺心理学》,其开拓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使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在其发展的第一步,就站到了世界美学发展的同一思想体系和潮流之中,而且朱光潜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在译介的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审美体验和认真思考,带着自己对美学学科的总体认识和理论构想对它们进行了清晰的逻辑关系的组织与阐发,这些都是值得后代美学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收稿日期:2002-03-19
标签:美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梁实秋论文; 谈美论文; 文艺心理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周扬论文; 文化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