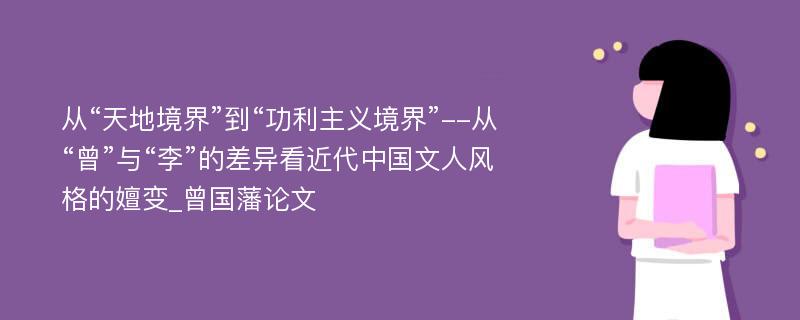
由“天地境界”到“功利境界”——从曾、李之别看近代中国的士风转移与文学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的士论文,功利论文,别看论文,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时期诗、文、小说三界都爆发了革命,加速了固有中国文学面貌的改变。古典时代所崇尚的圆熟简练、静穆悠远的文风迅速为一种激越亢奋、铺张扬厉的文风所取代,流风所及,出现了“以叫嚣为气盛,以粗豪为雄骏,以新词为奥衍,以俚语为雅饬”[1](P47)的文学时尚,这是时代冲击下人的心性结构改变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古典诗文的那种“沉潜于古人者深,而神明于矩矱者熟”[2](P16)、以“究心泽古”为正脉的诗风,因背乎时代趋势开始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主我、主情、主“动”、带有功利化和世俗化倾向的“布衣”诗歌和白话文学。这场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古今之变是如何发生的,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把握文学、文化的“现代性”变化可以有多重视角,既往的研究比较重视对社会政治经济这些客观结构的分析,但缺少从作为历史当事者的人的心态、体验结构入手来探究这种古今之变。实际上,这种心态(体验结构)的变化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内在。心态属于世界的价值秩序之主体方面,一旦体验结构转型,世界之客观价值秩序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动。纵观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担当历史领军人物的心态、精神气质的变化对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精神直观的角度而言,“现代性”意味着的就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3](P16)。本文试图从在清末影响巨大的两位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入手,考察清末两代士人知识阶层的心性结构、精神气质的变化,将曾作为变化的起点、传统的末代绝响,将李作为变化的先兆、功利主义文化的初级形态,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晚清士人心态、精神气质的变化与近代文学、文化转型的关系。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以精神直观的方式发现人的心灵存在着一种客观价值秩序。他将这种客观价值秩序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感官价值、实用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进入现代之后,这种心灵的客观价值秩序发生了颠倒和位移,位居其下的感官价值、实用价值和生命价值上升为主导价值,神圣价值、精神价值在人们的生活中开始下降,退居次要地位,他认为这种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颠倒最终引发了现代人的精神和“价值”危机问题。
这种对客观价值秩序的强调与舍勒对人的基本定位有关。他认为,人既是生物或生命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所以人是居于上帝和动物之间的存在者;神和兽都没有羞感,而人有羞感,而羞感正是人之为人的特性。[4](P163)他还用“位格”一词来指称处于精神活动中的人,通过对“位格”的分析来展示人的精神世界。“位格”指的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具体的、自身本质的存在统一,它自在地(因而不是为我们的)先行于所有本质的行为差异(尤其是先行于外感知和内感知、外欲求和内欲求、外感受和内感受以及爱、恨等等的差异)。位格的存在为所有本质不同的行为‘奠基’。”[5](P467)在这里,“位格”指的不是个性化的具体的人格,而是指高于个体人格之上的某种价值秩序,它突出表现为人的人生境界的差异。位格的差异生成了人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偏恶法则,由此造就不同的人生境界。
舍勒所发现的这种客观价值等级秩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也是将人定位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这种“神”性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指的就是人之为人的“灵明”之性、“天命”之性。冯友兰也曾将中国人的人生境界做了由低到高的区分。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当他做什么事时,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并且自己意识到,是在做这件事。正是这种理解和自我意识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我所称的‘人生境界’。……尽管人和人之间有种种差别,我们仍可以把各种生命活动范围归结为四等。由最低的说起,这四等是: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6](P220)
冯友兰所讲的四种人生境界中的前两种都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种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前两个境界可以说是来自天然,后两种境界则是人自己的心灵所创造的。自然境界是最低级的存在,功利境界比自然境界稍高一点,更高是道德境界,最高是天地境界。这样排列是因为,自然境界的人生不需要对人生有任何理解和自我意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还要有一点对人生的理解和自我意识;天地境界需要的人生理解和自我意识则最高。道德境界所讲求的是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所讲求的则是超越道德的价值。……人在道德境界中生活的衡量标准是‘贤’,它的含义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里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哲学就是启发人追求‘成圣’”[6](P221)。一个人对宇宙和人生的觉悟和了解不同,决定了人的不同的生存境界。
从“位格”和“境界”出发去考察近代人的生存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在曾国藩这一代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中,是存在着一种超验性维度的,这种超验性在西方表现为一种“神性”,而在中国则表现为一种“天道”,它与人的世俗的生存构成一种紧张和对立。舍勒将这类人形象地描述为“寻神者”,即用神性来丈量自身、规范自身的人。在中国语境中,它指的是一种对天道的遵循,类似于老子所说的“挈矩之道”,法之于天,称为挈,则之于地,称为矩。孔子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指的也正是这种“挈矩之道”中的自由。儒家以天为主宰,天在天为天道,在地内在于人为人道,人道或人性是来源于天道或天性,天道、天性透过人道、人性得以体现和彰显。既然天、理、道超越于人之上又内在于人,所以人应该与天合其德,取法于天道以指导自己的立身处世,由此形成“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自觉的“天人合一”的伦理体系。正如唐代李翱在其《复性书》中所云:“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7](P165)所以,要成为圣人,就必须能够“以性统情”,“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7](P165)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主静的文化,因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乐记》)。周敦颐说:“无欲故静,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周敦颐:《通书》)“主静”被视为是立人极之本,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至高之境,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主静”为天人之间构建了一个桥梁,静在动先,静极而动,才能动必中节,故而这种对于静的强调,将人定位于(天道)存在的倾听者、感悟者和守护者,而不是存在的主宰者和征服者。如此,由“主静”而达至的“天道”作为一个超验的维度成为善恶判断的终极标准,对从个人“躯壳起念的”情感好恶和功利诉求形成了约束。具体到曾国藩身上,他对于天人合一的追求主要表现为“以志帅气”和“以静制动”,所谓修身养性,也就是使人性归宗于天性,以“天命之性”来矫正“气质之性”,在自然人性之上树立起一种宗教性的内在的纪律和规范、理想和目标。
曾国藩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态中成就的最后一个内圣外王、道成肉身的“完人”,他在立功、立德、立言上都成就非凡,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在于其“主静”的功夫。他原字伯涵,20岁时“取涤其旧染之污,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改号涤生。他从青年时代开始立志进行这种人格上的修炼,好友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后代圣人,也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8](P42)他自己也意识到“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殆矣哉!”[8](P45)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决绝在日记中进行不断的自省、自咎、自我鞭策,以求自我提升。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日记中言:“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个人,何我遂甘堕落耶?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8](P45)这种自我鞭策到了一种非常严苛的程度,如同年十一月初八日记中就因为早上赖床而把自己骂为“真禽兽也”:“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8](P44)这是一种自我教化的功夫,追求的是一种高出实然的应然之境。
从其学问志向来看,曾国藩并不独宗程朱,他更重视邵雍、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乃至司马迁等,对春秋诸子之说也持开放态度。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9](P574)还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9](P653)他没有一般程朱理学褊狭的“道学头巾气”,也不满足于道德境界的生存,而更向往“与天地参”的“天地境界”,究心燮理阴阳的中庸之道、天人之学。
曾国藩对人生有一种悟境,他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充分的认识,这使他更为热切地转向对天道的追寻,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寄托于与天道的合而为一之上。他曾说过,“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余皆不为也”[8](P28)。可见,他于学问和事功之外别有怀抱,那就是儒家的“希圣希贤”、修身立德、内圣外王之学。曾国藩从32岁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被称为“修身十二款”。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10](P1785)他相信“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修身的最高境界是“慎独”,即“举头三尺有神明”,即一种不需要外在束缚、监督的宗教性的道德自律。他在率部攻破南京之后,曾有部将劝其反清自立。他当时写下了一副对联作为回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此联系集苏轼和王安石的诗句而成,从中很能看出曾本人所独具的胸襟和志趣,这是一种同天、事天、乐天的天地境界,非一般生活于功利、道德境界中人所能及,上联表现出一种与天合一的“天地好生之德”,下联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睿智和通达。所以,民国时期王闿运看到这副对联后感慨道:“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并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11](P606-608)
从文章气象上看,曾国藩把立德、立功、立言融于一体,开辟了新的境界。所谓“士先器识而后学问”、“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风格即人”,他的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是高度统一的,他的文章便是其独特人格的感性显现。他的内外兼修的人生追求自然显现于他的写作之中,使他的文章具有了单纯书斋文人所没有的恢弘气象,由此也使他成为了桐城派“中兴盟主”。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则认为还应加上一门“经济”之学,认为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也就是说,他除了传统士人的人文道德关怀之外,已意识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实用之学的重要性。表现于文章上,就是超出了早期桐城派的个人视野和枯淡趣味,在谨严有度、自然质朴之外别有一种雄奇瑰伟、阔大光明的气象。对桐城派所推崇的归有光,曾国藩认为其文不施雕凿、“有刻画而足以昭物情”,有可取之处,但其“置身不高,闻见不广,情志不阔,不免识其小而晦其大”,“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乎?神乎?味乎?徒词费也”。[12](P113)曾国藩把“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视为为文的关键,显然是一种高于“小乘”的“大乘”精神的体现。身处乱世之中,光是“气清体洁”已远远不够,时代需要他有更大的担当和抱负。
颇为难得的是,曾国藩于鞍马劳顿之中不忘读书论文,并最终形成了颇具创见的古文“四象八态”之说。这种超出个人的趣味偏好,将审美感受、诗文鉴赏提升到一种“元学”高度来定位、分析的理论,确有其独到之处。吴汝纶在《记“古文四象”后》做过这样的评说:“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由四而八焉。盖文之变不可穷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称量而审定之,以为某篇属太阳,某篇属太阴,此则前古未有,真天下瑰伟大观也。”[13](P301)曾将姚鼐论文的阳刚、阴柔二端,分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象,分别以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属之,而气势有喷薄、跌宕之分,情韵有沉雄、凄恻之分,趣味有诙诡、闲适之分,识度有闳阔、含蓄之分。这种将审美现象理论化的努力使其足可成为批评史上的一家之言,而这也与其“主静”的功夫有关。因为审美属于感性之学,很难加以理性化的归纳,“文之精微,父不能喻之子,兄不能喻之弟,但以俟知者知耳,此扬雄氏所以有待于后世之子云也”[13](P302)。而曾氏论文则得益于宋代邵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先天学”的启发,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象也来自于邵雍。邵雍认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是按照“先天象数”的图式展开的,并将这种先天象数归之于心,认为“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皆生乎心也”。[14](P518)此心既是个人之心,也是宇宙之心。人是宇宙间“物之至者”,灵于万物,所以能够领悟天心,达到物我一体之境。要达到这一境界,首先要懂得“以物观物”,因为“以物观物”则明,“以我观物”则暗,只有跳出个人的主观好恶,才能做到廓然大公,与天合一。人所以灵于万物,最根本的在于人能知天地万物之理,他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14](P506)。他还强调“反观”,要求既不蔽于物,也不蔽于我。只有这样才“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15](P213)。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涵养的功夫,从涵养着手,在情意上打破人我的界限,从而进入智慧的境界。哲学家冯契认为:“以我观之,得到的是‘意见’,以物观之,得到的是‘知识’,以道观之,得到的是‘智慧’。”[16]曾氏的四象八态理论跳出了个人的审美偏好,将人类主观的审美情态客观化,又以精神直观的方式,体验领会诸相变化的根本,由此对人类复杂的审美现象作出具体而又精微的阐释。这是以道观之的结果,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观性的“我见的扩大”(蔡元培语)和客观性的知识的独尊,而以道观之的智慧则呈退隐之势。就审美而言,意见和知识显然不能真正把握审美的奥秘,更无从将人导向一种“诗意的栖居”,所以,超越意见和知识的以道观之的智慧对于人的生存仍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曾国藩并没有超出其时代,有其固有的历史的、阶级的、文化的局限性,他的“天地境界”的达成有赖于传统道统、政统、学统合一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环境,一旦这种生态环境被近代强势的西方文化打破,曾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再现的末日绝响。
曾国藩之后的士人能进入他这种“人生境界”的已非常罕见。而且,近代以来,立功、立德与立言之间的分裂已不可逆转,这是因为传统将它们统合在一起的道进行了消解。功、德、言开始形成各自独立的规则,功属于做事的范畴,它主要遵循的是一种功利性的效率原则;言则主要成为一种对客观性的知识的追求,有其自身的规范;而德则主要成为一种个人性的品德、操守,失去了外王的可能,只能求之于己之心安而已。像曾国藩那样在政学两界都处于中心位置且具士林号召力的人物已经消失。比如他的门人、晚清重臣李鸿章,虽也是翰林出身,在事功方面不让其师,但在修身立德方面已相去甚远。这一点李鸿章自己也有所认识。他一生最推崇曾国藩,但也总是自愧不如。他在晚年曾说:“我老师道德功业周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17](P111)曾国藩在延揽幕僚时,尤其喜欢好德上进的朴厚之人,且有育人之心,所以其幕府人才辈出,入幕者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熏陶和磨炼。而李鸿章则不然,他取人偏重才干,“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文章道德,尚在其次”,而且“好以利禄驱众”,喜用同乡,所以其幕府弥漫着一种势利、谄媚之气,他的幕僚非但难有所长进,反而可能日趋卑俗。在曾和李处都当过多年幕僚的吴汝纶曾作过这样的比较:“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18]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曾国藩能够持己所学,陶铸群英,并且集思广益,诚恳待人,“于是人争自濯磨”[18];而李鸿章则独断专行,“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19]。与曾的以诚相待、持身刚正相反,李鸿章则对上奉迎取巧,对下操纵利用。他对僚属姑息纵容,“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又专恃利禄作“牢笼术”,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20](P8)而且他总是“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为了预防僚属“协谋为主帅害”,就耍弄权术、两面三刀,“在僚属中制造矛盾,使他们失和,借以从中渔利,达到操纵控驭的目的”[19]。因此,他所用多申韩之术,儒只剩下了招牌,他需要的僚属只是可供驱使的奴才,而不是平等互进的朋友和同道。故而时人抨击说:“少荃首坏幕府之风,以媚福济者媚曾公,而幕府坏,军务坏,天下坏!”[21](P57)民间也有“湘军多书生,淮军多无赖”的说法,由此可见,为首者的个人品格对其所统领的群体风气影响之大,这种影响进而会由士林向整个社会蔓延,由此在“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引发社会风气的整体性变化。其后“谴责小说”的兴起,也与这种体制内士人的功利化、世俗化、醉心功名利禄、丧失人格操守直接相关。
从现代性的价值位移这一角度考察,这种由曾到李的文化精神、气质的变化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的变动,即功利性价值开始由低等价值上升取代原本高居其上的道德价值和神圣价值。这种取代有其必然性,那就是支撑神圣价值的“天道”信仰此时开始陷入崩溃瓦解状态,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化对儒家的德性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功利主义开始成为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潮。梁启超在1905年说:“夫功利主义,在今且蔚成大国,昌之为一学说,学者非惟不羞称,且以为名高矣。”[22](P722)所谓功利主义,也就是一种将趋乐避苦视为人生终极之目的的主义,它认为事无所谓善恶,趋大乐,避大苦者,谓之是,谓之善,否则谓之非,谓之恶。这就导致了从寻找“神性”(天道)的人到立足“自然人性”的人的现代性变化。在西方,它意味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由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的转移;而在中国也同样意味着由“天命之性”向“气质之性”的转换,由以性统情的“复性论”向以情统性的“情本论”的转换。推动这种转换的重要动力就是救亡的功利诉求和物质万能的世界观。杜亚泉曾对这种物质主义所造成的精神虚无倾向做过这样的分析:“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也,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23](P36—37)
与堪为士林的精神领袖的曾国藩不同,李鸿章只是一个事务性的干才,他于其师,也可以说是孔子讲的“其知可及也,而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欠缺的是曾所具有的那种谦德,多的是一种自命不凡的骄矜之气;既无主静的涵养,也无希圣希贤的主观努力。当年曾国藩在幕府中,对李进行过精心而严厉的调教。有这样一则关于李鸿章的轶闻:“曾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李不欲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不得已,披衣而赴。文正终食无语,食毕舍箸正色谓李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有一诚字而已。’言讫各散,李为悚然久之。”这显然是曾国藩素来深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李鸿章日后回忆说,老师此举确实使他养成了能够早起的习惯,但他仍是就事论事而已,从内心深处显然还是将此视为小节。再如《庚子西狩丛谈》上记有一则轶闻,说李鸿章接替曾执掌北洋军政事务时,曾国藩问这位昔日的幕僚,打算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答:“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不管怎样,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听后,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后说:“呵,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自知失言,连忙说:“门生信口乱说,还望老师指点。”曾这才正色说:“依我看,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17](P123)李鸿章自己也说从此事获得很大教益,知道与洋人打交道也要以诚为本,但他显然无意亦步亦趋,从他处理天津教案和后来办洋务、外交的经历来看,他还是用了不少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其师都摆不平的麻烦事。问题在于,他在处理教案问题上的成功和曾的失败,似乎证明了他的这种灵活变通、纵横捭阖的功利主义似乎更能切合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所陷入的强邻环伺、朝不保夕的危局已经使人将“诚”与“迂腐”画上了等号,对于整日与“虎豹”打交道的李鸿章来说,为脱难济困,也只能穷于应付、随机应变而已。在封闭、单一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传统德性文化赖以发挥其功效的场域和环境,至此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士人的文化自信、从容心态都已无从谈起,这也是功利主义伦理在后来大行其事的客观原因。社会心态的转换自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决定的。因此,我们对李鸿章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道德评判上,还应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演变来看,道德与政治的分离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李鸿章也可以说不期然地成为现代非道德政治的滥觞,他自己也深知自己如此行事的无奈,在晚年也作过这样的自嘲:“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7](P121)这种“裱糊匠”的事业自然使他只能在功利境界中行事,被外部之事牵着走,修身养性、希圣希贤都无从谈起,且已无心至此。李鸿章的优长在于他的务实和勇于任事,他最讨厌的就是书生不切实际的空谈,曾说过:“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24](P175)他曾这样说过同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25](P284)从中可见他的价值取向所在。
与曾国藩的成圣追求不同,李鸿章追求的只是成为令人仰视的英雄和足可傲人的荣耀,他是一种有英雄主义情怀之人,在青年时代就留下这样的诗句:“男儿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入都》)对荣耀利禄的追求可以说是其人生最大的动力之一,确如其师所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他在谤满天下之时,仍恋栈不去,被人看做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典型。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讲“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24](P9),可视为一种公论。李的长处在于不避艰困、勇于任事,他临终还留下这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的遗作:“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内尘氛犹未靖,诸君莫做等闲看。”(李鸿章:《劳劳车马未离鞍》)至死他“双目犹炯炯不瞑”,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清末名臣至死都无法摆脱这种现实急务的压迫,以后的数代中国人也无从摆脱。传统主“静”的天道文化不得不让位于救亡图存的功利主义,以应对现实的急务,以免于亡国灭种的威胁,李鸿章也就构成了这种文化转型的最初的标本。所以,其英雄情怀、功利追求、务实眼光等也都与这种救亡图存的时代急务密不可分,这种时代急务也推动了士林风气由“醇儒”、“名士”向“志士”、“英雄”的转换,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也由“天道”、“彼岸”向“世俗”、“功利”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宗教性道德开始被世俗性的功利性道德和源于个人好恶的情感性道德取代,文学也开始由宗经、弘道向主我、主情、英雄化、功利化的方向转换。
人的精神气质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价值观的变化,而作为时代的整体精神气质的变化也推动了作为最高文化综合体的文学风貌的变化。真正推开近代文学、文化之门的是其后以“圣人”自居的狂者康有为和以“疯”自傲的章太炎,他们代表的是近代人在知情意方面的全方位的解放,而重新解读曾、李,是为了给这种近代的人性解放提供一个原点,看近代是从何处出发、起步的,这对于从现代性之外来把握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变化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