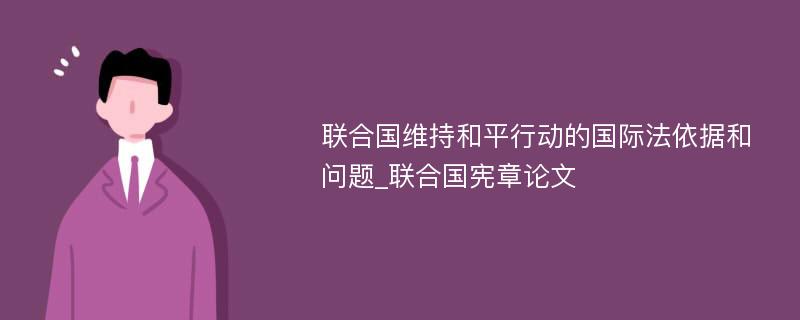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际法根据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国际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创设的“维持和平行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8年9月29 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表彰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缓和虽已实现停战,但尚未缔结和约的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实现和平谈判的开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维和官兵不怕牺牲和艰难困苦,为维持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充分肯定。
联合国维和行动自创立以来,经历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冷战时期的维和行动一般被称为传统的维和行动,冷战后的维和行动被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
维和行动正处于新的发展时期,某些维和行动的规模、使命范围、性质及其所依据的国际法根据都在发生变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维和行动的发展趋势和问题,促使其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效地维持国际和平,保障世界安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传统维和行动的国际法依据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依据问题,在国际间一直存有争议。问题集中在两点:第一,维和行动是否是“执行行动”。过去苏联认为是执行行动,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安理会负责。国际法院1962年对第一支紧急部队(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建立,于1956年11月—1967年5 月驻苏伊士运河区保证和监督敌对行动的停止和入侵军队的撤离)和刚果行动中心的咨询意见认为不属于“执行行动”,根据宪章“主要”但不是“专属”于联合国安理会负责,联合国大会也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1条和第14条决定或建议采取维和行动。第二,维和部队到底是大会的“附属机构”还是安理会的“附属机构”。前秘书长哈玛舍尔德在谈到联大决议建立第一支紧急部队的法律依据时说,该部队是作为联合国大会的“附属机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2条建立的。该条规定:“大会得设立其认为于行使职务所必须之辅助机关”。然而,早在1949年联合国安理会就把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纳入自己的权力之下,作为持久性“附属机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立即建立了停战委员会,委派出了调解专员和观察员,合称联合国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1949年2月安理会经与调解专员协商后, 将其作为自己权力下的持久性附属机构)。这就是说,两种说法都有其理由。
实际上,这些争论本身并未涉及到维和行动的法律问题的根本方面。在前一个问题上的争论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有关国家转变态度暂告平息。但它只解决了大会与安理会在建立维和行动的职权上的分歧问题,并没有说明采取维和行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在第二个问题上无论是把维和部队纳入大会的“辅助机构”,还是置于联合国安理会的“附属机构”的位置,都不能说明维和行动有宪章上的根据。宪章中没有明确的关于维和行动的条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原则和精神,又确实为维和行动这样的创举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宪章第1条所列宗旨第一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具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及其他对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争端或情势。”
只要留心联合国维和行动实践的主要方面,就不难发现,维和行动与宪章的这一宗旨是一致的,可以说宪章的这一条,就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依据。为说明此点,有必要对维和行动本身作一些探讨。
到底什么是维和行动,虽然迄今尚无可被各方接受的统一的定义,但从传统维和行动的实践来看,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1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有关当事方请求或同意的前提下由安理会或大会决定采取的中立的具体安全行动;(2 )是使用军事人员(包括少量文职人员)但不使用武力(仅限于自卫)的行动;仅以其在冲突地区的存在来防止、遏制、缓和、终止国际的或国家内部的敌对行动;(3 )是在冲突中止停火期间帮助恢复秩序、维持“现状”或协助履行有关临时决议,为冲突之和平解决创造气氛和条件的行动。所以,从实质上看,维和行动仍然是一种解决争端的和平方式,是未列入宪章第六章的和平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和平加威慑”的方式。这是避免根据第七章规定的办法解决争端的有效途径。是对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宗旨的创造性实践。
再从维和行动在实践中形成和遵循的指导原则来看,维和行动也充分体现了宪章所确认的正义及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是:
1、同意和非强制原则。首先,不但维和行动的建立、 维和部队和观察团(组)的派遣,都必须以当事方的同意或请求为前提,而且继续驻扎也必须有关各方的同意和配合。如1967年5月16日, 埃及政府决定终止联合国第一支紧急部队在埃及的驻扎;秘书长又未能说服以色列让其改驻埃以边界以防不测,于是该部队只得全部撤离。其次,派出官兵和观察员参与维和行动也必须会员国自愿。第三,维和部队若要落实某种解决方案也必须由当事各方同意,而不能强加于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关于当事国主权平等,领土完整等原则。
2、中立和公正原则。 维和部队(或观察团)必须严守中立公正原则,不介入冲突,不偏袒任何一方,以维护联合国的声誉,赢得当事各方对联合国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常履行其维和使命,有效地监督停火停战,协助恢复或维持和平。
3、限制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原则。 维和行动是“维和”而不是“造和”(Peacemaking),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强制的和平手段, 因而对使用武力作了严格的限制。根据有关的指导原则,维和部队只能佩带轻武器用于自卫,维和部队及其官兵只有在“遭到攻击”,或履行职责“受到武力阻碍”时,才可使用“最低”的武力。为此,联合国维和官兵被称为特殊的军人,用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说,他们“无战斗之敌,无战胜之地,武器用于自卫,效果靠自愿合作”。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精神创造出来的一种解决争端和冲突的“和平加威慑”手段。只不过这种“威慑”不是来自维和部队或观察团(组)的规模及其装备本身,而是来自于他们身后的巨人——联合国,来自于联合国的权威和道义的力量,来自于世界和平舆论的力量。
由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和平和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国于1988年9月22日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和特委会, 积极而有选择地参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二、冷战后维和行动的蜕变和问题
冷战结束,热战烽起,为联合国更加积极地采取维和行动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停滞了十年(1978—1987年)之后,于1988年开始迅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冷战后的维和行动在某些方面突破了“维和”的界限,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数量多、规模大、使命复杂化。
1988年以来, 联合国授权采取的维和行动达20 项, 仅1992 年—1993两年就建立10项,目前大部分仍在实施中。在世界各地执行维和任务的人员逾七万,1994年维和行动耗资34亿美元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维和使命日趋复杂,维和行动已不再限于在冲突地区起隔离、缓冲和监督停火、撤军的作用,从解除、收缴帮派武装、扫雷、清理战场到核查、监督选举,调查侵犯人权状况、安排、护送、分发救济物资等等,几乎无所不及。如前南斯拉夫“联保部队”的使命极为复杂,概括起来有四大类:(1)保护责任,包括保护“禁飞区”、“安全区”、 “保护区”等。(2)监督责任,包括监督停火、撤军、重武器、 粉红区(原南斯拉夫人民军占领区)和人权。(3)禁运和制裁责任, 包括对冲突各方的武器禁运,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制裁、封锁、扣押物资等。 (4)救援责任,包括救援难民和伤病员。在柬埔寨甚至建立了联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代行其部分国家权力,负责监督越军撤离,收缴各派武器,遣返难民和组织大选等项任务,其中一部分纯属柬国内事务。
2、部分维和行动突破了传统原则,维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新时期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多数遵守了传统的维和行动的指导原则,如1988年4 月派出监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联合国阿巴斡旋团,1988年8月派出的驻两伊军事观察团, 后来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等,都没有逾越过去一直奉行的指导原则。但是确有一些维和行动突破了传统原则,而带有明显的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执行和平”的色彩。
首先,不再限于同意。联合国“伊科观察团”并未征得伊拉克同意。在索马里,无论是美国等搞的“联合特遣行动”,还是第二期“联索行动”都受到冲突中某一方的反对和抵制。波黑塞族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也采取了更加抵触的态度。但是联合国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些问题,在索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坚持驻满了任期;在波黑联合国亦尚未认真考虑撤出维和部队问题。
其次,不再严守中立。在索马里和波黑,维和部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其内部冲突,打一派、保一派,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的现象时有发生。1993年下半年,美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缉拿、搜捕艾迪德(联合大会党主席),多次同艾派武装发生冲突,轰炸艾派驻地,甚至发展到向示威平民开枪,造成成百无辜平民伤亡。1994年2月5日,萨拉热窝市露天市场遭到炮弹袭击,造成数百无辜平民伤亡。加利秘书长竟于次日绕过安理会,致函北约秘书长韦尔纳,请求对塞族阵地发动空袭;而炮击事件到底是何方所为,至今仍是一个谜。1995年4月30日, 波黑冲突各方4个月的停火期满,战事升温,局势恶化,在此情况下, 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冲突各方在限期内交还从维和部队武器存放点抢走的重武器,但无任何一方理睬。秘书长却因拗不过美国的压力而请求北约于5月25日、26日两次轰炸塞族阵地,致使塞族将联合国378名维和官兵和观察员扣作人质(塞族称其为俘虏,因为他们认为联合国站到了他们的敌人一边),并废除其同联合国达成的所有协议。这种同有关冲突方对抗的行动,是与维和行动的初衷相矛盾的。最近英国前外相欧文辞去了欧盟波黑冲突调解人之职,并对美国的波黑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表达了他对联合国未能严守中立的强烈不满。
三是武力使用不再限于自卫。有偏袒,必有不平,而维和官兵受到攻击或被扣作人质就在所难免。再则,维和官兵执行诸如强制收缴武器、缉捕冲突中的派别头目,实施安全保护、封锁、制裁等项任务,也不可避免地要动武。这样武力的使用便大大超出了自卫的限度。如最近在波黑的维和士兵和塞族士兵就因争夺据点、武器库而多次发生交火,致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3、做法不同,效果各异。
1988年以来实施中的维和行动20多项,除了索马里和波黑以外,效果一般都比较好。如1988年到1991年建立的10项维和行动,包括阿巴斡旋团,两伊军事观察团,安哥拉一、二期核查团,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中美洲观察团等,它们分布在中亚、南部非洲、海湾和中美洲等传统热点地区协助有关冲突各方履行和平协议,监督撤离,核查选举,大多到1992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为结束旷日持久的南部非洲冲突,中美洲危机和两伊战争遗留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些在新的热点地区实施的以平抑国内冲突为主的维和项目,虽未结束使命,但大多局势得到控制,总的情况趋于好转。相反,在索马里和波黑的情况却很糟。索马里的美军撤出以后局势才开始好转,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以后局势进一步缓和。目前问题虽未最终解决,但冲突已经基本平息。波黑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最近战事恶化,和平遥遥无期。人质危机发生后,法、美迅速加强了在亚德里亚海的海军力量。北约以英法为主组建10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 已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正准备派往波黑;美国也在考虑派出地面部队,其使命尚未确定,是更深地卷入还是协助撤出维和部队,还有待于局势的发展。
索、波行动虽也称为“维和行动”,但却在很多方面背离了传统维和行动所遵循的原则,再加上冲突本身的复杂性,所以维和效果极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维合声誉因此大受损害,其维和能力亦受到怀疑。
三、完善立法,确保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效
几十年维和实践经验证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维持国际和平,保障世界安全的手段。但是由于近年发展过快,盲目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强制维和,出现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在适用宪章第七章方面产生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新问题。
由于宪章第七章本身的不完善,如对强制执行和平行动的规定不甚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等,加之冷战阴魂不散,大国利益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很难有效地运用宪章第七章授予的权力来实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在大国不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下,轻易决定动用武力“执行和平”是十分危险的。如波黑的局势因国际社会的过多干涉而趋于复杂,就很能说明问题。美、英、法、德、俄立场各不相同,美国同德国在希图削弱塞族方面利益一致,但美又不愿德在巴尔干坐大;英、法则希望保持巴尔干力量的均衡;俄罗斯更不愿其斯拉夫兄弟被过分削弱。大国在波黑的明争暗斗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混淆在一起岂有不使问题复杂之理!
联合国能否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维和行动”是否成功。而维和行动的前景如何,又将取决于能否解决好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当然还有诸如经费等其他问题)。
1、严格区分“维持和平行动”与“执行和平行动”的界限。 对于前者,应积极稳妥地对待,坚持和平为主,威慑为辅,使其不断完善,更好地服务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于后者,应该慎重周全,严格按照宪章第七章办事,应该做到慎重决策,战则速胜。维持和平行动可以旷日持久,如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四十多年过去了还在执行任务,也无人有怨言。但“执行和平行动”却必须快刀斩乱麻,作出动武的决定时就必须有把握、有能力,迅速制止冲突,结束战争,为最终实现和平创造条件。否则,联合国将泥脚深陷,置身于冲突的旋涡而不能自拔。
2、严格区分联合国维和与非联合国维和。 对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维和行动,联合国可给予指导和一定的支持,甚至授权,但不宜直接卷入,其责任经费等也应由区域性国际组织自己承担。对于个别国家或国际军事集团的维和(干预)行动,联合国应与之保持距离,在必要时还应以决议的形式加以制止。绝不可与之搅和在一起,不可将“联合国”旗号假人。如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在索马里实施“恢复希望行动”,实际却是希望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惹出麻烦以后,却让联合国去收拾残局。又如在波黑,从形式上看,联合国假北约之武力实施制裁、空中打击等项任务,而实际上却是北约假联合国旗号以贯彻自己在波黑的意图。北约轰炸塞族,联合国和官兵遭报复,这种联合国“代人受过”的现象应全力避免。
3、完善立法和维和机制,确立维和准则, 明确有关各方权利义务关系。虽然维和行动是基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但是宪章并无有关的概念及其具体实施的原则,迄今所遵循的仍是实践中形成的不成文准则,因而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要使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具权威性和法律效力,完善立法,制定实施维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和指导原则,用法律形式明确决定、参与、接受维和行动的有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武力行动的决定权在安理会;安理会不能推诿,其他机构和个人也不能越俎代庖。象最近在波黑的做法,就很不正常。美国要秘书长邀请北约轰炸塞族阵地;秘书长请求安理会讨论,安理会却说这是秘书长的事。结果在美国总统、副总统,大使等通过电话或拜访做“工作”之后,秘书长决定“邀请”北约于今年5月25 日、26日两次对塞族实施空中打击,引出了一场空前的联合国人质危机。联合国维和机制的这种缺陷,给了大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横加干涉的可乘之机。为避免这种现象,通过立法明确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秘书长在维和行动中的职责、权限、义务,做到分工配合,互相制约,是非常必要的。
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四十余载,其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完善。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执行和平”、冲突后“缔造和平”等行动,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引起的问题,应予高度重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的和法律的手段应该永远是解决争端的冲突的主要手段。
标签:联合国宪章论文;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论文; 波黑论文; 联合国秘书长论文; 国际法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