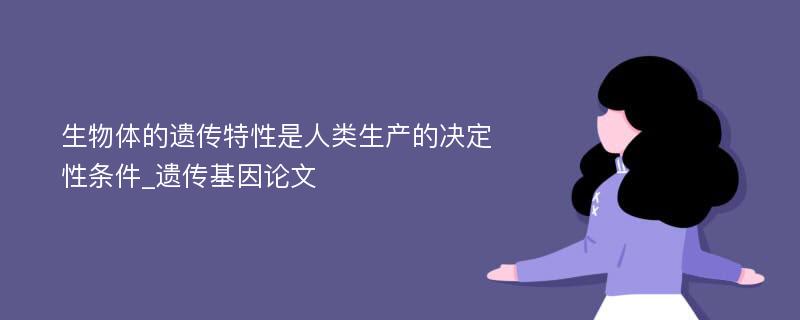
生物的遗传特征是人类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性论文,特征论文,条件论文,生物论文,是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说简单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在复杂的东西之前存在,但它只有在复杂的形式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开。低级的动物虽然可能包含有高级动物的征兆,但它只有在高级动物中才能得到理解。所以“人体解剖”,是理解“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二十世纪的后50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鼎盛年代。社会生产、科学技术以及其它的社会形式,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的社会本质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在这种条件下,再回过头来看人猿分化这一古老的命题,从中找出从猿向人发展的轨迹,有些地方就比较容易看得清了。特别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分子遗传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为揭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捷径。
一、人类产生的决定性的条件
所谓从分子遗传学角度考虑问题,就是在考察生物种属的生存与发展时,要看到它的生物的遗传特征,归根结底是由它的生物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决定的。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决定核糖核酸片断(RNA)。核糖核酸片断(RNA),决定蛋白质氨基酸的合成,从而决定生物的遗传特征,这是一般生物种属遗传与变异的总的趋势。
既然一切生物种属的变异都是通过生物的遗传基因的变异进行的,所以人类作为动物中的一个类,也不能例外。只是在从猿向人类过渡,与一般生物种属过渡不同的地方在于,通过猿体的内在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和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结构的变异, 所引起的猿体的变异不是随意的一种变异,而是在猿体的大脑皮质上形成人的理性思维的生理机制的部位,如在大脑的后区形成下顶区,在大脑的前区形成前额区等。正是这些先天的生理的机能部位,在与后天的社会劳动等条件相结合,在后天的社会劳动、语言等条件的刺激、激活、诱发下,使它转化为人的实际的理性思维能力,从而使猿转化为人。不过,如果将先天和后天进行综合的比较,显然前者更为根本。因为如果没有前者,其他的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说通过遗传基因的变异,引起的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是人类产生的决定性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中得到证明。
二、当代分子遗传学的证明
从分子遗传学出发考虑问题,就是从生物的内在遗传基因出发考虑问题。所谓生物的内在的遗传基因,就是指在生物染色体上,排列着的一个遗传的基本单位。这个遗传的基本单位是一个高分子化合物,它的化学结构是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 一个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决定一个或几个生物的遗传特征, 或几个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决定一个生物的遗传特征。
所谓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 是由两条多核苷酸长链组成的。每条长链都是由一个脱氧核糖分子与一个磷酸分子相间,在二酯键的作用下组成的,居于外侧。由每条长链上的脱氧核糖分子,经由羟基所携带的含氮有机碱基,在氢键的作用下,与对方链上的含氮碱基相联结组成横板,居于里侧。由于两条长链上所携带的含氮有机碱基共有四种,即腺嘌呤(A)与鸟嘌呤(G)、胞嘧啶(C)与胸腺嘧啶(T)。而在这四种含氮的有机碱基在对接时,又必须是按互补的原则进行。即腺嘌呤(A)必须是与胸腺嘧啶(T)、鸟嘌呤(G )必须是与胞嘧啶(C)相联结。这样在氢键和芳香环间疏水引力等因素的作用下, 就会使两条方向相反的多脱氧核苷酸长链,以一个中心轴为圆心做右手旋转的盘绕,形成一个双螺旋的结构。生物的遗传信息,就存在于这个双螺旋结构的碱基的序列中。
虽然生物种属的遗传特征,是由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 )决定的。但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却不直接决定蛋白质氨基酸的合成。 直接决定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的,是核糖核酸(RNA)。核糖核酸(RNA)也是核酸的一种形式,它与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的不同只在于,构成它的是核糖分子,而不是脱氧核糖分子。在四个含氮有机碱基中,胸腺嘧啶(T)被尿嘧啶(U)代替了。
在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以核糖核酸(RNA)为中介,指导蛋白质氨基酸合成时,核糖核酸(RNA)主要是采取三种形式。1、进入细胞核的RNA核苷酸,以DNA的碱基序列为模板,把DNA 结构中的遗传信息转录于自身,形成信使RNA(mRNA)。2、核糖体RNA(rRNA), 与核糖体蛋白质结合形成核糖体。核糖体是信使RNA(mRNA )展开的支架与合成蛋白质的场所。3、依赖于转运RNA(tRNA),把信使RNA(mRNA )的核苷酸的碱基序列顺序,转化为氨基酸的顺序,这时蛋白质就合成了。而在这整个从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经由核糖核酸(RNA)为中介,达到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的过程,通常就被称为DNA→RNA→蛋白质的中心法则。
固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在上述的基础上,又发现了RNA 的反转录过程和反转录酶的出现,在原核生物系统和真核生物系统中对调控基因系统的发现,以及对异染色质中的重复性的DNA结构的发现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生物的内在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 )决定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的这一基本趋向。还没有出现由蛋白质氨基酸决定脱氧核糖核酸的相反过程。因此所有这些发现,只是把这一研究的趋向变的更加深化、更加丰富罢了。
从上述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既然一切生物种属的生理遗传特征,都是由生物内在的遗传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决定的。那么像拉马克那种离开生物种属内在遗传基因的遗传与变异,认为即使是单纯在后天获得的生理特征,也是可以遗传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相反的倒是,如果从生物遗传基因的观点出发,又考虑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就是更符合客观实际的了。这就是只有通过生物种属的内在遗传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引起生物种属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的变化,以及这种生物种属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的变化,又是符合外在环境的要求,并能得到外在环境支持的,这种生物种属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否则它只有遭到大自然的淘汰。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生物种属的内在遗传基因的变异与外在环境要求的一致。
既然一切生物种属的变异都是通过生物种属的内在遗传基因的遗传与变异进行的,那么作为人是动物界中的一个类,它在从猿向人类过渡时,自然也不能例外。在这里与一般动物进化不同的只是,它通过猿体内在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 和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结构的变异,不是引起一般的生理特征的变化,而是引起在大脑皮质上生成了人的理性思维的生理机制的部位。如在大脑后区形成了下顶区,在大脑前区形成了前额区等。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它能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中,高于其它物种并战胜其它物种,而不为大自然所淘汰。
固然由于这一过渡年代发生的过于久远,以现代的科技条件还难以从直接材料上得到证明。但从间接的材料上,仍然可以看到一斑。如首先从当代人类与大猿类如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等,在有关生理遗传基因方面的异同,既可以看出它们是同源的,又可以看出以后的各自发展。从而表明人类与古猿类是同源的。人类是通过猿体内在遗传基因的变异从古猿发展来的。最常见的材料,首先是当代人类与大猿类在染色体数量上是最接近的,两者只有一对之差。如人类是23对,黑猩猩是24对,长臂猿是22对。其次两者在DNA结构上也是最近似的, 如通过非重复性的DNA 片断进行杂交实验可以看出人与黑猩猩在碱基序列的差异率只有2.5%,与长臂猿为5.3%,与非洲狐猴则为42%。差异率越小,血缘关系越近。最近还有材料表明,在异染色质的重复性DNA 片断上,两者也是近似的。如在9号染色体C带上的随体Ⅲ号,就是人与黑猩猩、大猩猩、猩猩所共有的。只是随体Ⅰ、Ⅱ、Ⅳ号DNA片断, 是人独有的。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近似,就决定了两者在蛋白质氨基酸的合成结构上,也是最近似的。如人与黑猩猩在由104 个氨基酸组成的细胞色素C上,和在由574个氨基酸组成的血红蛋白上就是等同的。
当然通过上述材料还仅仅是说明,人类是通过遗传基因的变异从古猿类发展来的。但它还不能说明这种遗传基因的变异,一定会在猿的大脑皮质上产生人的理性思维的生理机制。现代的科技条件也无力证实这一点。虽然是这样,但从当代对双生儿智力的形成,和对先天性智力病变或缺乏的研究中,却可以从间接上看到这种关系。
如从传统的对双生儿的智力研究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卵双生儿(MZ)智商(IQ)的一致性,总是要高于异卵双生儿(DZ)智商(IQ)的一致性。同样无论是就同卵双生儿(MZ),还是就异卵双生儿(DZ),它们与生父母的智商(IQ)的一致性,也总是要高于它们与养父母智商(IQ)的一致性。同样即使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生双生儿智商(IQ)的一致性,也要高于同养双生儿智商(IQ)的一致性等等。很明显所有这些智商(IQ)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都是来自于两者遗传基础的相同与不同。
同样,从对先天性智力病变或缺乏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现有的临床材料表明,凡属先天性智力病变或缺乏的患者,除去少数是由于胎儿在母体受创伤造成者外,余下的全与遗传基因的失常有关。如先天愚型道恩综合症,就是由于染色体出现畸型,形成三体型21(47+21),破坏了遗传基因的比例关系造成的。除此以外,多数的患者则是由于单个或多个遗传基因发生病变,引起先天性代谢失常造成的。
总之,虽然从目前条件还难以确定遗传基因定位与理性思维生理机制形成的关系,但是从上述材料中却可以看到,在人的理性思维的生理机制的形成上,与内在的生理遗传基因间有着一条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说通过当代分子遗传学的发展,所揭示的通过猿体内在遗传基因的变异,引起人的理性思维生理机制的产生,是实现由猿向人类过渡的决定性的条件。而这一总的轨迹,又由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发展,使它显得更加清晰了。
三、当代考古发掘的证明
在当代的考古发掘中,有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通过在东非和南非的发掘表明,在更新世早期即时间是从三百万年前到一百万年前这段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在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出现的时候,同时也出现了南猿的两个种属,即南猿的纤细种(也被称为南猿的非洲种)和南猿的粗壮种(也被称为南猿的包氏种)。这三者共同生存了有二百万年之久,在一百万前南猿的两个种属相继消失了,唯有早期人类后来又向前发展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和南猿的两个种属,都是从三千万年前的渐新世的古猿发展来的。在三千万年前的渐新世里,从猿猴分化开始,猿类为了适应在林间的“臂行”和长时间直立的需要,它就通过猿体内在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 和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结构的变异,使包括胸腔和内脏排列的序列在内的猿体结构,越来越向竖式发展了。后来又为了适应从两千万年前中新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空旷的干旱草原和广阔的林间地带的出现,古猿类通过猿体内在生理因素的变化,又使猿体越来越向着下到地面上生活的方向发展了,开始了人猿分化的过程。
虽然至今人们对这一分化年代的认识还不一致,但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最迟不超过从上新世到更新世早期的这一段时间,时间是在从五百万年前到三百万年前这段时间里。原来从中新世开始下到地面上生活的一支猿类,发展成为南猿的阿法种。南猿的阿法种是一个较古老的种属,它的身高只有一米多一点,体型细小,头骨与牙齿较原始,但它的手足比较灵活,已经用两足行走,能够下到地面上生活了。
正是这个南猿的阿法种,有可能在从五百万年前到三百万年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为了适应外在环境变化的需要,通过体内遗传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片断(DNA),和蛋白质氨基酸合成结构的变异, 使自己向前分别发展成为一科两属两种。即属于人科的人属的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和属于猿属的南猿的纤细种和粗壮种。南猿粗壮种是从南猿纤细种发展来的,是向着与人类方向相反发展的一个类。
但是到三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时,不管这些属于一科二属二种的动物,在一些具体特征上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如南猿纤细种的身高有1.2—1.3米左右,体重在60—70磅之间。南猿粗壮种的身高可达1.5 米左右,体重在130—150磅之间。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与南猿纤细种相似),但到这时属于这一科二属二种的动物,已经普遍达到下列特征;如由于牙齿的普遍变小,齿隙的消失,齿弓呈抛物线状,使它们的牙齿普遍具有咬切与磨嚼的功能;由于枕骨大孔位于头骨中央、髋骨与髂骨板变的短而宽,股骨向斜内发展,小腿的胫骨垂直,使得三者到这时都能用双足直立行走,只是不如现代人那样稳健;由于手足的进一步分工,与掌骨相联的拇指与其它指骨已能分开,并有对握能力,三者到这时都已经能利用天然工具了。一句话,手足的进一步分工,下肢已能直立行走,上肢已能利用天然工具,是一科二属二种动物发展到这时的普遍特征。那么又是在什么生理特征上的不同,能够使三者在一百万年前发生分化,使南猿两个种属消失,使人类得以发展下来呢?
这个在一百万年前使三者发生分化的生理特征,就是三者在脑容量上的不同。在南猿阿法种通过猿体内在遗传基因变异,向一科二种二属发展时,由于变异的方向和程度的不同,使三者在脑容量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如以当代的矮小黑猩猩的体重与脑容量的比例关系来推测,在上新世出现的南猿阿法种的脑容量,不会超过300立厘米。 而南猿纤细种的脑容量为450立厘米,粗壮种的脑容量为500立厘米(躯体较大)。而与南猿纤细种体型相类似,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的脑容量则为650立厘米,几乎超过南猿阿法种脑容量的一倍多。 如以单个能人的脑容量来估算,超过的数量可能还要多。如以O·H7 号能人的头骨片估计,它的脑容量可达到673.5—680.8立厘米。以ER1470号能人的头骨估算,它的脑容量为770—775立厘米。据说ER1590号能人的脑容量为750 立厘米,而有的能人的脑容量比它还要大的多。此后早期人类的脑容量更进一步发展了,到更新世早期和更新世中期,如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已达1,000立厘米左右。
可见在三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通过猿体内在生理遗传基因的变异,所引起的脑容量的不同,是南猿两个种属与早期人类的根本不同点。正是这个不同点,导致南猿的两个种属与早期人类发生分化。南猿两个种属在一百万年前消失了,而人类向前发展了。何以通过猿体内在生理遗传基因的变异所引起的脑容量的差异,会在人猿发展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这是因为:
第一,人体脑容量的增长,并不单纯是脑容量的问题,而是反映大脑皮质增殖的问题。古生物学提供的资料表明,动物脑结构的进化并不是采取简单地消失某部分或增加某部分实现的,而是在旧结构的周围增加新结构,并以新结构支配旧结构的方式进行的。如在远古的鱼类,主要是古老的中脑较发达。而在进入高等爬虫类和哺乳类之后,在中脑周围的边缘系统发展起来的同时,在大脑的其它部分上又覆盖了一层新皮质。而在进入人类之后,在人的大脑皮质层上,又增扩了下顶区和前额区等。正是如此,通过对脑铸模的研究表明,在南猿纤细种的大脑皮质上的顶叶已明显地扩大了。可是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人类的顶叶,比南猿扩大的还要多。有材料表明能人大脑皮质的下顶区,比南猿的下顶区要扩大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与人脑容量相联系的大脑皮质的增长,不是随便的一种增长,它是与人的理性思维生理机制部位的增长相关。如在大脑皮质上,出现了下顶区与前额区等。而在人体大脑皮质上有了这个部位,就可能使人体形成理性思维能力,从而使人体从利用天然工具,发展成为能够制造人工工具。正是因为这样,凡是在有人脑容量增长材料出土的地方,都会有人工工具出土的现象,二者是同步的。如在奥杜威峡谷底层出土O·H7号能人头骨的地方,在库彼福勒地区出土ER1470号和ER1590 号能人头骨的地方,都同时或在相近年代的土层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工具。此外像在哈达尔地区出土AL199—1号等能人头骨材料的地方,在司特克方丹出土能人牙齿的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人的理性思维的生理机制部位、人工工具的出现与人的脑容积增长的出现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人脑容积的显著增长,意味着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和人工工具的出现,它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人体脑容量的增长,又是和在人的大脑皮质上出现像布罗卡、威尔尼克等语言区有关。现代科技表明,人类语言的出现,首先是和在人的大脑皮质上出现语言区有关。如果在大脑皮质上没有语言区出现,既使像鹦鹉那样有类似人声音的发音器官,也不能形成语言能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人的大脑两半球上,会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语言区出现在优势半球上。这从霍洛韦的有关古人类脑铸模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依据他的研究表明,早在ER1470号能人头骨的内壁上,就已经有布罗卡区隆起的痕迹了。
当然这还只是就一般语言产生的条件来说的,如果不是这样,单就有音节语言出现的条件来说,除去要具备上述条件外,它还需要具备下列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要通过遗传基因的变异,使喉下移、声韧带陷入喉腔内、声带角变的越来越小,颏棘变的越来越大、颌骨后缩、舌头越来越灵活等等。从现有出土材料来看,这些条件的出现,最快也要在二、三十万年前的古人时期才会有萌芽出现。在五万年前的新人时期,这些条件才会成熟。可见人、人的理性思维的生理机制,与表达人的理性思维的最佳形式,即有音节语言的出现不是同步的,两者相差可能有二百万年之久。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人类出现的近三百万年的时间里,有二百九十九万年的时间,始终是处于旧石器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说是蹒跚而行。可是一当进入古人时期,人类开始出现表达理性思维的最佳形式,即音节语言。由于理性思维有了最有效的表现形式,从而使人类的社会生产也加快了发展步伐。在不到二十万年的时间里,就从旧石器过渡到中新石器时期。在不到一万年的现代人的时期里,使人类的社会历史经历了从中新石器、金石并用、青铜、铁器、手工业、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几个时代。从文字与青铜铁器、从现代科技与现代化生产出现之后,人类的社会生产更是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所有这一切的出现,又都是和通过猿体内在生理遗传基因的变异,引起在人体大脑皮层上形成了理性思维及其表现形式的生理机制部位相关。如果没有这一点,则上述一切就不会出现。
总之,无论是就当代分子遗传学提供的材料,还是就考古发掘提供的材料,它们都证明了通过猿体的内在生理遗传基因的变异,所引起的人的理性思维及其表现形式的形成与发展,无论是对人类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标签:遗传基因论文; 遗传变异论文; 大脑皮质论文; 大脑结构论文; 蛋白质结构论文; 蛋白质合成论文; 信使rna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