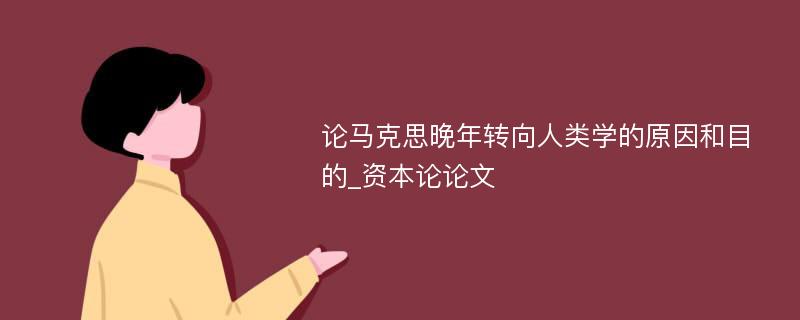
论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原因和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目的论文,人类学论文,晚年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 038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已为公认的事实,其中蕴含着的卓越思想已经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对于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的认识并未达到应有的一致。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期对马克思晚年研究方向转变的意义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一
探讨马克思晚年研究方向转变的原因和目的,某种意义上直接与了解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第2、3卷的原因有关。因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尽管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完成《资本论》第2、3卷的努力,但终究还是未能看到它的出版;相反,却在病魔缠身的艰难状况下写下了大量的人类学研究笔记。因此,马克思在最后十几年里未完成这部著作的原因就首先成为我们探究这一转变的原因和目的的焦点。
《资本论》第1卷发表后,马克思就积极工作, 尽一切可能加快《资本论》第2、3卷的写作。但迅速高涨的革命运动形势迫使他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理论工作,而投入到领导第一国际及随之而来的巴黎公社的实践中去。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欧洲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的形势,马克思打算“退出商业事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同时干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79页。)。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空暇回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上来。
马克思最初着手整理、修订《资本论》第2 卷手稿时非常注重研究爱尔兰、美国特别是俄国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其目的是为写作“地租”一篇准备材料,实现早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制定的分篇计划,即继《资本论》第1卷考察资本和雇佣劳动之后,在第2卷考察土地所有制及其与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为此,1869—1873年间,他在俄国友人帮助下,阅读了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以期“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49页。),从而使俄国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起到在第1卷中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典型作用。对此计划,恩格斯后来写道:“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1页。)。
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在整理《资本论》第2 卷手稿时恩格斯惊讶地发现,这部分手稿早在1864—1866年就写得“很完整”,在“地租”那一章中未看到有关俄国条件的任何论述,甚至恩格斯都不能确定马克思有关俄国土地关系资料的摘录是否有某些能够用于此卷的评注。
马克思花费数年心血专心致志地研究俄国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成果,竟没有被用于《资本论》的写作上来,当时就引起了资料的主要提供者丹尼尔逊的关注,他把1879—1881年间与马克思通信中马克思提出的有关《资本论》未能如期完成的理由,摘录后转给恩格斯,希望对恩格斯整理手稿的工作有所帮助。恩格斯读后认为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主要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使这一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而马克思提出的某些理论上的依据,不过是能使自己得到“宽慰”的理由。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判断是合乎实际的。1870年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中止了《资本论》的写作,“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页。)。直到1877年初, 他觉得自己的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遂于1877年10月—1878年7月做了整理出一个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第Ⅵ稿);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写出一个可以付印的手稿的尝试,是1878年2月写成的只有7页的Ⅶ稿。正是在这一工作期间,马克思意识到要是他的健康状况没有一种完全的革命,是连自己也不能满意地完成《资本论》的写作了,于是他决定抓紧时间对第2卷的材料进行全篇改造,匆忙写成逻辑不连贯、论述不完整的第Ⅷ稿,并希望恩格斯“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9页。)。1877年6月恩格斯就曾向读者预告“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可望不久就能付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0—121页。),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如期进行下去,因为“事实上,第Ⅴ—Ⅷ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8页。)。70年代末80年代初, 马克思与友人的通信反映出他一直被多种严重疾病所折磨。当1881年12月再次希望做一次完成《资本论》的尝试以献给他刚刚去世的妻子时,也首先考虑是花一些时间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8—239、252页。)。 在此情况下,完成《资本论》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直到1892年,对马克思健康状况非常了解的恩格斯仍然认定,马克思没有很好地利用研究俄国土地关系的材料以写作地租章节的主要原因,是“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
虽然如此,但并没有妨碍马克思“试着干点事”。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时说:“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 ) 。 正是在1870年后由于病况中止《资本论》写作的那段时间里,“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页。)。如前所述,关于俄国的土地关系就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他对巴黎公社失败后凸现出来的俄国革命问题的思考:“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这样, 最初为写作《资本论》中“地租”章节而进行的对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研究,就服从于为俄国革命指出一条现实的道路这个直接而迫切的目的,从此,马克思的“研究范围也已经大大扩大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
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状况密切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第一,唯物史观发展的需要。《资本论》第1 卷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实证材料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工人运动陷入低谷,东方的俄国革命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强劲势头。这时,俄国国内早就存在着的关于俄国社会命运的争论,则直接涉及到对《资本论》第1卷的理解及马克思本人的荣誉。因而, 如何能够把《资本论》第1卷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与俄国这个自1861年改革以来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非西欧国家的特殊现实结合起来,给俄国人民指出一条现实的发展道路,这个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的紧迫问题,就成为马克思慎重思考的中心。第二,指导俄国革命的需要。俄国革命是马克思早就关注的。50年代,马克思就把赫尔岑鼓吹的那种企图用俄国公社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论调,讥讽为“一种可笑的偏见”、“公民赫尔岑虚构的谎言”。由于“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3页。),因此, 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马克思一直试图通过论证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普遍性来批判这种俄国特殊论的错误。当他看到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述》、《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史》后兴奋地说:“这样,俄国人甚至在这方面要标榜其独创性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了。他们所保留的,即使在今天也只不过是老早就被他们的邻居抛弃了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页。)。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欧洲要通过俄国,而是俄国要通过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解放,所以当有人宣称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状况的原因时,马克思尽管认为是错误的,但还是说这“无论如何是应当加以利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38页。)。然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理论总是服从于革命实践。虽然他对农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但并没有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革命形势适时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给日益高涨的俄国革命以理论指导:在俄国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时,那种认为从农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对农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毕竟起了鼓舞革命者热情和毅力的作用。因此,虽然马克思认为没有义务跟这些人抱有同样的幻想,却对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持赞许态度。从促进革命运动发展的立场出发,就使马克思不能不重新审视以往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试图通过对之做更深入的了解,揭示出“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施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77页。) 的原因,从而指出一条符合俄国现实的革命道路。第三,如前所述,是写作《资本论》“地租”一篇的需要。
基于此,“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的基础上,于1877 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下简称《给“祖国纪事”的信》)中表达了对俄国社会前途和命运的基本看法。不言而喻,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有关“地租”的章节而研究的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与为了能够对俄国经济发展做出准确判断所研究的“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是同一种材料,其研究时期也是一致的。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在70年代研究俄国土地所有制问题不仅是为了写作《资本论》有关“地租”的章节,而且服从于一个更为自觉的目的,即为了对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对马克思的这一目的,恩格斯最初的认识也是不明确的。1885年当丹尼尔逊询问关于俄国经济问题的材料是否收入《资本论》第3卷时, 恩格斯也不能确信其中是否有某些能用于此卷的评注,直到1892年他才确认马克思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并在1894年《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个计划和目的。但无论如何,恩格斯并未否认写作《资本论》之外的其他目的,而且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详尽地谈到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信》的写作背景,可以说是对马克思这一目的的最好说明。
二
如果可以把《给“祖国纪事”的信》看作是马克思晚年思想转变的标志,那么,我们看到,这种转变过程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孕育。
还在1875年,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就对俄国公社所有制这一社会形式的前途,做出了与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信》及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中相似的结论。应当说,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观点是清楚的也是同意的,可是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又要多次表达自己的看法呢?这是否能够如有的论者那样理解为只是他对俄国革命者从道义上支持的一种策略呢?笔者认为不能。究其实质,这两封信虽然本身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毕竟是有差别的,是了解马克思晚年思想转变的原因和目的的关键,可以看作是标志着这一转变的两个不同阶段。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的信》是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而做出的被迫论战。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曲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增补中对赫尔岑的一句评语,武断地说马克思不同意可以在农村公社基础上过渡到新社会的看法,其实质是企图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完全机械的理解。由于对俄国社会的前途与命运的看法是与对《资本论》进一步说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相关的,因此马克思在信中对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做了直接了当的结论之后,转而论证这种可能发展的理论根据。他坚决反对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于一切民族,并以《资本论》中提到的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受到的命运为例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表述了一个自己即将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这就表明,经过若干年对俄国的专心致志的研究及已经初步得出的结论,使马克思确信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欧民族,在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会采取不同于西欧的形式。现在提到研究日程上的,就是揭示出这些民族非西欧式发展道路的历史与现实根据,以及如何才能使他们利用自己特有的形式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等等一系列的必然性。这样,由俄国问题而引发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道路与各地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关系这个事关唯物史观发展的重大问题,相应地就成为马克思关注的中心,这就更需要把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扩大,把理论的触角伸向人类历史的深处,转向古代社会的人类学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
如果说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信》只是提出了已经开始或正准备进行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那么,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则表明马克思运用该方法,沿着这条道路进行了数年的艰苦探索,因此可以把这封信看作是这一研究初步完成的标志。正是在1876—1881年这一期间,马克思研究了许多论述史前社会状况的著作和材料,其中主要有: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马克思对这些著作和材料作了详细的摘录,并评论了其中一些观点,形成我们看到的《人类学笔记》。从内容上看,《人类学笔记》着重探讨的是公社土地占有制、文明的起源、古代法制史、原始社会的结构、私有制的起源及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等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这显然是为写作一部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著作而准备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一目的在1881年3月最后一篇笔记写完、 研究告一段落、应查苏利奇请求他发表“你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7页。)时, 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中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在这封信中,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要回答这些问题,至少应该了解农村公社一连串的变化,但“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说明这一研究还未最终完成;另一方面,他对当时人类学对各种原始公社解体的历史“粗糙的描绘”感到不满,准备自己“加以阐述”、“撰述”,而且确信通过自己的研究,这种“撰述”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无论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展到足够证明下面两点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目的说得更明确:“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全部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页。)。
三
轻率地说马克思晚年由于转向人类学的研究而中断了《资本论》的写作是难以成立的;相反,否认这一研究的独立科学意义,得出它仅仅是为《资本论》的写作准备材料的结论也是片面的。本文研究表明,自70年代以来,为写作《资本论》有关“地租”的章节,马克思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状况的新认识,正可以被马克思用以为这一运动指出一条现实的道路,这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推动。为此,他在1877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跳进资本主义的泥潭中去。然而,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把唯物史观机械化、庸俗化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的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说自40年代唯物史观产生以来,对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更侧重于逻辑论证的话,那么,随着7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状况研究成果的发表,则为实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所以我们看到,尽管7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多次希望回到《资本论》第2、3卷的写作上来,但终究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著作,除了健康原因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确实深深地吸引着他——试图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马克思没有能够亲自实现这个目的,但这一未竟事业毕竟由恩格斯继承下来了。
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之于唯物史观的意义,正如恩格斯评论摩尔根的工作时说的那样:“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在这里,我们强调的还在于,马克思的这种继续研究也为理解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一现象找到了一把现实的钥匙。正是借助这把钥匙,马克思解开了东方社会之谜,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
收稿日期:1997—03—12
标签:资本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 地租理论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