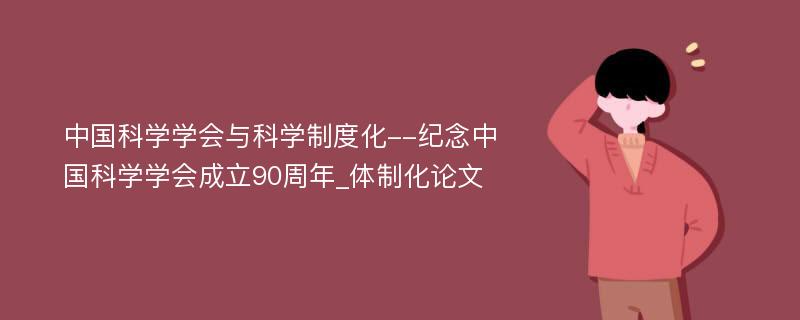
中国科学社与科学体制化——纪念中国科学社创办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社论文,国科论文,体制论文,周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科学体制化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科学体制化水平是衡量科学发展程度的尺度。因而科学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实现科学的体制化。所谓科学“体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就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近代科学的体制化包括三层含义:(1)社会接受科学活动的社会功能,科学活动因其自身的重要价值而受到全社会普遍尊重;(2)科学活动中存在一些特定的行为规范,科学家们在科学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交往、奖励乃至惩罚的行为规范,如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共有主义( Communism) 、无私利性( Disinterestedness)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Organized Skepticism) 等,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具有实现自身目标的自主性;(3)科学活动还必须同其他社会活动相互衔接、相互适应,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科学活动的社会规范。[1] 也即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大众所承认;科学有自己的操作规范和自主性;科学活动要与其他活动相互适应。
中国是否实现了科学体制化,如果实现了,又是在何时实现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中国科学体制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起步”[2],理由是1898年废除了科举制,兴办了西学,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完成了科学体制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标志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因为当时有了研究院所和研究经费;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科技至今也没有完成体制化,理由是中国科学未获得其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公有、普遍、无私利性、独创、怀疑主义的科学规范没有真正形成,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其实三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而要真正说明中国是否实现了科学体制化以及什么时间实现了体制化,我们只有从对体制化的认真分析中才能得出答案。在对西方的科学体制化和中国科学社(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的创立和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科学体制化,并且认为早在中国科学社的发展时期就已初步实现了科学体制化。
科学体制化是有关科学事务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进行科学交流的专业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交流会议的召开、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奖励机制以及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等诸多方面。而中国科学社在当时可以说满足了科学体制化的条件,虽然受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种种条件所限,这种体制化还不完备,但至少是初步实现了科学体制化,或者说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科学社是1915年10月25日留美青年学生胡明复、胡刚复、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周仁、秉志等人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正式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由任鸿隽担任社长,并于1918年迁回国内。历经四十多年,直至1960年才正式宣告解散。虽然它作为一个正式组织解散了,但它已融入中国现代科学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科学,尤其对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科学社是一个英美式的科学共同体,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在其影响下,科学共同体在20世纪20、30年代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科学团体达到42个之多,[3]成为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为科学的体制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成为体制化探索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建立则标志着体制化的正式形成,而在中央研究院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科学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科学社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群众性科学团体,一直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在它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直接推进了中国科技的体制化,造就了中国的早期科学家群,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到1924年,它的社员已达到648人,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建筑、机械、矿冶、医药、农林等学科的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据统计,至1949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已达3776人,[4]分布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各学科、各专业领域。从中我们足以看出它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学人才聚集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中国科学家成长和科学家群体壮大的摇篮,在中国科学体制化过程中,无论是科学家角色与科学家群体的形成还是学术社团的创建、科研机构的设立、科学交流体系的建成,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体制化的重要前提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基本上同步于科学体制化过程,它既是科学体制化的结果,又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方面。我们这里说的科学家与那些古代的所谓科学家即“偶然地”关心科学的人士有着显著的不同,以往那些偶然关心科学之士并未真正地进入这一科学社会学中所说的科学家“角色”。
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既是科学体制化的前提,同时它又有赖于科学的体制化。在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没有社会分工意义上的科学家角色,学者之间没有正规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学术交流和社会传播的渠道与平台,更不可能形成独立的职业共同体。在中国最早充当科学家这一角色的,是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科学社团的会员。之所以这样说,一是他们以现代科技为专业或职业。虽然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以科技为职业的近代科学家,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但他们主要是从事翻译和介绍西方科技或会通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工作,虽然具有一定的群体规模,但没有形成一定的团体,还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栖息之地;二是因为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活动是与科学体制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科学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科学之发达”,其组织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即除介绍科学之外,注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后,随着科学教育体系的全面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才真正形成。一旦形成了科学家角色,就有了组织实体和制度成为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的可能性。[5]
科技出版物是科学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W·迪克在评价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报》创刊的历史意义时所说:“从17世纪开始,定期刊物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说,如果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与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6] 中国科学社成立后发行了机关刊物《科学》,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宣传活动。《科学》创刊宗旨就是“科技救国”,它是现代中国科学建制完全确立之前第一份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份综合性科学刊物,是中国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科学》杂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吸引、团聚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据任鸿隽估算,从1915年到1950年作者不下千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是通过《科学》杂志的导引而逐步迈入科学研究殿堂,成为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人才。中国近代科学各门学科奠基时期的领袖人物大多在《科学》上发表过文章。而且中国科学社通过自身活动,对科学、科学研究、科学家特质的反复阐述和倡导,促成了中国科学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角色意识的形成。经过中国科学社和其他相应机构的大力提倡和传播,“科学”概念在中国已经生根,使区别于其他社会人群的“科学家角色”开始出现于现代中国社会,从而对中国科学体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进的大道。《科学》本身也大力呼吁建立科学建制。科学学会和科学期刊等社会建制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科学》创刊之始便成为一个不断强调的话题。在《科学》创刊期间,其主要创办人任鸿隽就在《留美学生季报》连续发表“建立学界论”、“建立学界再论”等文章,呼吁建立学术团体和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发刊“例言”第一条便是:“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故各国学界报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而当进学者之赖以交通智识者也。”[7]《科学》不仅大量传播科学知识,及时地将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新发现新成果介绍到国内,而且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强调科学的社会文化利用,呼吁创建中国的科学事业,寻求科学救国。在《科学》的发刊词中就提出了“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知识”。除《科学》外,中国科学社还陆续创办了《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科学译丛》等科技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使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为了宣传科学、推进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社还建立了图书馆——“明复图书馆”,1931年正式开馆,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传播和发展。
科学家的培养是科学组织机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基础性工作,科学教育是科学社会建制中的重要部分。中国科学社的大多数成员在大学任教,通过教学活动广泛地传播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了国人的科学素养,推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
在科研机构的创建上,中国科学社率先在中国建立起一批示范性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的科学体制化,促进了全国性、综合性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22年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科学研究机构。该所作为中国科学社弘扬科学、从事科学研究的实体,是中国科学社举办最为成功的事业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科研机构的典范。无论是在科研人才的培养、科研成果的产出,还是科研氛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塑造与传播方面,都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作为一个纯粹科研机构,通过科研成就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赢得了位置,与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互通关系,成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共同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
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中国科学交流系统体制化方面,中国科学社年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交流系统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缩影,从最初以交谊为主,发展到以科学交流为主,到抗战爆发前成为全国大部分科学精英的科学家盛会。中国科学社从成立后几乎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交流科学思想,其年会制度对中国科学交流体制化举足轻重。通过年会的召开,大大促进了科学的传播和交流。为了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交流,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社员论文专刊——《中国科学社年会论文汇集专刊》(1922年起发行),出版社员科学专著,有效地促进了科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科学社年会的逐年发展,数、理、化等学科也相继进入科学交流系统,到1936年形成了一个囊括数、理、化、生物、地质、地理、气象等多学科的全国性科学交流网络,成为各门科学的学术交流中枢。随着年会交流系统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各门科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为扩大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影响,加强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作了不少努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之间的纽带作用。为了加强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他们不但积极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而且邀请著名的学者讲课,通过科学社社员与国外学者的交往,吸引了一些在中国高校任教的外籍学者加入了科学社,这都有力地促进了科学交流。
科学奖励也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方面。科学奖励系统是使科学运转的基础性动力机制之一。奖励意味着对科研成果价值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断强化科学家创新性知识发现的价值,促使科学家继续从事科学的研究而不是转向其他的追求。科学的奖励系统一般包括两类:一类是荣誉性的奖励,通过同行科学家评价的程序,以颁发科学奖金和奖章等形式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或科学家给予奖励。另一类是承认,即通过“引证”别人的研究成果表示对该科学家的研究价值给予奖励(承认)。对于前者,往往通过建立奖励制度运作;对于后者,则是通过道德的规范维持的一种社会秩序。为了促进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引进了科学奖励机制,设立科学奖金,鼓励科学研究。其设立的科学奖金主要有以下几种:高君韦女士纪念奖、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纪念奖金、何吟莒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此外还设有生物学奖金、中国科学社科学研究奖章等。中国科学社所建立的科学奖励制度,由评奖委员会主持征文及审稿事宜,专家给予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评奖机制。科学奖励制度的设立将竞争机制引入科学,强化了科学活动的价值,有助于培养科学研究的兴趣,推进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
中国科学社在完善与促进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方面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改组后,就成立了具有专门学会雏形的分股委员会,打算发展成为囊括各专门学会的综合性社团。但是,分股委员会不仅没有完善建立起来,反而逐渐消失。这不仅使后来中国科学社向科学团体联合会的角色转换不能实现,也延缓了中国科学体制化在专门学会建设方面的进程。但无论如何,作为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母体,中国科学社对其他学术社团的成立和发展都起着指导或榜样的作用。以留日学生为主的中华学艺社在后来的社章修改过程中借鉴了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的很多地方。其他综合性社团如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技术协会等在组织结构上都借鉴了中国科学社的经验。各专门学会在组织结构上更是基本上参照中国科学社的社章,基本遵循中国科学社的组织形式:即制定了指导性文件“社章”,规定了各类成员的专业标准及其权利与义务;设置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等机构,并规定了领导成员的职权范围及其任期,重大决策需要由理事会等议决后在年会社员大会上通过;创办自己的专门会刊,发行专业论文或进行该专业的普及工作,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专门科研机构的成立,都有中国科学社成员的一份功劳。中央研究院虽然是蔡元培借鉴德、法国家科学院模式建立的,但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中国科学社的背景,并且大多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因此中央研究院在筹备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不受到中国科学社的重大影响。这样,无论是从进行科学研究到呼吁创建各类专门研究机构,还是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中国科学社对中国专门科研机构的体制化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皇家学会体制,另一种是法国皇家科学院体制,樊洪业作为研究科学体制化的权威人士,曾对这两种体制化模式进行了对比,[8]他认为,英国皇家学会没有实体研究机构,会员分散在学校、企业或者私人实验室内进行研究工作。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会员定期讨论并创办刊物进行交流,活动经费来自会员交纳的会费,不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支持,其活动是充分自主的。而法国皇家科学院则是实体性研究机构,主持人由国王任命。受聘院士领取皇家津贴,研究活动的自由程度取决于支持人的开明程度。中国科学社是模仿英国皇家学会而建立的一种体制。它“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即除了介绍科学之外,它着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9]具体表现在,中国科学社的活动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主要靠会费和社员的募捐,政府的资助很少;中国科学社尚未完全达到职业化水平。科学团体内部很分散,各团体间的联系也不紧密,尚未形成一个整体,不能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沟通,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各团体作用的发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科学体制化中的比较明显的英国科学体制化特征。
科学的体制化实际上是科学活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并成为社会整体的一个子系统而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互动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科学活动是在社会系统中展开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进入到“大科学时代”,科学同社会的关系就更加紧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与思想运动为科学的体制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氛围,近代前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在动荡的学术环境中,中国科学社排除各种社会干扰,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科学体制化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群众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一经成立便致力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科学本土化的探索以及规模宏大的科研机构设置计划,在四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直接推进了中国的科技体制化进程,对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动了中国各科学学会组织的创立与进展,培养造就了中国现代的科学家队伍,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类似于英国17世纪皇家学会创办时期的历史作用。
中国科学社在其存在的近半个世纪里,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它的大多计划都流产了,它的角色转换没有取得成功,除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外,中国科学社未能完全实现职业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职业化是体制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而中国科学社领导层及各部职员,包括其下设生物研究所职员多为义务兼职。而学会达不到职业化,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建制而长期存在。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科学化的体制化程度还比较低,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科学社的创办和发展确实堪称中国初步实现科学体制化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