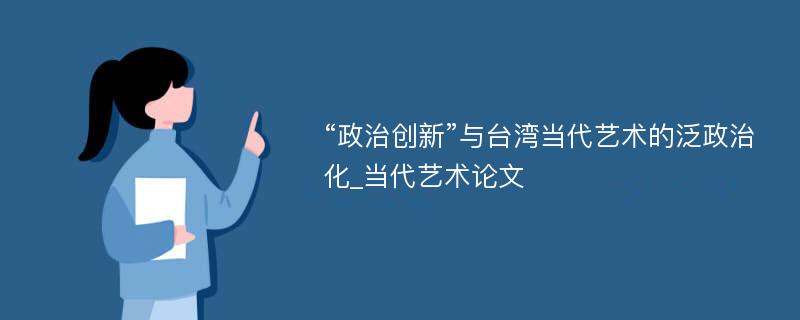
“政治革新”与台湾当代美术的泛政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台湾论文,当代论文,美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5-0102-04
一、政治权威的弱化与崩解
社会、文化的变迁与政治的变革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台湾当代美术的兴起是在台湾政治变革前后,这并非时间的巧合,而是两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台湾当代美术发展颇为独特的地方。国民党渡台之后,台湾处在严酷的政治管制之下,思想控制十分严厉。蒋经国掌握大权之后,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采取“革新保台”的措施。这一措施一方面给他的顺利接班扫清道路,也为未来的政治变动埋下伏笔。时隔不久,党外人士在1980年国民党重新恢复选举之际,又死灰复燃。重新兴起的党外势力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杂志等媒体来进行鼓噪,而是进行实际的政党组织。1986年仓促成立的民进党即是此种产物。“民进党的成立,说明台湾的反国民党势力经过长时期的体制外的斗争,已以一种较固定的组织形态得到确认。”[1]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为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要求,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紧急戒严令”,适度放宽基本民权的限制,并允许民众经其他国家和地区赴大陆探亲。这为未来的政治生态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预示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即将发生转型。蒋经国去世后,台湾政坛由政治强人集权的一元化统治宣告结束,台湾政坛开始波动。社会运动在80年代逐渐增多,形式多样,范围宽泛,如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等,社会运动已经在台湾社会形成一种风潮,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政治斗争方式。李登辉上台后,不断打击异己力量,使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最终导致“新国民党连线”成立新党,此后政党成立的风潮应声而起。到了1994年,台湾已经有了76个政党。岛内的政党斗争也趋于白热化。政党斗争、群众运动,各种社团力量,构成80年代末以后的混乱状况。这种混乱在思想层面上反映为“有什么不可以”的心态。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崛起、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和消费文化的出现,使台湾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通俗化。这个结果促使大众文化兴起,而精英文化逐渐衰落。有学者不无失望地指出:“台湾目前文化的发展,无疑失去了人本的基本立场。物质文明再蓬勃,没有社群文化、精神文化映现人性光辉,必然是暴发户式的庸俗文化。长此以往,中国文化将深陷庞大的黑洞,前途十分悲观。”[2]
哈贝马斯曾经刻画了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3]“这种与自由观念相联系的个人主义,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4]现代性一般表现为世俗化与“驱魅”的过程。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现代性表现为三个分离: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经济与道德的分离。如果把现代性的特征与台湾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图景相对照的话,我们便很容易理解这些混乱现象。“解严”本来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因为台湾社会一直在一个强人政权下,而“神圣家族”的结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根本价值“自由”的实现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但是,台湾社会一方面“去神圣化”,另一方面又构建成一个“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新神圣“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它又与世俗化运动紧密相联,“亵渎神圣、百无禁忌,随金钱物欲之流漂转”[5]。在政治解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变动的背景下,文化的解严也随之开始。文化的解严来自于对权威的挑战与亵渎。它一方面百无禁忌地挑战既有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否定自我。因而有学者认为所谓台湾当代美术就是“解严释放的‘集体性’或社会力量在美术领域的展现”[6]。与社会思潮一样,台湾当代美术在80年代后期也是首先“去圣像化”。对于政治权威的亵渎或戳穿,成为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手段。这时期的前卫艺术家热衷于解构强权人物的形象,把社会运动作为自己反叛的舞台,把美术下放到世俗的层面,揭掉其表面温情的面纱,把丑陋与伤痛呈现出来。80年代末以政治人物为题材的大幅肖像画,就是这种“去圣像化”的实践。这种前卫性的挑战姿态,呼应了当时的群众运动,换句话说,他们百无禁忌的批判与嘲讽态度是对于社会和权威的不加掩饰的颠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权威逐渐失去威严,“反传统”、“反体制”成为新生代美术家挂在嘴边的口号,传统美术被当作保守和“老人艺术”大加贬斥。台湾当代美术正是在这样的反抗和颠覆中兴起的。
二、社会思潮与美术思潮的泛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政治格局的动荡,影响到各种思潮的兴起。各种思潮的兴起,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暗潮涌动,最终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虽经压制,但不久就因蒋经国的逝世而汹涌而起。不少台湾学者认为,所谓“后蒋经国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仅源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对民主的诉求,也隐含着对大陆的分离主义倾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福佬人在各个社会层面上崭露头角。“某些下一代台湾精英,也承袭了上一代有关‘二二八事件’及曾遭外省情治人员迫害的族群仇恨经验。”[7]1987年解严之后,各种报禁、党禁也随之结束,被压抑已久的各种情绪爆发出来,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为突破口,宣泄不满和愤怒。这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一些曾被作为“政治犯”的作家,以自身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政权长久以来采取的专制政策,摆出“一种无畏的姿态以文艺的形式,直接向现行政治发起挑战”[8]。这些反禁忌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了台湾当代艺术家,对社会和政治压迫的反思与批判也成为一部分人的创作重点。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弊端丛生的现象也引起艺术家的批判和反思,各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也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对于台湾美术家来说,政治思想与美术创作有着扯不清的联系,政治、社会的变迁在美术创作中的曲折表现时时存在。台湾近代史是外来政权压制旧政权,近代美术史则是外来美术观念不断取代旧美术观念的历史。实际上,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初期,各种思潮就已经在这个地区生根发展,现实主义的创作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巨大转变。“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引发的灾难,在当时美术家的创作中也清晰地展现出来,但结果是当局的断然镇压,不少文艺界人士遭枪杀[9],各种思潮运动由此戛然而止。在50年代的“反共文艺”中,红色与向日葵甚至成了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符号而加以批判。这种压抑即使在60年代现代绘画论战中也丝毫没有缓解,最后的结果是多数现代主义运动人物在60年代末远走欧美。
在70年代的暂时沉默之后,80年代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又卷土重来,在解严前后,欧美艺术思潮已经有了兴起的迹象,流行于欧美的新表现绘画、超前卫艺术、涂鸦艺术、“坏画”艺术以及极限艺术、贫穷艺术甚至19世纪末产生的颓废艺术纷至沓来。各种艺术思潮的迅速更新和流行,烘托出岛内热烈活跃的艺术气氛。到了90年代前后,波普艺术、观念艺术、环境艺术、大众艺术成为台湾当代美术界热衷的表现形式和探索目标,而相关的西方艺术思潮也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这些思潮和本土化、主体性的争论混杂在一起,构成90年代台湾当代美术的乱象[10]。在各种新的艺术思潮席卷岛内之时,对传统艺术思想的审视和处置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来,台湾文化里就包含着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短暂的荷兰西班牙文化、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国民党带来的中原文化,这些不同文化的经历决定了台湾文化的混血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经国民党政权的肃清,非中原文化依然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在权威力量崩解之后,这些非中原文化迅速浮现出来,结合西方当代文化,构成台湾当代文化的复杂和多样特征。基于此,一些台湾史论家认为台湾文化是外来者文化冲击的结果,而百年来的文化变迁,使得“台湾文化已经无法再与中原文化划上等号”[11]。关于台湾当代美术的发展方向的讨论,无论是“本土化”论争还是“国际化”议题,都是与传统的中原文化相去甚远。关于“国际化”的提出原因有两个:一是“放眼于天下的创作态度”;二是“进军国际市场的需要”。至于“本土化”,本质上还是一种主体文化因客体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这与70年代因怨美情绪的高涨引发的“乡土运动”如出一辙。但问题是,这还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大距离的,“乡土运动”的本质思想仍是现实主义的美术思想,它与300多年来的文化传统并不能等位。况且,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浪潮也早已把这种现实主义的乡土艺术潮流冲击得一干二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西方思潮之多已经几乎让人无法厘清其来龙去脉,这与大陆的“85新潮”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有一点不同,大陆的传统绘画积淀深厚,即便是最为前卫的现代艺术,也无法撼动它的根基。台湾当代美术的多元化时代则不可遏制地到来。总体看来,纷乱的美术创作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材料主义[12]。持此观念的群体由海外归来的留学生组成,在面貌上基本是延续了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前卫艺术。极限主义和“材料主义”成为这群艺术家最主要的艺术观或创作观。“材料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为盛行,实际就是后来装置艺术的前身。“材料主义”在台湾发展的有利条件,是艺术家可以利用本土元素,对观念进行个性化的表达,但是早期的创作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精神层面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材料本身上,缺乏对本土经验的感情和智慧。(二)新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的出现在欧洲新绘画风潮兴起之后,受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很深,台湾的新表现派“挪用已有的图像、技法或风格,企图唤起观众的想象,表达民族或本土文化的寓言、意识形态象征、神话或想象世界”[13]。在实际创作上,表现派艺术家还缺乏民族历史的深层关照,也没有西方那种压抑、感伤、忧郁的风格特征。(三)抽象主义。抽象绘画在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80年代以后的抽象主义改变了以前的自动性手法,注重对于历史与人文的思考,运用象征、隐喻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怀,探索生命本质之所在。(四)泛政治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多元化波及到美术界,代表这种艺术观的大多为战后崛起的新生代艺术家,他们没有上一辈人的政治负担和艰难经历,在炙热的政治气氛中忙于对权威颠覆和嘲弄,在他们眼里,泛政治化思想与台湾当代艺术的契合才是未来美术发展的方向,“一旦作品中出现了政治性图腾,不论是否真的有台湾意识,也不管艺术性如何,便立刻被赋予道德性的意义,被合法地冠上‘本土画家’的桂冠”[14]。这最终成为主流化的美术创作思想之一。
可以说,泛政治化是台湾当代美术兴起之后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与台湾岛内的政治气氛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对于台湾当代艺术家来说,艺术作品不过是进行政治批判的一种手段而已,其艺术价值只能在发挥政治、社会效益之后才能体现出来。
三、当代美术创作的泛政治化
在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各种既有秩序遭到挑战,艺术权威被各种新势力消解,以前卫艺术为代表的台湾当代美术登上前台,他们一再突破禁忌,揭露政治与社会问题,以一种狂飙猛进的方式毫无顾忌地展现出“病态、颓废、混乱”的社会面貌,形式直接而浅显。
从精神层面上看,政治、文化批判是台湾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显著的特征。批判的主要参与者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私人资本的快速扩张,社会结构在70年代以后也发生变化,一批新兴的中产阶层崛起,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有着相互存依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上层阶级有一定的矛盾,又可能与上层阶级发生抗争”[15]。同时,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体有密切的关系,又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16],因而希望能够进行社会和政治上的改革。尽管政治态度不一,但对于政治戒严、社会禁锢、思想压制都是强烈反对的。随着社会运动的开展,社会问题成为批判的对象。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很多问题的相继出现并不断恶化,反对运动批评当时的社会状况“暴力横行,色情泛滥,处处充斥着奢靡和堕落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赖瓦解殆尽”[17]。
80年代的批判风潮,在解严之前就从民间开始萌动,在90年代中期以前达到高峰。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在当代美术领域,无论是艺评家还是艺术家,批评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权威的崩解使各种创作群体开始露出水面,被压制的不满情绪,通过强烈的批判、抗议以及露骨的讽刺发泄出来[18],“台湾社会在80年代后期显得异常混乱”,“无形的殖民文化仍然难掩盖台湾在文化上的贫穷,也难以抚平台湾社会内在的不安”[19]。
除了“政治革新”以及政治“解严”带来的冲击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经济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迅速,岛内外贸易往来频繁,台湾进入一个“资讯庞杂、含混多元”的后工业时代。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领域的空前扩张,深刻地影响了乃至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科学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神圣性、神秘性和纵深感,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导致了“反文化”和“反美学”思潮的出现。文化享受已经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是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从台湾社会现实来看,后工业时代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消费指数不断攀升、股市跌宕起伏、地产房价高得惊人、交通状况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以及其他问题如雏妓、吸毒、赌博、绑架等等,引发各界的强烈批判。政治斗争因党外势力的崛起而日趋激烈,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政治反讽主要是对长期以来的强权人物和政治生态进行批判和揭露,其方式强烈而露骨:
“政治是开运动会时强迫大家一齐去唱歌的运动场
政治是一个口号二个动作三个伪装四个分赃的场所
政治是一种有两种标准的法律
政治是愚笨的人欺辱聪明人的唯一机会
政治是最好赚钱的房地产
政治是环保局不敢取缔的垃圾场
政治是人心腐败的暗房
政治是一个字可杀死许多人的屠宰场
……”[20]
这些即兴式的语句尖锐地讥讽当时政治环境的混乱和肮脏,“在嬉笑怒骂中,还原政治的本来面目”[21]。政治反讽是台湾当代美术“解严”的第一步,其次才是社会批判。对于台湾文化的批判莫过于“殖民主义”宰制当代台湾文化的观点,论者认为台湾的成长无不仰赖欧美,“仰赖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本源文化逐渐流失,是无法产生身后有力的文艺之原因。当各种各样的资讯蜂拥而来时,台湾的本源文化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贬低或遗忘,即使台湾能够发展高度发达的文明,也是西方模式的文明[22]。对于台湾的美术教育,一些评论家批评台湾美术教育是“功利主义所主导的美术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是“畸形教育下的牺牲品”,而职业教育流于形式,“健全国民教育”更是口号中的花瓶。就是对于艺术家本身,批判照样存在,“多元化时代来临,适逢政治解严和台湾钱淹脚目,还有过多的资讯和价值取向,一起把台湾社会改造了。就美术而言,传统意义的画家已不多见,他们已经蜕变为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23],论者认为在经济利益的鼓动下,艺术家的文化自立与创作实质已经成了问题。对于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状况,同样令人不满,有批评说,“……对于台湾当代艺坛而言,女性意识下所产生的女性美学仍是相当次要的议题,在传统男性权威的制度里,难免会被误解为‘反对’男性的立场,甚至在女性自身的圈子里,许多女性艺术家拒绝被标记为‘女性’身份,并且同意传统男性中心思想的观点”[24]。女性主义艺术的作品一再对男女性别的不平等进行批判,主张女性的“诠释权”。这在从台湾最早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严明惠到年轻一代的刘世芬、陈慧峤、林纯如的作品中都可见得到。此外,对于政治黑金问题、道德问题、弱势群体问题以及对待大陆的政策问题进行的讽刺或反思也是其中内容。艺术家对各种问题的批判和反思,集中体现在大量的作品上,掀起台湾的文化批判风潮。
台湾当代美术在绘画上的政治“解严”首先表现为一种“去圣像化”运动,在80年代末,艺术家吴天章通过刻画一系列领袖肖像,消解了权威的崇高性,以个人的观看方式描绘领袖人物的真实形象。历史在这里变为容纳个人批判观念的容器,对于历史人物的形象准确与否,艺术家并不在意,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感觉能否清楚表达了,杨茂林的《神话系列》也是如此。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在同样的手法表现下显得触目惊心,这些直白露骨的表现方式给人强烈的印象。社会贫富的差距、社会道德的沦丧、官员腐败的丑恶,都成为批判的对象。又如黄位政的作品,通过漫画式的粗糙形象,讽刺台湾政坛的畸形和黑暗。侯俊明则把两性的冲突作为创作焦点,假借传统版画形式,对于社会、道德、人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样对于社会权威,解构主义艺术(Deconstruction art)作品采取的是怀疑、批判或者嘲弄的态度。解构艺术“表现了对社会体制中各种权威事务(或意识形态)的反动,它的体质是批判的”[25]。它们或以一种促狭游戏的态度向权威发出挑战,或以冷静的姿态批判社会的现象,或者对于官方政策进行批判和揶揄。对于历史,其批判方式是更为独特的错位拼贴方式,历史的原形被篡改,呈现凄厉残破的效果和荒谬的情结,历史的沉重与严肃被削弱,历史的脉络被打断,人们从中找到现实中的荒谬和虚幻,甚至滑稽。随后,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登上政治反讽和社会批判的舞台。因为“解严”前政治压抑的关系,以“装置”手法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较少呼应、探讨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面向的议题。所以,政治解放之后的几年内,台湾“装置艺术”的发展,很快呈现相当活跃的局面。例如,1990年4月,连德诚、吴玛俐、侯俊明成立“台湾档案室”,同年5月与“甘仔店”共同策展“庆祝第八任蒋总统就职典礼”,艺术家以装置手法针对台湾政治进行批判,直接而强烈。与此相似的是,为回应1991年“制宪国代选举”,“现代画学会”曾在高雄市串门艺术空间举办“台湾土鸡竞选专案——1991艺术与政治关系初探”活动,以反讽目前候选人的病态选举。1996年和2000年台湾大选造成的嘈杂和混乱也成为艺术家揶揄和嘲弄的对象,以游戏态度对待本来应为严肃的政治活动,反映出当代艺术家对于政客的厌恶和批判态度。
简言之,政治“解严”是“政治革新”的手段之一,也是其必然结果,而政治“解严”又使长期被压制的社会思潮得以汹涌而起,这是台湾当代美术将创作视角伸向政治领域,进行政治批判的主要原因。
四、小结
台湾当代美术是从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的复兴开始的。现代主义的复兴缘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政治革新”。台湾政坛的权威逐渐崩解,原本被压抑多年的社会各种力量和声音得以爆发出来,各种思潮和艺术形式纷纷凸现,台湾社会显得动荡不安。随着社会思潮的不断涌来,社会运动的热烈开展,台湾当代美术终于突破了长久的压抑,开启了一个多元和混杂的新时代。
深受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剧烈变动的影响,台湾当代美术在文化上激烈地反抗权威,否定旧的意识形态,批判社会现象。新一代的艺术家认为传统的一元推理方式已经不合理了,执著于追求一个权威,一种绝对正确的标准,一个答案等单线式思维,是“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这一观念为理论界所笃信,也为后来的当代美术实践所印证,艺术家们以不断突破樊篱的艺术形式与挑战姿态开创了多元、混杂、动荡的新局面。所有这些,都为90年代台湾当代美术的多元和丰富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在各种思想运动中所形成的一味反对权威和传统,也使台湾当代美术在此后的发展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美术创作的泛政治化;(二)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三)创作水平的低下。反对传统必然会带来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一味追求吸引人群的效果必然会带来作品的娱乐化倾向。最令人不安的是,作为传统绘画精髓的水墨画在水平和数量上都大幅下降,而且越来越不受重视。创作水平的下降还表现在前卫艺术上,由于观念先行,只要是能够表达某种政治观念或艺术观念即可,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并不是最重要的,这必然导致创作水平的下降。
总而言之,“政治革新”给台湾当代美术的多元和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促使当代美术快速发展起来,但也给当代美术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应进行辩证、冷静的分析,对两者的关系和利弊做出客观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