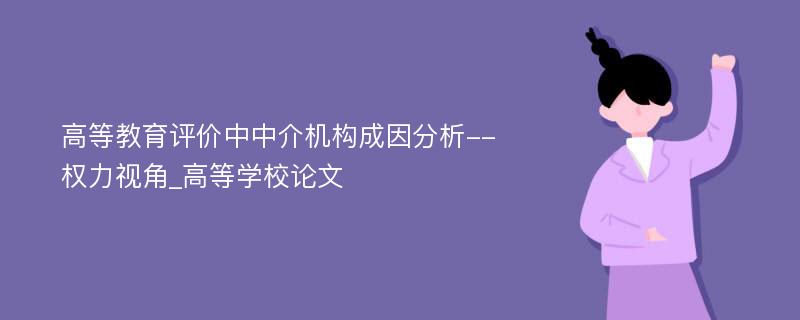
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成因分析——权力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视角论文,类中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研究者对“教育评估中介机构”这一概念并不陌生: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我国教育界为了区别于完全由政府部门操纵的教育评估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最早由陈玉琨教授于1994年在沈阳会议上提出,同年由王冀生教授首次在《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第一期见诸文字。目前,有研究者从词语含义、造词宗旨角度分析这一概念使用的不当。笔者以为这种不恰当只是称名不当,过于苛刻的批判是不恰当的,因为“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具体所指的事物是确定的:“一种界于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实体”,“一种专门性评估组织”。至于称名不当的原因,也许歌德的思考可以提供解答:传统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新生事物和新的思想认识,但是人们在获取新事物、新认识、新思想之后,由于没有更新的语言发展起来适应需要,往往“削足适履”,勉强使用传统的表达手段进行表述,结果“歪曲或损毁”了原意。但是对概念的质疑从细微处着手,有理有据,值得注意,所以在此采用了一个回避冲突的称谓“(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这与目前大部分文献中所指的“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内涵并无区别。
(一)
伯顿·克拉克在分析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权力时具有强烈的层次意识:一国高等教育系统从底部往上分析,一、二层次是基础结构,即系(讲座)与学部(学院);第三层是中层结构,整所大学或学院;四、五、六层所在的上层结构是各种行政管理实体,依次是(1)多校园的学术管理组织,包括多校区大学、州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2)州、省或市政府本身,具体是各种相关行政部门,(3)一国的政府及其相关部局与立法机构。克拉克还对处于不同层次的权力的诸多表现形式做了梳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表现为个人统治和学院统治的教授统治、基于学院式权力与个人权力结合而成的行会权力、基于专业技术能力的专业权力);“院校权力”(院校董事权力、院校官僚权力也即行政权力);“系统权力”(政府权力、政治权力、全系统学术权威人士权力)和“感召力”。这些层次不同表现不同的权力的运动与平衡就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实质。作为一种与高等教育系统密切相关的组织,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的产生应该可以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权力运动的角度予以解释。
(二)
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实体,它通过接受业务委托、对学校的办学能力和教育质量进行价值判断和(或)诊断,并以评估结果影响委托人与被评估者决策的一种专门行评估组织。”这一界定提供我们一个思考的入口:委托人与被评估者。通过分析不同委托人与被评估者情形背后表达的权力关系来解释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产生的原因。
高等教育评估主要是指对高等学校的评估,可以是对高等学校综合素质的评估,也可以是对高校教师、学生、教学、科研、课程、教育质量等单项内容的评估。而且更明确地说,被评估者是高等教育系统基础层次(大学的各学院、系及他们的联合达到的)的学术水平、专业能力评估或者与此相关的内容的评估,而不是对克拉克所说的中层结构的整个大学或学院进行笼统的评估。
1、委托人是国家/政府
教育权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后,国家会对实施教育的各教育机构进行方方面面的评估,以考察国家/政府教育投入的效率,并决定是否继续投入、如何投入。我国高等学校财政当前仍然以政府投入为主,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及其实际的重要作用,使得国家不可能在不作评估的情况盲目投入。
根据一般组织学原则,国家/政府借助高等学校行政权力(代表高等教育系统中层结构的大学、学院,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沟通基础学术层次与上层行政实体)或者自行组织评估机构对高等学校进行评估即可获得所需结果。但是,一方面,高等学校里以知识作为工作原料,充斥着源于知识的学术权力、专业权力,改变了高校组织的线性结构,而呈矩阵结构;结果,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并没有绝对的约束性。另一方面,高等学校行政权力要想对专业能力、学术水平实现有效评估,还是要依靠拥有专业权力/学术权力的教授们的判断,如此而来,评估中必然出现向学术利益倾斜。两种情形出现都不可能使国家权力满意,国家/政府不会对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得出的评估结果满意。
国家/政府对高等学校大量投入,评估过程中如果说不能要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至少要达到“公平和公正”,而任何高校系统内部的评估方式必定总与学术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不到不偏不倚;高等学校又是个独特的组织,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学术权力是高等学校系统内部最具权威的力量,任何行政权力倚重的评估方式往往遭到学术权力的抵制。那么,唯有寻找一种中间性的评估机构,既不受政府控制又独立于高校才有可能给出令双方都较为满意的答案!
2、委托人是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对高校的关注有目共睹,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在实行董事管理制度的高等学校内,社会公众把权力委托于董事会,也即那些院校的合法拥有者、院校经理人,“董事管理制度把外行直接放在权力的位置上”,导致这种情形出现:董事会要想对学校学术组织进行有效的评估,必须依赖于学术权力、学科能力;这种外行掌握的行政权力于内行掌握的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评估中难以协调。没有实行董事管理制度的高校,社会公众只能通过向更高层次的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的施加作用力,从而影响高等学校行政权力。这种情形与国家之所以成为委托人的原因相似。总之,高校董事会拥有的行政权力或者更高层次的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的权力都不能顺利完成对高等学校的评估,无法完成社会公众的委托。然而公众需要了解高等学校的信息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预测投资效果,必须产生一种能够担负这项职能,提供公正而准确的信息的机构。在公众委托人(董事会制度、政府)、高等学校(可信程度)无法提供这项服务后,只能是第三方中间机构。
政治学上认为,政府因社会公众权力的委托而生,所以,上述两种委托情形产生,本质上相同,都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的结果。事实上,独立于“政府”与“高校”之间,正是中间机构诞生的核心理由。
对评估中间机构而言,社会公众委托更多可能表现为无委托人情形,比如“中国大学排行榜”。其意义在于,政府、公众、高等学校、甚至教授(学术权力的拥有者)对学术组织发展的关注,有实际的需要。
3、委托人是高等学校
也有两种可能情形:高等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代表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层结构),对高等学校学术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估。作为行政权力,无法直接对学术成就进行评价,借助第三方评价,可以了解自己的工作绩效,对国家/政府、公众负责,而不致引起学术权力的强烈抵触。
也可以是基础学术组织委托,对自己专业、学科的发展水平在整个学校范围内、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甚至全球高等教育学术系统的位置做出评估,取其操作评估过程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三)
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的产生、运作的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
1、行政权力,国家、社会公众赋予的高等学校权力,理论上说,与学术权力之间不存在隶属、控制关系,但受国家中心的影响,行政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力非常之大。国家、学校行政部门对基层学术组织的评估往往可以顺利进行:虽然会遭到学术权力的抵触,但是学术权力相较与行政权力似乎不具实际效力,往往以学术权力的妥协告终。
2、如果作为中间机构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产生伊始就向政府或者高等学校某一方倾斜,结果会如何?倾向于政府权力,那么就难以做到对学术组织(高等学校)公正;同情学术权力、专业权威,政府难以获得公平对待;那么有必要产生这样一种中间机构么?
当然我们可以说中间机构可以实现公正,但是实际情形也很曲折:作为中间机构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工作需要专业知识、学科技能的技术支持,需要学术权威的知识、价值判断,如果政府相信中间机构中专业人士、学术权威的公正,那么什么促使政府对高等学校中基层组织中的学术权威、专业人士不信任?如果不信任这些专业人士、学术权威,中间机构失去意义,因为没有专业知识支持的评估可信度太低!笔者以为这种曲折可以归根于以知识为工作材料、按学科专业工作的高等教育学术系统的特殊性。
难道,“高等教育评估类中间机构”只是增加了又一种官僚协调的力量?笔者本身倾向于相信学者的公正、知识的公正以及政府全心全意地服务公众,相信诸多权力之间形成的某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