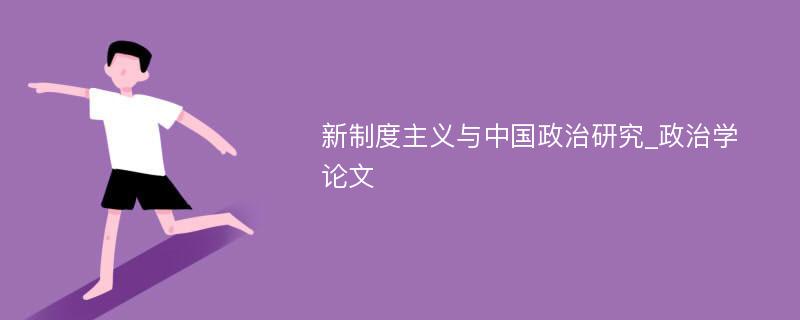
新制度主义与中国政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2-0113-06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学界兴起了研究制度的热潮,围绕新制度主义是否有意义,何种制度主义最能反映现实,新制度主义到底是一种规范理论还是实证理论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战。论战之后,新制度主义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话说,就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范式革命[1]。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治改革正逐渐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努力。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开始探讨制度问题,译介了许多新制度主义著作,发表了很多研究论著,新制度主义思潮已在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以下,笔者将对照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政治学界接受理论新思潮时的行为与态度,探讨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引入西方理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学研究主张。
一、新制度主义在西方
“制度”是政治学中最古老的话题之一。且不提古典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制度的关注,从政治学在19世纪末正式成为独立学科时算起,制度就是西方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整个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都是制度主义的。早期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包括描述—归纳、形式—法律、历史—比较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构成了旧制度主义范式的理论‘硬核’”[2]。当年美国政治学界领军人物如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伍尔西(T.D.Woolsey)等研究的重心都是国家体制问题,威尔逊的《国会政体》便是此类著作中的经典。
进入20世纪,先是芝加哥学派的兴起,紧接着是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还有影响极大的理性选择理论,旧制度主义范式迅速湮没无闻。戴维·伊斯顿对行为主义特征的总结也同样适用于理性选择理论,即:(1)政治学的目的是建立经验理论,从而最终成为一门可以预测和解释的科学;(2)社会科学应当探索理论范式,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相互支持;(3)价值中立,注重实证研究;(4)社会科学本质上是贯通的,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合作有助于政治学发展;(5)政治学者应当发展完善方法论;(6)个体主义方法论,政治分析应关注个体及由个体形成的集体行动,而非政治制度[3]。
尽管行为主义思潮及理性选择理论繁盛一时,但反思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呼唤制度回归的声音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早在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凯伊(V.O.Key)、达尔和伯恩海姆(Walter Dean Burnham)等已经感觉到,抽象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要获得历史数据,要研究长期政治变迁,就绝不能忽视历史和制度[4]。到60年代中期,各个政治学研究机构已经广泛地分化为“行为”和“制度”两大阵营,到处都有行为主义的拥护者和制度主义的拥护者,前者主要关注投票、公共舆论、政党和利益集团,后者则着重研究国会、总统制、官僚机构和司法部门等。当时有好几部获得美国政治学界最高奖伍德罗·威尔逊奖(Woodrow Wilson Award)的著作,都掺杂了制度主义视角,例如达尔在《谁统治》一书中对市长重要角色的描绘,鲍尔、波尔和戴克斯特(Bauer,Pool & Dexter)在《美国商业与公共政策》中对国会议员相对自主性的研究等。旧制度主义往往流于描述,过分重视正式制度和法律条文,而这些新制度主义取向的著作则注重理论构建,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正式制度规范上[5]。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制度主义思潮开始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兴起。诺斯(Douglass C.North)在70年代就开始构建自己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1978年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出版了历史制度主义名著《在权力与财富之间》,1979年社会学家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国家中心观。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James G.March & Johan P.Olsen)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撰文,正式宣告政治学领域内新制度主义的诞生。马奇和奥尔森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学理论存在背景决定论、化约论、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功能主义等五大问题,政治学研究决不应该忽视制度分析①。自此以后,新制度主义开始蓬勃发展。
在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泰勒(Peter Hall & Rosemary C.R.Taylor)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新制度主义被大致划分为三大流派,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一划分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共识。这三个流派对制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用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典型行为假设如固定偏好、效用最大化等,认为制度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对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激励或约束,理性的政治行动者面对制度应采取各种策略性行为。其代表人物有诺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谢普索(Kenneth A.Shepsle)、麦卡宾斯(Mathew D.McCubinns)、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等。
2.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从广泛的意义上研究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运作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强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代表人物有斯科克波、卡岑斯坦、霍尔(Peter Hall)、瑟伦(Kathleen Thelen)、埃文斯(Peter Evans)等。
3.社会学制度主义从社会意义、习惯、认知等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制度,研究制度的效率、异同、合法性等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由于其特定的学科属性,对政治学研究影响不大,政治学领域中涉及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是马奇和奥尔森。
进入新世纪之后,新制度主义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其面临的困境也日渐凸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新制度主义者仍然无法确切地界定制度,也很难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测量它,他们眼中的制度包罗万象,难以捉摸,既可以指宪法、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可以指文化、习惯、风俗、互动模式等极端模糊的社会现象。同时,新制度主义的几个流派在解释力上仍有诸多不足,在此不再赘述。
二、新制度主义在中国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注意到新制度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兴起。进入90年代,对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日益增多,西方著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还出现了一些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论著。
率先对新制度主义理论产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国内很早就译介了一些早期制度主义者的名著,例如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康芒斯(John R.Commons)的《制度经济学》等。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新制度经济学著作被翻译过来,例如科斯的《交易成本问题》,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人的文集《制度、契约与组织》,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亚洲的戏剧》等。另外,还翻译、撰写了许多制度经济学的教材和著作。中国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比较多,例如厉以宁教授早在1979年就出版了评论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6],周其仁教授运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农村经济[7]等。
从根本上讲,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方法传统。但新制度经济学对数理要求不高的理论论述方式,对其他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造成了强大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极感兴趣,积极开展理论介绍、比较和评价。例如杨瑞龙的《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8],陈振明的《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9],赵波的《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比较》[10]等。在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中,两类作品比较多:一为行政管理领域,受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研究探讨最小国家、政治腐败等问题;二为制度创新,援引诺斯和林毅夫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和政府创新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政治学者受到了很大鼓舞,进而引入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另一大分支——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制度下的理性选择(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IRC),该理论在政策研究中尤为常用②。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编著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早在1992年就被翻译过来并数次再版,他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等也被翻译过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也被翻译过来并受到学界的重视。
奥斯特罗姆夫妇对制度的看法、对制度演进的分析以及他们独特的治理理念,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陈剩勇等在对温州民间商会的研究中,考察了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组织模式及其治理机制,剖析了这一民间性、自治性和服务性行业组织的自主治理实践及其面临的制度困境[11]。陈敬德、何世晖在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时,认为由于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具有相当特殊的技术和经济性质,只有构建多中心体制即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多中心的资金安排等,才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12]。
相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直到晚近才被中国政治学界所了解。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可以认为直到1996年,也就是历史制度主义在西方最繁荣的时候,国内学术界才开始接触历史制度主义:当时翻译了凯尔布尔(T.A.Koelble)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一文;中央编译局何增科也在1996年发表了《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对包括历史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思潮进行介绍。
历史制度主义真正引起中国政治学者的注意,是从2000年开始的。在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两本杂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相继翻译发表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些代表作品,例如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的《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阿弗纳·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埃伦·M·伊梅古特的《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等。2004年,这些论文被收入《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一书,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介绍和研究历史制度主义的著作。与之类似的另一部著作是上海学者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等编辑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集》。
国内学者还撰写了不少介绍性文章,探讨历史制度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和演变。2001年,朱德米博士在《复旦学报》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文,介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思潮。何俊志博士在2002年发表了《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开专门介绍历史制度主义思潮的先河。此后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的文章不断增加,例如赵晖的《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特点》、魏少亮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与应用》等。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的何俊志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地位、发展脉络、优缺点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不少学者还积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念和分析框架研究国内外政治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连续撰写《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论著,从历史和制度的视角研究国家的治乱兴衰。王庆兵把历史制度主义运用到国际政党比较研究中,认为英国和美国不同的制度结构和政党组织特征塑造了选民的投票行为[13]。复旦大学的何俊志博士,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地方人大问题,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了各级人大很大的发展空间,最近出现的制度创新将会在实践中逐步落实[14]。
目前,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股研究浪潮。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冲击,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但可惜的是,至今还未见到学界有意识地探讨新制度主义思潮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
三、理论引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回顾新制度主义在中西方的发展和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政治学学术界在理论引入过程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西方学术传统缺乏整体认识,二是理论运用有失偏颇。应当说,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政治学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是比较迟缓的,而且大多数政治学者眼中的新制度主义就是指新制度经济学,直到译介历史制度主义思潮的时候,学界才意识到新制度主义的广阔范围。至于社会学制度主义,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比较盛行,对中国政治学界的影响不大,几乎看不到专门的译介文章。即使撇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谈,目前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引介也存在极大的偏差。
中国政治学界最初接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无疑是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主要是从诺斯、科斯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寻找灵感。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斯的国家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正是政治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在国际上,不能说没有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政治学者,政治学中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支就倾向于采用新制度经济学,但主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性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反观国内,在这方面,只有奥斯特罗姆夫妇的作品被充分引介过来。事实上除了奥斯特罗姆夫妇所代表的研究取向,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有很多理论分支。这些理论大多是为弥补理性选择理论的失败而建构的。比如70年代中期,政治理论家麦考维(Richard McKelvey)首先证明多数决定结果只存在于完全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就是所谓的浑沌定理(chaos theorems)。但政治学者谢普索指出,非均衡的结果并不表示现实世界就是永无宁日的混乱,而是忽略了制度这个结构限制性因素[15]。著名理性选择理论家赖克(William Rike)进一步指出,制度是偏好的聚合,如果要将其视为均衡的重要元素,就不得不承认制度也是人们所共同选择出来的[16]。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政治学内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才真正开始完善和发展。而麦考维、谢普索、赖克、麦克宾斯、泽比利斯等学者的经典著作远未被国内学者所熟悉,更不要说译介了。
至于历史制度主义,国内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卡岑斯坦的一些作品被相当一部分学者了解,他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被翻译成中文,但他首先被看作一个国际关系学家。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法俄中比较研究》、《美国社会政策——历史视角的未来可能性》等在西方学界早已是经典,但是《国家与社会革命》2007年才被翻译过来,其他著作至今没有翻译,对斯科克波的介绍性文章也极少。其他经典著作,如彼得·霍尔的《治理经济——英法国家干预的政治》、彼得·埃文斯的《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及其参与主编的《找回国家》等,国内学者进行认真研究的不多,更不要提翻译了。毫不客气地说,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著作迄今只有极少数被引入了国内,而国内详细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来龙去脉的,也只有何俊志博士的一部《结构、历史与行为》。
引介的不完整意味着知识结构的不完整,知识结构的不完整使我们对理论前沿无从认识,研究也只能浪迹于主流之外。不完整的译介还会让人难以把握理论的全貌,进而导致认识上的偏颇。最终的结果就是个别理论或著作影响极大,更多的理论和著作却不为人所知,或者即便某些著作被引介过来,但因失去西方背景,或多或少导致理论上的“误读”。比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的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翻译为中文[17],在许多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部论述社会发展的著作而已。但认真检视这本书,可以发现其中很浓的国家中心观和新制度主义的气息。摩尔的学生斯科克波正是继承发展其思想,才得以形成完整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塞缪尔·亨廷顿以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作闻名中国,并被归类为政治发展理论家。但若仔细分析《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理论框架,该著应归类为较早期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亨廷顿在书中提出了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程度[18]的著名主张。
新制度主义在西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动。但新制度主义又融合了这两大范式的许多成果,故而能够推陈出新超越二者。新制度主义的产生也与美国社会中长久存在的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抗有关。美国政治学中科学主义意味非常浓厚,行为主义者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一门“科学的”政治学,像物理研究一样发现政治学领域内的规律。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历史思潮重新回归,由此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尽管如此,反历史的政治研究迄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到2004年,《美国政治科学和政治学》(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杂志还邀请许多顶尖政治学家讨论美国政治学是否因为数量化而走错了路。反观国内,政治学著作极少用到量化分析和数理模型,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解仍然十分肤浅,所做的学术训练仍然非常有限。这并不是说量化和数理工具一定优于定性分析,而是说在根基不牢的基础上妄谈新制度主义,颇有逃避学术训练和避重就轻之嫌。
引介过程出现的诸多问题,无疑会影响到理论的应用。目前中国政治学界的许多应用性研究令人堪忧,某些研究沦为套词语、套口号乃至削足适履的游戏。这些研究一般是先大致介绍新制度主义的内容,然后在国内外寻找若干符合的政治现象,再把理论一套,一篇文章就此出炉。没有理论探讨,没有理论创新,也没有深刻的分析。学术界应当明了的是,采用制度主义思路进行研究,并不意味着就要把关于制度的基本观念重复一番,而重复一番也并不意味着就采用了制度主义思路。另一方面,尽管国内政治学界的新制度主义思潮轰轰烈烈,理论应用的领域却极为有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认真总结之后,发现国内应用新制度主义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三大领域:(1)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研究;(2)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关于中国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19]。
鉴于中国政治学界引介新制度主义思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完整地译介新制度主义理论,切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习西方理论不但要了解最新的理论思潮,也要全面把握其在政治学发展中的脉络。译介是加强沟通了解的必要步骤,可是零星的、只言片语的引介,只会导致理解上的偏颇。
其次,在引入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同时,还要巩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根基。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西方政治学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而是要求把它们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惟有加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修养,掌握社会统计方法及数理工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而理解西方政治学传统。
再次,推动新制度主义理论与本土研究相结合。学习西方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在理解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阐释体系,否则就只能徒具其形而不得其实。这要求我们注意两点,一是关注中国问题,二是理论研究和应用要推陈出新。在此,美国学者戴维·贝奇曼(David M.Bachman)应用新制度主义视角对中国大跃进起源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借鉴③。
收稿日期:2007-11-10
注释:
①James C.March & Johan P.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8,No.3.(Sep,1984):734-749.该文稍后被收入名著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一书,参见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1989:3-8.
②对奥斯特罗姆夫妇理论的详细评介,参见Edella Schlager & William Blomquist,A Comparison of Three Emerging Theory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49,No.3.(Sep,1996):651-672.
③贝奇曼认为,制度结构和官僚结构实际上约束了最高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参见David M.Bachman,Bureaucracy,economy,and leadership in Chin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标签:政治学论文; 行为主义论文; 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政治学研究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