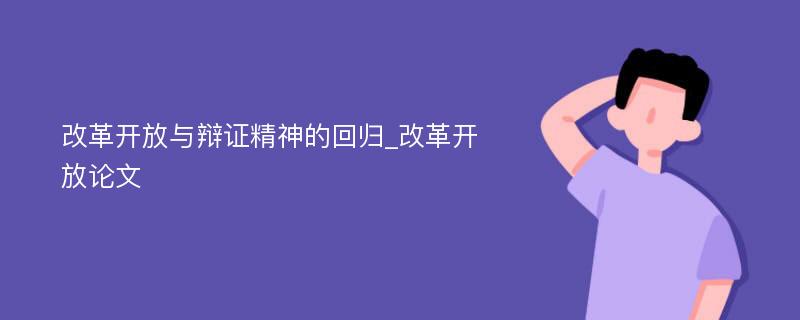
改革开放与辩证精神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社会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政治集中和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中国经验否定了上述观点。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亦无法解释中国经验。它曾依次提出了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各种核心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资源生产率、创新企业家、产业结构调整,上世纪80年代后又引入了产权制度。但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除亚洲“四小龙”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反而相继陷入“发展困境”。相反,上述核心要素在中国改革的30年中都以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形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因此,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合国情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等,第182页)
而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解读更为准确:“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造就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
本文认为,“中国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变迁,这种变迁背后是辩证精神由否定性到肯定性的历史转向。
一、为什么消解辩证法的“否定”前提?
我国哲学界以往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存在两大理论误区:一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误读为“否定辩证法”;二是对作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否定性本质的革命性、批判性作了片面的理解。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性的吗?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笔者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或思辨逻辑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绝对精神存在的本体形式,即存在的(自在)逻辑;二是指绝对精神之展开即外化或异化的逻辑形式,即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自为)逻辑,同时又是绝对精神借助于人而实现的自我认识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论、逻辑学、认识论是同一的。从绝对内在同一的“纯存在”,到展开了的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都是“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统一”,“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构成了黑格尔的逻辑程式。因此,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冠以“否定性”是误读。
首先,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明确指出:“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形成的理念”。(黑格尔,1980年,第63页)“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说明]这三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同上,第172页)显然,否定性绝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特质,即使是在第二方面也蕴含着肯定;相反,不包含肯定的否定,不是辩证法,而是怀疑主义——“彻底怀疑一切认识形式的否定性科学”(同上,第171页)。“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之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但哲学不能像怀疑主义那样,仅仅停留在辩证法的否定结果方面。……辩证法既然以否定为其结果,那么就否定作为结果来说,至少同时也可说是肯定的。因为肯定中即包含有它所自出的否定,并且扬弃其对方(否定)于自身内,没有对方它就不存在。但这种扬弃否定,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基本特性,就具有逻辑真理的第三形式,即思辨的形式或肯定的形式。”在这一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同上,第181页)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逻辑程式不是否定性的。
其次,黑格尔存在论认为,作为逻辑学开端的“纯存在”或“纯有”是绝对精神的最初形式,即“绝对就是有”。(同上,第190页)这种看似绝对肯定的“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因此“绝对即是无”。(同上,第192页)否定性的涵义一是纯粹的无规定性,二是自由。“当自由在自身把自己深化到最强烈的程度,本身也成为肯定性时,甚至成为绝对肯定性,这种自由就是否定性”(同上,2002年,第171页)。“这种自由,虽是一种否定,但因它深入于它自身的最高限度,自己本身即是一种肯定,甚至是一种绝对的肯定”(同上,第193-194页)。可见,纯粹的“无”也不是单纯的否定,只有“有”与“无”的统一才是真理。
又次,黑格尔对认识的描述亦然:“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在化建立了事物性,并且这种外在化不仅具有否定的意义,而且具有肯定的意义,不仅对于我们或者自在地有肯定意义,而且对于自我意识本身也有肯定意义。”自我意识的自在(肯定)——外在化自身即把自身建立为对象(否定)——扬弃了这种外在化和对象性(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意识的(辩证)运动”。(同上,1979年,第258页)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其思维形式和思维过程而言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不存在否定的辩证法;就其体系化的宏观逻辑构架而言,具有浓重的肯定性特征。
那么,为什么人们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辩证法”呢?原因在于教条化地理解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其实,马克思是从两个维度来分析黑格尔辩证法的:一是将之作为逻辑意义上的思维形式;一是将之作为主体把握现实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后者是时代主题的思想回声和主体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否定性的辩证法”指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首先,马克思同样积极评价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思维形式:“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同上,第177页)可见,作为独立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也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积极内核。马克思还说:“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同上,第159页)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维度和历史运动维度,意味着“否定性的辩证法”只是在把握现实、关照人的社会生成和自然的向人而生时,才是“否定性的”。
其次,无论是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的宏观叙事,还是对劳动异化的微观考察;无论是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主张中,还是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统一的理想中,马克思都是按照黑格尔的思维逻辑程式进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而且再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宏观历史进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个别性的方法,展开自己的全部论证。马克思还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说明,作为合理内核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形式,不存在单纯的“否定性”问题。
又次,我们可以把《精神现象学》看作法国革命的思想回声,代表了青年黑格尔对法国革命表现的自由精神的渴望和对其“绝对自由和恐怖”实践的反思。可见,马克思说的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恰恰是对这一隐含的实践关怀维度的揭示。作为绝对精神展开过程之异化、外在化表现出的否定性形式,实际上是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主题的理论折光。
二、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二维理解与辩证精神实践的历史反思
国内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硕果累累,主要体现在:一是确立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在主体上实现了由绝对观念到实践着的人类总体的转换,在辩证法的原型上实现了由绝对观念、物质自然到实践原型的转换的观念(参见陈晏清、王南湜等,第122页);二是实现了研究范式上由自然主义到生存论范式的进展(参见贺来);三是开启了黑格尔的“实践”对马克思哲学创立的意义研究和“实践智慧的辩证法”研究(参见王南湜);四是提出了由矛盾的辩证法向和谐的辩证法转变的新思路(参见张奎良)。但是,这些理论创见分别存在如下问题:基于实践的理论辩证法只能解释超验目标,而不能把握现实有限事物;生存论范式如果仅在理论视域上展开而不解释当代最为重大的现实生存——经济与社会发展,它实质上就还是抽象化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与理论辩证法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没有阐明从矛盾辩证法到和谐辩证法的逻辑中介。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将思维逻辑的辩证法与实践把握的辩证法混淆了;这样,人们就只能概念化地解释人的无限自由的生存活动,而不能解释现实人的实际生存,不能解读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国际秩序,更不能解读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不能说明“批判—否定性”的辩证法何以能实现“对话与宽容”及“自强不息”,更不能说明怎样过渡到“实践智慧”与“和谐思维”。
固然,关于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质的观念出自马克思的名言:“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但是,如果从上下文来看,马克思这里讲的是辩证法的自为的外向性的实践把握维度,而非内在性的思维逻辑维度。
其实,辩证法无论在康德还是黑格尔那里,都首先是一种相对独立于现实的逻辑形式。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仅是对康德存在论意义上的二律背反的批判性改造,也是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性继承。黑格尔的逻辑既是绝对观念自身存在(自在)的逻辑,又是存在自身的自我展现(自为)的逻辑;既是存在自身绝对抽象同一、自己规定自己的主观内向的逻辑,又是存在自身自己分化自己、给予自己以客观性的内容并扬弃分化、回归于统一的外向性逻辑。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践改造中,将黑格尔自我意识实践展开的辩证法,变成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并作为辩证法的现实基础;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存在变成人的现实存在、人的“实际生活过程”。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两个维度:一是基于实践本源性结构的内在性的辩证的逻辑思维形式;二是受现实宏观实践场域约束的、带着主体价值取向的外向性的方法论原则——被实践环境所把握又把握实践的辩证精神。
对于思维逻辑的辩证法,马克思不仅为其确立了实践性生存活动的本源,同时也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这一相对独立的思辨形式。黑格尔的内在性的思维逻辑将“知性或理智”、“辩证的或否定理性”、“思辨的或肯定理性”囊括其中,将之作为“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黑格尔,1980年,第172页)这样,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就将康德的空间性的知性逻辑与自己的时间性的历史逻辑融为一体。知性的形式思维成为一切辩证逻辑环节的前提,为辩证思维确立了确定性、明证性的形式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维度、尤其是其知性前提,只是作为自明的东西继承下来而并未展开,这一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忽略了。
对于辩证精神的辩证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否定性”的“推动和创造原则”。辩证精神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和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不同在于,“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个“物质的东西”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和自然化的“人”,也非黑格尔作为独立主体和客观存在的“意识”。因为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于是,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自由自为的否定性创造原则,就变成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黑格尔“人的发生的历史”变成了“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整个世界历史成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2000年,第154页)这样,辩证精神就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过异在的自我发现,而是对反映现实实践场域(社会存在)的时代精神的实践把握。如果说,“‘时代精神’就是标志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孙正聿,第214页),那么,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辩证精神就必须受到特定的“生活世界”的限制和实践场域的约束。这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所确立的唯物论原则,它是辩证精神的存在论前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第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思维逻辑形式和实践的辩证精神两重维度。前者不存在单纯的否定性问题,后者作为主体的把握实践的精神理念则必然带有否定或肯定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最终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生活世界”或实践场域。
第二,作为逻辑的辩证法包括知性逻辑并以知性逻辑的确定性、明证性为前提(第一环节),它的有效边界是在确定性的对象间的“联系”和自身“发展”界域。第一环节的知性前提是达于真理性知识的形式依据。第二环节的“否定”是过渡环节,表征对象与它物的差异和“联系”;辩证否定承认事物在运动中的确定性状态的存在,单纯的“否定”则是诡辩和怀疑主义。第三环节的“否定之否定”表征对象的现实“发展”。
第三,作为主体的外向性的把握实践的方法论原则,不是纯粹不受限制的无限自由的绝对否定性,而是受实践场域或条件约束、并带着主体的价值取向的辩证精神。它作为时代主题的反射和回声,可以是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关键在于“生活世界”的现实状态和时代主题。
19世纪是冲突的世纪,这决定了马克思的辩证精神首先反映了那个时代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时代主题。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自性,却是与“肯定”相伴的、并且最终是为了“肯定”的动力和方法性范畴。恩格斯在论证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规律的同时,也论证了辩证法的否定性精神;但是,他依然像马克思一样承认肯定的作用,甚至一样承认:“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恩格斯,1976年,第37页)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20世纪时,否定性辩证法得到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历史性高扬,对立统一规律取代否定之否定规律成为辩证法的实质核心,斗争性成为“绝对的”。(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56、557、412页)辩证精神的实践把握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和历史的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实践强化了辩证法的否定性精神。
毛泽东将对立统一规律做了“矛盾论”诠释,并确立了辩证法把握实践的唯物论前提——将实事求是作为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辩证思考的本体论基础,将实践场域的“实际”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矛盾对立的形式揭示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和解决矛盾的形式(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282、284、3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0页),取得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胜利,显示了否定的辩证精神巨大的实践力量。
然而,辩证精神对实践的上述成功把握,却固化了辩证精神的否定性形式,而忽略了辩证精神实践前提的实践场域。而将否定性上升为辩证思维的逻辑程式时,必然产生两个结果:或是陷入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否定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或是走入恩格斯所说的“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0页)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幸的是,这种形而上学化的“辩证思维程式”逐渐成为建国后的指导思想,否定性的辩证法成为政治第一、革命至上的意识形态范式的思维逻辑基础,成为“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方法论基石。
一些人至今没有充分注意作为思维逻辑的辩证法与把握实践的辩证精神的差异,并忽视其理论前提,使辩证思维的肯定性被遮蔽和知性前提被遗弃。这是导致辩证法的低俗化理解泛滥、陷入诡辩和怀疑主义以及人们对辩证法嘲讽与鄙视的主要原因。在实践把握上,过于强调“反思”而忽视对辩证精神的本体论前提——生活世界或实践场域的直面认知,以至于对中国人民伟大的创新实践“理论失语”,也使辩证精神失去解释时代的方法论魅力。
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法时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恩格斯,1972年,第465页)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主题的转换,辩证精神的转向也就成为历史的呼唤。
三、辩证精神的肯定性转向与“中国奇迹”的创生
1.辩证精神的肯定性转向与改革开放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意识形态理念由革命到改革、由封闭到开放,实质上实现了辩证思维由否定性到肯定性的转向。因为改革是制度的肯定性自我完善,而非否定性的制度革命;开放意味着制度的共存并立和相互交融,而非否定性的两极排斥和你死我活。教条主义是辩证精神的天敌,辩证精神教条化更意味着辩证精神的死灭。辩证精神的重生在于对其唯物论前提的恢复和重建,在于对辩证思维的知性逻辑前提的重建。这一前提的重新确立就是由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转变。正是因此,邓小平才将全部理论、战略、政策建诸于具体国情之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实践。
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开启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也凝结着战后的时代精神。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时代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转换。作为时代主题的理论回声的辩证精神也实现了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转向。
2.辩证精神的时代交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奇迹的主因”几乎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结合起来,仍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的创想。原因在于他们都信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教条,都在知性思维视域中认为公有制产权形式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东欧的相关改革,都认为不可能使“市场与计划”兼容,以至于倡导改革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内直到1990年还认为,国有企业按市场行事那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破灭了”。(张军,第52页)有人认为,“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没有能够在社会主义范畴内找到计划与市场有效结合的途径和形式有关”。(马洪,第13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不仅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且基于肯定性的辩证精神。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说,看似对立的两个事物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创建和实践选择,成为20世纪后半期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
3.辩证精神的肯定性转向与经济转轨路径的正确选择
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转轨大潮中,共识性的观点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双轨过渡”,实现了转轨绩效上伟大的领先;由于独联体国家选择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导致了“失去的十年”。笔者认为,决策者们之所以选择截然不同的转轨路径,关键在于奉行不同的思维形式。“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抽象出的标准模式,是知性思维的产物;“休克疗法”也是基于知性思维原则得出的计划与市场绝不相容后的必由之路;他们都是基于“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4页)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的缺陷是无视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想超越历史完成经济模式的瞬间置换。然而,经济转轨不是精神展开的逻辑过程,而是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无论是市场经济制度信息,还是系统的法制化规则,抑或主体交易的制度平台,它们的建立与完善都是一组过程集合,都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之否定。知性思维无力把握这一实践过程,辩证思维却对之游刃有余。从双轨并存到并轨运行,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就是辩证思维的逻辑轨迹和辩证精神的实践展开。
4.辩证精神的肯定性转向与中国的产权革命
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证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原因,也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关键要素。产权经济学证明,计划经济下公有制企业由于找不到产权实现形式而导致产权模糊和产权虚置、缺少责任主体,经济必然低效。而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竞赛中纷纷败北,并对此理论作出了经验证实。于是,如何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成为所有转轨国家面临的攻坚难题。东欧、独联体国家基于形而上学思维采取“全盘私有化”措施,结果不仅没有带来预期效率,反而陷入“转轨经济危机”。中国人民则以特有的辩证智慧通过三次大的产权革命,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并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首先,农业改革创造了“统分结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公有产权财产占有权与用益权的分离,产生了空前的经济效益,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开局。这实际上是辩证思维的肯定性转向的结果。其次,国企改革是改革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创新方式是将股份制作为国有经济主要的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理论前提是:股份制不姓公也不姓私,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于是,国有经济退出一般性经济领域,进入大有可为的命脉产业和关键领域,使国有企业从全面亏损变为充满活力。毫无疑问,改革的基础依然是肯定性辩证思维。再次,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调动了全民的创富能力,而且为转变和优化产业结构创造了所有制前提;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经济制度使国家具有了超常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仍保持了高速增长。这种两极兼容并生、互相促进、互相转化、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无疑是辩证精神的运行逻辑和实践形式。
总之,由于辩证精神由否定性到肯定性的转向,促成了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变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进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