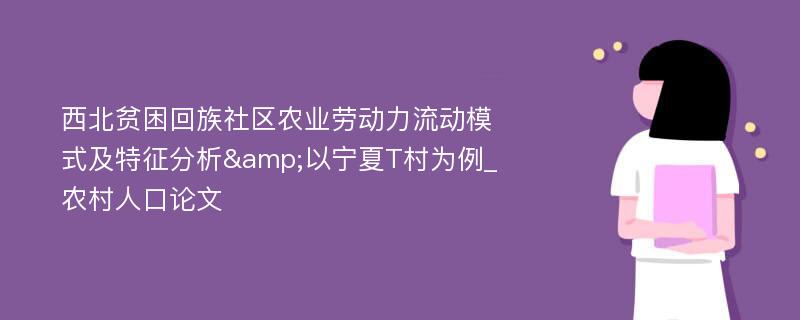
西北贫困回族社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和特点分析——宁夏T村的实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宁夏论文,劳动力论文,贫困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长期“隐化”的数以亿数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显化”,纷纷涌入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工潮”。人口城市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学者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纵观这些研究,从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大多是宏观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较大地域,所撰写的论文和专著冠以“中国”、“全国”、“我国”,“xx省”等字样的在量上占绝对优势。从研究数据的获得上,目前大多数研究成果所依据的数据,多采用的是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偏向于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宏观指标,因而难免有疏忽之处,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不高也就在所难免。社会的特殊的观点认为要充分解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必须研究潜在流动人口所在的特定村庄中的社会关系,不同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功能分化的不同会影响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式等(转引自史威琳, 1999)。受此启发,与上述成果不同,本研究从另一视角——微观地域(村域)、微观个体(农户)来探讨西北贫困回族社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和特点。同时,西北乡村回族的人口流动才刚刚起步,呈现出了不同层面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和现实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地点的选择
(一)研究地点的选择
T村隶属宁夏L县西镇,是回汉杂居的村落。L县地处六盘山西北麓,属宁南山区,是典型的西北地区,1972年被联合国列为不适合人类生存地方之一。T村位于西镇正北方向,距镇约2.5公里,地处黄土高原,属陇中山地与黄土丘陵区,冬季寒冷而干燥,春季多风沙,夏季常干旱,民间素有“十年九旱”、“三年两头旱”、“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之说,2005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庄稼颗粒无收。
T村地处宁南山区,是西北贫困的乡村之一,无论在经济上、地理上,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是处于边缘化的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不发达,没有任何乡镇企业,进城务工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受工业化的冲击小,也常常被人忽略,在这些地区中生活的村民的情境大多不被人知。但是,在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这些边缘化的地区正在被各种力量重新建构其情景,他们已经开始慢慢地在农村之间流动和向城市流动。笔者认为选择受工业化冲击比较小的T村为个案,便于对当前西北贫困回族社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和特点有更加准确的描述、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并辅以个案访谈资料。主要是采用普查的方式, 对T村114户人家进行了走访,目的是要统计出T村在2005年有多少回族户有劳动力的流动,占总人口的多少,有多少人曾经流动或者现在还流动在外以及这些流动劳动力的生存状况如何。
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和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大规模的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正在和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各个国家都不例外,但是转移的具体过程会因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的制度框架以及这种政策和制度框架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移民所提供的特有的机会、渠道和限制而在不同的国家中有明显的差别。就中国而言,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限制政策、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的制度背景,也形成了独特的流动方式和类型。
中国农村人口的跨地区流动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流动;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而后一种流动则更为社会所关注。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方式归纳为以下几种(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1997):
1.在城市企业中“打工”。进入企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政府或企业有组织的进入,国有和集体企业采用这种方式的比较多;二是个人进入,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多采用这种方式。其中个体进入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企业的主要方式。
2.进入城市的建筑队与装修队。主要有进入国有和集体企业搞建筑和装修以及由农民牵头组成建筑队,进城承包修建工程两种情况。
3.在城市中自我雇佣或成为雇主。主要指进入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和进入第二产业,自办企业的小部分。
4.其他。包括进入城市家庭服务的“保姆”、在街头巷尾揽活的散工等。
5.以北京“浙江村”为代表的“产业——社区型流动”。他们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方式,不仅在于其村民是带着综合性资源进入城市的经营者,还在于他们在所流入的大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基本属于自己的准社区,这个准社区不仅是一个聚居地,而且聚居促成了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的产生,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产业基地。
四、现状与问题:生存压力与理性选择
有的学者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或外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解释,指出: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和转移的一个主要原因;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是强大的市场因素;原有的就业用工、户籍管理、粮油票证以及医疗、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是结构性条件;城镇和农村社区有没有提供在非农行业和领域里就业的机会是重要的“外部条件”;文化层面上,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是明清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走了一条过密化道路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农村改革而发生的农民的视觉和思维空间的变化是他们外出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的文化背景(黄平,1997)。
文军则用八个字来概括了农村人口非农化行为的动因,那就是“生存压力”与“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大规模、长时间的农村人口外出或转移现象是他们在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文军,2001)。
T村的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都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而且同时由于遥远的距离,不便的交通和传统的关系,人们难以走出去。但是,同样由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不得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做出了“外出”或“转移”的理性选择。
根据T村2004年末的报表,2004年末T村全村总人口为543人,农业户数为114户,户均4.763人,其中回民93户,汉民21户;在T村所有的村民中,2004年60岁以上的有42人,占总人口的7.73%,其中回族29人,回族女性12人,汉族13人,汉族女性7人;70岁以上的有21人,占总人口的3.87%,其中回族13人,回族女性5人,汉族8人,汉族女性3人;80岁以上的老人有3人,占总人口的0.55%,全是汉族男性。没有关于村民平均寿命的数字。像中国的其他的社区一样,T村的婚姻也是父权制的婚姻模式,以从夫居为主。女子嫁到这个村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由于户籍制度的安排,其他形式的人口迁移很少。
解放后,T村就有了自己的小学,到2000年该村小学撤掉为止,T村小学前后只有50年左右的历史。村小学位于T村东北角,紧靠伊斯兰教(老教)清真寺,说是一所小学,实际上只不过是三间小土房,教室阴暗、拥挤,冬天寒冷。先后有4位教师在这里任教。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T村小学倒塌了,到现在没有自己的小学。现在T村大约有80个孩子在上小学,由于没有了自己的学校,学生只好分散到离T村约2.5公里和约2公里外的邻村小学和镇小学上学,冬天零下20多度,孩子冻得哭叫。渴盼能有一所本村的小学是T村村民的两大愿望之一(另一是解决吃水问题)。
据2001年派出所户籍管理统计资料,全村共507人,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179人(含小学在读者),初中文化程度的56人(含初中在读者),高中文化程度的13人(含高中在读者),中专文化程度的1人,文盲90人,其它19人教育程度栏为空。
在T村家家都有几十亩地,最多的一家现在家里只有老两口,却种着100亩地,但为什么还“不能解决温饱”?这与土地的质量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
根据T村所在的BJ行政村的耕地情况表(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比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41亩)要高出很多,但由于耕地多为旱地,人均水田面积少,主要靠天吃饭,所以农业产量不高,而且稳定性很差。2005年是宁夏南部山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庄稼颗粒无收,家家买水、买粮吃。
T村以农业种植为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吃苦耐劳的T村人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在正常年间,这里的村民通过“种田务农+外出打工”解决吃饭问题和日常花销,而在遇到灾害时,村民们则只能靠“政府赈灾物资+外出打工”找饭吃了。
表1BJ村历年耕地状况
单位:亩
年份年耕地面积其中水田 当年年末人口 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水田面积
1980年 9264 360
1158 7.98 0.31
2001年 30364 400
2647 11.47 0.15
2005年 17246 600
2782 6.20 0.22
资料来源:2005年7月的田野调查。
五、资源贫乏与行为逻辑:方式和特点分析
笔者2005年7月对T村进行了入户访谈,收集到了2005年T村曾经外出务工和现在还在外务工人员的相关资料,下面以此为基础对西北贫困回族社区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和特点加以分析。
根据T村2004年末的报表,2004年末T村全村总人口为543人,其中回族431人,汉族112人,这其中的431名乡村回族就是本文的研究总体。在431名乡村回族中劳动力共有266人②,占该村总人口的48.99%,回族总人口的61.72%;2005年,该村曾经外出的回族人口为33人,占该村总人口的6.08%,回族总人口的7.66%,回族劳动力总人口的12.41%。
(一)T村回族劳动力流动特征描述
1.流动者的性别结构。
性别
频数 频率 累积频率
男
24 72.73 72.73
女
9 27.27 100.00
合计 33 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7月田野调查
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冯海发,1997)中国跨区流动的农业劳动力中,性别结构的总体特征是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男性占75.19%。女性占24.81%。在东部地区男性占70.49%,女性占29.51%。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人数中,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28.10%和17.70%。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女性农业劳动者流动比例最低,而地处边陲落后黄土高原地带的回族社区女性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为27.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略低于东部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部回族社区女性的外出都是短期外出,而且主要是从山区到川区去从事其他农业活动,T村2005年外出的女性主要是到省会附近农村摘枸杞,而一年中最多只有3个月的时间能为她们提供这样的工作机会。2.流动者的年龄结构。
年龄(岁)频数频率累计频数累积频率
18岁以下515.155
15.15
18—35 2060.6125 75.76
36—59 824.2433 100.00
60岁以上 ____
____
合计
33
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7月田野调查
从年龄上看该社区流动劳动力以18—35的青年人为主,占60.61%,36—59的中年人次之,为24.24%,也就是说流动劳动力中84.85%是青壮年。这同全国的整体情况(95%的跨区流动者为青壮年)趋同。但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该社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流动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为15.5%。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西北贫困地区的失学率相当高,他们一般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承担起来了养家的重任。
3.流动者的教育结构。
受教育程度频数 频率累积频数 累积频率
文盲
515.15 5 15.15
小学
22
66.67 27 81.82
初中
515.15 32 96.97
高中
13.03
33 100.00
总计
33
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7月田野调查
在1996年全国流动农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者占9.77%,初中文化程度者为54.14%,小学文化程度者31.58%,文盲半文盲率仅为3.76%。(冯海发,1997),而到了2005年,T村流动者的文化水平依然很低,在所有流动的33人中,仅有5人念过初中,1人上过高中,共占18.18%。大部分流动者只念过小学,文盲率也偏高。
4.流动者的就业地域分布。
地域分布 频数 频率 累积频数累积频率
乡内 7 21.21 721.21
县内乡外 4 12.12 11
33.33
省内县外12 36.37 23
69.71
省外10 30.30 33
100.00
总数33 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7月田野调查
从流向上看,33名流动者中,流出社区之外但留在县内的(即本县乡镇和县城的)有11人,占33.33%;流出县外,但仍留在省内的共有12人,占36.37%,两者合计69.71%;流向省外的有10人,占30.30%,但是这其中有3人是到河南郑州学习念经,占流向省外人口的30%,这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独特的教育传承方式。
5.流动者从事的职业状况。
职务频数 频率累积频数 累积频率
工人
2 6.06
2 6.06
个体商贩
5 15.15
7 21.21
一般体力 18 54.54 25 75.75
种植业 3 9.10 28 84.85
念经
5 15.15 33100.00
合计 33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7月田野调查
或许是流动者文化素质过低的缘故,该社区流动者的54.54%主要从事一般体力劳动。其次是个体商贩和外出学习念经者,各占15.15%,每到深秋季节,T村回族社区那些脑子灵活的人,便结伴到银川、内蒙、青海等地收购羊皮、羊毛,然后再卖到兰州等价钱较高之地,这和回族善于经商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二)资源贫乏与行为逻辑:流动方式和特点分析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指出,虽然理性选择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起的,但它至少也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拥有许多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相对容易;相反,资源较少或没有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是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二是社会制度。制度约束可以提供积极与消极的制裁措施,以鼓励某种行动和削弱其他行动。(Ritzer,G.1996)正是因为受到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西北回族社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了不同的方式和特点。
第一,以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流动为主。西北贫困回族社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农民非农就业的道路,首先他们大多不是直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是有一个从山区到川区打工的过程,比如独特的“麦客大军”、“摘枸杞大军”的形成;其次他们的外出就业首先不是依靠自身的乡土关系网络求职,而是依赖政府劳务输出。向省外的农村地区流动主要是到新疆、内蒙古等地区,也形成了独特的“摘棉花大军”、“捞头发菜大军”。
对于农民外出就业的路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已经从同质人群构成的初级社会网络拓展到异质人群构成的次级社会网络,从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拓展到政府和市场提供的制度化路径,且市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王成斌,2004)也有的人提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还有多大的疑问?在西北贫困地区,连年的干旱,庄稼颗粒无收,外出就业是他们摆脱经济困境,解决温饱的主要途径,政府也把这作为一个大工程来抓。而他们的外出主要依赖政府的劳务输出,劳务输出已经成为部分贫困农民的“铁杆庄稼”,象东部其他农民工那样依赖自身的乡土关系网络外出务工的西北乡村回族很少,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西北贫困地区乡村回族的劳务输出以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的流动为主的特点。2005年8月25日下午,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火车站上人头攒动、彩旗飘飘。3000多名头戴白色标志帽、携带各式包裹的农民工踏上赴新疆采摘棉花和西红柿的专列。这是固原市委、政府大规模组织的南部山区群众赴新疆劳务输出的第一批务工人员。这次输出到新疆的务工农民预计在3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人能挣到2000元左右,比当地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还多。这对帮助农民增收、降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向城市的流动规模小,主要是在城市边缘地带从事重体力活,陷入了“低水平社会资本”的“社会隔离圈”困境。就全国范围内来说,整个西北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比例相对较小。据2000年的统计分析,在全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本文所指的西北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宁夏18.89%、甘肃15.20%、青海11.09%、新疆4.44%、内蒙8.85%、陕西22.23%; 而转移比例最高的上海则达到65.36%。③
在2005年T村曾经外出务工的回族劳动力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进城务工带人的是纯劳动力要素,主要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从事一些重体力活,如压下水道、挖沙、铁矿、搬砖等等,实际上与城市是相对隔离的。以T村为代表的西北贫困地区乡村回族的劳动力流动实际上陷入了“低水平社会资本”的“社会隔离圈”困境。“社会隔离”是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等人在对美国城市贫民区居民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通过正式途径(即市场途径)找到工作。因此,他们只有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工作机会,但由于居住在贫穷的社区,他们周围的邻居及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也多与其本人一样的贫穷无业人员,因此他们也很少有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质量更高的工作。这样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帮穷,越帮越穷”现象(Wilson,1987;Elliott,1999)。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下岗职工中也相当普遍。
西北乡村回族劳动力流动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回族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偏低。一个文化素质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仅难以有效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即使就业了,也难以取得较高的收入和保持就业稳定。
2.收入低。从外出收入看,西部外出农村劳动力平均年收入是4014元,分别比东、中部外出者少3817元和201元。④ 而在T村外出回族农业劳动力平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年平均收入。
3.职业多为干重体力活。在特定的制度、文化约束下,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时面临着的机会结构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但也因进入者所携带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差异,以及所进入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领域中需求、制度、文化约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西北贫困地区的乡村回族来说,普遍文化程度低,进城所拥有的是单一经济要素——劳动力,再加上他们流动的地域主要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所以他们进城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多为一些重体力活,比如:在城郊挖地基、压下水道、在砖厂抬砖、挖石头、拉沙子等等。
4.工作稳定性差。从工作稳定性看,全国平均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40%没有固定工作,经常变换工种和地点。而对西部打工者,无固定工作的比重高达46.7%,相比东、中部外出打工者分别是36.7%和36.9%。平均外出月数,西部是8.4个月比东部少1个月,比中部少0.3个月。⑤ 而对于回族劳动力的转移来说,由于受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不稳定性更强。对T村的回族劳动力来说,他们向其他农村地区的流动主要还是和种植业打交道,季节性很强;向城市的流动,由于主要是干建筑业等重体力活,而且流动的地域也主要在新疆、内蒙等地,受气候的影响大,一般每年10月份左右,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他们不得不返乡。
五、结语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大量消化农民人口和各民族人口的融散的统一,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城市不可能形成单一民族的聚居模式,城市人口结构的族裔背景必然是多样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是多样的。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在全国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他们在城市迁移就业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不是普遍存在的“农民工”问题所涵盖的,按照通常农民进城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背景,是难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况做出判断的。西北的回族更有其独特性。在西北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条件依然艰苦,到城市迁移就业已经成为摆脱经济困境的最主要策略。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迁移就业不完全是个人行为,也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结果,它要受到已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因为“人类不可能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地点,人类只能在即存的脉络中,直接面对社会与空间结构。”⑥回族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乡村回族的城市迁移就业将受到更大的制约,关注西北贫困地区乡村回族的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注释:
① 西北区域的地理范围在学术界是模糊的,传统上指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新世纪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西部的省区包括了在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鉴于历史上密切的民族交往和文化联系以及现实机遇的同等,因此,本文的西北区域指内蒙古、陕、甘、宁、青、新等六省区。目前这三省三区占国土面积的42.35%,生活着20多个民族。这六省区不仅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台,而且今天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
② 这里的劳动力是按18—60周岁计算的。
③④⑤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乡村劳动力调查基层表”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状况专项调查的数据。
⑥ S 肯德里克、P 斯特劳:《解释过去了解现在》第19页,王辛慧等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