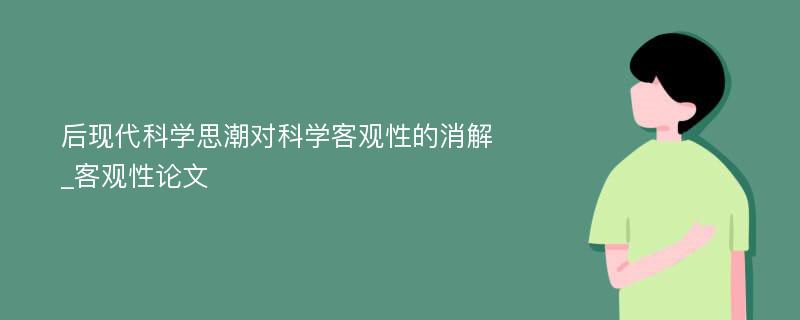
评后现代科学思潮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客观性论文,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1-0050-06
后现代科学思潮为融合“两种文化”所做的种种努力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其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倾向,那就是它对科学与人文两者界限的无原则消除,放弃科学应有的严肃性,以否定、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为代价,求取两种文化分裂问题的解决。这种解决显然只是形式主义的,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真正的目的,而且会使问题日趋严重。因此,我们对这种消极倾向必须引起注意并努力加以避免。
一、对科学客观性的根本否定
后现代科学思潮是后现代思潮的流派之一。一般可以认为,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是其典型代表。主张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的大卫·格里芬等人较好地避免了否定性的后现代科学思潮的偏颇,因而不属本文论述之列。范·弗拉森(B.C.Van Fraassen)等后现代科学论者的科学观,在本质上与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等人一脉相传,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为对科学客观性的否定。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旗手库恩创立“范式论”后,使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他看来,科学的范式并非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科学共同体在特定的心理条件下的相应信念,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使用的工具。所谓科学发展或进步,其实也只不过是“范式”的不断更换过程。这样,科学就只有好坏之分而无真假之别,谈论其客观真理性就成了奢谈。他断言,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观是幼稚的,波普尔所主张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过程的观点也是荒谬的,科学认识仅仅是心理学、社会学或语言学的主观过程。库恩以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否定科学及其发展的客观性,否定科学与其它知识甚至迷信的界限,他的科学观引发了科学哲学界至今尚未停息的科学真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实在论者坚持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从理论上对客观世界做出真理性的说明,而反实在论者则秉承库恩的观点。这种争论正是两种文化问题在科学哲学界之争的具体表现。
秉承库恩科学观,范·弗拉森声称,科学的目的就是给出经验上合适的理论。因此,科学的本质最终只是与个人的可观察经验相符合。由于个人经验必然受到个体主观心理因素和各种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因而表现出个体和文化的差异性,并因此使得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现象再无本质的区别。与库恩“范式不可通约”论相通,罗蒂认为科学理论在选择和竞争上并无标准可言,有的只是科学共同体的一致意见,或对某种范式的约定。科学理论是否成立完全取决于科学共同体是否认可和遵循某一范式。他因此说,谈论科学的客观性或说“硬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科学家并非去发现预先存在的事物或现象,而只是为某一特定的目的提供一种有用的世界描述方法,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有一种人为的有用工具,而非超然、客观的东西。从此可见,要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真理与谬误加以区分是困难的,更不能指望以客观性作为文化中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肯定某一理论,实质上是由于社会共同体各成员具有共同的兴趣、目标和准则而互相亲和的结果,科学是一种非强制性地达到主体间一致性的教养、礼仪、德性,是“合情理”的东西。理性和非理性、艺术和科学之间并无根本区别,人文学科同样可以称为理性的学科。作为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与其说科学有客观性,不如说它有“亲和性”,因此应放弃客观性,而以主体间性作为其理论标准。
费耶阿本德比库恩、罗蒂走得更远,他对于科学各观真理性的否定更为彻底。在他看来,“科学有其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的说法纯属神话。科学史表明,任何科学成就都是通过破除已有的方法而获取的,只有不断地“反对方法”,只有做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并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和科学观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色彩,按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每一个陈述、理论、观点和证明都有利于推动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即使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各方也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真的,不存在单一真实的“故事”取代与之冲突的“故事”的现实性。相反,“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1](p76)“相对主义认识论”“在揭露了客观主义框架的重要遗漏之后,以客观主义者自定的标准观之,客观主义就从其内部被瓦解掉了”。[1](p87)科学再也不能与客观真理、理性划等号,它只是众多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其中并无什么独特的方法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是虚妄的,科学与非科学甚至与伪科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文化传统,其中并无优劣好坏之分。
科学哲学的新历史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劳丹也坚决反对科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事业的观点,他主张科学进步在于解题能力的提高。对于促进科学进步的因素——社会文化的外在作用和科学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的各自地位,以及两者之间的界限等问题,劳丹由于远离了客观实践标准而无法清楚地加以回答。因而他只好说:“我们必须将评价之网织得足够宽广,以包括实际存在于历史背景之中与认识有关的一切因素。”这样,哲学、宗教、道德等也能够成为“科学的”了。“如果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具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宗教学说或哲学学说,而那种文化的思想家认为这些学说对于了解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根据科学理论或新研究传统是否被纳入到这一先验的信仰的预想体系之中来对之作出评价就完全是合理的。”[2](p122)可见,劳丹所持的认识论亦是相对主义的。当注意到科学认识及其结果——科学知识并非纯粹客观的时候,他是对的。然而,当他与库恩、范·弗拉森、罗蒂、费耶阿本德等人一样,走到了否定科学客观性一端,因而必然导致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并非对客观真理追求的时候,他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了。
二、消解科学客观性的解释学途径
后现代科学思潮如何消解科学客观性,其具体途径是否真实可行?不同的学派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具体方法途径。其中,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被人们公认为后现代思潮的先启者,他所创立的“语境分析法”为这一思潮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开了先例并提供了基础。[3]我们从此即可窥见后现代科学思潮对科学客观性是如何加以消解的。
伽氏认为,理解是普遍的,理解与人的存在有同一性,有存在就有理解和解释,理解甚至成了人存在的本体。理解无疑也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罗蒂曾着力加以阐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是分别以说明与理解、解释来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并认为说明与理解、解释截然不同,故而科学与人文之间就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与此相反,罗蒂认为对科学事实的说明依赖于理解或说解释,说明即理解,说明即解释,说明与理解实际上密不可分,从解释学意义上说,就是依据熟知的东西使被说明的东西成为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已有的理论观念与成见构成了对事实的认识,一切关于“事实”假设的描述,无非都是理论解释而已。自然科学不可能离开理解和解释,而必须从人文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完整的解释性理解,以作为说明的基础。这样自然科学就在许多方面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同属解释学范畴。科学理论离不开人文因素,这在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那里已得到确证。罗蒂因此进一步归结说所有的学科之间都有着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在于解释学的理解和解释,而不在于自然科学的描述方法和说明规范。
伽氏反对科学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论方法,极力纠正将逻辑与心理、事实与价值、精神与世界等进行机械二分所造成的偏颇,使主、客体关系从对立走向协调。具体的途径是以其“语境”为基点,从整体性、具体性和多层次性角度考察科学理性,即可发现科学不仅由逻辑所规定,而且还被语境历史地决定着。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乃至整个历史时期就都应视为文本加以阅读,如此就不能不关注和强调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性,自然科学因而就不再是一个具有特权的或者纯粹客观的真理,科学与人文两种知识就不能像科学主义者那样加以绝对划界,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联结因此得以重构,科学理性得以融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学的现实之中,其单纯的形式理性权威从而被消除,科学与人文相互渗透与融合从而成为可能。
伽氏的“语境”,从内涵上说是指为意义确定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这正类似于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中的“支持线索”或说“支持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皮亚杰的“认知图式”,还相当于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说的某一学科的“概念框架”或马赫的“先行观念”。所有这些都是指人们理解与接受新知识的背景与前提,它们可以是某一理论或范式,或者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历史背景,甚至可以包括所有社会、历史、政治、科学和心理等因素及其相互联系和作用。[4]仅就“语境”而言,它又可以狭义地指称为与意义理解相关联的上下文词语或某一特定的文本。伽氏认为,任一词语的意义都必须根据语境才能给出正确的理解。传统解释学由于受到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而主张返回相应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文本,以为如此可以消除理解主体的偏见与误解,进而达到对文本完全、客观的理解。其结果不仅令理解主体与客体截然分离,而且终令消除主观性,追求绝对客观性,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目标无法达到。伽氏认为,理解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理解主体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历史和社会所“污染”,先行的观念或理论无疑要影响理解活动的整个过程,他的这一观点正和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所指称的“理论先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相一致。他进而还指出,偏见也必然地参与理解活动,这与极力排除偏见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正相反对。诚然,伽氏在此所谓的偏见并非平常所指的谬误,而是指在特定语境下主体的某种意向性,或说是在“支援背景”下归结出的对事物加以理解的某种趋向性。海德格尔曾认为,任何理解活动都是基于“前理解”的,理解活动就是前结构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式。伽氏的“语境分析法”实际上是对海氏上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玻尔把微观领域中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关系,形象地归结和比喻为:“在现实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相似地,在伽氏“语境分析法”之下,理解的主体与对象也不可截然分离。伽氏以“游戏理论”考察“理解”活动,指出正如“游戏以及决定游戏的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一样,理解不在理解者或理解对象上,而在于两者的相互作用过程或说在于理解活动本身,理解者与理解对象——文本是相互交融、相互统一的,他用“视界融合”来指称这一现象。他的这些观点与皮亚杰“认知不在主体那里,也不在客体那里,而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也与波兰尼的“双向内居”即主体和客体各自的特性相互融入对方的观点相一致。伽氏明确指出,理解的对象是语境化了的对象,而语境则是对象化了的语境,两者之间不能相互超越而独立地存在。相反地,它们是相互依存和渗透、浑成一体的。一切意义的形成皆有赖于特定的语境,它不可能是由理解主体完全以主观的概念框架、信仰去规范对象所形成的纯粹主观的认识结果,也不可能是完全摈弃了主体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而获得纯粹客观的认识结果,而只能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和协同的结果。因此,对于理解对象的任何客观知识都是无法达到的,所能达到的只是一种关于意义的“约定”。这显然正与彭加勒的“约定论”相应合,罗蒂的“亲和性”又是这种约定论的翻版。伽氏似乎达到了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因为从他的“理解语境”观看来,理解已非仅为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联系,也非主体能动地认识客体的主观精神活动,而是一种关系和过程,其中并无主客体的严格区分,理解主体与对象两者的视界交互作用或说双向运作,其结果是产生新的视界,这一新视界既包括理解主体又包括理解对象的视界,二者已相互交融,难解难分。这就会导致如海德格尔所推论的同样结果:真理根本就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互符合的那样一种结构了。真理的获取不再是发现而是发明,符合论的真理观在此已不适用,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从而被消解,并被代之以约定性和工具性。伽氏的“语境分析”理论为后现代科学思潮各学派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起到了开启、奠基的作用,在其之后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如库恩、罗蒂、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相关理论观点,实际上可视为其理论观点的继承与演进,并日益走向彻底和极端片面化,乃至完全否定了科学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并对反科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消解科学客观性的内在根据
从伽氏到所有的后现代科学思潮各位主要代表人物,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把科学视为纯粹客观的观念的批判,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在具体的论证上也是有力的。他们关于科学乃至一切知识皆无可避免地包含有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或说非理性因素,可从自然科学本身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事实中得到证明。
所谓的现代科学在此是指20世纪所创立的科学理论,其中尤其是指量子论、相对论、系统科学等使人们的科学观乃至整个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学科理论。正是由量子论、相对论和系统论等构成的现代科学改变了传统的科学观念,使整个科学图景不再以“纯粹客观”的面孔呈现,而是以“人性化”或说“人文形象”展示。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在20世纪,对人类科学贡献最大的是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对人类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上存在着最大争议的也是这一学科,了解量子论对经典物理学的超越,就成为认识现代科学及其对人们的科学观和思维方式变革的关键。
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实验,冲破了经典物理学的框框,人类的科学认识,在真理性问题上经历着一个由绝对走向相对的辩证过程,量子力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量子力学中,种种不能为经典物理学解释的新的物理实验现象得以解释,“波粒二象性”得到了确认,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随机的几率现象在微观世界中起着关键的和支配的作用,量子论的哲学意味并非显而易见,因而也就不能轻易地加以理解,这就无怪乎会引起由两位伟大物理学家为首的“世纪之争”,即著名的“爱因斯坦和玻尔之争”,并由此引发了后来的对于世界本质上是决定论的,还是随机偶然的争论。至今有一点已经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微观领域中,科学主体与客体之间已经不像在宏观世界那样有着绝对分明的界限。海森堡曾就此指出,几率函数运动方程中包括了量子运动与测量仪器相互作用的影响,因为在观测与认识微观世界时,必须通过仪器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改变,才能得到相关的知识。而只有当测量仪器与观测者之间有相互作用时,前者才有意义,如果两者之间相互隔离,毫不相干,那么测量仪器也就不成其为测量仪器了,更谈不上发挥测量仪器的功能了。从此可见,测量仪器对被认识世界的干预和作用,归根到底是人的干预和作用,科学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一个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这正是玻尔有关“演员”和“观众”比喻的含义。哥本哈根学派的“互补原理”表明,电子等微粒的波动和粒子的二象性、位置和速度之间都是互补的,对微观世界中所发生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以及对它们的决定论描述也是互补的。主客体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结果,也就具有了波兰尼所谓的“双向内居”的关系。作为认识结果的科学理论既然是认识主体对自然世界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就必然包含着人的因素,即包含人的激情、兴趣、价值观、世界观等非理性(而不是反理性)因素。量子论的创立,使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微观领域观察过程的复杂性已表明,科学认识主体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科学及其认识结果并非纯粹客观的,这在当今已成共识。
后现代科学是当今科学认识发展特征的极端产物。量子力学明显地表现了当代自然科学与现代主义许多相反对的特征,例如,在量子论中,微粒的所有运动都可以在一个非连续的、不可分的、被称为量子的单位中加以描述,这就与传统机械论的物质运动观相对立。又如,量子论表明,对微粒“波粒二象性”的理解和把握必须依赖于实验条件和环境。对物质性质的认识有赖于物质所处环境的结论,是与机械论那种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物质的性质稳定不变的观点相冲突的。有学者因此认为,量子论的诞生标志着后现代科学的形成。[6](p182~183)此外,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的反映,同一事物可以多种方式方法描述,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所作的描述不尽一样,人们因此可以选择那些符合“人性”要求的方式。例如,最子力学创立初期,存在两种等价的形式,一是海森堡、玻恩等人建立的矩阵力学,另一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由于后者符合审美等要求,较有“人性”而为人们所肯定和选择。量子力学已令科学图景明显地以人文的形式展现,如果再放眼到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更会发现“人性因素无处不在”,无论如何强调自然科学认识结果的客观性,认识主体人的主观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必要的,并且也是无法完全排除的。从根本上看来,科学虽然不能像波兰尼那样认为是“个人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属人的而不是非人的知识。科学史家丹皮尔曾指出:“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6](p20~21)科学负荷审美、伦理道德等价值因素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尤能证明这一点。因此,科学再也不是无人和纯粹客观的,而是有人及人文因素的科学。在这一意义上,自然科学已经与人文学科相类似。
当前,不仅在微观、宏观且在宇观层次上皆发生了一场思想变革,这场变革以系统科学和演变科学,尤其是以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为标志,其意图是对包括牛顿力学、相对论甚至量子力学在内的经典物理学及其科学思想的超越。这场革命已波及所有领域,人们的思维焦点已从简单世界转向复杂世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必须予以有机整合认识的世界中,人的因素,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已成为人们必须关注的重要因素。从伽氏至库恩、罗蒂和费耶阿本德都一再强调科学中的人文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确切地说,打破“科学纯粹客观”的神话的企图至今已经达到。换言之,现代科学的后现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为伽氏等人消解科学客观性提供了内在依据。
四、科学客观性能否彻底消解
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因而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而人文知识则是纯粹主观的,因而就不具有真理性。这样,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就是互不相容、互相冲突的。后现代科学思潮消解科学客观性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根本上批判科学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打破、铲除了科学主义者所依赖的根基—科学是惟一客观的知识的观念,就能使科学靠拢、甚至归化于人文知识。后现代科学者破除科学是惟一客观的知识的观念的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达到了。然而,使科学靠拢、甚至归化于人文知识的企图却落了空。
科学认识结果带有主观性至今已不难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其客观性。就量子物理学来说,它也并没有否定认识结果的客观性,而只是认为在量子物理学中的客观性是包括主体因素在内的而非纯粹自在的客观性。正如海森堡所说:“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7](p22)微观世界的人化只是在量子物理学的实验中发生,而非在人的意识中发生,因而这种人化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客观过程。量子论所揭示的微观世界,虽不是牛顿式的必然真理,而是或然真理,但是,坚持客观性原则,尽可能达到客观性认识仍是其不懈的追求目标。微观世界的客观性是不可否定的,那种由于对微观粒子的观测难免人为的干扰就以为微粒客体成了主观的东西是错误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早就指出:“由于概念的形成依赖记忆,由于这些记忆与个人相应可能涉及不同个人的经验的截然不同的部分,因此概念总是具有依赖于个人的成分,或说主观的成分。”然而,科学又可以通过吸收尽可能完备的经验,弥补个人记忆的主观不足,从而填补经验中的主观间隙,接近客观性的理想。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除了在形成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中的主观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因素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直接加以考虑的客观特征,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着客观部分。”[8](p25)科学认识结果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而且客观性居于支配地位,两者的辩证统一性表现为主观性与之符合的客观性。科学理论如果失去了客观性,不再是客观对象的反映,而变成了纯粹主观臆造的东西,就不成其为科学,就不可能有什么像罗蒂等实用主义者所指望的那些实际用途,其存在就毫无意义。
后现代科学思潮对“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观念的批判是正确的,其对科学中内含人文因素即内含人的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因素的论证也是有力的,因而在较大程度上破除了科学是与人性无关的传统观念,这是其可取之处。然而,当其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并推论说科学其实与人文知识一样没有什么客观性,有的只是“约定”、“亲和”,真理也只不过是对付环境的有用工具时,就已从一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因而就成了谬误。矫枉过正,必然是过犹不及。若按着他们的路子走下去,必然是达不到使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协调统一的目的的,从罗蒂令科学向人文归化的失败,到费耶阿本德无奈地对科学与人文融合问题加以消解,就是证明。[9]
[收稿日期]2000-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