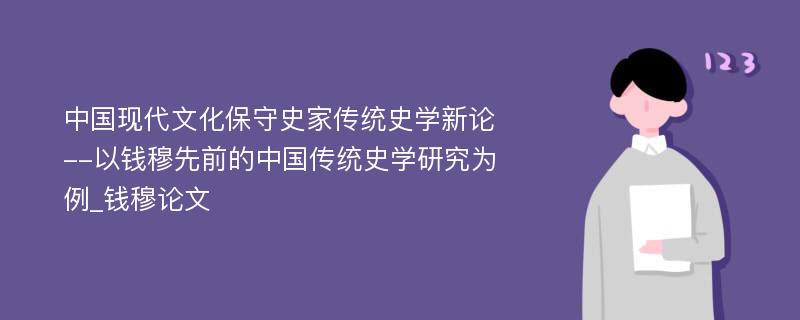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保守主义论文,史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4-0001-07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全面批判,主张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建构中国新史学以来,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进而建构中国现代新史学,便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核心问题。各派反传统史家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及其对现代新史学建构所具有的本质意义,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则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其中一些史家还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书写出与反传统史家不同的中国传统史学史。钱穆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之一,其史学思想以1949年离开大陆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传统史学的诸多方面,并提出了“史学殊无新旧”论,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建立新史学,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新史学体系的建立便是该思想的落实。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这一时期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及新书写,既是认识钱穆史学思想演变的基本途径,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史学界如何书写传统史学及其与现代新史学建立关系这一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系统的全面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考察和评析。 一、“礼”、《书》、《春秋》与中国史学的起源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史学起源,是决定中国传统史学书写谱系是否客观和科学的根本因素之一。钱穆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记载的内容及其功能来探讨中国史学起源和早期发展。他指出,先秦典籍分《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即“礼”,舍礼无历史;“史”、“礼”、“法”,古人一以视之;古人学问唯“礼”而已,守礼知礼者则“史”。《春秋》记载人事后,中国史学得以发展。 在讨论孔子与儒家六经的关系时,钱穆指出,先秦典籍“约而举之,不出《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凡申叔时所谓《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皆属之。《诗》者文学,凡申叔时所谓《诗》、《乐》皆属之。《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盖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春秋》、《世》、《语》、《故志》、《训典》之类是也。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是也。而后王本朝之制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旧贯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史实之变动,新例之创兴,而礼法亦随而变。……‘历史’即‘制度’,而《诗》、《乐》本包括于礼制之中;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唯‘礼’而已,其守礼知礼者则‘史’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1](P22)还强调:“至增孔子《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为六,而因以名之曰‘经’,此皆后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1](P23)可见,先秦时,经亦史,六经皆史,而史皆礼。钱穆在谈到春秋时期学术发展时亦指出:“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大祭前有会猎,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2](P93)封建家族和国家的祭祀活动及其记载,即是以后的历史,且偏重于政治和宗教的内容。同时,“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2](P93—94)。这里谈的是对祝史从事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异相关礼仪活动的记载,也成为后来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因此,他总结说:“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2](P94) 此后,钱穆又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对此观点作了补充和修正,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发展及其特征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典籍流传至今者可分两类:一是“礼书”,“‘礼’本是指宗教上一种祭神的仪文……中国古代的宗教,很早便为政治意义所融化,成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礼,亦渐变而为政治上的礼。……中国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为伦理意义所融化,成为伦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礼,又渐变而为伦理上的,即普及于一般社会与人生而附带有道理性的礼了”[3](P72)。此言阐述了“礼书”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很早就摆脱了宗教性,而兼具政治与伦理性。二是“春秋”,“我们现在不妨称之谓‘史书’。中国人是最看重现实人生的,因此他们极看重历史。发展最先的《诗》、《书》,早已是一种极好的史料,而还不能说是严格的历史。从西周中叶,周宣王以下,直到春秋时代,孔子以前,中国各地史书便极度发展,当时有叫‘百国春秋’与‘百国宝书’的,可见当时的史书和礼书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列国之间了”[3](P74)。钱穆修正了原来的观点,将原属“礼书”的《春秋》单列为孔子以前典籍的一类,意在突出西周中叶以来各国《春秋》编撰在整个中国典籍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史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此外,还揭示传统史学发达的原因,即中国最看重现实人生,故而看重现实的历史,由此重视历史记载。 钱穆将礼、诗等中国早期典籍与中国史学起源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中国史学起源于“书”和“诗”,因这两类典籍记载的内容均是与“礼”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春秋”记载人事后,史学得以发展。春秋时期,中国文献分礼书、史书两类,是由中国重人事即重历史的文化精神决定的,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和特征决定了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发展方向。钱穆从中国上古历史发展及其文化精神的角度、而非仅从史学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发展和特征,这无疑是深刻和精卓的识见。 二、中国史学的自由、人本精神与历史认识的理性主义 中国史学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钱穆认为,中国早期“史”职的演变表明中国史学脱离了宗教和皇权政治的束缚,具有了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而中国学术从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兴衰,则体现了中国史学脱离政治势力走向自由和人本的精神。此外,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态度又含有浓郁的历史理性主义。 钱穆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与欧洲中古不同,自孔子作《春秋》后就脱离了宗教羁绊,“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汉代太史属太常,仍为宗庙职司一员,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迁不以此自限,发愤著《史记》以续孔子《春秋》,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东汉班固,以非史官为史下狱,得释后以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2](《引论》,P16—17)。通过考察孔子、司马迁和班固撰修史书的发展过程,钱穆阐明了以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到东汉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和政治的束缚,转变为自由的民间学术,这种学术自由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具有自由精神,还具有人文精神。钱穆认为,先秦的王官之学流为百家,于是“史官”外复有“博士”,两者同为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的官吏。“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博士官”则为新兴百家学的代表。到汉武帝采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博士始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的学者,同时兼负国家教育之责,博士弟子遂为入仕唯一正途,“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四百八十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一百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具‘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2](《引论》,P17—18)。通过对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考察,钱穆阐明了中国学术及史学重人生伦理教育、脱离宗教而将人生意义寄托于现实世界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人本主义此后主宰了中国传统学术和史学的发展路向。 中国史学的另一基本精神是历史认识的理性态度,这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根源之一。钱穆说:“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2](P6—7)而且,“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2](P9)。钱穆从古人编撰中国古史所蕴含的历史人文理性精神来揭示中华文化和史学的积极意义,发掘出中国传统史学和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亦批驳了随意否定中国古代古史编撰真实性的各种疑古史观。 钱穆通过对中国古代早期发展史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考察,发掘出传统史学所具有的自由、人本和理性精神,显示了他力求在理论高度来揭示中国史学的本质和特征,也回击了近代以来诸多反传统史学家指责传统史学的专制性、愚民性、不科学等诸多违背现代史学精神和价值观的简单化做法及各种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 三、史书体裁的创新、通史撰述与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向 重视从中国古代史学体裁丰富性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道路,是钱穆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他认为,多样化的传统史书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特别是通史体裁的创立和不断完善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突出反映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变革路向。 钱穆强调,中国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历史记载最完备的国家,根源在于不断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2](《引论》,P1)。结果是,“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唯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4]。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之优长是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创写新的历史,“通史”的创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尤害新史之不断创写”[4]。钱氏认为,《尚书》为最初史书,然书缺有间;《春秋》为最初编年史,《左传》网罗详备,为编年史之进步;《史记》为以人物为中心的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团体性而崭然露头角;《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始,适应了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始有杜佑《通典》为政书之创作,乃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继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乃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乃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郑樵《通志·二十略》的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家谱、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然而,南宋以来,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未出现好的通史,可谓“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时至今日,“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2](《引论》,P8)。 可见,钱穆注重从历史知识的表述和书写方式——史书体裁,来考察中国史学的进步与革新。他认为,新的史书体裁尤其是通史体裁能从更多角度和方面记载历史事实及容纳各类历史知识。史书体裁特别是通史体裁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即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进步与发展,会通精神与方法是中国史学传统和精神之所在。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中国古代史家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和编撰中认识到,不同社会历史内容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认识与书写,因此,他们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综合贯通各种体裁,取其长以补其短,不断创造新的体裁来书写历史。这是史学表达形式——历史编撰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进步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钱穆继承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结合时代精神,认为通史体裁最能记载和反映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体现中国历史延绵不绝的精神,因而代表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正轨和极则,撰写新的中国通史是中国现代史学建立的基石和标志所在,他声言: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2](《引论》,P8)。 钱穆主张创建以通史为模式的新史学,亦在批判中国现代史学界诸多片面强调历史考据和专精研究的风气。他声称:“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2](《引论》,P8)抗战时期,他撰写《国史大纲》,即是将此史学理论付诸实践的重要成果。 四、中国古代史家与中国史学思想 钱穆在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时对中国古代史家多有涉及,尤为推崇取得通史成就和拥有通识意识的史家,如孔子、司马迁、杜佑、司马光和郑樵等。不过,钱穆论述较多的则是孔子、黄宗羲和章学诚,从中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诸多独到认识。 钱穆高度评价了孔子及其《春秋》的史学思想与成就,称其奠定了中国史学及文化的发展道路。他称赞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视野之第一个”。“而《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民间史之创作。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而孔子即为中国最伟大之史学家,又为第一史学家也。”[2](P100,100—101)孔子的《春秋》有三大功绩:“为史记编年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功三也。”[1](P12)后来,他对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史学和文化史上的贡献作了进一步阐述:“第一:是孔子打破了当时国别为史的旧习惯,他虽根据鲁国国史,但他并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在他的新史里,却以当时有关整个世界的霸业,即齐桓公、晋文公所主的诸夏城郭国家和平联盟的事业为中心。第二:是他的新史里有一种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底人生批评。他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如楚国、吴国等,其先虽因其不能接近诸夏文化体系之故而排之为夷狄外族,到后来亦随其文化之演进而升进之为诸夏,与中原诸国平等看待。第三:史书本来为当时宗庙里特设的史官之专业,现在由孔子转手传播到社会,成为平民学者的一门自由学问。”[3](P74—75)总结和归纳钱穆对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化史上贡献的评述,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开始将原属王官学的史学变成民间学,使之成为全社会共有的学术;二是《春秋》为中国史学编年之祖;三是汇国别史为通史,具有世界史的观念;四是在民族文化观上,既倡导尊王攘夷,又以文化高低来区分诸夏与夷狄;五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褒贬史事和人物。钱穆的上述评价充分揭示出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作用,体现了钱穆史学思想的新儒学特征。 钱穆认为,宋代以后的史学走向“衰微之末运”,对清代考据风批评尤烈。然而,他对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认识及评价又是历史和具体的,如高度评价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和清代中叶的章学诚在学术尤其是史学上开时代风气的贡献。 钱穆突出强调了黄宗羲“以经史证性命”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分析了黄宗羲史学的特点,指出其治史有两个特点:“一曰注意于近代当身之史。……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此其治史注意于当身现代之史,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研古者一也。二曰注意于文献人物之史。……此其治史注意于文献人物,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考订者又一也。此种重现代、尊文献之精神,一传为万季野,再传为全谢山,又传为邵二云、章实斋。浙东史学,遂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5](P35)钱穆充分肯定了黄宗羲史学及其对浙东史学创立的作用,既是对清代学术史和史学发展的新解释,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误读清代学术中经史关系的有力批评。 关于章学诚的史学成就与地位,近代学人均以文史家目之。钱穆则称,其经史之学突破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樊篱,切中了乾嘉经学考据积弊,是清代乃至中国学术史上扭转风气的史家。对此,钱穆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第一,阐发了章学诚即事言理、以人伦日用求道和学贵实用的经史思想,破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樊篱。他说,章学诚于汉学攻击颇为深刻,“曰:‘六经皆史也。’‘古之学不遗事物,未尝离事而言理。’‘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不足与言道。’‘搜罗遗逸,襞绩补苴,不足与言学。’‘故学务当今而贵实用。’因谓圣人学于众人,大成集于周公。而卒归于浙东学术,言史,言经世,言性命,言行事,言学问,一以贯之,而溯源于阳明之教。盖戴派学术,其持论本与浙东王学相通,而其学问从人,遇为亭林博雅一途。故于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语,终不免受其牢笼。自章氏之论出,则顾氏之说自破,而吴、皖学者考核古训、古礼之精神,亦且废然而知返也。”[1](P293—300)第二,阐发了章学诚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和史学切人事的思想。章学诚说,天人性命之学,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六经中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不足言史学等。钱穆说,这些思想表明,“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5](P429)。第三,发掘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实质与意义,阐明其“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5](P430)的原因和内涵,进一步彰显了章氏史学的经世之旨。钱穆说,章氏所言“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此为实斋‘六经皆史’论之要旨。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5](P432)为此,钱穆盛赞章学诚的学术对继起的今文学派影响颇深,“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5](P433),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当两汉经学极盛之际,而有王仲任;当两宋理学极盛之际,而有叶水心;当清代汉学极盛之际,而有章实斋。三人者,其为学之途径不必同,而其反经学尚实际之意味则同。是亦足见浙学精神之一端也”[1](P300)。钱穆通过对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为核心史学思想的深入诠释,表明了自己的史学主张,即经学即史学,经史为一;史学必须切人事,义理必须从历史中求取。这些思想既对近代以来清代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新回答,又从历史角度阐明了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理论立足点。 五、史学立场下的乾嘉考据批评和史学的经世致用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论清代学术及其考据学,《国学概论》等著作对清代考据亦多有论述。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喜从史学立场着眼,他对乾嘉考据尤其是其不求致用弊病的批评,进一步反映了其对传统史学的认识。 《国学概论》对清代考据有褒有贬,与后来一意批评清代考据者有所不同。他说:“今综观有清一代学术,则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不可不谓其主要之标的。彼辈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弗待言,然乾、嘉诸儒以下,其治学方法之精密,则实有足多者。近代胡适,盛称以为合于科学的精神。”[1](P311)又称:“盖自有清儒之训诂考核,而后古书可读,诚为不可埋没之功。其学风之朴诚笃实,亦自足为后人所仰慕。然其间工诣既有高下,得失亦复互见。”“最其所至,实亦不过为考史之学之一部。”[1](P314、315)视经学为史学,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钱穆自然会受此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史学立场评述清代学术史,充分肯定黄宗羲和章学诚的经史成就与地位,批评乾嘉考据的流弊,上文已有论述,此不再言。此后,钱穆对该学术问题又颇多新论。如高度评价曾国藩在经学外扩开史学的贡献,称曾氏的《圣哲画像记》按姚鼐的学问分义理、词章、考据之说,对古代三十二位大学问家及其著述作了分类,“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引之父子),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7](P95)。钱穆推许曾氏所论考据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因为“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地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7](P96)。 清乾嘉考据的另一弊病,是背离了中国史学讲民族气节和重经世致用的传统。钱穆说:“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复绝焉。”[5](《自序》)他认为,清代学术无经世之志是满清文化高压政策造成的。“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指乾隆对士人所言之语——引者),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5](《自序》)又说:“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5](《自序》)此言对满清文化高压政策导致清代学术无经国济世的抨击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钱穆对清代考据缺乏经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情怀的批评颇为精卓,《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经典之作。不过,钱穆对清代考据在典籍整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积极影响缺乏同情的理解和评价,亦有失偏颇。 六、钱穆中国传统史学新书写的特征和意义 由上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内涵、本质特征、发展历程和现代价值作了多角度的研究,并对近代以来片面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做法及观点予以理论回击,进而提出要承继中国史学的传统来创建中国现代新史学。不同于当时阵营庞大的反传统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和描绘,钱穆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特征:一是重视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来重构中国传统史学史。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初期和晚期论述颇多,即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及其孔子的贡献,明末清初到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黄宗羲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与成就。钱穆对这两个时期史学予以集中和深入的论述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关联,即均是围绕经史不分、史学切人事以经世的思想主题进行的。他对经史关系的新解读回应了近代以来不断贬低和肆意否定传统经学价值的各种观点,对经史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这比单纯就史学论史学要深刻得多。二是站在文化的高度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内涵和普世价值。钱穆通过对学术史的考察,指出中国史学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由独立、人本主义、历史理性、经世致用等精神和原则。而这些精神与原则所蕴含和体现出的自由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理性、实用理性等,正是中国现代反传统史家批评和否定中国传统史学与文化的思想准则及方法论。因此,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内涵和精神的这种阐发,成为对反传统史学相关观点的一种针对性极强的回击,有助于人们树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价值的新认识,这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是比较少见的。三是倡导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传统本位论。钱穆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道路的研究与肯定,强调“通识”意识和通史撰述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核心理念,对历史上通史的撰述及其史家予以高度肯定,倡言“史学殊无新旧”,主张中国现代新史学应当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史学通史的继承和发展上,体现了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 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价值的多角度和多层面研究,重塑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正面形象,批驳了将传统史学与中国现化新史学相对立的做法,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发展,即中国现代新史学开出了新的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西化思潮盛行,史学界亦受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左右。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等著述中全面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主张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中国新史学的创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至深至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史学界具有统治力和影响力的新史学流派的眼中,如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疑古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及其现代价值不是遭到批判和否定,就是被忽视或贬低。虽有一些史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对传统史学多有同情和维护,在史学实践方面也有继承和发展,但多缺乏较充分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和新书写,虽显落寞,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上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然而,钱穆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史学观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相比于其晚年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1950年代以后,钱穆撰写了大量著述和文章,其中,专著有1961年初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73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名著》和1989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发微》。此外,1975年初版的《中国学术通义》、1979年初版的《历史与文化论丛》、1984年初版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著述中也收录了诸多专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论文。这些著述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和精神、中国传统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西史学比较等作了系统和深入论述,描绘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全景,深入揭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和价值。其次,如果与同时代的史家相比较,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尚不及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全面和深入。1942年,柳诒徵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等十个专题,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比中西史学及其文化,系统和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理论、发展面貌、主要特征及精神价值,1948年汇成《国史要义》由中华书局印行。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熊十力称《国史要义》“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真不朽之作也”[8](《熊十力函》)。此外,钱穆的一些观点不免有失偏颇。如他对清代考据学在典籍整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积极影响缺乏同情式的理解及更加客观的评价。 [收稿日期]2014-03-25标签:钱穆论文; 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国学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史记论文; 读书论文; 尚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