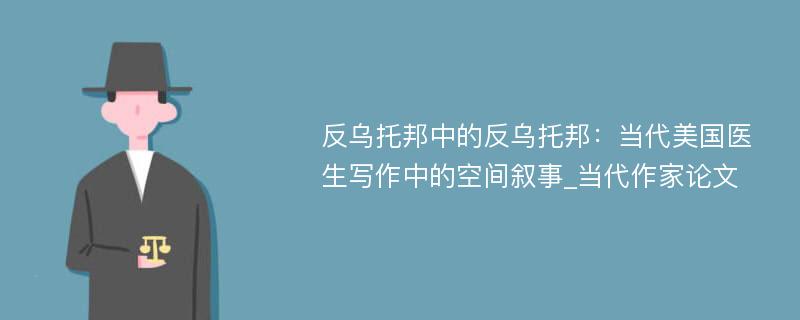
异托邦中的异托邦: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当代论文,医生论文,空间论文,异托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83-07 随着叙事理论在医学界的渗透发展,当代美国文学与医学的结合在过去四十几年里得到长足发展。美国当代文坛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医生作家,如外科医生理查得·谢尔泽(Richard Selzer)和内科医生亚伯拉罕·佛吉斯(Abraham Verghese)等。他们既是医生又是作家,他们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中间地带诉说在生死苦难面前的点滴感想,反思多重身份碰撞下的生存状况。文学与医学在美国当代语境下的结合既是文学积极参与时代中心话题的表现,也是医学界抵制理性崇拜和科技至上的狭隘理念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探索。可以说,文学与医学的结合既是文学的自觉,更是医学的自觉。医生书写(Physician Writing)①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把医学目视(the medical gaze)从患者身上内转到自身的产物,也是他们以局内人的角度从内部解构医疗话语霸权规训作用的尝试。 医生书写有别于其他文类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医院场景。无论是虚构叙事,还是非虚构叙事,医院始终在医生书写中扮演一个不可取代的角色。医院不仅是医生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促成故事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医院在控制人类疾病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先进性,但它同时也是现代医学话语霸权实践其权力的平台,是社会按照既有规范(norms)规训越界个体的场所。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体系中,医院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一直是他考察的重要对象之一。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更为理解医院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以及发生在这个密闭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1967年福柯在一次建筑研讨会上对空间问题进行专门阐述。在其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中,福柯追溯了空间理念发展的历史。[1]中世纪的等级定位空间是一个由森严等级制度划分的场所的集合,如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划分等。而伽利略的发现使人类意识到一个“无限的,并且是无限宽广的空间,”也即广延性空间。福柯的空间观有别于古典哲学和经典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他认为现代空间概念的关键词是“位置。”“位置由点和元素间邻近的关系确定……而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2]空间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单一同一的。空间是各种关系以及各种异质元素互相作用的场所,或者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由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的复合体,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基础。而如何在这些权力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常是现代焦虑感的根源。 福柯进一步指出,在这一个个权力网络中,某些特定关系的集合所定义的特别的位置便构成了异托邦(heterotopia)。福柯认为,“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3]异托邦存在于每个文明和每种文化中。其存在撕开了现代社会理性有序的外装,展示的是被抑制的和被边缘化的疯癫和非理性的世界,是更真实但同时又可能令人更加不安和焦虑的另类空间。监狱、公墓和殖民地这些被边缘化的、与现实社会异质的空间结构便是很好的例子。需要指出的是,福柯设想的异托邦具有现实和虚拟想象多重性质:有些异托邦有明确的位置,可以指认;有些异托邦在现实中并不以实体存在。按照福柯的设想,当今的网络空间以及诗学空间等都可以算是异托邦的一种存在形式。无论有无实体存在,异托邦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们能把理性世界所抑制的真实世界的另一面,如暴力、死亡、疯癫乃至狂欢等充分展现出来。这些空间结构是各种权力关系相互作用,尤其是边缘地带与权力中心抗衡的基础,更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否认,不可忽略的存在。 从这个层面上讲,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性写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场域——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异托邦;其次,医生书写创造了一个诗学空间来抵制理性至上和科技至上的职业规范以及社会规范。通过叙事,医生作家尝试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交叉空间(也是边缘空间)展示医院这个异托邦里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后果。医生书写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试图从边缘空间介入现实,建构新的自我的有益尝试。 一、偏离异托邦:医院空间 福柯在其《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梳理了西方医学发展的轨迹,重点讲述西方医学如何从古典分类医学发展到症状医学再到临床医学。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的是西方医学的三次空间化,也是治疗场景的空间变化。第一次空间化中,分类医学赋予疾病“一种组织,并被划进科、属、种的等级系列”。[4]分类医学认为,“疾病具有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5]基于此,分类医学的诊断和治疗依托于描绘疾病种属关系的表格和图像,“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6],而忽略了作为疾病发生的场所——人体。社会空间更加不在分类医学者考虑的范围内。因此分类医学所产生的是“没有深度的投影空间、一个只有重合而没有发展的空间”。[7]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序的同质的族谱式平面。正是由于对疾病朴素和本真的认识,“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没有特许的区域,也没有医院环境施加的强制——在其诞生和发展的场所自发地分化,而这种场所应该反过来又成为疾病自我消除的自然场合”。[8]这个自然场合便是家庭。这是一个最自然,也是最自由的社会空间。 在医学的第二次空间化中,疾病跟身体的关系得到重视,疾病不再是超然于身体实体的存在。对患者身体的关注使医学逐步摆脱了简单的种属归类。医生通过医学目视的作用和对身体变化等的精细感知,重新审视人与疾病的关系,并致力于复原疾病在人体这个动态空间所体现出来的厚度,或者是复杂度,如关注具体患者的动作、姿态和其他种种表现。[9]第二次空间化实际上把疾病置于人体这个神秘的空间中,并确定了医生、病人和疾病所构成的复杂权力网络。但此时医生对人体内部空间的了解仍有限。 这两次空间化产生的较为朴素的和自然的医疗实践也是当代美国医生作家关注的对象之一。从1970年代起便活跃于文学与医学领域的外科医生谢尔泽在其叙事中便多次表达对居家治疗的怀念之情。如其故事《骗子》(“Imposter”)讲的便是一个患病的逃兵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并利用最自然、最原始的方法以及当地的草药等为当地人治病的故事。[10]这里没有侵入性的治疗(aggressive treatments),也没有特效药,更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那个伪装为医生的逃兵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对患者加以适当的干预,仅此而已。这种怀旧既展现了谢尔泽一直以来对人体奥妙的欣赏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过度机械化和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现代生物医学的抵制,也即对医学第三次空间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控诉。 第三次空间化是“在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分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11]随着医学的发展,尤其是解剖学的发展,医学目视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至的人体内部空间。第三次空间化颠覆了前两次空间化所产生的医疗实践和医疗机构,促使了现代医院的出现。福柯认为医院的产生,也即医学的第三次空间化,“揭示了一个群体为了保护自身而如何实行排斥措施、建立救助方式以及对贫困和死亡的恐惧做出反应等等的方式。”[12]医院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面对种类越来越多和杀伤力越来越大的疾病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疾病本来是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疾病所处的社会空间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在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下,新疾病出现,既有的疾病也可能产生变异或者并发症等,疾病不可避免地变得多样化了,而且更加复杂,更加不自然。因为各种现代化技术的介入,以及现代医学对数据、影像等的过分依赖,居家治疗似乎已经不太现实。疾病也逐步从最原始和最自然的家庭环境转移到医院这个复杂无比的现代人造场所中去。福柯认为,疾病在社会空间里的转移,也即从一个大众共享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也不是单一的)中被转移到一个专门为患病个体所设的异质空间里,促使患病个体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产生变化。 在生理层面,福柯把医院看成是把患病个体从一个自然的、原生的家庭环境转移到一个“各种疾病混杂的邋遢花园”[13]。疾病在这个复杂又危险的环境中不断改变其本质,变得扑朔迷离。福柯关于医院的评述看似过于偏激。不可否认,医院的存在以及基于医院资源的各种现代化治疗技术控制了很多过去的致死性疾病,从而大大延长了人的寿命。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因为各种疾病在此场所交叉汇集,互相作用,加上人为的因素等,有些疾病朴素和本真的特性已经发生变化,从而出现了各种交叉感染或者并发症等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比原来迫使人们到医院就医的问题严重得多。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在其散文集《阿图医生第一季》(Complication)和《阿图医生第二季》(Better)便多次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揭露了医院这个异质空间里的种种问题,如制度上的非人性化、各种医疗失误、交叉感染等问题出现的可能性。[14]医生作家的作品曝光了很多医学界以往讳莫如深的话题,因此也被称为“医生揭秘文学”(Physician Unmasking Literature)。这种业内人士的揭秘把红十字下的肮脏和混乱暴露无遗,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一直以来被神化的场所和被英雄化的职业形象。 在心理层面,医院成了病痛苦难、孤独感、绝望情绪等主流社会所抵制的负面因子的集合地,并最终在社会空间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如贫穷等。现代社会的这种排斥措施在妖魔化疾病的同时,也边缘化了患病主体。由于制度性权力以及知识权力的规训作用,某一些人被贴上病人的标签,并被置于医院这个封闭的空间中。跟监狱一样,医院空间实际是福柯在《另类空间》中提到的偏离异托邦的典型例子。当权者通常把相对于社会认可或者提倡的所谓行为准则来说显得异常的个体置于偏离异托邦中。在医院这个特定场所,这里的人们,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患者,偏离的是社会关于健康的集体想象。个体只有健康,才能完成相应的社会责任;另外,失去健康,不仅代表着在社会空间里的失职,而且成为社会的累赘和污染源。 不同于远古时代,现代社会的疾病观过多地把生病与个人责任联系起来。疾病已经超越了身体和生理的范畴,而成为一个道德事件,乃至政治事件。例如,人们往往把艾滋病和同性恋或吸毒等与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相左的行为联系起来,患病成了个人行为不检点的惩罚。这种刻板印象实际上是对患病者一种道德上的评论和谴责。艾滋病医生作家凯特·斯坎那尔(Kate Scannell)在其回忆录《好医生死了》(Death of the Good Doctor)中,以一个个真实例子质疑这种刻板印象,她通过叙事再现了艾滋病人的真实生活,同时也还原了本该在场的个人情感。[15]另外,在关于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叙事里,艾滋病则往往与黑暗的非洲大陆(the dark continent)联系在一起。普遍认为该病可以溯源于非洲原始部落中的不文明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妖魔化非洲大陆,此时艾滋病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16]这些叙事把生病这个最正常不过的身体事件极大地复杂化了,赋予了疾病过多的隐喻性意义。苏珊·桑塔格(Suzan Sontag)在其名作《疾病的隐喻》中把病痛描述为“生活中黑暗的一面,”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着双重国籍,一个是健康的国度,另一个是疾病的国度。”[17]的确,病痛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经历之一。但是,疾病并不是生来就平等的。有些疾病,如癌症或者艾滋病等,由于其自身的致命性、传播途径和表现形式等,从一开始就被社会污名化了。桑塔格反复强调疾病的隐喻化给患病个体带来的伤害常常要比疾病本身大得多。关于疾病的隐喻化解读展示了社会对疾病的种种想象,也展示一种归因心理,似乎把得病原因与“他者”联系起来,便可以划清自己与疾病的界线;似乎把患病个体隐藏于医院这个异托邦中,便能展现出全民健康的影像。 异质空间的划分和维持跟权力中心和边缘地带的力量抗衡不无关系。当权者规定了哪些属于规范的行为,哪些属于越界的行为,并以这些规则规训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从而建立和维护一个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经过理性规范的场所。异托邦的出现是某些不驯服的个体被边缘化的结果,它展示的是理性世界所抑制的真实世界的另一面——病痛、死亡、疯癫乃至狂欢等,但这才是最本真的存在。关于死亡的呈现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理性主宰的主流社会中,死亡是禁忌词语。而在医院这个异托邦中,死亡成了生存其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大小手术前都会被告知死亡的可能性、绝症病房中讨论的是如何死得更有尊严等。理性社会的禁忌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了。外科医生理查得·谢尔泽(Richard Selzer)在其短篇小说《怜悯之心》(“Mercy”)中便通过文学手法再现了癌症晚期患者在剧痛折磨下所做的最后挣扎。他笔下的年轻医生与病患家属面对的是如何使病人能更安详地死去。[18]印度裔内科医生亚伯拉罕·佛吉斯(Abraham Verghese)的成名作《我的国家》(My Own Country)描写的是在艾滋病这场世纪瘟疫中人们面对死亡的极端恐惧。[19] 佛吉斯的叙事中关于私生活的描述也从另一个侧面个很好展现了医院的异托邦性质。私生活,尤其是性生活,在社会传统规范中是不雅的话题,一般人不会与陌生人讨论该话题。但是在医院这个特别场所中,关于私生活的话题已经没有任何神秘或者不雅色彩了。佛吉斯的病人多为男同性恋患者。问诊过程中,他了解到这个隐秘社群的性活动相关细节,并将这些细节通过文学手法再现出来。他的叙事也因此有很浓重的窥视意味。在医院这个权力关系网中,因为知识的不对等导致了力量的不对等(the imbalance of power),病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20]为了得到医学帮助和治疗,他们不得不放低对尊严的追求。当代美国医生作家书写的正是桑塔格笔下的“疾病的国度。”偏离健康轨道的人在这里接受治疗,或者规训,以期重新回到社会中去。这是一个与主流社会异质的异托邦,这里流行的是另一种语言——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这里实行的是另一种社会制度——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健康,其他一切社会职责和禁忌都显得不重要了。医生作家的书写便是以局内人的角度向外界展示一个被封闭起来的令人不安和焦虑的世界。但是这个异托邦是所谓正常社会和正常生活的投影,是一个更真实的存在。 二、镜子异托邦:文学与医学的交叉空间 一直以来,关于医院权力关系网络的讨论重点都在于患病个体,而医疗场景中的另一个主体——医生则往往被简单化为受到医疗话语体系规训的客观理性的权力实施者。当代美国医生作家的书写则进一步细化了医院这个异托邦里的权力关系。同监狱、军校和工厂等空间一样,医院里也出现权力的空间化,也被分离出许多不同的单元,不同社会成员对应不同的等级。例如,美国医生作家萨缪尔·申(Samuel Shem)的《上帝之家》(The House of God)勾勒的便是处于医生权力体系中最底层的医学实习生的生存状况。[21]处于职业化过程中的医学生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还有来自上级医生的种种压力,乃至嘲笑和辱骂。而医学生相对于病患来说便属于强势者了。通过夸张和讽刺等文学表现手法,申再现了医院权力网络中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和抗衡。不同等级的出现以及权力自上而下的实施使这个密闭的空间充满压力,随时可能爆炸。维持这个密闭空间的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种关系的定位和对应权力的规定。在这过程中,知识起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掌握知识的个体在运作知识的时候便拥有了权力。在医生队伍里,经验丰富的年资高的上级医生利用其知识权力管理控制着下级医生(包括医学实习生)。在医患之间,因为知识的不对等,医者相对来说拥有更大权力。医者是观看者和言说者,而患者则往往处于被观看和被言说的地位。古今中外,医生的崇高形象无不带着英雄主义色彩,甚至被神化了。但这种宏大叙事创造的是一种幻想,是大众的美好愿望,也是现代生物医学一直追求的目标。和英雄医生相对应的是遵从医嘱的患者。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医院权力关系网络的稳定性。 1978年,美国医生作家大卫·希尔菲克尔(David Hilfiker)发表的一篇短文动摇了医疗话语霸权苦心经营的这种稳定性。在这篇学界称为“令人震惊”的文章中[22],希尔菲克尔反思了自己误打活胎的严重医疗失误。因为“现代医学对医生有着完美无缺的期望,”[23]失误虽然确实存在,但医者往往讳莫如深。希尔菲克尔的叙事迫使医学界和整个社会重新面对医疗失误等一直得不到正视的问题,重新思考医者在整个医学权力系统中的身份和地位问题。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被现代生物医学抽象化的患者,同时还有受到医学权力规训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医者。 上世纪70年代,随着现代生物医学各种弊端的逐步显现和叙事理论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美国医学界把目光投向文学。希望文学与医学的结合能实现人文关怀的回归,从而抵制现代生物医学重理性和重科技的狭隘理念。美国医学院校纷纷开设医学与文学相关课程,并聘请人文学科学者为医学生授课。人文医学界更是掀起了一场叙事转向运动。哥伦比亚大学叙事医学项目主任瑞塔·莎隆(Rita Charon)于2001年提出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概念。作为一位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莎隆强调除了扎实的业务能力,医者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叙事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以“认识、吸收、解读关于疾病的种种故事(包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病人的故事),并被这些故事所感动。”[24]叙事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文学熏陶和叙事训练(如文艺写作等)来实现。莎隆所发起的叙事医学运动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得到热烈反响。美国当代医生叙事的蓬勃发展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反集体想象中的高大上形象,医生作家以手中笔书写在生死苦难面前的切身经历(lived experience),感悟生命的神秘,反思医学的自我尊大,以及体制中人的生存状况。他们希望文学的介入能把被现代生物医学抽象化和机械化的人(包括患者和医者)带回医疗场景中来,重新弘扬医学关怀(caring)的本质。 通过叙事,医生作家实际上是在医院这个异托邦中建构起另一个异托邦,这个异托邦的存在更真实地反映了医者的生存状况。这个异托邦基于医院,同时又存在于文学和医学这两个不同学科所构成的交叉空间。这个交叉空间与前半部分讨论的医院异托邦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福柯在论述异托邦时,所举的例子大多为真实可见的存在,如花园、度假村和公墓等。但是他也强调,异托邦“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之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25]也即有些异托邦并不像他在《另类空间》一文中所举的例子一样能在现实中以实体存在,如当今的网络虚拟空间。异托邦具有现实和虚拟想象多重性质。福柯举了镜子的例子来阐释这样复杂的存在。他认为镜子空间是一种混合了乌托邦和异托邦特性的特别空间。一方面,虽然观看主体看到了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但镜子中产生的影像并不真实存在,这是镜子的乌托邦。另一方面,“在镜子确实存在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26]镜子可以作为乌托邦存在,也可以作为异托邦存在。当它作为异托邦存在的时候,它反映了现实存在,并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连接起来。福柯认为:“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另一端的虚拟的空间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自己。”[27]在镜子异托邦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在镜子中的“不在场,”因为真实的我存在于镜子外。这个从“不在场”到“在场”的意识转换,实际上是观看主体的目光从虚拟的我投向现实的我的过程。此时,“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28]镜子中那个虚拟的我使我看到存在于现实空间的我。通过镜子这个起到桥梁作用的连接点,我穿越于虚拟与现实世界各种关系中,并在这两个世界交叉所构成的权力空间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形成对自我身份的认识。这个认识自我或者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受到所处社会文化语境影响的自我身份重构的过程。[29] 文学对于医学正是起到镜子的作用。医生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在虚拟的文学世界中再现自己的行医经历和感想,并以此来反映现实存在。医生作家在作品中看到现实中的自己在各种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各种关系间的权力抗衡。现代生物医学崇尚理性和科技的理念导致了人文关怀在医疗场景中的严重缺失。情感的流露和表达往往被贴上低效和无能的标签,医者成了对付疾病的机器或者能运用机器和工具的客观理性的匠人。而文学与医学共同构成的这个异托邦中,借助镜子作用,医生作家把医疗场景再现出来,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等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物,与现实空间存在直接的依凭关系。在医生叙事里,医生作家犹如在照镜子一般,既能看到自己,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并不在的地方。这是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混合空间。说其真实,是因为故事反映的是医生作家的切身经历;说其虚幻,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学科交叉的空间医生作家才能让这些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外科医生作家理查得·谢尔泽认为,“在手术室,医者和患者都需要被麻醉。患者通过麻醉减轻疼痛,医者通过[精神的]麻醉来抑制正常人[面对血淋淋的人体内脏器官]所产生的情感反应,从而使手术顺利进行。因而当外科医生剖开患者身体时,他自己的身体不会流血。”[30]为了使医疗活动顺利进行,医者的情感需要受到抑制。谢尔泽和其他医生作家纷纷肯定这些情感反应的重要性,同时深信书写能使这些被抑制的正常情感复原,从而使被工具化的医者在文学与医学的交叉空间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完整的自我。谢尔泽在其日记中写道:“只有医生作家没有被麻醉[并变得麻木不仁]。他看到一切,也不过滤掉任何东西。”[31]医生作家回顾并再现工作过程中的情感历程,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现代生物医学话语和职业要求所抑制的另一个自我。这是对过往经历的一个再经历过程,而且这一次经历能使其更完整地体验整个过程。理性的控制在这个特别的文学空间中被极度弱化了,医生作家展现的是一个个更真实的自我。在其散文集《最后的期末考》(Final Exam),医生作家陈葆琳(Pauline Chen)从一个器官移植专家的角度袒露医者在死亡面前强烈的无能感和无助。[32]谢尔泽在其作品中,如《怜悯之心》等,也无数次讽刺了医学的妄自尊大和医者痛苦的自我认识过程。儿科医生作家佩里·克拉斯(Perri Klass)在其半自传体小说《别人家的孩子》(Other Women's Children,1990)讲述的是女性儿科医生在家庭和事业间挣扎的经历。[33]为了在这个权力网络中生存发展,女主人公不得不放弃自我,根据职业规范规训自己的言行。她苦苦追寻的是如何在母亲、妻子和医者这三个身份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生存于男性话语统治下的医疗体系中的女性的无奈和伪装。而这些正是现代医学话语体系所抑制的非理性的因子。 对非理性的崇尚在艾滋病专家、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古巴裔医生作家拉斐尔·坎普(Rafael Campo)那里被推崇到了极致。人的身体性(corporeality),尤其是欲望(desire)是坎普作品中的一个关键词。现代生物医学崇尚理性和科技,追求的是建立医者的英雄形象。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医者的身体性,或者具体来说,人类情感的表达以及人的弱点在医学话语体系中均被抑制了。但是坎普和其他人文医学学者认为医者只有承认了其身体性,才能走下神坛,才能与病人进行真实有效的沟通,从而体现医学的关怀本质。基于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身体性在医疗场景中的表达并不现实。而文学则为有自觉意识的医者创造了一个自由和安全的表达空间。坎普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能拯救陷于困境中的医学。在他看来,诗学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再现,更是现实空间的补充和扩展。他写道,“在诗歌中,我可以将耳朵贴到我的病人胸前;在故事中,漫漫长夜里我可以躺在病人身边。我的手与纸接触带来的愉悦让我重新体验了我触摸病人皮肤的愉悦。我对他们[病人]的爱是跳跃在我的诗歌中的韵律。”[34]诗歌使坎普重新回到医疗场景中去,并把本该在场的情感复原,从而使自己更加完整地体验到整个医疗过程。这里没有冷冰冰的医疗器械,没有抽象难懂的数据和术语,没有客观理性的医者,也没有所谓温顺的病人。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体之美的欣赏,对生命奥秘的感叹,对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关系的探寻。 坎普在其诗歌《你使我心中的医者显现出来》(“You Bring Out the Doctor in Me”)中讲述的是医者和病危的男同性恋患者在艾滋病这场世纪瘟疫中的情感故事。当医者走进病房为瘦骨嶙峋的患者检查身体时,医者和患者的目光交汇,碰撞出情感的火花。坎普在诗歌开头创造了一个浪漫(或者色情)的氛围,叙事者把消毒水的味道变成香水味,把病服看成了睡衣等。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病痛的束手无策则被转化为对医患之间犹如情人般紧密联系的渴望所取代。破除隔阂的根本在于医者卸去客观理性的职业外装,以本真示人。在诗歌的结尾,叙事者更是从患者的角度看到了医者的“无助”、“无知”、“麻木”和其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35]坎普强调的是医者的弱点。病危的患者知道医生“并不能治愈他,”所以他恳求医生“爱他”。[36]坎普诗歌中大胆的色情意象和暧昧的医患关系容易引起误解。他倡导的这种情人般的医患关系具有超验性质。他借情人关系这个隐喻来表达在不治之症面前,人类所能做的便是去除制度性隔阂,从而建立一种亲密无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体现医学的终极目标——关怀人间苦难。 而正是关怀人间苦难这个终极目标使医学与文学的结合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文学的介入为医者创造了一个表达诉求的补偿性空间。这个空间是对现实的关照,也是对现实的补充。医生作家通过回顾工作状态中的自我,把在工作中被剥离开来的感情复原,从而在客观理性的职业要求和有血有肉的苦难见证人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医生书写的回顾性意味着工作中的医生和写作中的作家两个不同身份的分离。正是这种距离和空间间隔使医生作家能以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反思并再现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医生作家看到的不仅是完整自我的不在场,更重要的是重构自我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在文学与医学交叉构成的异托邦中,医生作家通过艺术手法对现实种种现象进行重置、置换、转化和提升,挣脱现代生物医学的规训作用和集体想象的困囿,使非理性的因子自由表现自己,从而重新建构一个虽然不完美,但更真实的自我。医生作家表现和阐释的是被权力压制而不得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这些存在虽然没有物理性质和可触摸性,但它们是现实的影像,它们的存在阐释的是医生在这些现实发生的医疗场景中真实的感受,它们展现的是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很隐秘的“异质空间。” 医生书写的隐秘异质空间与医院这个显现的关系场所紧密相连,共同构成美国当代医生书写的特色。通过书写,医生作家重点呈现医院这个被边缘化的他者空间中的权力网络关系和自己在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中的异托邦体验。更重要的是,书写是医生作家从边缘视角介入霸权关系网络的一种比较安全和保守的策略,也即在学科交叉所构成的非此非彼的自由空间中,医生作家可以把理性社会中种种非人化的(depersonalized)规定推翻,把一直以来附加在其职业形象上的种种光环去掉,让内心的真实浮现出来。借助文学手法,医生作家希望谱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塑造一个个更真实的而且更完整的自我,并以此来颠覆医生英雄形象的宏大叙事和质疑医疗话语霸权的规训作用。 ①另一个说法是Medical Narratives,但该说法包含意义甚广,既包括医生作家和医学生的文艺作品,也包括医疗相关的书写,如病历等。此外,因为国外有学者(如Suzanne Poirier,2009)曾专门研究医学生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作品,为区别起见,本人使用Physician Writing来特指取得行医资格的医生作家的文艺作品。此处的physician取其广义,泛指医者,包括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等。关于Physician Writing这一说法的解释,详见孙杰娜《阈限·叙事——当代美国医生作家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的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