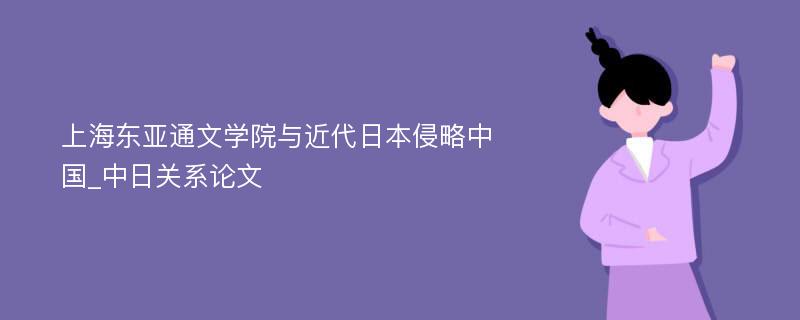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上海论文,书院论文,近代论文,同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1;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52-06
日本所设东亚同文书院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所神秘学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它鲜有研究。1995年苏智良先生在《档案与史学》第五期发表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1997年1月单冠初先生在同一刊物发表了《试论东亚同文书院的政治特点——兼与西方教会大学比较》。笔者1995年留学日本时曾接触到东亚同文书院的史料,近几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该书院的史料,拟从书院与近代中日关系这一新视角,对其产生背景、历史活动和危害进行探讨,并就教于识者。
一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开设的,在探讨书院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将该会的情况略加叙述。
日本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它的出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激怒了觊觎此地已久的沙皇俄国,因此出现了“三国干辽”之事。俄、德、法三国联合打压日本之后,乘势伸张在华势力,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即成。这种国际形势引起日本朝野内外的关注,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1897年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毅、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新闻界的陆实、池边吉太郎等人组成了东亚会。几乎在同时,常年活动于中国的大陆浪人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和日本政界要人近卫笃麿、大内畅三等人组成了同文会。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流,组成了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四条纲领:1.“保全中国”。2.“协助中国与朝鲜的改革”。3.“研究中国及朝鲜的时事,以期实行”。4.“唤起日本国内舆论”。[1](p470)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组织怎敢妄称“保全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和朝鲜进行改革”?它之所以提出如此的纲领,是因为该组织拥有着雄厚的政治资源,它的会员多为明治以来日本各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898年该会成立时,会长是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近卫文麿之父),16名评议员中有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和清浦奎吾,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谷干城,肥后藩主细川家族成员长冈护美子爵等等。即使普通会员也非平庸之辈,如后任驻华公使的宗方小太郎,后任驻美、驻德大使的植原正直和小幡西吉,江藤新平之弟江藤新作,以及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非常有名的头山满、平山周、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等。
所谓“保全中国”其实隐藏着不可示人的目的。如前所述,列强瓜分中国之祸完全由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肇端,接下来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使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坐立不安,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不得不变换手法。于是,1898年成立的隈板内阁提出了所谓的“大隈主义”,声称要援助中国、“帮助中国改革和自强”、“保全中国”等等。“保全中国”实际上是“兴亚论”的代名词。在此之前,在对外如何扩张侵略的问题上日本国内曾有“脱亚论”和“兴亚论”之说。所谓“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兴亚论”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使东亚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起来,对付欧美对亚洲的侵略。[2](p3)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就是一个“兴亚论”者。他认为,西方对亚洲的侵略是种族性的,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他曾提出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宣称“东洋实为东洋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属于东洋人的责任,清国国势之不振,其弊端在于政治,不在于民族,如能共同携手从事于保全东洋,并不是不可能”[3](p16)。从近代中日关系史来看,所谓“兴亚论”或“保全中国”论,显然是指在日本还没有能力独占中国之前,决不坐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于是假借保全之名以保留日本独吞中国的机会。对于这种谬论,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先生曾指出:“这种日、朝、中的反帝联合或亚细亚的主张,只有在反对日本本身的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如果不反对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仅仅反对欧美的侵略,那么这种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只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而自己却在亚洲扩张势力的一种政策。”[4](p231)综上所述,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出现及其纲领都与日本的侵华策略相连,从实质上讲,它是受日本对外政策影响的一个政治团体。
东亚同文会组成后,要求会员把“保全中国”作为压倒一切的急务,密切注视。它在日本东京设立本部,在中国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立支部,发行报刊,调查中国情况,同时决定在中国开办学校。据该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记述,“东亚同文会在关于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方面,早就有在南京设立东亚同文书院的计划”[1](p488)。不过,这个计划的出笼却是受荒尾精的影响。
荒尾精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1886年他被日本参谋本部以现役中尉身份派到中国,在日本老间谍岸田吟香的资助下,以商人身份在汉口开设药店“汉口乐善堂”,以做买卖作掩护,进行收集中国情报的活动。当时日本陆军的主流派主张日本应该集中兵力破山海关而直取北京,速胜而缔约,达到割地赔款之目的[5](p39)。在中国活动三年,荒尾精详细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军事侵略中国并非上策,因为那样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且耗费国力。另外,他亲眼看到了欧美列强肆意抢占中国的市场,而日本在对华贸易上远远落后于欧美。他认为“要把东亚大局获到盘石之安的首要手段,为中日两国的经济提携,尤其以积蓄能够同欧美列强相颉颃的实力为急务”[1](p482)。为此,他主张在中国设立“日清贸易研究会”,一边培养中日贸易专家,一边调查中国商业情况,把中国的贸易权从欧美手中夺过来。由此看来,荒尾精并不反对侵华,他只是主张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即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1890年他回日本述职时,将他在中国之见闻与收集的情报资料写成了两万多字的《复命书》,呈送给日本参谋本部。据《对华回忆录》上记述,“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藏相松方正义、农相岩村通俊等听到后,对于他的雄图,大为赞赏”[1](p483)。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开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该所实际上是一所专门招收日本学生的学校,学制三年,所学课程主要是汉语、商业地理、经济等。该所共办三年,有89名毕业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停办。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该所的学生几乎全部投入对中国的战争,《对华回忆录》这样记述该所学生在战争中的表现:“该所的毕业生,几乎全部抱着献身祖国的志向,有的担任军事翻译,远赴前线,有的带着秘密使命,潜入敌境,血染草原。”[1](p485)
1897年,荒尾精在台湾染上鼠疫而死,他的旧部下几乎都投奔到近卫笃麿的门下,参加了东亚同文会,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根津一。根津一是荒尾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两人都“把天皇、军国主义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基础和动力”,并成为至交。根津一曾担任“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副所长,帮助荒尾精主持校务,他加入东亚同文会后,受近卫笃麿的重用,担任该会的干事长,处于一种决策地位,东亚同文书院正是在他和近卫笃麿的策划下出笼的。
二
1899年近卫笃麿访欧归来途中到达中国,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在华设学事宜,刘坤一表示赞同。1900年5月东亚同文会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校址设在南京鼓楼附近。因义和团事起,1901年3月该院迁往上海。当初预定,待事态平静后,再度回迁。当时上海已是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政治、外交中心,并且是原“日清贸易研究所”所在地。因此,根津一建议将上海作为永久院址,同时将其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关于书院的设立,《对华回忆录》这样评价:“在可以成为本院前身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停闭八年以后,再度开办对华教育机关,意义最为深长。”[1](p489)
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20年;第二个时期从1920年至1931年;第三个时期从1931年至1945年该校解散。
第一个时期,书院校舍最初设在上海高昌庙附近,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期间,该院校舍被战火焚毁。是年8月,该院迁往日本长崎,11月又迁回上海赫司克而路临时校舍。1917年迁至徐家汇虹桥路新校舍。这一时期,根津一一直担任该院院长。他把荒尾精的侵华谋略完全贯彻到书院的运作中,以至于书院的创办宗旨与“日清贸易研究所”一脉相承。
1900-1920年东亚同文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年入学的日本学生少则50人,多则达100余人。该院初设政治科和商务科,修业年限为三年。在课程设置方面,两科必修的课程有:儒家伦理、汉语、英语、中国政治地理、中国商业地理、民法、法学通论、中国制度律令、中国农工商史等。政治科的课程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刑法、国际商法、中国近代外交史、近代政治史等。商务科的课程有:中国商品学、中国近代通商史、商法、商业算术、簿记、商业学、财政学等。[6](p335)上述课程大多与中国有关,并且以商业和经济为重点。
东亚同文书院以研究中国情况为专务,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实地调查,因此,调查旅行是该院的重要活动之一。其实,这也是荒尾精在“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期就提出过的。荒尾精曾宣布,每一个学生在上海学习三年后,应该在第四年到中国内地旅行,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正是这样做的。从第一届毕业生开始,每届学生在第四年都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数人一组,或乘车或徒步,按照书院规定的路线,所谓“沐雨栉风”、“风餐露宿”,深入中国内地调查旅行。旅行调查的项目涉及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商业、地理、交通、风俗习惯等。
这一时期,书院的调查旅行活动范围广,有些调查,目标非常明确,直接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如1902年,日英同盟缔结以后,日本外务省指示同文书院,调查中国西部边境地带俄罗斯侵蚀中国的情况,书院便派遣林出贤次郎等五名学生到中国新疆一带调查旅行。1905年林出等人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达乌鲁木齐,最后到达伊犁地区,共用270多天,行程4500多公里。调查旅行归来,他们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从1907年起,日本外务省开始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提供补助金,该院的调查旅行扩及中国各省区。
1914年,东亚同文会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在东亚同文书院增设农工科,为开发中国资源培养“人才”。日本政府同意后,书院于是年9月增设农工科,招收日本农工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授以农学及土木、采矿、冶金等知识,毕业后从事于中国的生产工业。1922年,据说由于书院财政窘迫,又废止了该科,同时停止政治科的招生。
第二个时期,根津一因病于1922年辞职,日本岩手县知事大津麟平继任,三年后近卫文麿继任院长。1921年,东亚同文书院的修业年限从三年改为四年,同年,日本政府“颁布敕令,将该院改成专门学校,按照日本专门学校令处理”[7](p42)。
这一时期,该院的调查旅行活动扩展了前期的路线和调查项目,使其更加专业化和细密化,因此,被称为“圆熟期”。在不同地区,其调查主题不同,比如,在中国南方是金融,在北方是羊毛,在山东、河南是棉花,在湖南是茶叶等等。这一时期,该院的调查旅行范围大、时间长,有的长达半年之久。比如,1920年,第十八期学生的调查范围扩展到云南、四川、两广等地,第十九期更扩展至青海、宁夏等地。
这一时期,该院除招收日本学生外,从1920年9月起,还经办了中华学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同时,东亚同文会还在中国设立了天津同文书院(后更名为中日书院)和汉口同文书院(后更名为江汉高级中学),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增设针对中国学生的教育机关,主因如下:
第一,试图以办学来联络中日两国感情,消弭《二十一条》造成的中国高涨的反日情绪。1914年,日本乘欧战中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出兵占领了我国山东,1915年又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中国开始出现强烈的反日情绪。《东亚同文会史》中这样记述中国的反日游行:“游行队伍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中国人眼中,日本已成了仇敌,他们带着偏见,不管见到哪个日本人都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6](p88)东亚同文会对日本侵华的事实不置一辞,却把中日关系的恶化看做是感情上的问题,打算开办对华教育以联络两国感情。
第二,与西方列强争夺对中国的教育权。东亚同文书院经过长期在华活动,发现西方教会学校正在中国迅速增长,而日本除在东北办学外,在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学校。另外,它注意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大批留日学生纷纷弃学归国,而此时美英等国却在利用“庚款”办学,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鉴于上述两种情况,东亚同文书院于1917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扩大在华教育活动的补助申请书。与此同时,日本国会的一些议员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模仿美英利用“庚款”在华办学。日本政府最后决定将在中国兴办教育的事务交给东亚同文会办理,这样就出现了上述中华学生部、天津同文书院等学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探讨天津同文书院等校的问题,只对中华学生部的情况略加叙述。
中华学生部初设商务科,修业期限4年。但由于当时反日空气浓厚,凡与日本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受到中国人的唾骂,很少有人愿意上日本人学校,当时报名上中华学生部的只有6人。中华学生部的课程与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课程大致相同,只是将中国语变成了日本语。中华学生部一直不景气,1921年虽然招到了35人,但到1924年只剩下7人。招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民众反日空气浓厚、军阀混战以及社会动荡等。1925年中国兴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西方教会学校及日本学校都受到很大冲击,中华学生部也不例外。1928年,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等有关外人在华办学的规定,要求外人办学限期立案等,但东亚同文书院坚持该院为日本人学校,拒不立案登记。中国方面则宣布,不承认中华学生部为正规学校。这样,1931年,中华学生部停止招生。
第三个时期,近卫文麿因政务繁忙于1931年辞去院长职务,由日本国会议员东亚同文会理事大内畅三接任,1939年大内畅三辞职后,东亚同文会理事长矢田七三郎继任。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期,因战争原因该院曾迁往日本长崎,4月又迁回上海。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该院再次迁回日本长崎。日本占领上海后,1938年该院再次迁回上海。因原校舍已被战火毁坏,该院占用上海交通大学为校舍,一直到1945年解散为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书院的调查旅行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其活动被限制在日本占领区,但他们借助侵华日军及日特机关的帮助,继续进行调查旅行。这一时期的调查题目多是配套日本的侵略,应日本的侵华机构的要求完成的。比如,1939年,书院的调查旅行项目明确规定,调查在占领区内“外人权益状况,日本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新政权的统治经济等”[3](p159)。
1938年11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申请书,要求把该院升格。一年后,该院获准升格为大学。升格后,该院设大学预科、大学部和研究部。预科修业年限为二年,大学部为三年,研究部为二年。预科招收中学毕业生,大学部仅设商务科,招收该院预科生。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亚同文书院随之解散,结束了它在中国长达46年的活动历史。后来,东亚同文会会长、二战战犯近卫文麿畏罪自杀,该会群龙无首,宣告解散。
三
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中国人重视,因为单从形式上看,它只是教育活动,并且最初以“保全中国”相标榜,后来又以“两国联络感情”为幌子,这使人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看清楚它的实质。另外,甲午战后几年时间里,中日关系有所缓和;20世纪初,中国又出现留日热潮。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幻想,人们对东亚同文书院就更难洞察其真实动机了。比如,东亚同文书院开学典礼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余联沅等清廷大臣都派代表参加,并送去架辞,对其“保全中国”的“义举”大加褒扬。再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3年游历日本时,在东亚同文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曾说:“昔当敝国危急之秋,首倡保全中国者,自东亚同文会始,前会长故近卫公,现会长锅岛公爵及会员诸君,皆以热诚图东亚之幸福。名之所至,实亦副之。”[6](p15)又比如,1900-1931年期间,中国政府都没有重视同文书院调查旅行的严重性,不但给书院学生颁发旅行许可证,而且政要名人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等还为他们题词。如孙中山曾给第14期学生的旅行志《风餐露宿》题词:“壮游”。[9](p62)直至今天,还有人搬出孙中山先生的题词来为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正名。
但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并不像某些人描述的那么清白。如前所述,东亚同文会的历届会长及其会员大都是日本政界要人,这一雄厚的政治资源决定了该组织与日本政府的特殊关系,所以,自1990年起,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一直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政府给予东亚同文书院大量的资助。自1899年起,日本政府每年给予该院“经常费”4万日元。从1918年起又开始增拨临时经费,到1923年为止,日本政府共给予该院补助金263万余日元。1923年日本用“庚款”办学时,制定了《特别会计法》。根据此《特别会计法》,该院自1923-1934年间共接受补助金385.7万日元,1935年又有34.5万日元。[1](p505)《特别会计法》规定,支出款项以岁出250万日元为限,而该院每年平均能得到34万日元以上,约占总数的13%,可见日本政府对其重视程度。
第二,东亚同文书院是受日本政府直接控制的。该院虽然属于东亚同文会的学校,但它却直接受日本政府管辖和监督。东亚同文书院的院长任命、系科的置废、学制的变更以及校舍的迁徙等事务,大都由日本政府决定,甚至连书院教师资格也要由日本官方认定。比如,1921年7月,日本政府专门颁发“三二八号敕令”,规定东亚同文书院的教师须具备下列条件:“(1)帝国大学或官立大学毕业,或经帝国大学或官立大学考试及格得有学士学位者。(2)经外务大臣认可者。”[7](p42)再如,中华学生部是经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和外务省批准后才设立的。连东亚同文书院自己也承认,“东亚同文书院是在外国领土上设立的治外法权学校”,“学校的管辖权属于外务省”[6](p85)。
第三,日本政府每年为书院选送约百名学生,费用由学生所属各府、县负担。以该院第二十一届(1921-1924)学生为例,其118人中,有91名府、县奖学金学生,19名“满铁”资助学生,5名日本外务省资助学生,3名由其他单位资助。另外,日本官方对该院毕业生的待遇也有专门规定,1921年的“三二八号敕令”规定,该院毕业生的资格与日本国内专门学校相同,“并可享受今后召集及免除高等文官检定考试”[7](p42)。
纵观其在华46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操纵下,该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培养侵华分子的基地。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院的办学目的是为日本培养侵华分子。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宗旨曾宣称:“讲中外之实学,育中日之英才,一树中国富强之基,一以固中日辑协之根,所期在保全中国,定东亚久安之策,立宇内永和之计。”[6](p325)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前所述,该院的课程设置大多与中国有关,通过长期的汉语学习,加上特殊的专业训练,这些同样长着黄皮肤的日本学生,留上长发或戴上假发套,就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内地活动。根津一担任院长时,曾亲自讲授伦理课,他把中国儒教与日本神教杂糅在一起,向日本学生灌输忠于日本天皇的思想。“根据根津的设想,燃烧着‘天皇的忠诚战士’使命感的行家们,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像水浸染一般席卷中国才是最理想的。培养这些尖兵,乃是根津的东亚同文书院的任务。”[10](p77)
其次,该院学生的旅行调查,为日本政府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视的情报。自同文书院创设起到抗战结束,书院的调查旅行延续了45年,参加者达5000人,旅行线路700条,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每个角落。他们的调查项目涉及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类似于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普查。他们把搜集到的政治、经济情报撰写成所谓的调查报告,每年印五份抄本,分别提交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一份。后来,以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同文书院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省别全志》。毋庸置疑,这些调查报告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情报。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英国一个军中记者拜会中国某官员,在谈及东亚同文书院时,该官员叹称:“这是德国对法国历史的重演,1870年之役,德人对法国之一切远较法人清楚,今日,日本对中国亦然。”[7](p54)后来的事实证明该官员的确是有远见的。
再次,该院的学生直接参与了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据《对华回忆录》记述:“当1904年4月,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时,恰逢日俄之战,毕业生中有很多从军者,与当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事迹如出一辙,实可称奇。”[1](p490)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时,该院应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要求,曾出动50余名学生为日军做后勤服务。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应日军要求,该院曾派出多名学生出任随军翻译。抗日战争期间,该院院长大内畅三曾极力鼓动学生参战,他说:“我们忠勇义烈的军队,在中国语言不通,不熟悉地理,很不方便,你们书院学生要发挥作用,去做军事翻译或后勤勤务,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9](p169)这样,该院学生大多加入日军侵华队伍。如1941年,根据日本文部省的训令,该院学生编成4个中队,参加侵华战争。再如,1943年,因日军前线兵源缺乏,向日本大学征兵时,该院学生三百余人再次加入日军,甚至连该院教授也应征入伍。
最后,该院的毕业生有不少在日本侵华机关中工作。据1938年的调查,该院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人留中国,其中有415人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机关中服务,剩余的均在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务等部门工作。由于该院与日本外务省有不寻常的关系,其毕业生曾任职于外务省的有近200人之多,日本在华领事馆内也有书院毕业生。[11](p54)另外,该院同侵华组织“满铁”有很深的关系,其毕业生从第一期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在“满铁”就业的。
综上所述,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上,担当了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先锋作用,它的历史已成为日本侵华史的一部分。
应该指出的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虽然深受日本侵华思想的影响,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在中国长期生活后,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欺凌中国人民的现实,感悟出“兴亚论”的欺骗性。这些有良知的学生逐渐地转变为反战积极分子,用自己的行动,为中日友好尽了义务。比如,1930年该院学生中曾出现左翼组织“中日斗争同盟”,该组织积极进行反战活动。1930年12月26日,日本海军实习舰见习官140余人参观同文书院时,该组织学生安斋库治、白井行幸等人乘机向士官生散发传单,,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另外,在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就读的中国学生,虽然接受了日本的殖民主义教育,但身处中国的抗日氛围之中,大多数学生并没有成为亲日分子,他们不顾书院的迫害,勇敢地投身于中国救亡运动之中。比如,1923年,中华学生部的学生就以中国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起草了收回旅大宣言书。但无论该院日本学生还是中国学生的这些反对日本侵华的行为,都是与东亚同文书院办学的目的相反的。今天,某些人把这些学生的反战行为拿出来,为东亚同文书院涂脂抹粉,是徒劳的。因为东亚同文书院不仅没有支持这些进步学生的活动,反而用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甚至逮捕等手段来压制学生。
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书院学生来说,去大旅行的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9](p236)笔者想问的是,假如今天中国也派几千名学生去日本各地调查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人该作何感想?还有的学者说:“平心而论,规模宏大的书院学生的社会调查,其深度与广度,都超过了旧中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任何一次调查。这数以千册计的调查报告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5](p44)笔者认为,如果这也算是东亚同文书院的贡献的话,那么某些人所谓的“侵华有功论”也可以大行其道了!
【收稿日期】2001-10-15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日本侵华论文; 上海东亚论文; 荒尾精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二十一条论文; 旅行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