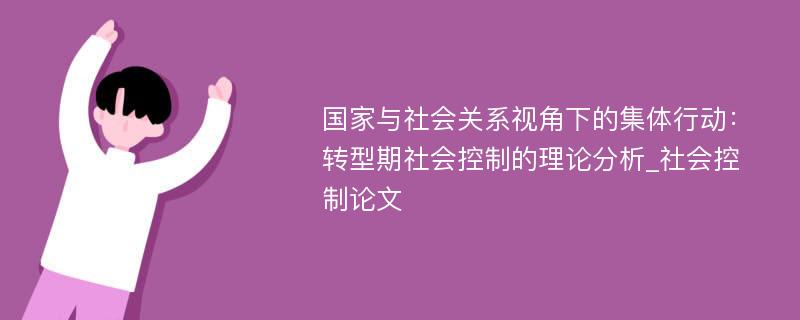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集体行动——对转型期社会控制的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社会关系论文,视角论文,集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3-0140-06
中国社会从总体性、一元化的结构转型为分化的结构,群体利益的分化常被用来解释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状况。群体性事件是社会不稳定的显性表现,学者们经常使用“集体行动”、“集体抗争”等术语指称这类事件①。它们的意义大体一致,都是指采用群体聚集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利益分化形成的社会矛盾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冲突性的集体行动,张翼指出,真正位于社会最底层的阶层具有发生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客观上的利益分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差异并不直接导致冲突的意识或冲突的行动。一些收入并不低却认同自己是社会下层的人,更易于产生社会不满的情绪②。这一研究从社会结构的客观状况与主观认同的错位的角度,说明了利益分化必须通过某些结构性因素作为中间变量,才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之类的冲突性集体行动。李汉林等认为,许多矛盾和冲突引发的社会问题是“结构紧张”产生的张力所致,社会“怨恨”情绪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他们还从阶层结构、单位制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和教育水平等六个方面分析结构紧张③。该研究明确了导致集体行动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不同构成部分在相互协调和资源获取两个维度上的紧张关系。
笔者认为,还可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入手,分析社会结构因素的张力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较之阶层地位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视角更强调利益分配的过程与利益固化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利益分化这一结果。尽管可能处在相同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同类别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这可能成为社会成员对阶层或阶级地位认知与客观状况(利益分配的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李汉林等人对单位差异这一结构因素的分析表明,非单位成员在地位不一致与社会失范两方面的感受明显强于单位成员,这一研究实际上已经触及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了计划经济高度控制的特点,单位是资源分配的主要渠道,这与当时经济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社会结构因素(如非公经济人士、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工等群体)从原有体制中分化出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随之变迁,利益分配与社会控制的格局也发生相应变化。“市民社会”、“庇护主义”和“法团主义”三种理论,为分析我国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参考框架。“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制衡的关系模型,当代中围的现实与这一模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社会群体的行动较少表现出制衡国家的倾向;“法团主义”与“庇护主义”理论则提供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模型,更有助于分析我国当前社会控制方式以及社会群体相应的行动特点。
一、“市民社会”理论与非政治化集体行动
“市民社会”理论多见于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引发政治自由化,处在改革前沿的人们将成为政治改革的领导者。这仅是狭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实际可以称作“西式民主化”理论。Burks通过对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改革与增长,新生的社会阶层会极大地与民主化进程相关联,新社会阶层怀着强烈的兴趣推进自由,从国家控制当中摆脱出来④。Burks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中集体行动一定与政治诉求相联系,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不适应此进程,因此这个时期社会冲突一定会带有政治色彩,东欧和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政治变革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理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上,这种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会催生类似西方的市民社会。有学者认为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导致权力结构变化,新的经济精英能够获得比行政精英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行政精英的权力受到了来自市场的挑战⑤。更有学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有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制衡的新生力量⑥。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能套用这一理论去解释。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国家行政影响力在转型时期有所削弱,但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础,而且边燕杰等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转型中行政精英在市场化过程中更有机会受益,其社会地位不会下降⑦。国家控制资源的能力得到延续,所以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没有下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的确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并不是作为与国家相制衡的力量发展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样行政力量从城市中退出的时期,因此类似西方式社会自治很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传统资源⑧。社会力量多是作为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定位和发展的,大多数社会组织不仅在人事上与行政组织交叉,运作上也依赖官方的认可和资助。
这种理论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如果“西式民主化”理论成立的话,转型期以集体行动为代表的社会冲突行为应该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诉求,所谓“市民社会”中的主要力量——新中间阶层在与国家互动过程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并没有政治诉求,典型的事件一般针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失当(如2008年6月贵州瓮安事件、2008年7月陕西府谷事件)或者针对利益的相对损失(如2008年9~10月川渝教师罢课和2008年11月渝、鄂、甘等地出租车和个体客运司机罢运)。这些事件较少涉及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集体行动的主体通常是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对经济利益的诉求是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转型期中国并没有出现如“市民社会”理论所预言的制衡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利益诉求被限定于政治话语以外,因而我国转型期集体行动没有政治色彩。
二、“庇护主义”与“法团主义”策略的社会控制作用
“市民社会”理论经常忽略的因素之一就是缠绕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庇护主义(Patron-Clientelism)理论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庇护关系一般是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利用影响力和资源保护被庇护者的利益,被庇护者则以服从、支持或服务于庇护者作为回馈⑨。对中国的研究表明,单位中的管理者将个人的影响施加于员工,他们控制着岗位流动和物质利益分配等资源,这使得单位的分配能力比国家更直接,这些情况迫使雇员加强与上司的个人关系,行为上接受控制⑩。庇护网络沿着正式的社会设置一层层从个人延伸至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理论上,市场化联系的增强会逐步弱化这些庇护关系,同时增加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但可以看到庇护主义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控制社会的策略。经济改革后国家对企业、群体、单位等社会组成部分在制度上的正式控制关系减弱,非正式的联系依然保持相当的影响。
庇护主义在非正式控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控制策略通过向特定人群分配选择性的利益,实现政治权力安排,获取支持和控制的机会(11)。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庇护主义所形成的利益分配网络,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通过非正式渠道调节体制内、外群体的利益关系。这个网络所涉及的领域,因利益分配引发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庇护主义的控制方式所能涉及的人群必定是有限的。而且庇护网络需要依附单位这样的正式社会组织延伸,所以在体制内,拥有不同资源的组织对其成员行动的控制效果不同,有研究发现单位对集体行动具有分割效应(12);在体制外,这种控制能够涉及的范围则十分有限。
另一种理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描述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特征。国家将一些权力分配给机构或组织,坚持主导的意识形态,同时由国家授权在该领域形成一定自主性。其具体例证就是,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团体只有一定程度上带有国家授权的特征才能正常发挥功能。法团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观察视角。一方面,从利益获取上看,得到国家授权的团体或组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专属利益,按照一定规范分配给其成员,并获得成员在政治上的认可;另一方面,从意见表达上看,法团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国家认可的社会团体或功能性利益团体,社会的不同意见得以整合并进入体制,“使决策过程有序地吸收社会需求,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不损害秩序的限度”(13) 。具有此种沟通功能的法团主义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转型期体制内外人群的利益冲突。法团主义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策略之一,我国转型时期的法团主义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研究表明,如果国家主导下的法团主义取向越来越强烈,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则越来越不明显,政府对这类组织的控制就越显著,同时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中越来越缺乏自主、独立和自治的地位(14)。随着社会团体官方色彩的加强,其更倾向于封闭而不是开放,在社会控制中的广度和效度都有可能减弱。
有国外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庇护主义和法团主义混合的特点(15)。一方面,转型期中国新社会阶层“在政治上表现得并不积极,但大部分人却急切地通过个人关系去联系政府,以解决特定生意上的事务”(16)。这种情形在部分私营企业主身上有一定代表性,显示了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庇护主义特征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国家则组织了工商联和各类行业、企业协会等社会团体,通过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合作性经济体来替代政府部门的直接管理,这些团体一定程度上带有法团主义的特征。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转型期中国社会控制方式的特征表现为,一方面社会被重视具体利益的现实主义观念驱动,而且应用庇护网络去解决问题的策略仍然比较有效;另一方面,国家努力通过法团主义策略构造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管道,提供一种集体行动之前尝试用中国式协会去解决问题的机会。把法团主义与庇护主义混合在一起,这种控制方式保持了国家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主导角色,同时避免了经济利益分配矛盾转化为集体抗争的行动。法团主义与庇护主义同时出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当中,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了转型期国家社会控制方式的特点。
社会转型时期,由国家延伸至社会领域的庇护网络(工作单位等)和法团体系(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等)构成的社会控制方式,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利益发挥一定的协调作用。这种控制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但近几年集体抗争行动呈多发态势的原因,也与这一社会控制方式的特点有关。
三、社会控制系统的排他性与集体行动的原因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有利于分析集体行动在特定时期多发的原因。应该说,转型以来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特点决定的社会控制模式比较有效地保持了总体的社会稳定,但无论是庇护网络还是法团体系,都无法回避其本身固有的局限。相对于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结构转型的趋势而言,庇护主义和法团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特殊主义”。庇护网络依附于正式社会设置,并有条件地选择其惠及对象;法团主义调整的对象同样不是普遍的,主要行业、有声望的群体或者新社会阶层中精英群体的诉求意见,在法团体系中得以与国家沟通。因而,由庇护网络和法团体系构成的社会控制系统具有一定“排他性”。
这一“排他性”在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时表现得更加明显。由于资源有限,庇护网络存在一个边界,为保证资源分配的效率和质量,庇护网络不会随着体制外群体的大规模增加而不断扩大;承担法团功能的利益团体本身就处在自利职能与公共职能的两难之中,为避免诉求声音变小,它也不会随着社会群体的分化不断分割成更小的利益团体。大量群体不能涵盖于既有社会控制体系之内,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就会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寻求利益保障。
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可以从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分化进程中寻出些端倪。1997年5月2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要抓好1000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以江苏为例,1997年末,私营企业数量为69900多户,到1998年,很快上升到107700多户。这次改革对增强经济活力、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过程的社会影响也很明显,首先,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发生变化,分化出原生态(白手起家)、次生态(改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获得股权后变成私营企业主)和新生态(民营科技企业的企业主),这三类私企业主本身与国家的关系就存在差别。工人这一传统社会阶层构成更加多样了,包括垄断企业工人、一般国企工人、转制国企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企业工人等类型。群体的分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从社会控制体系中脱离出去。
20世纪末企业制度变迁的同时,相应的社会结构转变在其他领域同样发生,如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变迁,又如住房商品化和急速城市化运动等。大体集中于同一时间段的经济社会变迁,都产生了一定利益受损群体,并以脱钩、改制、下岗、离职、迁移、市场化、企业化等方式游离于既有社会控制之外。2000年前后,我国社会学界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社会加剧分化的趋势,并形成了多种理论解释:一是资源重聚说,经济改革使中国从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化社会,但社会经济、文化、组织资源从20世纪末开始逐步向部分人集中(17);二是社会底部形成说,由于资源重聚,弱势群体的规模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结构,一个庞大的底部正在形成(18);三是断裂说,社会利益的分化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原子化状态,整个社会由不同的碎片拼成,或者处于社会底部的社会成员,呈现与主体社会结构脱离的特征(19),等等。上述三种理论都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描述了群体分化加剧的趋势,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资源重聚”意味着通过法团体系和庇护网络实现利益分配和社会控制的系统基本保持在原有的界限以内,甚至有所缩小;“底部形成”意味着在单位化利益分配体系与社会控制体系以外的人群规模扩大;“社会断裂”意味着国家与“体制外”、“体制内”两种社会群体的关系已经出现明显差异。
社会控制体系有“排他性”是集体抗争事件发生的原因。现代社会控制实质是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换取合法性认同和支持,因而社会控制手段与利益诉求渠道相辅相成。社会群体有相对稳定的诉求渠道时(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其利益可以相对顺畅地表达,社会控制也得以实现;反之,需要通过相对极端的形式表达利益,则危害社会稳定。排他性质的社会控制体系面对短时期迅速分化的社会时,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体制外人群利益诉求,形成下述情况:一方面,受惠较大的群体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联性不断增强,庇护网络和法团体系逐渐固化,不同群体利益结构因此得不到动态平衡,加大了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另一方面,社会底部的形成和断裂,导致社会下层处于庇护网络之外,在没有相应的团体为其代言的情况下,更多地采用群体性抗争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形成了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态势,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局势。
四、集体行动的走向与对策
当前出现集体行动的状态,是社会控制方式与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之间张力作用下的结果。我国社会控制方式形成于历史选择和制度不断演化的辩证过程中,显然并非朝夕间可以完全改变。面对当前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与处于社会控制有效范围之外的大量群体,必须突出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公共性,注重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并引导社会冲突走向有序化解决道路。
第一,缓和与分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矛盾的可控性。一般有两种作用可能导致原本分散的社会矛盾成为叠加的社会矛盾。一是各类矛盾和社会问题向某一类人群集中,弱势群体不仅经济收入低,往往社会生存能力也弱于其他群体,所以社会问题很容易在弱势群体身上同时发生,引起严重的受挫感。二是弱势人群在地理空间上聚集,改变了城市人口的政治地理态势。目前这一趋势还不明显,但在今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老城改造和新城区开发,受房价的引导作用影响,经济能力较低的群体会在城市中心衰落区和边缘新建区聚集,形成弱势群体空间聚集的格局。原本分散的冲突转化成在特定人群、地理空间上叠加的冲突,会增加社会冲突控制的难度。
要分散与缓和社会矛盾,必须从改变当前社会控制手段的“特殊主义”入手,促进形成利益共享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十二五”期间社会建设重点定位于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正体现了这一思路。把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公共性突出出来,弥补利益分配层面的不足,使社会福利不再依据人群身份或地域差异而有所差别。此外,也需要防止社会矛盾在空间上的集聚,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注意更新、改造棚户区、外来务工者集宿区等弱势群体集中的区域,鼓励开发建设不同收入人群混居的社区;把引导人口居住的机制从价格导向转为福利导向,加大城郊集中居住区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配套建设力度,以较好的社区服务和便利的生活条件,而非较低的房产价格引导人口居住。
第二,引导社会情绪,及时有效解决直接利益矛盾。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社会怨恨情绪,集体行动的诉求从具体利益走向抽象价值。针对具体经济利益受损发生的群体性、对抗性事件,其目的是挽回利益损失;而反映抽象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矛盾的集体行动,其目的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经济利益,而是反映价值倾向,表达社会不满。涉及抽象价值的集体行动无论是在影响的范围、参与人员的投入程度、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在解决难度上,都高于具体的利益冲突。
及时与有效地解决矛盾,是化解社会怨恨的必要手段。及时性要求政府正视集体行动,准确给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定性,健全政府对民意的响应机制,避免矛盾遗留或积压;有效性要求深挖社会矛盾的根源,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决策过程,逐步完善意见表达渠道。同时,要设置“安全阀”。科塞认为,“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20)。为缓解对立情绪,可以增加政府领导与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平台,提供公开提出批评意见的平台,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社会宣泄功能。
第三,引导社会冲突走常规化和有序化的解决道路。在既有控制体系之外,集体抗争行为或群体性事件不得不总是通过个案的方式分别解决,这可能催生“民粹化”或“工具化”倾向。一方面可能导致矛盾积压,而群体事件将矛头不断指向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利益受损群体逐步有意识地以群体聚集抗争为工具,利益矛盾动辄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达。赵鼎新认为,“中国目前处理集体行动的方法是有效的,但还不够,尤其是民粹主义一旦兴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把社会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处理”(21)。集体行动走向“民粹化”和“工具化”会极大增加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负担。如果社会矛盾在空间和人群上相对集聚,且具体利益的冲突向抽象的冲突转化,原本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甚至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
关键是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引导社会冲突有序化解决。如,加强和完善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建立案例依法推广的制度,避免类似的集体行动重复出现;挖掘调处矛盾的社会力量,引导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调停、仲裁社会矛盾。
注释:
①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第110~123页。
②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5~121页。
③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21~130页。
④R.V.Burks,“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Reform”,In Plan and Market: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edited by Morris Bornstein,New Ho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373-420.
⑤ V.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no.54,1989,pp.663-681.
⑥ David Strand,“Protest in Beijing: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in China”,Problems of Communism,no.39,1990(May-June),pp.1-19.
⑦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边燕杰、罗根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27页。
⑧郑也夫:《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02~111页。
⑨James C.Scott,“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 ,vol.66,1972,pp.92-120.
⑩Andrew G.Walder,“Organized Dependence and Culture of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1,1983 (November),pp.51-76.
(11)陈尧:《政治研究中的庇护主义——一个分析的范式》,《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90~91页。
(12)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98~130页。
(13)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4)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73~174页。
(15)M.Pearson,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07.
(16)M.Pearson,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p.107.
(1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8)李强:《“丁”字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55~73页。
(19)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0)[美]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2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学海》2006年第2期,第23~25页。
标签:社会控制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政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社会矛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