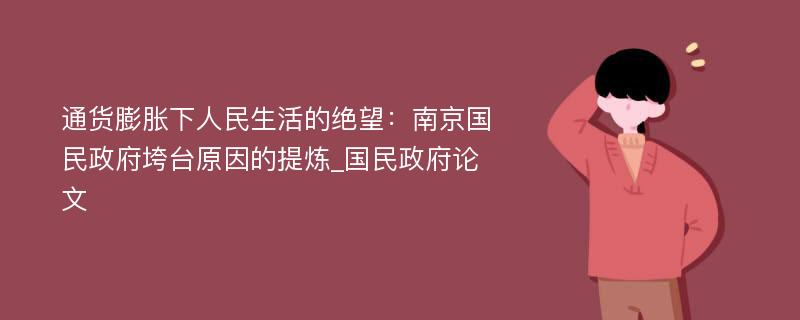
通货膨胀下人民生活的绝望——南京国民政府覆亡原因的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通货膨胀论文,人民生活论文,绝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1-0072-05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对大多数平日节衣缩食方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使他们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报纸在叙述了物价上涨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8],“一般贫民大受威胁”[9]。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食粮与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价飞涨的侵袭。食粮一日几涨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普遍,“已不成新闻”。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静海县城的集市,由于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遂随风上涨。清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至午时涨至九万元。小麦每石由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二万元,指身为业之平民及薪水阶级之公务员,闻讯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区,“百元烧饼,逐渐缩小,已缩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卖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压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车夫竟愤然大呼,“干脆来个原子弹,大家玩完”。记者认为这虽为气话,却“道尽市民苦闷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受战争影响,煤炭运输不畅,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以开滦煤矿为例,由于铁路运输的阻挠与破坏,“矿场存煤七十八万多吨”,而“青岛只能用粮食当煤烧”[12]。进入1946年后,受内战影响,各地煤荒已相当严重。开封粮价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竟导源于煤炭的缺乏。“官办的电灯公司,因无煤,停止供电;面粉公司无电停磨”,遂至土面价格飞跃增长[13]。天津郊县的唐官屯,“入冬以来,天气日寒,煤荒以愈趋严重。本镇之五家煤厂,存底为数过少,煤价乃一日数增,十日前尚卖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则售百五十元,烟煤末售百五十元,过筛煤块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记者感叹,“无衣无食的穷人们,又将怎样过这严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买不起过冬的煤炭,连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对此犯难。1947年9月记者走访北大的教授宿舍时,特别提到了煤的问题。“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15]。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16]。教法文及诗歌的闻家驷先生的太太,不无感慨地向记者抱怨:“一个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钱呢,这叫什么日子!”[17],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18](126)。显然,大家都愿意以煤为例来说明生活贫困的程度,一方面与煤炭对生活的重要性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煤价的高昂密不可分。
国共战事的进展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物价。因为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维系在物价的涨落上。连具有文化蕴涵的知识阶层,有时也不得不因生计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物价上来。1946年12月山西战事正酣,“烽火燎原于全晋”。面对中共军队的“攻城掠地”,太原各界民众“均认此严重之局面,尚属次要问题”。他们心中的首要问题,是“太原物价有涨无落,人人感到生活的重压与前途之危殆,咸恨贪污无门,囤积无资,点金乏术”。连阎锡山都不得不从战事中分出一部分精力,专门处理物价问题[19]。其原因,由于物价竞涨,“普通公务员及平民已陷饥寒交迫之苦境”,“设若物价再继续上涨,治安亦将成问题”[20]。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
“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五千元涨到一万一千五百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河南大学教授从三日起罢教,省垣各中小学亦再四酝酿着。各级公务员们则自己饿着肚,妻儿挂起嘴,表面没有罢‘班’,实际早巳怠工。辅导处进修班因为受额外学生三百名的影响,九日起已实行停炊,弄得这八百多无家可归的青年,为了活,向各机关奔走呼号。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并且弄得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21]。
总之,物价飞涨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涨的环境中谋生活”[22]。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收入减少的综合,已使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穷苦的小民发愁的连泪都流不出来了!坐在办公室的‘老实公务员’都呆得一声不响,即便有话,也是含着泪的”[23]。他们对生计的恐惧,超过了对战事的关心。“人民街谈巷议,咸以物价为话题”[24]。他们并不是对政治麻木不仁,而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逼迫。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强要他们对政治有所关心的话,那往往也是因生计艰难而对政府产生出不满与怨恨。面对生活必需品漫无限制的涨价,“万千家无宿粮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薪水阶级及穷苦群众陡然色变,心头像压着万斤重的铅块。神经脆弱的人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23]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二、抢购风潮与生活绝境
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疯狂抢购相伴随。物价上涨声中,商家“重货轻币”,囤积现象严重,导致市场上货物短缺,引起物价进一步飞涨。纸币的贬值,激起了普通百姓疯狂购物的欲望。为了减少损失,他们把手中的以及储备的纸币都拿出来投放市场,以尽快换成实物。多么井然有序的市场,都经受不住这三者的轮番轰炸,更何况当时还处于战时的特殊环境下!因此,进入1948年以后,尤其是金圆券改革失败以后,国统区进入了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与全民抢购的颠峰,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通货膨胀超出了国民政府的控制能力。金圆券改革与限价政策的实施,只使物价稳定了一个半月。金圆券改革的迅速失败,一方面与金圆券的过量发行有关,一方面则与人们对新货币的信心不足密切相关。以往的教训,时刻提醒着人们对物价的提防。1948年10月上海抢购风潮的兴起,“据上海经营督导处发行人说,是由烟税调整香烟加价而引起的。一般人以为其他货物不久加税,价格也将跟着上涨,所以马上纷纷抢购。而抢风一起,各商店又恐怕物品卖出后难以补进,提早收场并将货物退藏,更加刺激了抢购的风潮”。由此可见,滥觞于上海的全国抢购风竟然缘起于一件很小的突发事件。看似偶然,实则不然。这种情况的形成,总起来说还是由国民政府一手造成的。“人民经受长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痛苦经验,心理十分脆弱敏感,一闻涨声,对币值信心立刻动摇”[25]。
大城市由于人口密集,又是物品消费市场,最先刮起抢购风。上海是第一站,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城市。“各呢绒店、绸布店和百货商场,都是人如潮涌,个个袋内好象装满了金圆券,争先恐后的要把他们换成货物,许多店家商场的多数货物,都被抢购一空”[25]。在抢购风潮中,人们已不敢过问物价的高低。因为,“物价一天数变,这时不买,转一下身又是另一个价”。“商人们都有这般心理:货一出门,恐怕就再买不进,为着保险,就干脆更提高些”。所有的日用品市场,几乎全部“随人喊价!同是一种东西,同是一个时候,而价钱却可以相差甚远。因为卖的根本就不大想卖,宁存货不存钱,所以买不买由你”[26]。
1948年10月虽说是全民抢购的高峰,但市场上可供抢购的东西却极为有限。正因如此,社会经济秩序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在河南开封,“米面油盐买不到,煤炭柴火无处找,有钱的人都作了难,无钱的穷苦百牲更不能不苦到极点”[27]。“偶然遇到乡人推车来城卖面,必然你争他夺,大家抢购”。10月3日,一乡人推白面一小车进城,“大家自动的都往各人的面袋里装,顷刻间已将一‘车面粉购买一空,末买到的人向买到的人要求分让,而买到的人又执意不肯。初则口角争吵,继则大打出手,一时秩序大乱。后经多人从中调解,结果将面平均分配,才算了事”[28]。广州“每一家米店门前,都拥集着一群老弱妇孺鹄候买几斤公价米,每家米店只限售公价米两包,许多人站了半天,结果仍买不到米”[29]。天津的大街上也“拥挤着潮涌似的人,有老、有少、有公务员、有太太、小姐,每个人都神情紧张地向着布店、百货店、呢绒庄、皮鞋店挤来挤去”。“这些人,不挑剔货色,不争论价钱,买东西就像不花钱似地拼命挤”[30]。上述仅为各地点滴,若要详细了解各地抢购的概貌,阅读10月16日青岛的一篇通信便可一目了然:
“青市区遭遇到空前未有的难关,全市商店成了自动罢市状态,起先是食粮恐慌,全市买不到食粮,后来百货、绸缎,布匹亦步亦趋,市民及黄牛党转移注意力于百货,绸布,因此争向百货店、绸缎、布匹店抢购,不作生意的市民也跟了上去,这等商店没法应付,只好关门大吉。经政府强迫每天开门四小时,在每天开门营业四小时的时候,实际上不过仅开三小时,若改为二小时,不用说只能开一小时了。而现在呢,其他商店如鞋帽、化妆品、茶庄等店铺也索性把门关起来不营业了。还能照常开门的,只有中西药铺,而西药铺内比较贵重一点的药品也说没有了。据说,连棺材铺也把门关起来,怕人去抢购”[31]。
为了应付抢购,上海河南路呢绒店采用抽签购货办法。先请顾客们依次排队,然后举行抽签。签上载明准购的货色,如××呢等,抽中的即凭签购货,但也有很多人抽到空签,便算白等一阵[32]。在抢购风潮中,人们已非常盲目,几乎见什么都买。据当时报纸登载,“上海一家西药房门前的挤购行列中,甲客突然回头问乙客:‘你预备买什么?’乙想了一下,反问:‘你要买什么?’甲告诉他:‘有什么买什么”[33]。市民在大城市购物困难,便到近郊抢购,从而也将抢购风带到那里。天津郊区的静海即遭遇此事。天津市民苦于购物困难,每天“约三四百人乘车来静海抢购食物,不择目标。七日一批人购到茶食店、青菜铺,连粉条都用口袋装运天津。粮市供不应求,集市上都被抢购干净了”[34]。静海禁止粮食外运后,他们仍有对付办法,“来到静海县城购买玉米面蒸成饽饽,用包袱背往天津,救一时之急。每天干这种工作的人来来往往,麋集静海车站”[35]。
在这种环境里,各地都告粮荒,到处都闹紧缺,人们的基本生活已无法保障。物价自然仍是涨得厉害,“一般薪水阶级已经受到了水涨船不高的痛苦”,但是,相对于物价来说,货物的短缺更令人揪心。抢购风虽在持续,但多数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好多商店的货品都卖光了”[30]。10月8日是河北滦县的集期,“市场之各货均告绝迹,食粮市有斗无粮,居民多有钱买不着米,各种食物,猛涨之余,而且买不到手,只得仰首兴叹”[37]。
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已经超出了国民政府的控制能力。他们唯一能够实施的物价管制,只会刺激黑市价格的持续猛涨。而对于真正影响物价的关键要素——人心动荡、物资短缺与战争败局等,他们却束手无策。广大民众已到了生计无着、衣食不保的地步,“由于购不着米,家无隔宿粮的职工阶级,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38]。社会秩序也到了混乱不堪的程度,抢米事件此起彼伏。为了有饭吃,有些人竟不惜入牢。退伍军人王禀其,到上海谋事无着,骗了一件毛线衣被移送法院。在审问时,他“当庭要求法官加重判他的徒刑。他说:‘与其在上海饿死,不如暂且关在牢间里度过年关,再等出路”[39]。无独有偶,苏州一个关在牢内的年已六十多岁的吸毒嫌疑犯被法院宣判无罪后,“他反而不痛快,要求法官再还押。他说,离开了监狱,外间没有饭吃,愿在牢内住下去,坚不肯交保”[40]。这种例子虽不具有代表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解放前夕普通百姓生计之艰难。而且,由于物资的短缺,生计的困难已波及到各个阶层。正如抚顺通信所言:“现在是上等人家吃高梁米,中等人家吃豆饼、豆渣,下等人家吃草根树皮”[41]。
广大人民的无以为生必然影响到政府的统治。即使在国共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民,也是在一如既往地奋斗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生存是他们最起码的要求,但就连这点,国民政府也不能满足。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影响到各个阶层,他们生活质量的下降乃至朝不保夕,已经使国统区弥漫着败亡的气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不由得发出感叹:“国家如此,不亡何待?”[4](231)复旦大学教授储安平则愤然指出,“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42]。一个抽调了民众支持、遭遇经济崩溃的政府,已很难再维持其统治。更何况它还同时存在着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等严重问题。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国最后几年内,由于内战紧接在八年抗战之后,国民经济在未得恢复之前又大受损伤。为了应付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加大滥发纸币的力度,从而将通货膨胀推向恶性发展阶段,物价飞涨、物资短缺是其突出表现。在物价飞涨声中,各阶层人民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他们的具体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物资的短缺,使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由艰难而陷于绝望。抢购风潮之后,国民经济更是全面崩溃,广大人民也因食粮的缺乏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到生活无法维持的时候,他们对政府自然失去信心。一个失去民心、经济崩溃的政府,即使不存在军事失利、政治破产等问题,也同样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
〔收稿日期〕2002-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