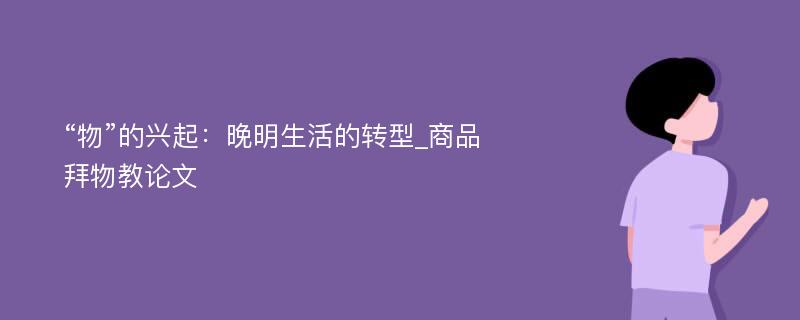
“物”的崛起:晚明社会的生活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5—0068—10
自20世纪初叶以来,晚明社会生活风习中的“奢靡”问题就已进入史学界的视野,逐步获得了充分的讨论。①多数研究都力图在“奢靡”世风的现象描述和史料发掘基础上,提纲挈领,发现和把握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向,那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问题。②当然,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晚明社会生活的消费结构、消费效果,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奢靡”只是商品经济虚假繁荣的表象,不足以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反而桎梏了经济的自由发展。③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表明,关于这一问题尚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相关讨论中,有学者曾将晚明“奢靡”风习与“崇奢”观念概括为“商品拜物教”现象。④我们知道,“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人之“异化”的概括,其实质在于以商品形式出现的“物”,遮蔽了社会交换中个人之间的实际关系,使人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一些‘物’”,并使“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和心灵发挥作用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⑤在这一观念启示下回顾晚明史,我们会发现,“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与晚明的日常生活形态变化、社会生活风气转变,以及生活观念、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结构蜕变之间,体现出了某种历史的同步性和连续性。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考察晚明社会生活形态、秩序及其内在组织力量、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而呈现出日常生活转型与社会裂变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对已有的讨论有所补充。
一 “物”的崛起:晚明社会的“商品拜物教”
在考察晚明社会生活的“奢靡”风气时,人们通常会引用嘉靖间松江人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中的一则《禁奢辨》。⑥在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中,作者一反“黜奢崇俭”的正统观念,大胆为“奢靡”辩护。⑦这在中国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却也是空谷足音。⑧就本文论题而言,该文对江南地区“奢靡”习气的描述,为我们窥见“商品拜物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提供了线索: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纹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富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工易事,羡补不足”者也。
这段记载展现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种以“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渠道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生产者、服务人员和消费者分别构成了这一关系的两端。如果陆楫的说法属实,即后者是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强取豪夺来获取商品或服务,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设,此时的“物”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逸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性质。⑨也就是说,在日益蓬勃的占有、消费和享受物的欲望助推下,“物”的地位日益凸显,开始扮演新社会关系的维系者这一重要角色。同时代的张瀚也注意到这一历史动向。他说,明代前期京师的工匠大都是隶籍于匠户、以工抵罪的人,各地工匠很少外出谋生。明中叶以后,政府工程数量锐减,对于匠户的管理也“渐加疏放”,然而京师工匠总量并未锐减,反而云集辐辏,以至“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若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没有了行政强制和财政保障,四方工匠为何不远万里涌入京师?张瀚说:
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珰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自古帝王都会,易于奢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袭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⑩上层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习气造就繁华的城市景观,这似乎是历史的通例,不足为奇。本文之所以将“物”的崛起作为晚明时代之特征,就在于这一时期,“奢靡”之风不仅弥漫于京城或江南的少数商业重镇,而且扩散到大江南北,几乎席卷了士农工商各阶层,所谓“俗尚日奢”、“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已经成为时人对世风的一致认识。张瀚的描述暗示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原本由行政力量和户籍类目制度掌控的百工细民,逐渐变成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劳动力。(11)这些人与消费者的关系,是以“物”的交换建立起来的。并且,人们对感官体验、物质享受的追逐愈没有节制,这种关系就愈加紧密和牢固。时人已经注意到此,部分开明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其在民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如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对此他自然不以为然,但也表露出一定的“了解之同情”:“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12)同样的见解还见于谢肇淛的《五杂组》等。(13)就此而言,“商品拜物教”的核心特征,即“物”在商品经济和新的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
尽管“物”的崛起在扩大生产、带动就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它还是遭到了尖锐的批判。这就要考虑到“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特征,那就是欲望的释放。马克思曾说,“商品拜物教”非但不能把人从欲望、异化劳动和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自由的主体意识,反而会刺激人的感性欲望,使人为了追逐“无生命的东西”即直接、片面的享受而沦为“物”的奴仆,坠入欲望和异化劳动的深渊。所以他又把“商品拜物教”称作“感性欲望的宗教”。(14)晚明时期,针对“奢靡”世风的批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放纵物欲所带来的人格异化的警觉,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批判观点的锋芒,主要还是指向其对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如吕坤曾说,往昔士民生活俭朴自足,“自饱暖以外无过求,自利用之外无异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人们崇礼尚义,安分守己,“偶行于途而知贵贱之等,创见于席而知隆杀之礼。农于桑麻之外无异闻,士于礼义之外无羡谈,公卿大夫于劝课训迪之外无簿书”。(15)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在“奢靡”习气的波及下,世人变得好逸恶劳、放纵欲望,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本心”,“百亩之家不亲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业……身衣绮縠,口厌刍豢,志溺骄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为”。更令其愤慨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和价值观念、伦理秩序均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人们“以农工为村鄙”、“以勤俭为羞辱”、“以教养为迂腐”,“子弟不知有父母,妇不知有舅姑,后进不知有先达,士民不知有官师……目空空而气勃勃,耻于分义而敢于凌驾”。似乎只有“耳目之玩”、“游戏之乐”能引起人的兴趣,成为世人趋之若鹜的人生目标,(16)这是“物”在既定社会关系、伦理秩序之解体过程中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而言,晚明社会生活的“奢靡”风气实则预示着一种“商品拜物教”景观的形成,作为商品形式而存在的“物”在晚明社会关系的渐变进程中发挥着除旧布新的中介和催化作用。晚明工商阶层为迎合市场需求而争相“呈能而献技”、“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的热情表明,一种奠基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潜滋暗长。它以世人对感官享受和物质体验的高度热衷为契机,把欲望对象——“物”推向了时代前沿。
从前引陆楫、张瀚、王士性、谢肇淛、吕坤等人的言论来看,晚明知识分子已经隐然察觉到“物”之崛起的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和历史走向。他们对于这一趋势和走向的不同态度则表明,晚明思想界已经开始了分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观念图式。其中较为通达开明的人士对工商业在民生、就业方面积极作用的肯定,堪称此后所出现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观念的嚆矢;而那些激烈抨击世风人情的正统派知识分子,尽管并未提出兼具时代性和建设性的观念,但他们的言辞中所流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传统社会规范、秩序和伦理关系几近“大坏极弊,瓦解土崩”的危机。如吕坤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就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清醒。他没有像张瀚、王士性那样把“世风败坏”的罪责简单推到某些特定人物或阶层身上,(17)而是将其称为“势”之必然:
势之所在,天地圣人不能违也。势来时即摧之未必遽坏,势去时即挽之未必能回。
也就是说,尽管俗尚奢靡、世风颓丧,是与“道”相悖而行的,但“大段气数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违,天地亦顺之而已”。(18)“物”的崛起就是这样一种“道”之所不必然,然而“天地圣人不能违”的历史大“势”。
二 “奢靡”新生活:物质性的凸显与蔓延
将“物”的崛起概括为“商品拜物教”,是就其社会属性而言的。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物”则更多体现出其“物质性”的一面,也就是其作为生活资料、感官欲望和审美趣味的对象的形式。前文所引的史料也都表明,对晚明人而言,“物”的崛起首先是一个生活层面的问题。人们对于社会关系、伦理秩序之蜕变、解体的发现,大多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观察。因而,将“物”还原到晚明的日常生活形态及其变迁中,通过社会、日常生活两种视野的交叉与融合,或可更细致地抽绎出“物”的崛起所象征的历史动向。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肇极于明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水准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历史的空前高度。此前,由于整体经济、社会水平的限制,在传统日常生活形态中,“物”(物质)与“心”之间维持着一种极不对称的平衡,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一种物质上简单粗粝的生活方式,而把心性修养、精神体验放在突出的位置。人们对于物质性内容的要求,被限定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层面,并与相应的社会身份相勾连;人在感官和趣味方面对“物”的需求,也常借助于一种超越物质体验、现实利害的间接、审美的方式来实现。(19)直到明代前期,这种生活观念和日常生活形态,依然占据着主流。晚明时期,人们在批评“奢靡”世风时,经常把明代前期“简朴醇厚”的生活风气作为参照系。如前文提到的张瀚就说: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20)
所谓“画一之法”,不仅体现在服饰上,而是包括饮食、器用、房舍、乘舆、节庆礼俗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据《明实录》载,明太祖认为元朝失政源于“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贵贱无等,僭礼败度”,(21)因此,他在位期间,就士农工商各阶层日常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颁布了明确规定,以期重建“礼乐”制度、维护统治秩序。嗣后,永乐帝等也有类似的举措。这些繁琐、苛刻、蔓延遍布日常生活每个细节的规定,在《明史》的“礼志”、“乐志”、“舆服志”等文献中均有呈现。严刑峻法,加之以历经长期战乱,经济社会尚待复苏,张瀚所描绘的明初四民“人遵画一之法”、各安其分的日常生活图景,就不难理解了。从明初至中期成化、弘治年间的社会生活风气,一直是简朴醇厚、恪守礼法的。“家徒四壁”、“环堵萧然”、“身无长物”等构成了时人描述其日常生活状态最常用的关键词。(22)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的生活观念中,也极少表达超出“温饱”的物质诉求。(23)
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农业的复苏、工商业的日渐繁荣,以及政治生态的缓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有关生活理想的表述中,“物”的地位逐步凸显出来。人们不再满足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而是期待着在日常生活中充分体验和享受物质欲望、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快乐,追求一种“逍遥余岁,以终天年……受用清福”的世俗生活目标。(24)与此相应的是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传统“造物”工艺的提升,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如据王锜《寓圃杂记》载,晚明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25)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所谓“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一幅盛大的物质文化景观——在这种内在生活观念蜕变和外在物质供给日渐充裕、精致的综合语境下,晚明人的日常生活中对“物”的重视和利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有学者注意到,晚明时期,人们不仅关注物质生活的充裕,而且倾心于玩物、赏物,借“物”来构筑养护生命、颐养性情的生活空间。(26)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凸显出来,并逐渐渗透到情感、审美和精神领域,最终催生了一种前面所论及的以“奢靡”为症候的崭新的日常生活形态。
一般而言,所谓“奢侈”,是指日常生活中“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其表现有二:一是从生活物品的数量上而言,表现为“挥霍”;二是从其质量上而言,体现为“精致”。(27)这两种奢侈化生活倾向,在晚明的“奢靡”风习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呈现。生活于嘉靖、万历年间的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不吝笔墨,以整整一卷文字记载了嘉隆以后松江等地世风日趋奢靡浮华的生活景象,如服饰方面:
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嘉靖时,民间皆用镇江毡袜,近年皆用绒袜,袜皆尚白。而贫不能办者,则用旱羊绒袜,且与绒袜乱真,亦前所称薄华丽之意。
又如家居器用方面:
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28)
范濂所记的还有出行乘轿辇、游乐坐画舫,乃至笙歌戏曲、卖婆帮闲等现象,也都是旧时罕见而近日波靡成风的。这些生活景观和社会现象,基本上不外乎“挥霍”与“精致”两端: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鞋袜、服饰、家具等用料日趋名贵,制作工艺也崇尚精致华美;另一方面,非必要的消费,如书房禅室、乘舆画舫、歌吹舞伎等,呈现出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这两种表现,在“人遵画一之法”的明初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常见的,因此,在正统知识分子眼中,晚明世风人情已经“僭滥之极”。(29)所谓“僭”,是指“奢靡”风习所引发的社会规范、伦理秩序危机,这一点前文中已有论述,并且后文将详论其内在机制。这里先看所谓“滥”,也就是日常生活形态本身的变化。
如果暂时搁置“奢侈”一语暗含的道德判断,我们大概能推测:当“奢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景观时,它可能意味着该社会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奢侈是历史的、相对的,尽管有“超出必要的开支”这一界定,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域或阶层的人而言,“必要”的开支却是不稳定的。范濂曾感叹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30)他没有言及,鲜衣美馔、肥马轻车之流行,实则奠基于时代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此,王家范先生的抽样调查证明,明中叶以后,士民阶层的最低生活标准有了显著提高,(31)前引范濂所举的下层民众穿“暑袜”、用细木家具、布置书房禅室等均是明证。嘉靖名臣张罗峰(璁)曾说:
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普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今乃人人侈用,一变至此,诚不可不反正还淳。(32)
“人人侈用”已是不争的生活事实。范濂、张璁等人或许并非看不到这意味着民生的改善,引起他们忧虑的,是在一种物质供给空前丰富充裕的生活形态前,传统“安贫乐道”、以“心”御“物”的生活观念已丧失了约束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背弃了“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用物原则,(33)而是追求“适用美观均收其利”,(34)这就导致了人们把更多的心思、机巧消耗在如何营构赏心悦目的日常生活情境上。换言之,人们不再满足于那种超越感官欲望和物质享受、与现实利害隔绝的间接的古典式情感、审美和精神体验了,而是借助于“物”来装点和营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情境,通过日常的、感官的物质体验来满足情感、审美和精神诉求。这无疑表明了人的审美和精神生活对于物质性体验之依赖的强化,亦即前引马克思所言的由追求直接的、片面的感官享受所导致的人的“异化”。晚明冯梦祯在《真实斋常课记》说自己平日除“教子弄孙,对老妇宴,语娱小姬,有客对客”等家常事外,几乎把所有的空闲都消耗在玩物、赏物上:
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35)
名满天下的陈眉公(继儒)也积极宣扬,生活的真义在于“一人独享之乐”:
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36)
斯风日炽,就连下层贫士平日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37)甚至有人把“长物”标榜成“才、情、韵、趣”的象征,(38)为搜罗、积蓄“长物”而“呕心出血”、“典衣破产”。(39)在他们看来,“长物”已变成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这表明基于日常生活的水平的提高,物质性不仅凸显于人们的生存需求层面,而且蔓延到情感、审美活动的领地,在精神生活中开疆拓土,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一种以物质性凸显为表征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逐渐趋近、融合的新生活形态崭露头角。当这种生活形态风靡开来时,它对于当时社会的既定秩序而言,就会形成显在的威胁了。
三“时尚”:穿行于日常生活与社会间的“物妖”
前文已粗略论及“物”在晚明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之蜕变、解体中所起到的中介和催化作用。这里想深入分析的是,“物”的这种中介或催化作用是如何产生的?晚明日常生活形态转型与社会裂变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关联?
马克思在谈论“商品拜物教”时曾说,商品经济中“物”之表面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非其自然属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赋予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竞逐、崇拜“物”,从而使其蒙上了一层“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魔法妖术”。(40)饶有趣味的是,在晚明知识分子对“奢靡”世风的议论中,有关“物”的批评也流露出浓郁的神秘气息和怪诞意味。如何良俊看到,时人大多沉迷于物欲诱惑“溺而不能返”,他愤然感慨地说:“自中人以上有不能免者,其能奋然自拔者几人哉?”(41)许多人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看来不啻为耸人听闻的说法,来概括这种“物”的“惑溺”——“妖”。如王士性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进退上下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42)
这段描述印证了前引范濂的说法,即苏州(吴门)乃是时下流行的精致、清雅的生活方式的发源地。前文提到,王锜曾说晚明苏州“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所谓“多”,是就生产规模而言;“巧”则指生产技术、工艺的提升。张瀚曾说,由于从业人口增加,百工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不得不争相“炫奇而贾智”,通过提高服饰、器用的形式美感来吸引更多主顾“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所制器物自然“巧几于淫”。(43)王士性所说的“物妖”,就是指这种奇技淫巧。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概括出“物妖”的两个核心特征:一是精巧雅致,二是风行海内。就此而言,它们并不具备不可知的特质——众所周知,在传统观念中,妖与鬼、神等都是超自然的神秘现象或事物。大致而言,天地为神祇;人死为鬼;妖则指由物而生的邪魅精怪,所以通常说成“物妖”、“妖物”或“物怪”。(44)晚明时期,有关“物妖”的记载并不罕见,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说法,如“服妖”、“墨妖”、“扇妖”等。(45)这些耳目之内的日用平常之物,何以被冠以妖异、神秘的称谓?
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引入一个相关概念:“时尚”。一般认为,“时尚”(fashion)是指起源于中世纪晚期欧洲宫廷和上层贵族间的流行生活风气和现象。而据笔者考察,在汉语传统中,至迟在唐宋时期,“时尚”就常用以指称社会流行风气和好尚,到了晚明时代,“时尚”一语所概括的世风人情则具体到服饰、器用、休闲娱乐等流行生活趣味、方式上来。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用“时尚”指称日用器物的流行样式;(4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用它描述休闲娱乐方式和服饰风格;(47)文震亨《长物志》用它描述玩物、赏物的生活趣味以及流行的器物形制;(48)而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时尚”则被用来全面概括时兴的生活方式、趣味和好尚。由此可见,晚明时期已经出现了生活“时尚”的自觉。王士性所抨击的“物妖”,以及其他人眼中的“服妖”、“墨妖”、“扇妖”等,皆是时尚中的流行之物,具体而言,有苏扇、苏绣、苏铸、苏笺、吴帻、吴笔砚等;而由这种时尚之“物”所支撑起来的生活方式,则被时人称为“苏样”、“苏式”或“苏意”生活。
“物妖”这一说法的奥妙,就隐藏在时尚的趣味及其社会效应中。在传统观念中,日常生活并非孤立、个别的,而是与世道治乱、宇宙大化存在着普遍的关联。“妖”通常被视作穷途末世的征兆,(49)“物妖”、“服妖”、“墨妖”和“扇妖”等说法,同样诞生于此种关联性认识。(50)在古人看来,妖之所以反常、有害,在于其新奇、艳冶的感官呈现方式,(51)能勾起人无限的欲望,进而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而这正是所谓“时尚”的要义。法国学者吉勒斯·利浦斯基曾说,时尚从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诱惑的美学”。(52)从王士性等人对“物妖”、“服妖”等的描述来看,新奇与美观是其所向披靡的制胜法宝。也就是说,附着形式上的感官和审美“趣味”是为物“赋魅”的关键所在。晚明的生活时尚,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感官和审美趣味的魅惑。据李乐记载,万历间“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若辈皆好穿丝紬、绉纱、湖罗,且染色大类妇人”。(53)为此,他曾专门作过一首诗来讽刺这种服饰风尚:
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4)
这种艳丽的服饰风格遭到正统知识分子的大肆抨击。然而“厌常喜新,去朴从艳”是人之常情,(55)在时尚的诱惑面前,且不必说“嗜尚乖僻,专欲立异尚”的浮浪子弟,(56)就连以维护风教伦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也丧失了洁身自好的自主性。如对“奢靡”风习颇为不满的范濂,也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到时尚的潮流中:“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至习俗移入,贤者不免!”(57)前文提及,明初士民各阶层日常生活谨遵“画一之法”,这种秩序井然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是由政治力量和传统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共同组织、运转下的稳固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秩序。时尚的风靡,在改变了日常生活形态的同时,也冲击、瓦解了其背后的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顾起元曾以女性服饰为例揭示出这一社会症候。他说,传统礼制对女性配饰的款式、颜色和用料等均有明确规定,旨在借用一种装饰性的手段来区分身份贵贱、规范女性的日常行为举止,如裙裾上的玉佩,“系之行步声璆”,令佩戴者有所顾忌,名曰“禁足”——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文明化的“软暴力”,而它正是传统生活观念的核心要义。然而,当时尚的潮流袭来,人们醉心于饰物本身之材质、花样的翻新,只在装饰性和趣味性上下工夫,反而忘记了饰物背后的观念初衷。顾起元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古取其用,今取其饰”,(58)他所标举的“用”与“饰”的差异,深刻揭示出时尚所潜在的“除旧布新”的力量。
时尚的另一要义在于其自我翻新的迅疾性。凡伯伦说,时尚中的美感与趣味“没有一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59)张瀚曾记载,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60)顾起元也说,南京妇女服饰“三十年前(引者注:万历初)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61)这说明时尚中的趣味在装饰性和审美性之外,还具有其他的内涵,那就是自我标榜的身份诉求和个性冲动。社会学理论认为,趣味是社会区隔的标志,发挥着“阶级”的诸种标志功能。(62)晚明时期,追逐时尚的行为背后往往潜藏着一种从整齐划一、秩序分明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中破茧而出,重新确认自我身份、等级地位的冲动。如通俗小说中经常有对市井小民、流氓无赖模仿读书人服饰风尚的描述,(63)而道学家们则往往指斥这种模仿泯灭了“贵贱”、“等威”,(64)无疑均表明了趣味的身份标志意义。时尚之所以翻新迅疾,除了商业运作的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65)
在时尚的大潮中蠢蠢欲动的人们,为了标榜个性、凸显自身的身份,追逐感官和审美趣味的满足,强化俗世日常生活的快乐,将礼法与道德、伦理规范弃如敝屣。(66)其影响所及,不仅重构了一种以“奢靡”为症候、以物质性凸显为实质的日常生活形态,而且诱发了“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以及既定社会关系、伦理秩序的危机。就此而言,作为欲望对象的“物”,似乎是诱发生活风气和社会秩序蜕变的罪魁祸首,其被斥为“物妖”,就不难理解了。“物”在晚明生活转型和社会裂变中所发挥的中介或催化作用,正来自其对时人日益膨胀、不断释放的感官和审美趣味需求的满足。与传统的生活和审美观念相比,这种“趣味”的世俗性、日常性和物质性空前凸显,因而可以称之为一种日常生活美学。对此,笔者将专文讨论,兹不赘述。
四 余论
布罗代尔提出,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必然性生存需求的逼迫,还广泛牵涉到各文明类型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和秩序。(67)他认为15至18世纪欧洲社会兴起的生活“时尚”反映出一种“勇于与传统决裂”的社会动向,代表了“该文明的活力、潜力和要求,以及人生的欢乐”,(68)正是这种“除旧布新”的冲动,成为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晚明时代的中国,伴随着“物”的崛起、“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以及“时尚”和“物妖”的风行,中国社会内部也滋生出一种勇于与传统决裂的历史动向。(69)这种背离传统的“活力”和“潜力”,不仅呈现为本文所详论的追求世俗人生、日常生活之快乐的生活实践,而且在文艺、学术和思想领域也有积极的显现,这就是晚明美学史、思想史研究领域所津津乐道的“浪漫洪流”和“早期启蒙思潮”。(70)在这种意义上说,“物”的崛起所预示的晚明社会变迁,实为一种全方位的结构性蜕变,亦即中国文明的一次自我调适和历史转机。
至于这一调适和转机为何不曾蝉蜕出近代社会的崭新形态,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考察范围。在这里,本文最后想申述的是,“物”本身并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在社会层面而言的“商品拜物教”中,“物”的虚幻独立性和客观性是由商品关系所赋予的;在生活层面而言的“感性欲望的宗教”中,“物”的“魔法妖术”是由人本身的感官欲望所赋予的;“时尚”,尤其是屹立于时尚潮头的“物妖”,成为关联和维系晚明生活转型与社会裂变之历史同步性、一贯性的形式载体。“物”就像一条绳索,一端牵连着商业和商品经济,另一端则锁系着人的感官欲望和审美冲动。关于前者,学界已有充分的论述。而对于晚明的欲望释放潮流,迄今的研究仍大都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前文多次提及的吕坤曾说:
儒戒声色货利,释戒色声香味,道戒酒色财气,总归之无欲,此三氏所同也。(71)
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长期浸淫在“三教”文化氛围中的人们,尤其是饱受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训诫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何会燃起世俗生活的热情,敞开胸怀尽情拥抱在传统观念中向来被作为人格和生活境界之对立面的“物”?从本文的引证来看,晚明批评“奢靡”、抨击“惑溺”的声音不可不谓高亢,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人们离经叛道,投身生活时尚的洪流?这些问题,都是更待深究的。
注释:
①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张其昀《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1、2期)、汪伯年《明人生活杂纂》(《新史地》1937年第1期)等。1935年,吴晗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中较全面地概括了晚明文人士大夫阶层奢侈生活风气的诸多表现及其对时代文艺、学术思潮的影响(《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1期,1935年4月19日)。50年代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等一系列史学命题的提出,晚明的“奢靡”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参见钞晓鸿《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7页。
②如傅衣凌从“奢靡”习气中看到“城市中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将“俗尚奢靡”观念的实质概括为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启蒙思想”(《明代后期江南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7—109页);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将社会生活风气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日用”思潮等进行了关联性探究,概括了其对“封建伦理关系”的冲击(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208页);徐泓、余英时等则从思想史角度讨论了“崇奢”观念与儒学近世转型问题(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邢义田、林丽月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社会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318页;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向》,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京广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164—211页)。
③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二》,《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④赵靖:《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拜物教思想》,《赵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202页。
⑤[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4页。
⑥赵靖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6—547页。原文本无标题,“禁奢辨”是该书编选时所拟的篇名。
⑦参见[美]杨联陞《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传统中国的一种罕见观念》,《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8页。
⑧郭沫若1954年发表《〈侈靡篇〉的研究》曾就《管子》中所表现的通过大量消费促进生产、带动就业的经济思想展开分析(《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7—167页);前引杨联陞论文也有相关讨论。
⑨马克思:《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8—89页。
⑩张瀚:《松窗梦语》卷4,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页。
(11)赵轶峰:《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2)王士性:《广志绎》卷4,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9页。
(13)谢肇淛《五杂组》卷15谈论京师不论“贵贱”出行皆好“乘辇”时说:“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14)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15)吕坤:《呻吟语》,吴承学、李光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16)吕坤:《呻吟语》,第86—87,215—216页。
(17)吕坤说:“坏世教者,不是宦官宫妾,不是农工商贾,不是衙门市井,不是夷狄。”《呻吟语》,第214页。
(18)《呻吟语》,第205页、第207页。
(19)笔者在《闲情何处寄?——〈闲情偶寄〉的生活意识与境界追求》一文第三部分“生活意识的觉醒与‘美活’的境界追求”中有详细论述,《文艺争鸣》2011年2月号(上半月)。
(20)张瀚:《松窗梦语》卷7,第140页。
(21)《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55,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册,第1076页。
(22)如顾起元云:“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客座赘语》卷1,谭棣华、陈稼禾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页)何良俊也说,“孝、宪两朝(引者注: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众多官职显赫的人家平日生活“只如寒士”(《四友斋丛说》卷34,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页)。
(23)如崇仁理学大家吴与弼曾说:“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为幸。”其弟子胡九韶则认为,只要“生太平之世,无兵祸”、“一家乐业,无饥寒”、“榻无病人,狱无囚人”,就是享尽了“清福”(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页、第45—46页)。
(24)高濂:《遵生八笺》,王大淳整理,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09页。
(25)王锜:《寓圃杂记》,张德信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页。
(26)[英]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Polity Press,Cambridge,1991;毛文芳:《晚明闲赏美学》,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
(27)[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0页。
(28)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笔记小说大观》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本,第13册,第111页。
(29)龚炜:《巢林笔谈》卷4,钱炳寰整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页。
(30)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第110页。
(31)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二》。
(32)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1—132页。
(33)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页。
(34)李渔:《闲情偶寄》卷4,单锦珩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35)冯梦祯:《快雪堂集》卷4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64册,第648页。
(36)陈继儒:《太平清话》卷2,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8页。
(37)孙枝蔚:《埘斋记》,《溉堂文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1145页。
(38)如沈春泽《长物志序》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李渔宣称器玩的摆放布置不但显示主人情致,甚至于庙堂经济的才略:“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人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非特泉石勋猷于此足征全豹,即论庙堂经济,亦可微见一斑。”(《闲情偶寄》卷4,第230页)
(39)程羽文:《清闲供》,虫天子:《中国香艳全书》,董乃斌等点校,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册,第281页。
(40)刘召峰:《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考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41)何良俊:《何翰林集》卷14《何氏语林序论·惑溺第三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42册,第122页。
(42)《广志绎》卷2,第33页。
(43)《松窗梦语》卷4,第78—79页。
(44)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册,第306、470—472页。
(45)晚明文献中有关“服妖”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载万历间张献翼、刘凤等人身着奇装异服,被时人目为“服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82页);该书《补遗》卷4载成化、弘治间从朝鲜传入的“马尾裙”形制怪异、风行一时,亦被称为“服妖”(第913页),类似记载又见于王琦《寓圃杂记》卷5(第41页)、陈洪谟《治世余闻》卷3(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页)、于慎行《穀山笔麈》卷15(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6—177页)等;戴冠《濯缨亭笔记》卷3云:“弘治壬戌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鲶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倡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积几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子部第1170册,第452—453页)关于“墨妖”、“扇妖”等不赘举,见《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条,第660、663页。
(46)《遵生八笺》,第598页。
(47)《万历野获编》卷25“时尚小令”条,第647页;卷26“物带人号”条,第664页。
(48)《长物志》卷2“盆玩”条,第96页;卷4“鱼类”条,第127页;卷7“灯”、“文具”条,第272、312页。
(49)《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第1888页。
(50)如《汉书·五行志》云:“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73页。
(51)在古汉语中,妖常常与“美”、“艳”、“巧”、“媚”、“异”等连用(参见宗福邦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10页),这些逾越常规的感官印象,构成了妖的外在形式。
(52)[法]吉勒斯·利浦斯基:《西方时尚的起源》,杨道圣译,《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1期。
(53)李乐:《见闻杂记》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817、914页。
(54)《见闻杂记》卷10,第817页。
(55)《见闻杂记》卷10,第913页。
(56)《广志绎》卷2,第33页。
(57)《云间据目抄》卷2,第110页。
(58)《客座赘语》卷4,第111—112页。
(59)[美]凡伯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0页。
(60)《松窗梦语》卷7,第139页。
(61)《客座赘语》卷9,第293页。
(62)[法]布迪厄:《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范静哗校,《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63)《无声戏》中说苏州平民王小山“头戴一字纱巾,身穿酱色道袍,脚踏半旧红鞋,手拿一把高丽纸扇”(《李渔全集》第8卷,萧欣桥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三侠五义》中说侠盗白玉堂“乔装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样,头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双厚底大红朱履,手中轻摇泥金折扇”(陈世杰、任曼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情梦柝》中女扮男装的若索“头戴纯阳巾,身穿白缘领石青绸服,脚下京青布靴”,男子楚卿则“头戴飘摇巾,内穿荔枝色缎袄,外披白绫绣花鹤氅,脚下大红紬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据范濂记载,此类装扮是读书人中所流行的服饰风尚:“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云间据目抄》卷2,第110页)。
(64)《松窗梦语》卷7,第139页;卷4,第76页。
(65)《客座赘语》在描述人们的心理时说:“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这表明“当时”与否已经成为身份的表征(卷9,第293页)。
(66)顾起元说,“服舍违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为严备”,而晚明士民却置若罔闻,这无疑是“法久就弛”的表现。更令其忧心和无奈的是,士大夫中如果有人谈及法令、制度,大家通常的反应却是“不以为迂,则群起而姗之”(《客座赘语》卷9,第293页)。
(6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4页。
(68)《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81—382页。
(69)布罗代尔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顶面具延续若干世纪保持不变”,他曾引用一幅18世纪中国官员的肖像画来证明中国服饰长期一成不变,殊不知该画虽作于清代,但肖像主人公的衣冠服饰显然系宋代文官形制,并非写实(《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68—369页)。笔者认为,虽然这显示出布罗代尔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入,但其对“时尚”与文明进程之关联的概括,仍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70)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08页。
(71)《呻吟语》,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