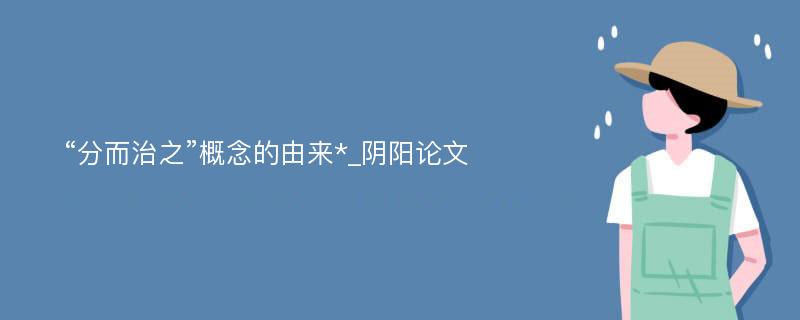
“一分为二”观念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为二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分为二”的命题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一分为二”作为一种正式的书面表述,那是比较晚的。隋代学者杨上善在注释《黄帝内经》时说:“一分为二,谓之天地也。”北宋哲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说:“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亦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但在先秦两汉诸子的文章中,有着许多类似的表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吕氏春秋》言:“太极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又,《淮南子》:“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为阴阳,阴阳和万物生。”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一生二”,“太极生两仪”,“一”分为“阴阳”等思想,即“一分为二”的思想。在这些说法中,“一”表述为“道”“太极”“太一”“浑沌”;而“二”除了直接表述为“两”“二”之外,还表述为“阴阳”。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一分为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的一种表述方式。人类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总有其具体的形而下的发生学基础。“一分为二”作为一种纯粹抽象的哲学观念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当人类从地平线上站立起来时,开头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具体事物的分类接触到这个规律;后来,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略有提高,才用象征的手段来把握这个规律;最后,当理性觉醒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于是他们用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来表述这个规律。这是一个从具体概念经过象征概念再到抽象概念的发展过程。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追索“一分为二”这一哲学概念所经历的“具体——象征——抽象”起源过程。
人类的认识的发生是认识主体和物质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主体和客体是靠实践联结起来的。“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1〕所谓认识主体,指的是在实践中认识并改造物质世界的人;而物质客体,指的不是单纯的客观实在性本身,而是那些被主体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改变和整理着的客观实在性。客体一定存在,存在不一定是客体。只有人类实践活动的“手电光”照亮的地方才会被人类看见,这个地方的事物才能进入人类的认识领域。其上无物,其下亦无物!自然界的事物在没有和人的实践活动发生直接联系时是不能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当代著名发生认识论研究者皮亚杰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经验有两种:一是“物理经验”,一是“逻辑——数理经验”。物理经验的形成是“从运动学或动力学的角度把客体在时空上组织起来”〔2〕,形成“广义的因果关系”〔3〕。而逻辑—数理经验则“来源于行动本身,因为它是从行为的协调中抽象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从对象本身抽绎出来的”〔4〕。 这种“行为的协调”在于“把主体的某些活动或这些活动的格局联合起来或分解开来,对它们进行归类、排列顺序,使它们发生相互关系,如此等等”〔5〕。很明显,皮亚杰所说的第一种经验起源于实践活动所接触的对象间的关系,即活动的内容方面。而第二种经验则起源于实践活动本身的结构,即活动的形式方面。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其实包含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认识的内容起源于人类在实践中所组织起来的客体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认识的形式(亦即思维方式)则起源于实践活动本身的结构方式。
在旧石器时代,初民刚刚从地平线上站立起来,他们的实践活动主要是狩猎采集活动。在狩猎活动中,初民拿了矛或石球之类的工具去捕获野鹿、野牛、野马之类的野兽。这时牛、马、鹿之类的动物进入初民的头脑,成为他们最初注意并力图加以认识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它们的认识内容。而另一方面,初民的猎获牛、马之类的动物的活动格局决定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此时人类狩猎活动结构只有三个要素,即“人——矛或石球——牛、马”。在这里,用于结构的事物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故而这种实践活动结构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亦具有具体性特点。在具体性的思维方式之下,初民初步对实践中接触到的与他们生计密切相关的最重要的事物进行最简单的两分式的分类。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昂在对旧石器时代欧洲60多个洞穴壁画的艺术形象进行长期的调查、整理、统计和研究以后,发现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几乎一半以上是马或野牛。由此,他将这两种动物分为A组(马)和B组(野牛),并发现了一个基本主旋律,即“雄性—雌性=马—野牛”〔6〕。也就是说,“马”(无论是雌雄)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看来都是雄性的,而“牛”(亦无论是雌雄)却都是雌性的。当然这并不是原始人不能凭视觉分辨出雌雄的外在形态,而是他们在内在的观念上作这样的区分。这是马与野牛结合的“二元主题”〔7〕。据此, 他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具备了一种“两分法的分类法”〔8〕。而且,古昂发现,在有些洞穴中,A组动物和B组动物又各自一分为二,于是,整个系统就表现为“双重配偶”,“即表现为公野牛与母马相对,母野牛与公马相对。”〔9 〕如果我们把古昂所分析的马与野牛看作第一个层次上的一分为二的“两分”,那么,双重配偶便是第二个层次上的二分为四的“两分”了。我国一些学者发现,西方文化这个重要的文化拟象与中国文化竟是惊人的相似。朱狄先生在《原始文化研究》中论及此问题时说:“也许勒鲁伊—古昂的假设会被人们斥之为荒诞的,不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关于‘牛—马’的‘二元论体系’也可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找到,而且内涵也完全相同,即牛代表雌性,马代表雄性。”“但为什么马为男性,牛为女性,《周易》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因此也是一种‘先验的体系’。但这两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何以会有如此巧合,实在令人费解。假如勒鲁伊—古昂的解释基本正确(细节上的失误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避免),那么中国殷周之际的《周易》将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就在‘马—牛’二元论上相遇了,这是最早的中西文化的相遇,也是在构成世界始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的相遇。”〔10〕
中西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分道扬镳,但是就其开头来说,都是从“人类潜能的全弧上”截取下来的一段,在文化发生的最初阶段上,东西方初民的思维方式并无多大区分。野马和野牛在初民狩猎经济阶段作为初民长期的、稳定的、重要的食物当无疑问。从艺术表现的考古实证看,虽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尚有待出土,但我们可以推论:很可能中国与欧洲一样,这种“两分法的分类法”也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帝王世纪》和《易传》皆言伏羲“伏牛乘马”,这里的“牛”“马”已经是作为被初民驯服的动物而进入初民的观念,这是农牧经济阶段的事情。而牛马作为野生动物和人类生活发生联系当在狩猎经济时代。我们认为,《易传》中的牛马二元对立观念是初民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经济时代就产生了的而被砌到《易传》这一文化典籍的大厦上的一个原始观念的砖块。“马”“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初民的意识是在狩猎经济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发掘提供了证据,丁村文化中与人类并存的哺乳动物就有野马、原始牛。许家窑文化中亦有野马、原始牛化石。在旧石器晚期河套人所创造的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掘中亦发现有原始牛和蒙古野马。峙峪遗址“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多的野马,至少代表120个个体〔11〕。初民将“马”与“牛”这两种具体事物去进行两分法的分类,这是“一分为二”观念的萌生阶段。
随着生产实践的进展,初民的实践活动的结构出现了变化,于是初民用具体的事物来进行两分法的分类逐步为用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来进行分类所代替。这种变化是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阶段的到来而出现的。
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阶段,初民的实践活动不再是直接采集果实和捕捉野兽为食,而是先与土地打交道,土地上长出的庄稼才是初民的食物。这种间接性使初民的活动格局出现了大的变化。他们首先需拿了石斧之类的砍伐工具,芟除杂草,割去荆棘、砍掉树木,或者放火将草木烧光,整出一块土地,然后,才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当新苗长出以后,初民又盼望老天能够风调雨顺,阴晴得时,方能有所收获。这样,初民对于他们不能直接控制和把握的“阴阳”等自然现象产生了畏惧与亲近的双重感情,这些自然现象“才对人获得特殊的意义”,成为崇拜的对象〔12〕。只有在农业经济阶段,初民的实践接触到阴阳风雨这些事物或现象,阴阳风雨才成为人类注意和认识的对象。因此,我们前文所引述的先秦两汉典籍中将“阴阳”作为“一分为二”观念的具体内容,其产生年代当在原始社会的农业经济时代。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初民的“两分法的分类法”用“牛、马”来表示的时候,这两种动物是第一种生产实践中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但因为这时性活动对于第二种生产即“种的蕃衍”领域中的作用由于时间间隔太长,因而直观式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对此进行认识,所以“牛、马”又被用来表示第二种生产领域中的观念和认识。彼时他们一概将无论是雄马还是雌马都看成是雄的,而把无论是雄牛还是雌牛一概都看成是雌的。而在农业经济阶段,由于初民的实践活动结构不断复杂化,结构要素不断增多,从而初民已经摆脱了具体的、直观的思维方式而转变成了象征的思维方式〔13〕。由于春种一粒粟,到秋天方能收万颗籽,初民可以对这长达半年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把握,故而这种思维结构亦被运用于第二种生产领域,性与生育的关系这个隐秘被人类的实践的手电光照亮了,于是性活动被列为实践活动的结构。这样初民就具备了将两种生产领域分开表达的能力。但是在采集和狩猎经济时代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即将“两种生产”合一来表述,这一文化传统当然也要影响到农业经济中。于是,他们用“阴阳”这一概念来进行象征式表述。阴阳最初来源于初民在农业经济中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阳字均与日相联系。阴,甲骨文未确认,金文“阴”相对于阳,有云复日之意。但阴阳之义并非限于这两种具体的自然现象,而有扩大化、普遍化的倾向。范文澜先生曾说“阴阳”指“男女之间那个事”,《尚书·周官》中说“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这里的阴阳又指社会现象。不仅如此,阴阳又扩大“指一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阳是刚、健、热、伸的象征,阴是柔、顺、寒、屈的象征,这是其自然属性;阳是贵、富、尊,阴是贱、穷、卑,这是其社会属性;阳是君、父、夫,阴是臣、子、妻,这是其等级属性;阳是善、仁、爱,阴是恶、戾、残,这是其道德属性。阴阳以自己的属性来规定自然、社会、政治、道德等各种现象的属性;而自然、社会、政治、道德现象亦以阴阳的属性为自己的属性。”〔14〕这样,“阴阳”已经走在了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的中间,一方面它的确指具体事物,而另一方面它又指一种较为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象征物,是初民的“一分为二”的观念由实体化向着普遍化、抽象化过渡的中介。诚然“阴阳”始终基于某种它无法摆脱的具体个体直观,然而“阴阳”观念又同时包含着普遍性因素,虽未达到纯粹“一分为二”观念的那种抽象程度,但已经把独立实体提升了一步。因而,“阴阳”处于转折关头,它竭力摆脱直接物质世界的狭隘和局限,奔向更自由、更普遍的观念。这是“一分为二”观念产生的第二个阶段。因为阴阳既是具体的事物,又有普遍性因素,因此在文明时代诸子著作中还被保存着原始形态。
当“轴心时代”到来的时候,人类的理性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觉醒。这时生产技术领域中红铜和青铜特别是铁出现了,人类实践变革、重组事物的功能大为扩展。人类已经由消极地应付自然界转为积极地改变自然界。在农业经济阶段,人类因为无法把握阴晴,才发展出象征的思维方式。而这时,人类对于冶铜冶铁的技术上的每个环节,都是他能够实实在在地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技术准确地把握的。自然界不存在着现成的铜与铁,需要人类的实践去变革、改构自然物才能得到。当人类把握自然物以及改构自然的趋势不断加强,认识便逐步被建立在理性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于是思维方式又逐步由象征思维方式向着理性思维方式过渡。人类对于宇宙的根本规律的认识也更加系统化、抽象化。先秦两汉的哲学家们在表述他们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看法时,已经可以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把这个规律表达出来。例如“一生二”“太极生两仪”的说法就是如此。但他们有时还露出借用“阴阳”这些象征思维方式时代的尾巴来。这个尾巴,到了宋代的哲学家那里,终于被彻底割掉。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就是:“一分为二”这个哲学命题,并不只是文明时代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才产生的观念,它最初萌生于初民狩猎经济时代“马”与“牛”的二元对立观念,经过了长期的由具象化中经象征化再向抽象化的发展,而到了理性觉醒的“轴心时代”,“一分为二”的观念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正式形成,成为中国哲学范畴的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到了隋代特别是宋代,成为正式的文字表述。
注释:
〔1〕〔2〕〔3〕〔5〕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27、30、26页。
〔4〕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7页。
〔6〕古昂:《姿势与语言》,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 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7页。
〔7〕〔9〕古昂:《史前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 18、118页。
〔8〕古昂:《史前艺术的宝藏》,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361页。
〔10〕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74—37 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2页。
〔12〕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0页。
〔13〕朱炳祥:《论神的观念的起源》,《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14〕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
标签:阴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