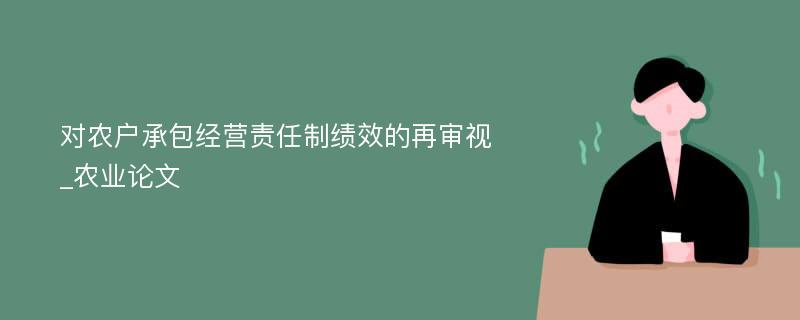
农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再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责任制论文,绩效论文,承包经营论文,家庭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它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对粮食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很少有人对它的作用提出疑问。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经历了1985—1989年的粮食增长停滞期,再加上1990—1991年粮食过剩和1994年供不应求的周期性波动以及1996年至现在的又一轮粮食供给过剩,怀疑是否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出了问题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主要的论点有: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作用“一次推动说”,即该制度的作用是一次性的,当它激发出的劳动积极性快速推动农业在1984年上了台阶后,其作用逐渐消失;“田地分块细碎说”,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规模过小,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发挥。这些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也获得了一些实证的支持。比如,黄季焜教授指出,1978年前10多年的粮食平均增长速度略比1978年以后的快(黄季焜,1998)。而就作者所知的支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绩效的实证分析所得结论都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林毅夫,1988,1992)。有人燃起了怀旧情感。伍山林认为农业小规模集体经营是有可能的(伍山林,1998)。不过,他的数学模型只是把问题归结为生产队集体劳动有效程度系数的大小上,而在集体劳动条件下,或者在自留地比例可以变动的情况下,劳动有效程度系数是否足够大未作进一步探索。结论似乎真是如此吗?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农业、对粮食发展的积极作用是短暂的吗?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作用是短期的这个结论多多少少给人留下了一点惊诧。这个曾经如此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在短短的数年内农民自觉自愿地用它在中国的大地上取代了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它的有效性竟然只有六、七年时间( 1978 —1984年)?显然,深入研究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绩效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深入理解当前农业、粮食发展状况,弄清楚当前粮食经济、农业经济乃至农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确定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向、途径等都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绩效如何?是否仅是在1978—1984年有绩效?它是否在改革开放20年来都有绩效?它是否对整个农村经济有绩效?它是否对农业经济有绩效?它是否对粮食生产有绩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较详细地对1977年以前和1978年至现在两个时期进行了统计实证比较分析,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性假设检验数据分析
这里统计显著性检验的目的是考察1978年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建立以来它的运行是否比1978年以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有绩效。这里不比较经济总量的水平,因为无论制度有绩效与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总量一般来说呈现出上升趋势,这类比较意义不大。有意义的比较是经济总量变化的快慢。同时,个别年份或者较短时期的比较往往是偶然因素或者极端情况造成的,结论缺乏一般性或者普遍性。因此在分析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5、1998;中国农村经济统计1997;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7;199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本文这一部分主要对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粮食总产量的有关效率与速度指标进行了差异显著性检验。按照我国统计口径,第一产业就是农业,采掘业和森林工业归入工业。
关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显著性检验。使用1957—1998年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第i年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减去1记为x[,i ],即年增长率,i=1表示1957年。指数以上年为100, 以不变价格计算。1957—1977年为第一期,1978—1998年为第二期,x'[,k'],v[,k],n[,k]分别是第k期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样本平均值(算术平均值)、样本方差、样本量。问题是1978—1998年期间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否显著高于1978年以前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采用不配对的u检验法。
检验统计量u=(x'[,2]-x'[,1])/[(v[,1]/n[,1] )+(v[,2]/n[,2])][1/2]
表1 检验参数和结果
k n[,k] x'[,k]
v'[,k]
x'[,2]-x'[,1]
3.05
第一期
211.9 51.1u
1.79
第二期
214.95 9.7 显著水平p 高度显著0.037
第一期的增长率百分点的平均值为1.9,第二期为4.95。 观察到的差异显著水平不仅超过了0.1,而且超过了0.05,为0.037。可以得到统计检验结论:1978年以来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显著地高于人民公社制度时期。这是一个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比人民公社制度有绩效的十分有力的统计证据。
关于粮食发展的数据分析。不少人发现1978年以前的10多年粮食生产的年增长速度并不亚于1978年以后的粮食年增长速度。黄季焜教授指出,1970年至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 %(各年增长速度的算术平均),在改革时期,1978—1984年为4.7%, 但在1984—1992年仅为1.8%,1978—1992年也只是2.7%,与改革前差不多(黄季焜,1998)。实际上,把时间再拉长一点也有类似的现象,1962年粮食总产量1.6亿吨,1977年2.8亿吨,年均增长率3.8 %(几何平均);而1978年粮食产量3.05亿吨,1996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05亿吨,1997和1998年的产量还不及它,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也才2.84%。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是否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粮食生产没有绩效?是否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只是一次性的?显然,不能急于下结论。因为除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粮食生产发生作用外,粮食收购政策、价格政策也会对粮食生产发生影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需求对粮食生产也有着导向作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给了农民,农民将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粮食生产效益低,农户将自主地调减放慢粮食生产的增长,加其它作物的生产,10多年来粮食播种面积由80.3%降到了1997年的73.3%。不过,如果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确实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无论粮食种多种少它应该在效率指标上表现出来。据于这个推测,下面我们对粮食单位播种面积产量和粮食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进行数量分析。分析方法仍是u 检验法。数据序列从1957—1997年,前后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57—1977年(1957—1965年的数据正好是人民公社的极端后果与其后的大力度调整恢复,在数据列中应该要保留则都保留,要剔出则都剔出),第二时期1978—1997年。分别对上述两个指标的年度增长率(因为单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期比前期高也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只有它们的变化率上的差异才更能说明问题)进行前后两期的比较显著性检验。
关于粮食单位播种面积产量增长率1957—1977年与1978—1997年两个时期的比较显著性检验。
表2 粮食单位播种面积产量年增长率数据%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年份增长率
19573.24
1971
2.88 1985-3.47
19587.38
1972 -4.15 1986 1.33
1959
-6.51
1973 10.22 1987 1.98
1960 -20.01
1974 4 1988-0.57
19613.63
1975
3.35 1989 1.5
19628.31
19760.9 1990 8.28
19637.03
1977 -0.97 1991-1.45
19649.04
1978
7.63 1992 3.31
19655.89
1979 10.18 1993 3.71
19668.77
1980 -1.81 1994-1.64
19673.29
19813.4 1995 4.34
1968
-1.49
1982 10.51 1996 5.74
1969
-0.32
1983
8.69 1997-2.37
1970
12.15
1984
6.26
表3 检验参数和结果
kn[,k]
y'[,k]V'[,k] y'[,2]-y'[,1] 0.55
第一期 21 2.7
47.6u 0.31
第二期 20 3.25 18.1显著水平p 0.4781
y'[,k]表示第k期粮食单位播种面积增速百分点的算术平均, 其余符号和统计量同前。数据分析结果:1978年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以来粮食单位播种面积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y'[,2]=3.25%,1957—1977年为y'[,1]=2.7%,改革开放以后快于改革开放以前。 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前后两期单位播种面积产量增长速度的差异显著水平p 的显著程度不够高,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推断改革后的粮食生产方式确实比改革前富有激励作用。这可能是粮食单产变化率除了受制度因素影响外,还可能存在奇异值或者偶然因素干扰过大,造成观察方差较大。为了深化认识,进行下一步的检验。关于粮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1957—1977年与1978—1997年两时期比较的显著性检验。检验统计量同前。为了观察关于粮食劳动生产率推断结果的稳定性,依次做了五次比较,原数据组进行一次,从原数据组去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又进行一次,从数据组中再去次大值、次小值进行第三次,…,直到第五次。
z'[,k]表示第k期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年长率百分点的平均值,k =1为1957—1977年,k=2为1978—1997年。从表5中直接看, 改革开放以后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平均数每一次都大于改革前的平均数。由于第一次检验中粮食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前后两期差异显著性临界,故进行了剔出异常值的稳健性检验。逐次剔出异常值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推断结果逐次稳定,给出两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存在显著的差异的结果。从较细致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起初统计推断的不确定性确实是由个别奇异值所引起的。比如1958年粮食劳动生产率的超常增长,达到27.82%。这与当年盛行浮夸风数字本身不可靠有关。 并且在那年农业劳动力骤减,从1957年的1.93亿人减少到1.55亿人,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由当年“大跃进”大规模抽调农业劳动力所造成,不得不在第二年就将大量劳动力清退回农村。(如果把1957—1997年的数据做为整体统一去掉最大值与最小值,然后再分前后期进行比较稳健统计,也能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数据处理最后结果:有充分把握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显著或者相当显著地大于人民公社制度时期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一统计结果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表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粮食生产仍然是有绩效的,并且这一绩效不是短暂的,而是一直到现在仍在起作用。这个作用实际上比我们计量得到的还要显著。因为,这里粮食劳动生产率数据的分母使用的是农业劳动力,包括了农、林、牧、渔各业的劳动力,并不仅是从事粮食生产的。有很多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大量地转移到其它种植业、养殖业、林业以及非农产业上来。所以实际的粮食劳动生产率更大,其增长率更高,只可惜未掌握系统数据。
表4 粮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数据%
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
1957 -2.791967 -1.7 1988-3.83
1958 27.821968-7.39 1989 1.06
1959-19.061969-2.99 1990 6.43
1960-17.51197012.34 1991-4.91
1961-13.341971 0.8 1992 0.71
1962 0.671972-3.52 1993 6.93
1963 2.9319738 1994-0.52
1964
6.21974 2.61 1995 6.3
1965 2.431975 2.97 1996 8.85
1966 4.631987 2.07 1997
-2.430
表5 检验参数及结果
检验次数 N[,1] z'[,1] v[,1] n[,2] z'[,2]
v[,2] u
显著性p
1 21
0.11996.020 2.44726.6
0.958 0.169临界
2 19 -0.33046.218 2.55021.6
1.511 0.066显著
3 17 -0.06524.716 1.81120.9
1.130 0.129临界
4 15
0.28311.814 2.64913.3
1.796 0.036高度显著
5 13
0.5387.5812 2.760 9.8
1.878 0.030高度显著
三、几点认识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积极作用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从它在局部地区开始建立到在全国各地普及为止所表现出的普及效应,以往大多数学者计量、评价和讨论的主要是这种作用。到1984年全国各地都基本上建立起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时,这种作用开始消失。所谓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作用是“一次性”的,实际上指的就是它的普及效用。另一种作用,或许更为重要,即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激励机制唤醒了农民劳动热情的作用,可称为它的激励效应。这种激励效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上述的数据分析已表明了这一点。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绩效性不仅仅表现在粮食生产上,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农村经济中甚至于整个国民经济中。关于农业总产值的显著性检验已表明改革开放后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相当显著地高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农业的绩效性比起对粮食生产还要明显。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粮食产量的增长率的绩效性似乎还表现出负的影响,只是数据分析探索到粮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上才发现对粮食生产正的绩效性。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正绩效性是众所周知的,它使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解放了农业劳动力本身,农民有择业的自由,产生了极大的生产力。农民跨区域的大流动,参与创造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奇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更是一个出人意外的收获。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7年的70%左右,并且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7年49.9%。有人估计1996年乡镇企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已达1.35亿人(黄季焜,1999)。1997年乡镇企业中工业增加值11985亿元, 而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也才19835亿元,其中国有部分9193亿元。 乡镇企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必须从两个实际出发,一个是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另一个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几千年来,集体劳动和企业化生产组织一直没有成为农业劳动的基本形式,即使是在当代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家庭经营仍是农业劳动的主要形式。只是工业出现以后集体劳动和企业组织才成为工业的基本生产形式。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规定的。它的特殊性主要在于生产过程的生物性,它只能遵从生物的自然生长过程进行培育,生产顺序工艺不能随便更改。农业集体劳动的产品未留下个人劳动的清楚痕迹,这使得通过检验劳动产品来计量个人劳动在其中的贡献成为不可能,再加上劳动场所广大产品周期长,自然界影响很大等,这些都使得劳动的计量和监督成本太大,并由此造成农业劳动一般不具有分工的规模经济。因此,农业集体劳动有效实施的难度极大。由于血缘和生理的联系是人类社会中最亲近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家庭为劳动单位,相互信任感强,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仍表现出很高的适应性。而工业劳动不同,企业中工人集体劳动,但劳动有具体的分工。每个工人负责产品生产的某个具体环节,在该环节上他的劳动一般可较准确计量(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工人们的劳动是便于区别的,工人的个别劳动在最终产品中可以留下他的具体痕迹。个人对最终产品的贡献是便于确定的。搭便车的机会很少。计量和监督成本大大下降为内部分工的规模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企业组织也随之而诞生。中国农村拥有几亿户农民,每户耕种一块土地,以农为生,生产规模狭小限制了土地规模经济的发挥。不过,这不能用集体化的方法把农户集中起来进行共同劳动来解决生产规模狭小问题。农业集体劳动缺乏绩效,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这是有经验教训的,也是前述实证分析证明了的。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的隔离发展,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严重滞后于城市,农民的生老病死等社会保障问题基本上由自己负责,那一小块土地实际上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不能随意剥夺。把土地强制性集中在少数种田能手中,似乎可获得土地规模经营,但从更大的方面看,社会总福利受到了损失,得不偿失。在没有对农户相应补偿的条件下,土地集中只能坚持农民自愿原则,出路只能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建立和健全市场化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当农民刚转移出去觉得非农岗位不大稳定时,他只会采取对土地使用权租、借、转包或者土地入股等方式;当他觉得非农岗位稳定时,他会卖掉土地使用权。无论何种方式都能使土地使用权得到集中。
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应该在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应该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中心。在农业生产中发展农民自己的互助合作组织是农业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积极方向。它把分散的农户联系在一起,相互帮助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强他们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保护自身利益。不过,选择合作的形式应该特别注意。农业集体劳动集体管理的形式在我国目前生产力条件下,已被历史证实是行不通的(讨论仅局限于农业,并非指村、乡、镇的非农产业,也非指村级经济综合体,也排除个别特殊现象,实际上在村级经济综合体内对农业的管理也是个人承包经营为主)。农民的互助合作应该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以契约、市场为纽带,以自愿为原则展开,发展产前、产后、产中的各种合作社,如供销、运输、加工、信贷等的合作社以及股份合作社,同时建立建全各种社会化服务。农业的改革无论怎样搞都必须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其实质就是保证国家对农产品的索取权。这在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时期,相当多的工业品是投资品,再加上国际关系紧张,工业品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国防产品,保持对农产品的强制性索取以维持工业和城市自我封闭式的发展是可能的。但是,当国民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以后,生产出的工业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如果居民有支付能力的商品需求跟不上,特别是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需求跟不上,势必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出现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以后才减弱的)。当前我国的生产过剩现象与人民公社制度时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因此,保护农民利益实际上也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1984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增长趋缓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无关。合理的一面是指就粮食发展的长期趋势来说,当粮食生产能力由长期不足发展到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略有余时,粮食的生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将被粮食需求决定。当供大于求时,粮食价格下降,农民不愿意提供更多的粮食。此时,并非粮食越多越好,政府目标应该转而追求粮食供求平衡。由于粮食需求只能随着人口和收入增长而缓慢增长,粮食产量也只能随着粮食需求而缓慢增长。不合理的一面是指,在一、二年的粮食跳跃式增长后,往往出现一个数年的粮食增长停滞期,这主要是比较僵硬的粮食价格政策和流通体制造成的。等到供不应求的问题紧迫的时候,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一旦供大于求又为财政负担问题所忧虑,采取一些对农民不利的政策(施锡铨等,1998)。这里的关键是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而不应限制或者否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创造了1984年以来能够满足粮食需求并且略有余的生产能力,应该做的是改善它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
中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狭小,这是一个事实,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土地规模经营狭小的途径以获取规模经济。用归大堆、集体劳动的方式来解决已为历史证明行不通。这是由于农业集体劳动成果中个人劳动贡献鉴别的困难以及监督成本太大导致分配的平均主义,从而引起搭便车、偷懒盛行,劳动效率低下。各国的农业发展史业已证明在农业上没有劳动力的规模经济,只有土地和资本的规模经济。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通过对拖拉机等生产要素的假不可分性的分析否定了大农场一定比小农场效率高的观点;美国农业部农业专家杰麦得安分析了大量不同规模农场的生产费用的资料后也认为单人或双人经营的机械化家庭农场效率最高(彭群,1999)。农业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以至于绝对数一般都呈现或将呈现下降的趋势。不能用劳动力的规模不经济去解决土地规模经济问题。
收稿日期:2000—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