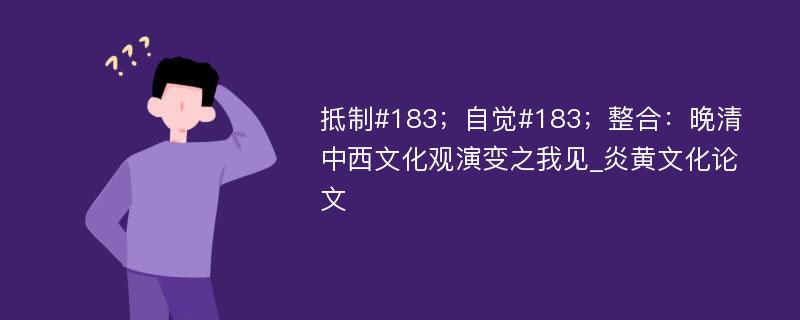
抵御#183;自觉#183;融合——晚清中西文化观演化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晚清论文,我见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言文化,乃社会文化,即广义的文化。泰勒曾给出过包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罗列式定义,据此,文化可概括为物质(晚清称器物)与经济、制度及政治、精神和价值(观)几个方面。尽管社会文化定义繁多,但泰勒定义的朴素及描述性得到了较多赞同。本文即采此定义。
中国古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存在,盛唐尤甚。但当时之西学,并无任何优势,所以亦无东渐之说。元明以来,西学东渐持续不断,但西学并非明显强势,中学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及自我优越性认同从未丧失,因此仍无实质性的对话,完全不及反思,仅是中包容西而已。晚清以降,西学以强势东渐,引发或迫使中西文化对话(斯宾格勒意义上的。亨廷顿之文明冲突学说,实乃汤因比不同形态文明的生灭构建了一部人类史,以及斯宾格勒文化对话学说——战争亦为对话的形式之一的逻辑拓展),反思遂启。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由此衍生、发展。
与近代强势西方文化对话,衍生了中国人的文化担忧心理。超越本土视界,也衍生了一切相对弱势文化中人的文化担忧心理,影响至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文化心理更有强化趋势:担忧本土文化泯灭于其中。①本文仅希冀通过梳理、厘清近代中西文化对话的史实,尤其是恪守中学之人对西学精粹的主动认同,以及力倡西学之人回归中学要义所表达的文化自觉,并辨思之,达成与客观相吻合的结论。以利于解除全球化背景下自卑情结质的文化担忧心理,并认清在此心理掩饰下的文化利益(私利)立场。
历史的起点即实践的起点,与认识的起点即逻辑的起点一致。近代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因鸦片战争战败,率先表现为对西方先进器物尤其是军事器物的认同。1842年,林则徐在发配伊犁途中,忆及中英两军对阵,感慨言之:“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抢,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见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据此,他提出了与英夷作战的八字方针:“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器良是第一位的,“良器中,第一要大炮得用”。②因英军器良,林则徐追根寻源,在广州任上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名为《四洲志》的资料。1841年8月,流放途中与魏源会于镇江,将此资料交予了魏源。魏源为不负林之重托,复痛感鸦片战争之战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遂暂弃国学研究,专事了解世界,于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其指导思想即载入“叙”中之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据说此言原出自林则徐。魏源概括的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同期,广东名儒梁廷相于1846年撰成《海国四说》一书,对英美两国介绍尤详,其对蒸汽机及其应用的描写,在时人眼中犹如天书。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从传教士大卫·雅裨理处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专习精研,于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10卷,这部史地巨著对西方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加详尽、准确。
除对西夷先进器物的高度肯定外,有识之士已然开始关注西夷制度的先进性。姚莹在《康輏纪行》一书中,粗略地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尤其关注英国的议会制度。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作了详尽描述。《瀛环志略》则对西方民主制度多有褒扬:“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但即使对先进器物的介绍,也遭到传统文化的“围剿”,先进器物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姚莹写道:“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岂可不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顾不知犯忌讳耶?”姚莹还记述了朝廷重臣、士大夫阶层对介绍西学者的斥责:“矜奇眩异,骇人耳目,浮薄妄为,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之事,侈新异域贪四夷之功。”严令“皆以侈谈异域为戒。”③难怪林则徐给友人写信言及中英武器巨大差距时,嘱其千万不能以信示人。为固守传统,有人甚至将不平等条约视为天朝施恩于海外的另一种方式,实在匪夷所思。更离奇者乃“西学中源说”,“中国乃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④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顽固性甚至亦同样表现在有识之士身上。林则徐被蒋廷黻先生誉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虽看到了西夷器物(主要为军火)的先进,并欲了解之,但内心深处,对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仍是抵制的。1850年4月,他获恩准返回福州家乡。11月,闻有英人欲租住福州城内房屋,他勃然大怒,组织士绅联名写信质问地方政府:中夷焉能同处?他还认为西人嗜牛羊肉,若不从中国进口大黄、茶叶以辅食之,必将因消化不良而毙命。“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所以从根本而言,西夷不足道也。蒋廷黻先生由此又说:“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⑤魏源亦言:“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矣。”⑥这不仅传续了董仲舒天道不变的原则,亦实为后来“中体西用”论之滥觞。
此文化生态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败遂成必然。战败的直接军事原因,固然在集重兵于京畿地区,致海防空虚,然支持这一军事布局的理念,却是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私家天下观念及其礼教仪轨。朝廷即国家,君即天,朕即天下。所以咸丰愿意以减免英法产品的进口关税来换取英法公使不驻京城。因为朝廷重臣们上书历数英法公使驻京的无数弊害,归结为“去我衣冠礼乐”。咸丰闻知英法公使见他将不跪,仅施躬身之礼,痛感有失天子威仪,干脆东躲西藏避而不见。甚至算好西方公使不在京时,乘便由承德返京。若公使欲入京晋见,便借口“秋狩”,迅即离去。疲于奔命感染风寒,加之内心焦虑惶惑不安,终于一病不起。吕思勉先生认为,咸丰乃一血性男儿,且有雄心壮志,但其于外在形势和内在文化束缚中,亦无可奈何。维新运动之际,有识之士回顾以往,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20余年间,“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左宗棠也曾喟叹:“书成(指《海国图志》)魏子殁,二十余载,事局如故。”⑦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西方器物文明充分展现了其强势,再无视之甚至排斥之是不行了,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追求西方器物文明的洋务运动由此勃兴。即便国势已至不堪,自强派(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仍屡遭守旧派非难。1866年,奕訢等人因认为西方器物之先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奏请慈安慈禧批准于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由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之官入馆研习。大学士倭仁上奏折反对道:“立国之道在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若科甲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则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奕訢引用李鸿章等人的话反驳之:“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因此“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御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⑧所幸奕訢深得慈安及慈禧信任,倭仁等遭斥责,被迫收回了奏折。1874年冬,因日本犯台事件发生,清政府海防之议骤起。李鸿章等人主张采借西学,任用洋人,甚至可以借西夷之款,编练西式海军。顽固派谓之:“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他们甚至以子之矛,击子之盾,谓曾、左、李均为科举正途出身,并未读过洋书,但均以大义为社稷立下大功。李鸿章被驳得无言以对,于情急中居然说出了“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之类的话来。⑨鉴于现实的威胁,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总算被通过。1880年,刘铭传建议修建铁路,奕訢、李鸿章等予以支持。顽固派人物屠守仁言:“自强之道,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也。”⑩致李鸿章“未便再言”。奕訢也“未敢主持”。修建铁路之事于是又耽搁了多年。反对派之屡屡反对,乃唯恐西学动摇中体。洋务派实际上也不欲动摇中体,终以“中体西用”论应之。薛福成总结道:“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11)
冯桂芬所撰《校邠庐抗议》,被后人公认为采西学谋自强的宣言书。虽于1883年才正式刊印,但书稿早已流传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之间,对洋务运动影响甚远。此书《采西学议》篇言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不可谓不犀利。但也随即声明:“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在书之《制洋器议》篇中,更强调:“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可见中学为体早已是自强派与守旧派的共识。
据中体西用方针,洋务运动遂成一场将先进器物文明、经济形态“嵌入”传统制度文化的运作,而罔顾二者的相容性及先进内容在旧制度中的可否成长性。对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等人所创的社会经济生活(系统)乃嵌入社会生活(系统)之说,笔者历来不赞成。不仅因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倒退,更因其有违常识,是一种为构建而构建的论调,同乎闭门造车。因为经济生活(系统)是发生的,其他社会生活(系统)乃以经济生活为前提、为基础而发展的。而据“嵌入论”,则无所谓社会系统因应于经济系统的(并非同时)发展。但以“嵌入论”来表达洋务运动,倒是非常精当的。其谬误,也可由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实证之。幻想将先进器物、先进经济(近代企业)嵌入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相悖于近代企业本质的种种做法便油然而至。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等,均乃旧制度结合新经济的自然产物。核心仍是专制政治权力的一元化控制:将新经济看作是扩大专制政权控制的对象及拱卫专制政权的手段。企业遂成为了新衙门,器物(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因制度束缚而终于不可能。制度的陈旧及强化,阻碍器物(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另一机理为社会资本积累指向土地资本:大量工业利润重新转化为土地资本,商业利润亦然,而地租及土地资本不易也不愿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资本。落后国家,近代工商业资本的积累主要源于农业——地租及土地资本的转化。旧制度框架下,企业亦为官府垄断,为官服务,实质乃强制民间资本支持官办企业,控制民有资财。因而还是经营农业——土地保险、稳当,与旧制度的相容程度高而排异程度低、低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下近代工商业发展资本短缺即所谓“缺血”,导致社会转型即社会大文化系统转型举步维艰。这就是制度文化陈旧导致制度体系陈旧的恶性循环。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富国强兵的双重目标无一实现。罗荣渠先生说:“自强运动的失败,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现代化发展大潮的关键一步。这次失败根本改变了中日两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国际地位与格局。”(12)美国学者罗兹曼指出:“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所需要的)明确行动太不相称。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近)现代化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国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及其腐蚀性是造成19世纪中国失败的基本原因。”(13)一句话,洋务运动失败于中体。
此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于文化意义上,实乃用外来语汇包裹的传统思想及实践,虽涵有若干争平等的农业社会主义言词,但“照旧完粮纳税”及后宫嫔妃制度等,足见其旧制度文化之底蕴。《资政新篇》虽表达了洪仁玕对西方器物及部分制度文化的认同,但从未付诸实施。况且,洪仁玕还有救世天父——真命天子的“英杰归真”一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太平天国的文化观,对晚清社会并无深刻、持续影响。
梁启超言,中国近代变革自鸦片战争战败至民国初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此有自强运动。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此有维新运动。第三时期则是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因此有启蒙运动)。(14)梁任公所言之第二时期,应包括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因三者的共同点均是痛感中国器物文明之落后根源于制度之落后,均认同西方的先进社会制度,均诉诸制度变革而希冀中国走向富强。三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变革制度的手段即路径,维新与立宪,秉持改良主义立场及路径,属体制内变革。革命则持体制外变革的激烈立场与路径。
前已述及,鸦片战争后的1840年代,中国有识之士在介绍西方器物文明及地理概貌时,已涉及西夷制度之介绍,并蕴涵了对其先进性的肯定。魏源虽强调中国之道不变,但亦觉察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先进性。他介绍美国总统四年一任,“亦有再留一任者,终无世袭终身之制。”美国的“议事诉讼皆四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会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国乎。”“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事无大小,必须各官会议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15)他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为公”的表现。至维新派,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判及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褒扬,已是锋芒毕露不遗余力。康有为直言:“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究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君主民主皆虚位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16)谭嗣同对衡阳王子申所言“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深表赞同,并言:“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直接驳斥了“中体西用论”。(17)变法的当务之急是废除君主专制,使民众成为国之根基。“万事万物莫不以群强,以孤而败,类有然也。”所以必须“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以拨乱之具也。”(18)直接将帝王专制贬斥为“孤”、“乱”,二字之微,大义彰显,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切中中国落后之根本。梁启超言,变法就是学习西方,但并非仅学其船坚炮利。“所以强弱不在兵,昭昭然矣。”“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19)因此变革中国政体乃当务之急,政体乃中国之病根。
维新运动失败后,逐渐转化为立宪运动。清廷出于“皇权永固”计,亦拟以“宪政”实现之。真假宪政之辨,遂成当时社会认知之焦点。立宪派一面揭露清廷立宪之伪,一面进一步伸张了对西方近代制度文化之认同,他们针砭清廷的所谓行宪官制:“环顾今日之所谓中央官制,非不衙署灿陈,隐然如各文明国然。然一窥其内容,则唯汲汲以中央集权为秘计。且各部集权皆可从缓,独兵政与财政两部,一若唯恐稍纵即逝者,其用意果何在乎?”清廷所言之预备立宪,“其预备实行专制之时代已乎?集兵权,敛财赋之端已开矣。”(20)“是仍俄国假立宪名义,阴行专制之伎俩而已。”(21)“今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几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阻碍民权之发达,违背世界之公理,土崩瓦解,岌岌可危,即无外忧,而天下前途已不堪设想矣。”(22)为达变革制度、实行西政之目的,立宪派愿与清廷达成最大的妥协。当此底线已守不住时,革命邃然而发。
孙中山先生最初亦为改良主义者,其所撰《上李鸿章书》即是明证。当他认识到改良已不可能变革中国社会制度时,决然走向革命。其对革命理念之伸张,足见其对西学之吸纳。孙先生认为,宇宙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23)人类进化之时期可分四阶段:“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是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24)中国比西方落后,就在于尚未能进入民权时代。惟实现民权,方能卫民族,利民生。孙先生认为,民权时代内涵,一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见中西学在基本价值观层面,具内在统一性和同一性。孙先生一生,引用最多之语,即“天下为公”四字。书写最多之言,亦此四字。天下为私,已道破了数千年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之积弊。
制度变革,已然是社会大文化系统之跃迁,是旧制度文化体系的倾覆,必触及既得利益者之利益,必招致其竭力反对。中国近代化中,除光绪外,鲜有出于中华民族之大义而主动变革旧制度的领导者。即使是达成新旧制度的局部均衡亦不能容忍。维新、立宪相继失败,走向共和唯有通过革命。辛亥革命的一大功绩,就是将共和之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启蒙运动亦赖其催生。辛亥前后,中国近代社会进入了梁启超所言的第三时期: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中国之不足。三个时期,三种不足之感,渐次深入。表征的已不仅是西学强势东渐,且已渐成主流文化之文化生态。
晚清中西文化观的另一深刻现象,是逆西学的强势影响,回归中国文化(立场)。谓之回归,并非守旧派顽固派对西学之抵御,对中学之僵守,而是倡扬西学、践行西学者,对中学的再审视与再认同。
以变革中学制度文化为己任的维新派,已融中西学于一体,以中学阐扬西学。康有为将其所主张的西方议会制度(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附会于儒家经籍之中,提出《尚书·尧典》即已申扬了民主理论:尧舜“询于四岳”,就是“四岳共和”;“辟四门”就是开设议院等。在《孔子改制考》中,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精粹汇至,均可为改制的思想依据。“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诸子纷纷创教,竞标宗旨,非托之古,无以说人。”遂有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等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述康有为所作《孔子改制考》时,进一步发挥道:“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之所托义。……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世,皆孔子理想所构成也。”因中国古制、古代思想文化之先进与文明,所以“对当时之制度未有善处,而思有以变之。”(25)即皆可依古托古以变之。当下,亦可依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变革中国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是相通的、共同的。如“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如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26)
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严复,更其如此。严复少年时代即习西学,青年时代留学英伦。严复的文化贡献,主要是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并对之阐释发挥,推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之更新。严复一生,除晚年外,高度赞同西方文化,透辟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不仅在科技即自然科学,根本则在社会科学、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推求其(指西方富强——引者注)之故,则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27)他考辨探究了中西学之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驩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故此,中西根本不同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中国之所以弱明矣,西方之所以强明矣,中西文化之劣优明矣。(28)如是,中国要保种自强,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就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严复尖锐批判了顽固派的守旧文化观,指斥其弊害有三:一是“则古称先”,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二是言行不符,言是行非。悖弃孔子本意者,正是此类人等。三是狂妄自大,“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而“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蘄亡”。“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29)
但同一个严复,晚年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惨状及中国现实之顽劣,竟然一蹴而就地回归了传统文化立场。“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于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30)他回归中学研究,并以弘扬孔孟为己任,乃至于一反其早年认知,强调中国尚不具备废除君主制行自由民主制的条件,遂助袁世凯复辟帝制。其间虽有袁氏的利诱,但严复将复兴、弘扬中学大义寄望于直接废黜了清廷、且至少在表象上也赞同以西学维新中国的袁世凯,应为主因。
章太炎早年专治国学,12岁即从其外祖父读经。及青年,又追随国学大师俞樾深研经籍。年再长,目睹清廷腐败,转求西学以图更新。与曾广铨合作,译介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精习了进化论并信仰之,乃至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言:中国自宋以后,仅有退化而无进化,以至有今天之局面。为期望于进化,中国迫切需“师天下”,师天下以进化中国。他痛批皇权,甚至直斥有鲜明改革取向的光绪;倡民主共和制,甚至反对代议制,呼吁全民直选。但他又强调,应以国粹(他谓之真孔子学)激励中国人的种性。一反曾经之讥讽,发出“孔子,古良师也”之喟叹。(31)他一边鼓吹民众革命,一边研究、讲授国学。后人盖棺论定,公认鼓动西式革命和弘扬国学乃章氏一生两大成就。这一看似矛盾的价值取向,表达的正是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但其受西学之启迪,融西学之精义,应是不争的事实。孙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枢——专制主义以及为虎作伥式论证,一贯深恶痛绝,亦为世人共知。但孙先生自己言其学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2)他反专制私利(私天下)主义,以“天下为公”对之;他求自由民主平等,亦以“天下为公”倡之。孙先生还多次说过,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礼记》所言的大同世界。“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33)“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34)鉴于孙先生之思想体系并非以史学为重,当时的史学研究亦存在种种局限,其所言中国古代的民生主义事实并不一定精准,但他所强调的关注民生乃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吻合史实,乃其所言之大义。可见他在习倡西学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坚持。同时,孙先生对西方社会弊端的认识日趋清晰,明确提出中国不应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35)必须“节制私人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即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36)中学优良传统,随孙先生思想之发展深化,愈益秉持。
上述史实,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强势东渐之西学,中学在理性反应尚未构建之际,呈现出盲目否认、抵御之姿态。一旦强势西学之优势即说服力呈现(首先是器物层面),主动学习之便成为一种选择。并渐次深入至制度、思想层面,以探寻并学习先进器物文化之成因、之根基。由是,西学便呈欲取代中学之势。但是,中学的理性反应于此中亦渐次建构,文化自觉即主体意识及主体性遂凸显,中西学的各自优势于对话中开始融合。这一过程蕴涵了人类文化进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论及不列颠在印度的双重性历史作用时,揭示的正是这一规律。当然,文化对话并不一定采用激烈冲突的形式,尽管这一规律昭示的逻辑具普适性。晚清中西文化观演变轨迹,于本土、外来文化之相互关系及其演化,可有深刻启示。
社会文化对话及文化发展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如梁任公所言,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这是落后文化追寻其落后原因的思维逻辑,亦是其变革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具有强制性即必然性。因器物由制度决定,制度则建构于一定文化基础(狭义文化),又在与文化的互动中发展。三者共建、同构了社会文化体系。文化之冲突、变革因此而层层递进,一如黑格尔所言的“理性的狡计”,即本体的狡计。当冲突仅在造物层面展开而未涉及本体时,本体于深处得意地黠笑。唯有进及本体,质、因才呈现,于文化对话双方才公平,也才有意义(功用)。
凡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对话初始,必遭抵御。外来文化越是强势,本土文化越是被迫,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御性就越强。此种较强或强抵御关系,即使在直观地、经验性地利于本土文化的器物(物质与经济)层面,也坚韧存在,充分显现。其机理有三:其一,文化自尊立场。凡文化对话的开启者、主动者,其必有所长。反之,凡文化对话的被开启者、被触动者,其必有所短。两者相较,优劣分明,越分明者,文化落差越大,亦易造成被动一方理解、接受的困难性与迟滞性。所以便有西夷军队(人)腿不能屈,只要设法将其掀翻于地,其便不能爬起,遂可击杀之等种种谬说。即便已完全理解了外来文化的先进性,但因本土文化实乃民族长期行之守之之体系,即便陈旧,亦是其区别于他民族的质。一见己质如许落后甚至不堪,顿觉颜面尽失,自卑情结必生,由此,反弹必至,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抵御。若不能充分发掘、强调本土文化的种种长处,本民族焉能历史悠长,又岂可安身立命。这是面对文化危机的文化生存论证。观1840年代至洋务运动时的种种守旧派之所论所为,直接否定西方器物先进性的不多,多者乃申张本土文化之精神优于西夷器物之精良。如此,西夷器物可为我所用,但我之文化则可统驭之,遂有中体西用论。这在本质上,乃文化自尊立场,明知不足,偏偏袒之,强作仍可立足状。类同讳疾忌医,终至病入膏肓。其二,文化担忧(虑)心理。社会文化,乃一有机体系,即使局部不足,亦必有全局之因。弥补局部,将变更全局,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如此,外来文化步步深入,本土文化进退失据。洋务运动未完,维新运动又起,表达的就是这一认识与实践的逻辑。本土文化能安存否?将灭亡否?不能不令本土文化中人忧心。愈是浸淫其深者,愈忧心,遂致抵御。亦有忧心而至绝望而不抵御者,如后来的王观堂先生。陈寅恪先生解释其自沉昆明湖之举,乃是因为王观堂先生是已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其人已融于中国文化,与之同体同命。眼见中国文化如此劣势,痛感失却安身立命根基,遂绝望自沉。王观堂先生作为一代宗师亦有如此文化判断,其他担忧者便可想象。只是他们尚未绝望,也不愿为中国文化殉情(当然,客观上也完全无需殉之),遂采激烈抵御之态。其三,文化利益即社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之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J·布坎南有一极深刻思想:政府、政党、制度乃至公共物品等等抽象概念,仅有指称意义并无实践(实际)意义。对之绝不能作抽象把握、抽象研究。这些概念的背后,均是活生生的人。而他们,均服从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因此,对其选择、决定(策)之研究,均应作利益之实证分析。如公共物品之生产、供给,不能一言概论之“民众(公民)之需要”即可。应实证分析之,哪些民众需要?有没有民众不需要?甚或直接就是以民众利益名义的官员需要(想想很多政绩工程,不能不钦服布坎南)。社会文化何尝不是如此?任一社会文化体系,均构建了相应的文化利益格局,其背后均是活生生的人。任一文化利益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均是以此为生且比他人生得好得多的人——哪怕这一社会文化体系导致绝大多数人生活得不好或不够好——焉能不顽强抵御该社会文化体系的可能变动?遑论跃迁了?!如器物(经济)的分配者,制度(政治)的安排者,意识形态的选择与解释者等等。文化抵御的背后,是利益的捍卫,皆利益使然也。这一思想的源头,其实是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民主文化的背后,是为了捍卫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极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获取极高的利益甚至无穷的利益,乃至可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样的极端私利,只能亦必须用文化的名义捍卫。岂止抵御,还有内心自明的不道德的批判与斥责。上述种种,混合纠结,构建了强韧的抵御。
但是,落后文化被淘汰亦是必然的。落后文化之所以落后,一乃其有违直至悖逆于人类普世价值(观)。而得到人类首肯、尊重的民族性,恰恰彰显了其普世(价值)性。二因其无助于甚至阻碍、损害民族利益的增长。文化选择,归根结底是民族利益乃至人类利益的选择。如此,晚清才呈现出梁启超所言的社会大文化观进化的三个时期。(科学)技术层面的利益(获益)是显见的,其先进与落后一目了然。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制度利益(获益)、思想利益(获益)则是深层次制约性的,是逐渐显现的。三个时期内涵不一,但指向均是民族利益。这一进程,既是摒弃落后文化之律,亦为接受先进文化之规。落后文化,究其渊源,产生于、固化(制度化)于统治者个人及统治集团的私利,属黄宗羲所言“以一己之私利,夺天下之公利”可“谓之国贼”者。其最终必与民族利益——人类价值(观)冲突,遂尽显落后性,遂非主流化,遂边缘化,终致被淘汰。决定机制是民族利益的(客观、自然)选择。民族利益和人类(普世)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此可谓之人类文化选择(发展)公理。
抵御虽客观存在,但凡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终将被本土文化吸纳,融于本土文化。换言之,文化的先进性,不论外来的还是本土的,是不可抵御的。从形而上层面言,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她源于人类内心的永恒追求的意向。从文化对话的具体层面言,先进文化非可抵御性之机理亦有三。其一,现实地增进了本土文化体系的利益。诚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但是,现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弥补。“从长远的观点看,现代化增进了全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37)晚清中西文化对话,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与进程。或言,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与进程,就是中西文化对话的开启。尽管其是外迫型的。先进外来文化,可更新、促进、强大本土文化,这已是史实,并仍为事实。既如此,凡有一点民族关怀、国家关怀、社会关怀者均会不同程度地吸纳之。并无什么学识的慈安慈禧,多次支持了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自强派,动因即在此。洋务运动者自称为自强运动,底蕴亦在此。后来的维新、立宪、革命运动等等,更其如此。但对如何切实增进民族、国家之利益,后来者认识得更加透彻与全面。
其二,先进文化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普适性。(38)但凡创始者可以赖以发展、强大,并能跨文化系统传播且被非创始者广泛接受、采用的文明成果,均乃人类共同的文明。虽然她首创于某一国家,甚或某一民族,如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顾准先生考定: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当且仅当发端于英国,乃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首创。因为只有当时的英国,具备了后来被称之为近现代化诸多内容的诸多必须条件。除英国外,其他国家均未充分具备这些条件。从这一角度讲,其他国家的近现代化均是学习(英国)型的,区别仅在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为什么这一学习运动达成了普遍性呢?因为近现代化的内涵如工业化、市场化、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等,均乃人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产物,均乃人类共同的文明(文化)成果。所以,凡人类者,不会或不会长久拒斥。正是在此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言:“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从长远的观点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39)人类究竟是否存在共性的价值共同的文明,这并非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人类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基础何在?有人从国家战略利益角度探讨之,虽有一定道理,但远非根本。单纯功利性追究不能解释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民跨民族跨阶级的联合,也无法解释很多史实:如大西洋宪章;如开罗会议对法西斯国家历史上所获一切侵略利益的否定,这就是台澎金马回归中国的开端;如租借法案与护航法案;如驼峰航线;如海狮计划失败后,英国拒绝纳粹的诱和,而与苏联签订的对德联合作战协定等等。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法学家鲍勃说:“纳粹,是20世纪可耻的一页,堕落的一页。此次审判的原告是人类的文明。”(40)可谓一语中的。否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人类共同文明(文化)基础、共同伦理基础,是对人类的诬蔑与贬低,是否认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质,实际上是否认者的自我贬低乃至自我否定。可见,人类共同的文明,人类进步文化的普适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不存在仅属一个民族、乃至一个阶级的先进文化,即使首创者确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但其得以传承、积淀于人类历史,成为人类文明中的熠熠生辉者,则因其已超越了民族与阶级,成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构成民族、阶级对人类文化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价值观既受启发于前人,且已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就是明证。历史、实践、认识、逻辑的终点也是一致的。实践是出发点,亦是归宿点。
人类共同的文明,源于共同的人性。人的自然属性(生物性)相同,这毋庸赘言。历史唯物主义恰恰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人类生物性(物种)的延续,是其社会延续的基础。人首先要衣食住,才谈得到其他。即首先是其生物性的实现,才谈得到其他。因此,利于(不是部分,而是大部,并走向全部)人的生物性实现的文化体系无疑是先进的、优越的。源自西方的人类社会的近代化内涵吻合这一标准。自然属性的共性立即生成了社会属性的共性,即人类共同的社会性,首先是基本的伦理。孟子言,恻隐、善恶、恭敬、是非、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并为仁义礼智信之端也。人类关助弱小、尊爱老少,实因人类种群延续、发展之需。这一伦理,实际上是(物种)生存伦理,许多高级物种皆有。人类的生物共性还产生了实现种群延续的自由性、选择性权力的共性等等。因此,道德是因生物性而发生的,并非康德所言是原生的(先验道德律)。可见,否定人的社会属性之共性,且截然割裂、区别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否认二者联系的种种说法,违背科学乃至常识,是荒谬的。因此,更(符合、顾及)人性的社会文化,更人性化的社会文化,当然会被推广,被承认。即使离人的自然属性较远的社会属性,也是由自然属性多级多次衍生派生的,也是有共性的。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是最社会化的动物,直观表现就是人结成了社会(荀子早言:人能群),人对社会有很高的关注度和极强的参与欲。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有助于此社会性的实现呢?惟民主政治!即马克思所言:真正的、普遍性的民主。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逐步实现了此目标。民主政治,满足了实现人的共同的、最高的社会性,致人类虽诉求(利益)不同,而合,而和,真正成就矛盾统一体这一宇宙的普遍法则。积蓄既久其发必速(毛泽东语)的少数压迫整体的专制主义,乃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反动。所以,受此西来文化影响,痛斥痛陈专制主义之无穷弊害,批判反对专制主义之自私利己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呼吁民主宪政,追求走向共和,成为晚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此线自1840年代有识之士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中已显端倪。
其三,落后文化具备理解、接受先进文化的认知性基础,这也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共通性、互同性。虽然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认知技术性问题,如:如此之多的西学术语,能够被中国文化准确地理解、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符号系统,能被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迅速找出与之相对应的意义与关系等等。毫无共通、互同认知基础的外来文化,是不可能被理解和接受的。这也从纯粹技术性角度表达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性。绝对陌生——不相容的话语——符号系统,是不可能跨文化传播的,遑论认同。有此共性认识基础,即有了比较、鉴别标准,不同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可被“读”出,进而被认同、传播。
承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稳定下来后,本土文化的回归即民族文化的自觉亦是必然的。其机理亦有三:首先,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过后,本土文化在与之长期的相识、共存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弊端必将显现(无缺陷的文化是没有的)。对此弊端的指认,一方面源于本土文化的先进内容,一方面源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标准。如严复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感(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争夺,确然),并由此回溯及西方文化的缺陷,对之作了犀利的批判。如孙中山对于早期、较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有悖于民生、民权的揭示。孙中山甚至偏颇地批评天赋人权观为实现不了的假平等观、结果平等观。这显系误读,有专行挑刺之嫌。天赋人权观强调的恰恰是他本人所主张的起始点的平等(观),人们政治地位的平等(观)。但由此,亦可窥见文化自觉立场的兴起与强化。种种对西来文化弊端的揭示与批判,表达的是对西方文化的审视。这一审视,已非守旧派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抵御,而是冲击之后镇定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全面认知。它既不同于盲目拒斥立场,亦不同于盲目接受立场,是一种冷静的比较、鉴别。于此中,外来文化的不足更易显现,民族文化的自觉及自信自强则逐步凸显。
其次,民族文化的先进内容永远不会泯灭,且会被不断发掘。康、梁、严复、孙中山等对孔孟之学的肯定性立场,可为明证。康梁的托古改制论,虽有策略性考虑于内,但其对孔子原则的阐扬,当属无疑。孟子之学,源自孔子及子思,孔子之学,源自周公(姬旦)。周公之学,见载于《尚书》召诰、康诰等篇,乃周公以商纣覆亡教育成王之思想,可概括为“敬天、明德、保民”。帝王并非最高权威,天在帝王之上。天考察、监督帝王,就视其对民如何。从此意义,天民合一。孔子承袭此,并完成了天民合一的逻辑结构:天是仁的。天造万物,万物皆仁。悖仁即逆天,气数必尽。孟子据此,面斥梁惠王,并谓桀、纣之流为“一夫”,并非君主。可见,周公、孔孟之学,乃教育、规约帝王之学,为民谋利之学。胡适先生言“为帝王师”之学。冯友兰先生言,先秦诸子,除法家外,均站在民众立场,为人民说话、谋利。这才是中国文化之精髓要义:大众关怀,为民代言,为民谋利,与民同命。这一文化精神,是人类永恒的文化指向、文化追求,历久弥新,永不淡逝。确如晚清诸多有识之士所言,其与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之学异曲同工,甚至更彻底、深刻(在世俗政权的形而上意义上)。周公孔孟之学的精髓要义,后来被《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帝王儒学所歪曲和遮蔽,被帝王们强制推行,成为专制国家意识形态。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履,被发掘与澄清,再次奠基了中国文化,使其先进,值得恪守。当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实为打倒帝王儒学)口号后,张申府先生言,打倒孔家店,救出真孔子。
再次,葛兰西称文化乃社会的深层结构,她相对于国家机器等社会表象结构而言。深层结构是坚固的,因其是基础的、整体的。变革它比变革表象结构要困难得多。而且,深层结构只可更新,绝无可以摒弃一说。她与社会同体,无从摒弃。套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之本体、场域、惯习范畴来表达社会文化体系的坚固性也许是恰当的。社会文化体系之本体,乃人、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结构、载传文化理念大义即价值观念的经籍文本。可见,她已然是民族的构成,是民族存在之基础,是民族存在的呈现与表征。场域,即本体展开、作用的空间,它是经验的。社会文化场域,即其实现域,它既实现本体,又强化本体,它与本体的互动,是经验性的。通过此种经验性,使本体由抽象而具象,由一般而具体,从而表达、完成了本体。文化中的人,实际上具有本体与场域的统一性。惯习,是认知、认同、行为、传承。它既具经验性,又具抽象性,它是实践中的延续,又是创造的实践。实质上,它是场域的具体、质感与流动。设场域是静态的,惯习则是动态的,它对本体的作用以及与本体的互动,与场域同。三者的相互作用,坚固了社会文化体系,致其根深蒂固。这恰恰表征了葛兰西的深层结构思想。所以,任一民族文化体系,虽必须亦必然发展,但绝不可能沦亡、消失。她会不断地自悟、自觉,她是民族的表达、呈现、民族的实现及民族的传承与延续,她就是民族!她作为自在性文化必在与他文化的对话(冲突乃对话的形式之一)中走向自为,走向更新。章太炎认同万物皆由原子(阿屯)构成,认为万物皆有“心”(质),遂有“种子识”(元意识、主体意识),遂有“志”。“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41)此一“竞”,促成了万物之进化,达成了主体之凸显。(42)任一文化体系,莫不若此。文化之质,即区别性,即主体性,促使其竞、变、显,既保持了自身,又优化了自身。民族的存在、发展,就是其文化的存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存在、发展,表征了民族的存在、发展。民族与其文化,同体同命。人类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主体间性之认同之实现。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惟世界的,也才真正是民族的。全盘西化论、全球化可能遮蔽乃至取代本土化论,均乃伪命题,是谓谬论。对此担忧抵御者,实为杞人忧天或另有所图:以恪守文化之义,谋一己私利。
先进性的相容、相融、整合,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法则,乃天下大势,根本上具非可逆性。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作者附言: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陈远焕兄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注释:
①连深谙西方文化的萨义德及其思想的赞同者,也采用了后帝国主义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乃至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一串串术语,自卑情结质地表达了这种心理。
②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0页。由此可见普世价值观的存在与成立:对物质文明的共性认同至少是其一。
③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同治六年刻本。
④转引自王韬:《原学》,《弢园文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页。
⑤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本,第25、26页。
⑥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⑦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左文襄公文集·卷一》,清光绪十六年豫章刻本。
⑧宝鋆等编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2页。
⑨李鸿章:《朋僚函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2696页。
⑩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1页。
(11)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6页。
(1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7页。
(13)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4、270页。
(14)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49-251页。
(15)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32页。
(16)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王处辉等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晚清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184页。
(17)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6-197页。
(18)谭嗣同:《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30页。
(19)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王处辉等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晚清卷,第227、228页。
(20)《论今后之朝局》,《时报》1906年12月5日。
(21)《立宪近论》,《时报》1907年2月21日。
(2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11-612页。
(23)《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1页。
(24)《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6页。
(25)梁启超:《读春秋界说》,《饮冰室文集之三》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页。
(26)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一册,第40页。
(27)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
(28)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29)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46页。
(30)严复:《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与熊纯如书》,转引自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8页。
(31)参见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诸子学略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2)《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33)《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页。
(34)《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72页。
(35)《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0页。
(3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4页。
(37)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38)普适性概念源自自然科学,意为普遍适应的、适用的、可验证的。社会科学的普世性一词源于此。
(39)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第47页。
(40)参见庞绍堂:《人性的光辉,人类的胜利》,《MBA素质教育论坛丛书》第二辑,南京大学商学院编印,2007年,第73页。
(41)引自徐复:《訄书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42)严复、章太炎等人对中国文化精义的恪守,曾经甚至迄今被诸多人士批评为倒退、守旧,至少是表现了他们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从文化自觉立场看,实非如此!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天下为公论文; 中体西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