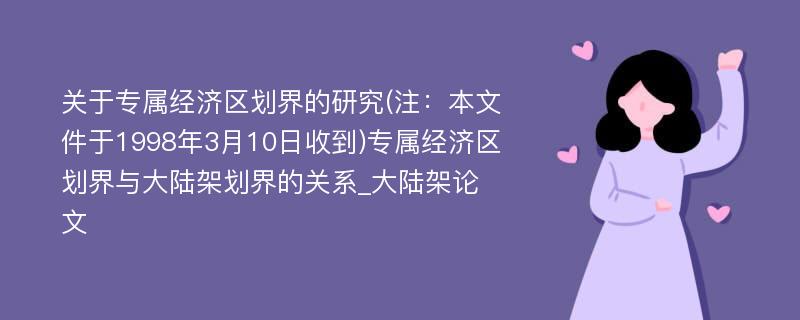
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研究——(注:本文1998年3月10日收到。)——专属经济区划界与大陆架划界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属经济区论文,大陆架论文,本文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专属经济区法律概念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的出现和被广泛接受,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一次在普遍性的国际公约中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沿海国有权主张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也使国家间的海洋划界从主要涉及大陆架划界发展到包括专属经济区划界。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海洋划界中,专属经济区划界是否必须与大陆架划界保持一致?
一、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同一界线
(一)法律根据
从理论上看,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同一界线可以基于以下理由:
1.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范围重叠。大陆架的范围,根据《公约》第76条第1款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根据《公约》第57条的规定,是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因此,就上述规定而言,在从领海基线起200海里的海域内,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范围是相重叠的。
2.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律制度雷同。(1)沿海国在大陆架上和专属经济区内行使的都是主权权利,并且这种主权权利是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注: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第1款和第56条第1款。)。(2)《公约》关于在大陆架上和专属经济内建造、管理、操作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规定完全一致(注:参见同书第60条和第80条。)。(3)《公约》关于大陆架上和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规定完全相同(注:参见同书第十三部分。)。
3.《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驾的划界规定完全一致(注:参见同上书第74条和第83条。)。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由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联系紧密,会议所采取的立场是在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采用同一原则,从1976年的《订正的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开始,第74条和第83条的措词就完全相同。
4.基于实践中的需要,专属经济区应与大陆架保持同一界线。(1)可以避免相关国家在同一海域内管辖权相冲突。假设A国在它的专属经济区内建造人工岛屿,它将根据《公约》第60条2款的规定,享有有关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规章方面的管辖权,如果此海域恰好在B国的大陆架之上,两国之间就会产生管辖权冲突,因为B国根据《公约》的规定,也享有同样的权利(注: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0条的规定,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比照适用第60条“专属经济区内的工人岛屿、设施和结构”,因此,B国也享有在自己的大陆架上建造人工岛屿的权利,相应的也享有有关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规章方面的管辖权。这样,它与A国在同一海域就有可能发生管辖权相冲突的问题。)。(2)可以使相关当事国节省人力、财力,避免就同一海域的划界问题进行两次谈判,一次为大陆架划界,一次为专属经济区划界;如果相关当事国提请第三方解决划界争端,也可以使它们避免提起两次请求(注:Fara j Abdullah Ahnjsh,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Maritime Boundaries and the Practice of Stale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Clarendon Press,Oxford,1993,P138.)。(3)有利于资源开发和方便资源管理。在同一海域,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界线不同,会产生A国大陆架的上覆水域是B国专属经济区这种情况,不利于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基于上述理由,在划界实践中,相关国家常规定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同一界线。
(二)国家实践
一般来讲,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的海洋边界协定主要是大陆架划界协定。事实上,在1975年前只有9个协定考虑了经济区或渔区的划界问题(注:Colson,The legal Regime of Maritime Boundary Agreements,In Edited By Jonathan I.Charney and Lewis M.Alexander,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 I,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P45.),其中四个协定是在南美国家之间签订的,包括1952年秘鲁——智利、秘鲁——厄瓜多尔(注:1952年的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关于领海的圣地亚哥宣言,确定了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秘鲁的海上分界线。),1972年巴西——乌拉圭,1973年阿根廷——乌拉圭海洋划界协定。其余五个协定为:1957年挪威——苏联关于划分瓦朗格尔峡湾海域边界的协定;1968年阿布扎比——迪拜岸外疆界协定;1969年阿布扎比——卡塔尔;1973年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1974年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注:上述协定,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与此相反,在1974年以后,仅涉及大陆架划界的协定只有十个左右。国家实践表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国家接受了单一海洋边界的概念,一些国家在划界协定中明确规定“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同一界线”。例如1979年多米尼加——委内瑞拉缔结的海洋划界协定第一条就规定:本协议所划定的海洋界线构成两国之间已经建立的或者可能建立的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大陆架、特殊经济区以及任何其他海洋或者海底区域的边界线(注: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554页。)。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法属新喀里多尼亚(1993)、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1988)、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1989)海洋划界协定,都规定“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同一界线”(注:朴椿浩编著,王丽玉、李红云、张海文译:《国际海洋边界——太平洋中部和东亚》,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 页。)。
(三)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
在现有的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专属经济区(或渔区)与大陆架同一界线的案例有四个:1984年美加缅因湾海域划界案、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洋划界仲裁案、1992年法国(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加拿大海洋划界仲裁案、1993年格陵兰——杨马延海洋划界案。
缅因海湾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开放签署后,国际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案件,也是国际法院自1946年以来,根据当事国的特别协定第一次以设立分庭的形式审理的海洋划界案,同时它也是第一个用单一线既划分大陆架又划分渔区的国际司法判例。
国际法院分庭认为,适用于海洋划界的基本习惯国际法是,“划界不管由直接的协议或由第三方的裁决来实现,都必须建立在适用公平标准并使用能够保证公平结果的方法的基础上”(注:《缅因湾海域划界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段。)。分庭强调,每一个划界案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第一个案件都有不同的公平标准(注:《缅因湾海域划界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6段。)。具体到本案,分庭被要求划一条划分大陆架和渔区的单一界线,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不对两个目标中的一个给予优惠而又损害另一目标的标准或标准的综合,应优先考虑由于其中立性而最适合多种划界用途的标准。分庭提出了在本案划界中应考虑的首要标准是“从地理中衍生出来的标准”,包括海岸线长度之间的合理比例,不隔断一国的海岸线,岛屿等(注:《缅因湾海域划界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段。)。最后,分庭在划定缅因湾的第二段边界线时,考虑了两国海岸长度的比例和加拿大的海豹岛,并对边界线作了相应的调整(注:《缅因湾海域划界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段。)。
在缅因湾案中,国际法院面临着发展用一条单一线划分大陆架和上覆水域的法律的任务,分庭通过强调“中立性标准”,确认可以划定大陆架和上覆水域的单一界线,但并不认为划定大陆架和上覆水域的单一界线是一种法律义务。分庭指出,在确定大陆架和渔区的单一界线走向时,“应优先考虑由于其中立性而最适合多种划界用途的标准”,这种“中立性标准”主要基于地理因素。在该案中,分庭没有考虑地质地貌因素和经济因素。分庭提出的“中立性标准”理论,已引起了争论。该案法官格罗斯(Gros)对判决投了反对票,在其反对意见中,他批评分庭采用的“中立性标准”。他说:“我发现难以把握什么样的标准才能不给予‘优先对待’一个目标以免‘损害’另一个目标,同时还‘适合’于两个目标。这些词语需要解释,而判决没有提供解释。如果以适当的意义适用它们,这些标准必须既不损害大陆架也不损害水体,所以它必然是缺乏效力的标准……。”(注:International Courter of Justice Reports,1984,P369,Para14.)
国际法院分庭在缅因湾案中,第一次面临决定用一条单一线划分海床和上覆水域应适用的法律和标准的问题,分庭通过强调“中立性标准”,确认可以划定大陆架和上覆水域的单一界线,并指出这种“中立性标准”主要源于“地理事实”。1985年的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洋划界仲裁案是西非国家之间第一次请求第三方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案件,也是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第二个大陆架与上覆水域同一界线的案例。它和1992年法国——加拿大海洋划界仲裁案均与缅因湾案保持一致,都强调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并主要基于地理事实对案件作出了裁决。而在1993年的格陵兰——杨马延案中,国际法院在决定划界线的最后位置时,没有完全适用“中立性标准”,国际法院考虑了两个因素:扬马延和格陵兰之间相关海岸长度的差别和双方当事国对自然资源的平等利用。第一个因素无疑属于“中立性标准”,第二个因素是为了确保双方当事国能平等利用争端区域内的毛鳞鱼资源,它主要涉及渔区划界,而与大陆架划界无关。1993年的格陵兰——扬马延案判决,对缅因湾案中提出的“中立性标准”是一个挑战,它表明在用一条单一线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或渔区)时,根据具体情况,并不需要完全适用“中立性标准”。
上述四个案例,都肯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海洋区域,它们对国际法是否要求用一条单一线来同时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或渔区)这个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二、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界线不同
(一)法律根据
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是两种完全独立的法律制度,这从1982年《公约》分别以第五、第六两部分加以规定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内陆和地理不利国家(包括阿拉伯集团)与日本曾主张由于已建立200海里经济区制度,大陆架概念应取消,然而鉴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法律制度和范围上有明显区别,会议没有采纳废除大陆架制度的提案。
1.两者在范围上有所差异。《公约》第76条第5款规定了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最大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2500米等深线外100海里。而根据《公约》第57条的规定,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最大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因此专属经济区与宽大陆架的范围差异甚大。
2.两者的法律制度不同。(1)沿海国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是固有的,它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注:参见《公约》第77条第3款。);而专属经济区要“主张”才拥有,它以沿海国的宣告为准。(2)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涉及所有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除定居种生物外,则主要以非生物资源为主。
3.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时考虑的相关情况不同,大陆架以海床和底土为重点,而专属经济区则以水域为主,为使划界得到公平解决,两者考虑的相关情况有可能不同。一条对于大陆架来讲是合理的边界线,对专属经济区并不一定公平,因此,公平解决并不要求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线总是相一致(注: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w,University of Cambridge,International Boundary Cases:the Continental Shelf,Volume one,Crotius Publications Limited,1992,P40.)。
基于多种因素考虑,在划界实践中,相关国家并不认为专属经济区划界必须同大陆架保持一致。
(二)国家实践
国家实践已表明,大陆架边界并不总是作为专属经济区边界,根据需要,它们可以是两条不同的界线。
1978年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了托雷斯海峡海洋边界条约,这个条约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取得的,这是解决海洋争端的最佳方式。条约建立了海床和渔业管辖权的不同界线,它们在大部分地方是一致的,但在托雷斯海峡地区分开了。由于该地区的地貌形状,海床线的延伸从基线量起,超过了200海里,反之,渔业管辖权的边界线终止在200海里的地方(注:H.Burmester,the Torres Strait Treaty:Ocean Boundary Delimitation By Agreement,Americ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76,1982,P333.)。托雷斯海峡条约的产生很有意义,它表明在国家实践中,单一边界并不是必然的或强制性的,因边界不同而产生的实践问题,可以通过当事国间协调解决。
有时相关国家已经划定的大陆架边界,不是位于等距离的位置,那么,得到较少海底区域的国家,可能会坚持在解决专属经济区边界时取得相等的水域。例如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1971年和1972年的大陆架边界协定,把较大一部分居间的海底划给了澳大利亚。后来,印度尼西亚提出,覆盖在海底上面的水域应该平等划分。两国在1981年10月达成渔业监管和执行协定,该协定建立的临时性渔业线是一条中间线,就将澳大利亚海底上面的某些水域划归印度尼西亚管辖(注:普雷斯科特:《海洋管辖范围问题》,载G.肯特和M.J.瓦伦西亚编、国家海洋局海洋科技情报研究所译:《东南亚海洋政策》(内部资料),第50页。)。
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之间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会采用不同的界线。1989年民主德国——波兰的海洋划界协定,建立了一条新的海洋边界,不同于1968年协定中的大陆架边界,主要原因是双方当事国延伸它们各自的领海到12海里,产生了导致妥协的新情况。在1989年协定中,波兰通过扩大领海获利,确保了波兰的航行利益;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得到了波兰在渔区和大陆架区域外的让步〔21〕。在该协定中,双方当事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协议达成了一条不同于1968年大陆架边界的新的海洋边界。
三、结束语
在现有的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还没有出现大陆架和上覆水域界线不同的实例。从已有的采用单一线划分大陆架和上覆水域的案例来看,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肯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海洋区域,为使划界得到公平解决。它们并不反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采用不同的界线。
综上所述,根据国际法,国家有权选择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一界线或不同界线。国家在划界实践中采用不同的界线,反映了不同的法律制度在划界时考虑不同因素的法律要求。单一界线,虽然有利于资源开发和资源管理,但在一些情况下,很难保持一致。已经划好的大陆架边界,往往受到地质或地貌因素的影响,因此以后划的专属经济区边界,虽说已有前苏联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实例,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否能与大陆架界线保持一致,还十分值得怀疑。而且,对于宽大陆架的国家来说,当它们能够根据大陆架制度对更多的海床享有主权权利时,很难想象它们会简单地为了实践中的方便,而采用一条单一边界,尤其是当重要的资源利益位于大陆边缘时。因此,在实践中,划界当事国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协议采用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相同的界线,也可以采用不同界线,两者都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标签:大陆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