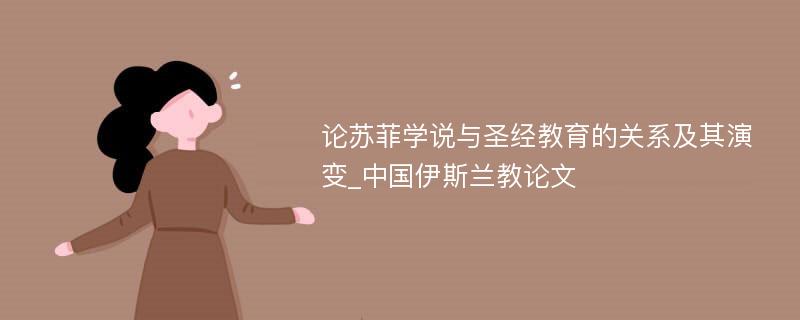
试论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及其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堂论文,试论论文,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以来,经堂教育的倡兴、汉文译著活动的展开、门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三大“中兴”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接续,联系密切。尤其是经堂教育的创立,使中国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了由下而上的社会“民间化”、制度化发展阶段,并对后两个阶段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建设和生生不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经堂教育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始终坚定地走着一条尊奉伊斯兰“元典”(以《古兰经》学、认主学为主的伊斯兰原启、原创经典和原则)精神,历代经师、阿訇以自己“尔林”(知识)、操守(德行)密切联系民众,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道路,在世界伊斯兰教文化格局中,显示出显明的中国伊斯兰特征。至于经堂教育的作用、功能、贡献及历史经验,论者甚多。本文拟就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的关系以及苏非主义对经堂教育的影响及其流变,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
苏非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在承认“安拉”为独一最高主宰的前提下,以喜爱真主、人主融通为最基本信念,以苦行、苦修的禁欲主义和人神冥想、内心祈祷的专心致志方式,认识真主,接近真主。中世纪以来的伊斯兰哲学思想发展史上,苏非主义思想对伊斯兰教正统派和什叶派的教义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伊斯兰教教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苏非主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苏非主义思想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历代经师和承传弟子及广大穆斯林大众,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在著名的经师、阿訇身上表现突出,胡登洲及其弟子都多少与苏非主义有关系。
《经学系传谱》有胡登洲“遇叟得道”的“纪事”:有位缠头叟曾向胡出示一本苏非著作《母噶麻忒》,后又向胡传授该书。(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26~58.)后来,《母噶麻忒》被列为经生的读本之一,这显然与缠头叟有一定关系,也说明胡登洲受过苏非主义著作的影响。胡登洲的嫡传弟子海文轩“严气正性,秉直不阿,真暗室金灯,迷津宝筏也。”他接受和研究苏非派的哲学,从正确的教乘和道乘升至引人为荣的第三道乘的指导者(穆尔什德),故被海内称为“晒黑”(即谢赫、筛海),犹华言仙种也。不仅教内之人“咸知”其“归主有光”堪与西域有道筛海并传不朽,而且“汉教”之人亦称其“遐升九霄”。(注:金祯、杨学.海东阳及其墓碑“清真教述圣公碑记”[J].回族研究,1991,(4).)
马明龙从学冯伯庵时,就曾接触苏非主义经典《米尔萨德》。后开学江夏时,适有缠头名极料理者云游至楚,侨宿于寺,明龙遂师之,“拜师入道”,得关于《米尔萨德》之较深传授,达到以书字译此经为《认己醒悟》的程度。
常志美是一位由钻研《遭五》、《满俩》、《白亚尼》三经,“拔此数经之精华”,“获开诸经之钥”,(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26~58.)能通于诸学而起家的著名经师。可其最受门人尊崇的是,在执教于济宁东大寺时遇缠头极料里,欲请购极料理所展示的《富尔斯》经而对方不予,后河间经师白赞廷却命自己的儿子白耀宇携极料理所授之经《富尔斯》作贽送给了他。从此,他通过相对解明《米尔萨德》、《富尔斯》,基本掌握了《米尔萨德》深义,并将这一苏非经典的传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后来居上的云南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马德新,早年负芨陕西求学时,受到陕西学派名师们以精研一本苏非主义理学经典、自立门户为荣之风的熏陶,但门宦在甘宁青的不断形成,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如何将坚持哈乃斐逊尼派正统和正确理解苏非学说统一起来的问题,故有“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的感叹。后游学、朝觐,请教以斯莫恩来等知名学者,方意识到过去“尝观群经,犹不及觉,今闻君命,豁如梦醒。”继之又阅安萨里所著的《以核呀矣经》,才真正弄明白,“遂不复再问道乘、真乘矣”。(《四典要会》)基于此,马德新才将云南学派中讲授的苏非经典学说同门宦中实践的苏非学理有意识地区别开来,并将经堂中的苏非主义正式纳入安萨里主义的轨道,开辟了自成风格体系的云南学派先河。马联元作为一代经学大师,在国外如印度、伊拉克等地求学时,师事阿布杜·哈米德,学习纳格什班顶耶的“迪克尔”,更说明他接受过苏非学理和实践的熏陶。诸如此类的其他著名经师还有许多。
从经堂教育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苏非主义很早就传入中国。早期来华的两位苏非传道者值得注意:一位是上文所言、著名经师马明龙师从的“极料理”,此人乃“深通理学入道之秘者”;(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26~58.)另一位是著名经师张中“执弟子礼,以师事之”的印度“胡僧”阿世格,此人“唔言性道,考证古今。或言天人之奥,或穷性命之征,或究理道之旨,或谈修证之功。”(注:张中.归真总义[Z], “欣度师以麻呢解缘起疏”.)他们对中国著名经师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名不见经传的苏非传道者就更多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穆斯林经师、阿訇和教众产生了影响。
二
苏非主义思想对经堂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历代著名经师身上,而且更明显地表现在经堂教育所采用的课本和教材方面。历来经堂教育中所说的“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又称“赛拜嘎”(阿语,意为“逾过”、“竞争”,又引申为“步伐”、“教程”)经,(注:杨杯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357 ~359.)成为经堂教育的必修课本。 经堂教育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基础课包括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三门,是深入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工具课;专业课包括认主学、经注学、教法学、圣训学、哲学、文学等。专业课中,阐释苏非学说的著作占了不小的比例,其中除一些带有苏非思想的经典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有所增损外,大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迄今为止,仍在中国经堂教育中广为教习和流传:
1.《米尔萨德》(Mirsad)波斯文本。它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兰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书成于13世纪中叶。此经分五门 40篇,其中第一门3篇,讲此经的纲目与题旨;第二门5篇,讲人身性命的造化根源;第三门20篇, 讲今世调养性命的正事;第四门4篇,讲善恶之人的不同归宿;第五门8篇,讲士农工商各种人的职业与修持。胡登洲再传弟子冯伯庵设帐云南蒙化时,当地庠生马某才从家中柜中取出此经,招从人呈进给伯庵。马某“亦不知祖父何人之所遗”,反正冯伯庵初阅后称此经“兹土未传”。伯庵习得此经之文之理,授予马某,马某又遗传该经于其子。马明龙作为冯伯庵的名弟子之一,也得到《米尔萨德》的传授。到常志美与其弟子舍蕴善、伍遵契时,对《米尔萨德》的理解、传授、译释都达到了纯熟的程度,尤其以伍遵契汉译本《归真要道释义》最著名。《米尔萨德》一直成为经堂教育常设教材之一。
2.《艾什尔吐·来麦尔台》(Ashaat al—Lama'at)波斯文本。作者是阿布都·拉赫曼·加米,他以苏非派的观点来阐释认主、爱主、近主的苏非思想体系。本经典被伊斯兰世界推认为伊斯兰哲学的杰作,是认主学的最高理论。(注:杨杯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357 ~359.)《来麦尔台》是经堂教育中唯一的一部波斯文认主学教材。经堂教育中阿訇们以能讲此经而自豪,就是在一般穆斯林民众中,也有“没讲《来麦尔台》,认主学没学全美”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部经典在伊斯兰教认主学上的重要地位。《来麦尔台》曾多次被我国伊斯兰学者解译,刘智《天方性理·采辑书目》中将该经音译为《额史尔》,意译为《费隐经》;庞士谦(1902~1958年)阿訇译为《额慎而亭》,并介绍该经为伊斯兰认主学的最高理论精华。汉译本有舍起灵(破纳痴, 1630 ~1710年)的《昭元秘诀》广泛流行于世。
3.《虎图布》(Khutab)原文为阿拉伯文,后被译为波斯文流行。它是对阿拉伯文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释,圣训选编者是圣训学家伊本·沃德安(伊历?~594年),波斯文译者不详。(注: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A].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366.)本经典成为经堂教育中讲解精神功修的必读课本,带有显明的神秘主义色彩。清代刘智《天方典礼·采辑书目》中列有《胡托布》,汉译名《圣谕》,流传至今的汉译本有1923年天津光明书社印行的李虞辰(?~1936年)阿訇的《圣谕详解》。
4.《艾尔白欧》(Arbarn)波斯文本。作者哈萨谟丁·本·阿劳丁·努吉巴迪(生卒不详)。它是阿拉伯文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释文本,其基本内容也是讲解精神功修,更是“纯粹道学”的。(注: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A].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366.)
在经堂教育选用的课本中,以上反映苏非思想的两本著作、用苏非主义的观点注解的两本“圣训”,在“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中占有不轻的比重,足见苏非主义对经堂教育的影响。此外,经堂教育中还有许多供选读的经典和课本,也大多与苏非主义有关。如《母噶麻忒》(Mapmat),其“经中多意外昧语,乃品位进级之经也,计章五十(每章约三页,每页三十八行,并讲义字句约七八万言)”;(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富尔斯》,“多蕴《米尔萨德》之注释”,“乃破此经字义之典”;(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克世富艾哈查蒲》,“乃开幛幔、溃壅塞、启蒙蔽、 解羁绊之经,方臻理极义尽之境”,亦译《开幔之经》,(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可对《米尔萨德》和《富尔斯》“尚未释然”之处予以“清释”。(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此外,还有一本《默格索特》,全名为Maqsad al—Aqsa, 意为“至高的目的”。 该书作者为波斯人阿齐兹·本·穆罕默德·纳赛斐(? ~1263年或1293年)。刘智译称《研真经》,舍蕴善“以书字译”之,取名《归真要道》。该经书被看作苏非主义概论性著作,对那些“不能深入吾教之经学者,则授以所译之《归真必要》等经,终则亦能悉通教范,精达先天之理”。(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
总之,在传统经堂教育所使用的课本中,除《古兰经》及其注释和文学类、教法学类经典之外,属教义教理类的经典只有《阿戛伊德》一本属正统派官方教义学(艾什尔里—安萨里教义学—新凯俩目)的范围,其余大都与苏非主义有关。
在经堂教育中,代代经师、阿訇、经生们学习苏非经典,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不可避免地打上苏非主义的烙印。经堂中要求学者在学业、授业方法、个人品性、训诫和守贫等五个方面能为人师表,(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讲经、学经“则当示群迷而归正,诲后进以务学,达则奉明命而传经授徒,穷则循圣行而律身济己”,(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在学识上无论学成与否, 均应“富则惠人,贫则自守”。(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而要达到“传经授徒”或“律身济己”、“富则惠人,穷则自守”,通过学习苏非著作进而修心养性则可以实现。纵观经堂教育发展史,自从它创建倡兴后,学经求学者的家境往往贫寒,授业讲经的经师、阿訇中的富裕者也不太多,故经学师生的求学历程是相当艰苦的。客观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加上苏非主义著作的影响,使许多经学师生修成学业后,往往按苏非的生活方式廉洁自守,安贫乐道。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胡登洲本人“昼夜钻研,刻苦考察,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安于衽席者数年,乃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穹理之源。”(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舍蕴善取道号“破衲痴”, 更是苏非的所为,他还“读修道诸经(即推黎格忒之学,乃《米尔萨德》并《勒默阿忒》诸经),兼观性理,合其旨义,统成一家之说。”(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 ~101.)因“多内养功夫,故童颜鹤发,精神饱满”。(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舍蕴善的弟子赵灿取道号“裕心贫者”,他“行厨断火薄朝夕,愧视腰缠不足看”、“一椽容膝寄茅檐,最苦蝇飞酷日炎”、“屋漏连朝淫雨稠,乏薪悬釜事堪忧”,从而不得不“食带生荞面”,“以蔓菁根充食三日”。(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51~101.)这都是他到外求学、游学艰辛历程的生动写照。 还如胡登洲的三传弟子穆有礼,“后入峨嵋山不返”;(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二传弟子冯少泉的学生马世英,学了“理学道德之经,遂轻尘世”而中止学业。(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 ~101.)又如常蕴华和李延龄的弟子马事一“轻尘务施,巨富倾家,甘贫自守”,(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弟子张化宇“学成而轻尘出世”, (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1~101.)弟子石安宇“其学既成,深得入道归真之理,遂贱世而负出尘之念”。(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51~101.)还有冯通宇的弟子王明宇赴麦加朝觐途中被掠至西藏为奴,后遇一“吾教道长”并拜之为师而获救。道长“授以修道尽性之学”。以后在“馨都司托呢”(印度斯坦)授学并建道堂,死后葬于该地。(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51~101.)不难看出,上述经堂师生在学习苏非主义著作后, 有的按苏非生活方式度日,有的隐世修功办道等,反映了苏非主义对经堂教育的深远影响。
三
在伊斯兰教史上,从安萨里调和正统信仰与苏非主义到伊本·阿布杜·瓦哈布(1703~1792年)排斥苏非主义的六个世纪内,苏非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内实际上居于统治地位。中国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内,特别是明末以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早在元代,史料就载有不同苏非教团的云游传道者的事迹,他们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区来到中国,将苏非著作和教理思想及功修实践传入中国。他们的影响被中国伊斯兰教所吸收、融合,终于以经堂教育的统一教材和参考读物形式出现,一些穆斯林追随者甚至按照苏非家的生活方式从事宗教生活,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苏非的雏形。因此,苏非主义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概括地讲,苏非主义对经堂教育及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苏非主义经典一度是经堂考试中的高级课本。中国苏非教派产生前,中国穆斯林在学习《古兰经》和教义学、教法学等的基本经典的同时,又积极学习苏非主义经典,只是把苏非主义的认主、近主的纯粹理学纳入“讨黑德”(认主独一)的信仰体系,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和坚守“伊玛尼”(信仰),只是缺乏苏非派别的实践和制度化。而且,经堂教育在后来的发展中,强调“中阿”并授,有些苏非经典被弃置不用,而更注重教习经训、教法和有关教义等方面的著作,并增加文化课程。这些都表明苏非主义对中国经堂教育一度产生过相当影响。后来,西北苏非派别兴起后,不仅将苏非主义经典予以保留,而且选用的教材和参阅经典更为广泛。尽管如此,经堂教育中的“十三本”(或“十四本”)经,仍是经堂广大师生和穆斯林教众公认和遵奉的传统经典。
2.汉文译著活动是站在“经堂教育”的文化高峰上构建中国伊斯兰文化大厦的。没有经堂教育的发展,汉文译著活动也难以展开。汉文译著活动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高质量的文化建设工程。汉文译著活动将中阿并举,对中国伊斯兰教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建有开启山林的功绩。由于绝大多数汉文译著者均系经堂教育出身,所以,苏非主义对经堂教育的影响,也同样反映在汉文译著中。如问世的汉文著述(包括译著),不少都带有浓郁的苏非主义思想,同时也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早出版的王岱舆的《正教正诠》和张中的《归真总义》就属于这一类,后来的伍遵契、舍蕴善、刘智等人的译作都明显地带有苏非主义及其思想特征。此外,汉文译著形成的一套“汉克塔布”话语系统,对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教内外人士理解伊斯兰教、理解苏非道学,架起了沟通和了解的话语“桥梁”。
3.中国西北苏非门宦的形成与建立同经堂教育有密切的联系。西北苏非门宦的各支系创始人,大多是经堂教育中品学兼优的著名经师、阿訇,苏非主义对经堂教育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苏非门宦的产生做了学理和思想上的准备。苏非门宦则将苏非主义思想及学理进一步组织化、实践化,延续了苏非主义的影响,并且对后来的经堂教育产生了影响,如西北各门宦都更为注重讲习《古兰经》的苏非派经注,苏非主义理学、哲学典籍,并且诵读苏非主义的赞圣诗等,进而丰富和发展了经堂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4.经堂教育的倡兴、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门宦及门宦制度的形成,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三者的宗旨都是为了挽救教道衰微及复兴哈乃斐逊尼派的正统。经堂教育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和延续的教育形式和文化功能;汉文译著则是将伊斯兰教提升到与中国文化开展平等对话、理解和沟通的高度,并且打破“在教言教”的单一立场,努力做到“伊教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在立足伊教、放眼各教(儒、释、佛、道等)的学习、比较中,表现出空前的学术胸怀和胆识、勇气;西北苏非门宦的形成初衷也是为了挽救教道的衰微,以满足甘宁青穆斯林精神和心灵的需求,它们强化了广大穆斯林的内聚力,促成网络状的西北穆斯林群体社会,在历史上这一积极作用不可低估,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世俗化,才导致了一些不应有的消极因素。这三者之间,都贯穿着苏非主义的深刻影响。当然,我们在剖析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时,必须强调一点的是,伊斯兰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也一样,因此苏非主义哲学思想与其他教派哲学思想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而发展的,况且西北门宦与苏非主义及其思想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否则容易造成误解。要正确理解中国伊斯兰教派发展历史,必须历史地、客观地、理性地去思考和认识这一文化现象,方可得出科学的结论。
苏非主义对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影响及其关系流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前人的探讨和研究也不多。对这一课题的深化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认识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从而对中国伊斯兰教有一个全面、深层的理解和研究。这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一种期望。
[收稿日期]2001—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