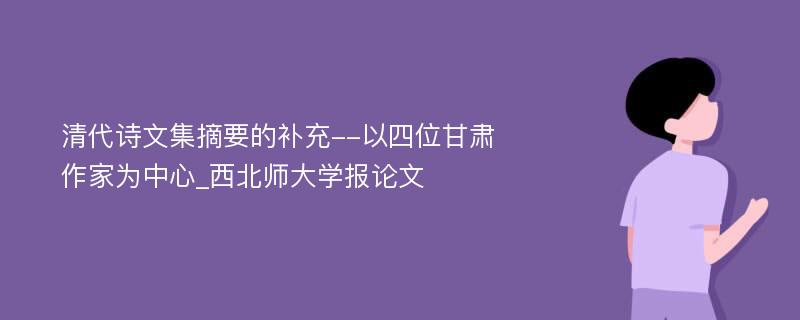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四位甘肃籍作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集论文,总目论文,清人论文,甘肃论文,四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1-0065-05
清代诗歌的文献学著作,从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到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再到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越来越向全面、系统发展(如果按实际情况结合散文,那么中间还应当加上张舜徽先生所著《清人文集别录》;假如再推及其他各类文献,则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与原有的《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配套,覆盖面最大)。这里面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问世最迟(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以下简称《提要》。),其学术价值与质量也最高。
作者柯愈春先生,像袁行云先生一样沉潜此书三十年。他以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员、记者部记者、总编室编辑的多重身份,跑遍了全国各地的主要藏书单位。全书三巨册,著录清代诗人(包括少量仅有散文者)近两万家,别集约四万种,这个数字与《清人别集总目》基本相当。各个作家名下,都尽可能介绍生平履历、著作版本及其主要收藏单位,并附有大量的考证以及扼要的评论。虽然其中著录的收藏单位没有《清人别集总目》那么广泛,同时省去了作家的传记资料目录,但关于作家本身的介绍、著作版本的考察,特别是相关的考证文字,大都体现出深厚的功力,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做过深入的研究。全书基本上按照作家时代先后进行排序,以及《后记》提到的已经搜集而尚待整理的“大约十五万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的清人别集十余万种”、大量“集外诗文及其他遗篇佚简”等等,这些也都是十分明显的表现。如果说《清人别集总目》主要还是一部工具书的话,那么《提要》则与《清诗纪事初编》、《清人诗集叙录》一样,完全称得上一部学术专著,并且从最后正式出版的时间上来看,也真正是后出转精。
《提要》的问世,无疑代表了当今清代诗歌文献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以目前我国的学术制度,和许多藏书单位对线装古籍阅览的高额收费,估计在将来的日子里很难再有哪个个人能够像柯先生这样从头做出类似的巨著,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了,例如笔者过去曾经提到的更为专门具体的《全清诗集总目提要》之类(注:参见拙著《清诗知识》第五辑之八《清诗总集研究的硕果——读〈清诗总集131种解题〉》,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71期,《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因此,即以现在的《提要》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本书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关系到本书以及日后《全清诗》、《全清文》等内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问题,更是解决一处是一处,完成一家多一家。并且可喜的是,当本书正式出版之时,柯先生才六十岁出头,作为一位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来说还算相当年轻,他本人也将继续从事这些方面的修订工作;有关读者的各种发现,正可以最终汇集到柯先生那里,共同为本书出力。
本着这样的精神,笔者特将若干读书所得陆续整理成文字,提供给柯先生以及其他有关读者参考。所涉作家,仍按《提要》原先的次序排列。有些同时关系到《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附此一并予以提出。限于篇幅,本篇仅以四位已有点校本专集的甘肃籍作家为中心,厘为一束。
一、张晋(卷八,上册,第206页)
张晋,字康侯,号戒庵,甘肃狄道(今临洮)人。顺治八年辛卯(1651)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曾官江苏丹徒(今镇江)知县,卒时年仅三十一岁。《提要》此条末尾曾提到:
孙枝蔚《挽张康侯》诗,谓“狱中诗更好,读罢断人肠”,“何曾明罪迹,能不悔词场”,未识何事系狱。
按张晋狱案,即著名的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江南科场案”。该年江南乡试,张晋为同考官。案发之后,与正副主考官及其他十七名同考官均被清廷处死(包括此前瘐死狱中者),“妻子家产,籍没入官”。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刑部量刑上疏在顺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辛酉”(二十八日,公元1658年12月22日),后被顺治皇帝严旨“重加惩治”,具体施行当已是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也就是《提要》所定张晋的卒年。上引孙枝蔚挽诗,原见《溉堂集·前集》卷四“五言律诗”,编年即为“己亥”,系本年同体裁作品第五题(凡二首,所引两联均出第一首);最早第一题已是正月“十四”,而后面第二题仍作于“春日”,由此可以推知张晋殉难的大概时间(包括消息从北京传到孙枝蔚所在的扬州)。
又张晋有弟张谦,《提要》同卷曾著录其《得树斋诗》,但未明其与张晋的关系,也不详生卒年,因此次序反置于张晋之前(上册第193页)。按今人赵逵夫先生曾校点整理张晋《张康侯诗草》(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其中即附收张谦《得树斋诗》;此外还撰有《清代诗人张晋生平考辨》(注:原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清初甘肃诗人张谦》(注:原载《庆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张晋交游考》(注:见《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等一系列专题论文,不仅前述张晋狱案曾做考证,而且张谦的生年也已经获得解决,即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小张晋十二岁(参见下文)。至于张谦的卒年,据有关考证则大约在清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拔贡”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李观我纂修《狄道新志》(卷五张谦本传曾提到“遗稿”云云)之间。另狄道在清代属甘肃兰州府,《提要》两处均称“陕西”,亦为小误。
以上张晋、张谦兄弟二人,《清人别集总目》也曾著录(分别见第2册第1089页、第1098页),并且还列有上及赵逵夫先生点校本《张康侯诗草》;但有关行年,仅提到张晋“卒年30余”,因此同样应当予以补充和修订。
附带关于上及《狄道新志》张谦本传,其中称张谦“年甫十四即有诗成帙,为孙豹人所欣赏。后著作数千首,悉为士林脍炙人口”,这里“年甫十四”云云不无疑惑。考孙枝蔚(豹人其号)《张牧公得树斋诗序》曾说:
及祸难稍平,牧公由江南侍太夫人过维扬,蹴一椽暂憩息其下,予乃得与牧公再一相见,……然予尚不知牧公之能为诗也。未几,牧公又过江去,相别辄复年余。盖牧公今年才二十一岁,其疲顿舟车之间如此。
此序既见张谦(牧公其字)《得树斋诗》卷首,亦载孙枝蔚《溉堂集·文集》卷一(个别文字略有出入)。上及赵逵夫先生《清初甘肃诗人张谦》一文,已根据《溉堂集·前集》卷五“五言律诗”《张牧公见过溉堂》编年,推断为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所作(张谦生年即据此推算)。此外《溉堂集·文集》卷一此序排在第一篇,第二篇《送无言归黄山序》据正文所述仍作于“辛丑岁”,而卷内同体裁作品也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次,因此更可以确定此序作期只有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这一种可能。而所谓“祸难稍平”,结合下文“相别辄复年余”来看,应该就在张晋殉难的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当时张谦已经十九岁,然而孙枝蔚却还不知道张谦“能为诗”。因此,上引该本传以“年甫十四即有诗成帙”与“后著作数千首”相对举,而将“为孙豹人所欣赏”属之前者,恐怕与事实并不相符,至少在行文上易生歧义。而另考《张康侯诗草》所附张晋《戒庵自识》,曾提到自己“十四岁知声律,今一纪矣。……箧存古近诗千七百余首”;又张谦《得树斋诗》内《晋陵东园逢方十五彦博弟三首》,其一有“见汝诗成帙”之句,原注说:“彦博年十四,为诗几三百首。”上引该本传称张谦“年甫十四即有诗成帙”云云,估计很可能就是由这两条特别是后一条记载牵连而致误。至于此后几种地方志的类似说法,则显系沿袭该本传而来,毋须再辨。
二、邢澍(卷三十四,上册,第959页)
邢澍诗文,旧有民国年间冯国瑞所编《守雅堂稿辑存》。今人漆子扬、王鹗两位先生共同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校点整理,重新编排,并经李鼎文先生审订,于1992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仍旧。《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第1册第372页)著录邢澍,于今本均未提及。
特别是关于邢澍的生卒年,《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乃至此前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卷四十八邢澍小传均作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至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但据冯国瑞《邢佺山先生事迹考》(可见今本附录一)征引邢澍(佺山其号)弟子张廷济《桂馨堂集·感逝诗·注》,邢澍实际上生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六月二十八日”,按照今本《校点说明》的现成换算即为公元1759年7月22日。奇怪的是《清人诗集叙录》该小传也曾提到“《桂馨堂集》有《感逝诗》”,却不知为什么没有留意到这条具体的记载。至于邢澍的逝世,尽管旧说多有分歧,但李鼎文先生《邢澍》一文(可见今本附录二),参照冯国瑞《邢佺山先生事迹考》所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曾提到道光三年癸未(1823)邢澍藏书已散入书商之手的情况,同时访问邢澍的后裔,最后结论为“邢澍卒于道光三年八月初八日,即公元1823年9月12日,享年65岁”,这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此,《提要》等书的有关记载,至少是其中的生年,恐怕都应当更正才是。
三、王权(卷四十七,中册,第1600页)
王权,《提要》称其“生于道光四年(1824),卒年不详”。按今人吴绍烈、路志霄、海呈瑞三位先生,曾共同校点整理王权诗文为《笠云山房诗文集》,于1990年5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集卷末附有张世英所撰《心如先生墓志铭》,叙述王权(心如其字)生卒时间十分具体:
生于道光二年十月壬寅[初一],卒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一日],春秋八十有四。
按今人路志霄、王干一两位先生共同编纂的《陇右近代诗钞》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末尾也曾附录这篇墓志铭(王权入编该书第八家),完整标题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重宴鹿鸣赏加四品衔陕西补用直隶州知州富平县知县甲辰恩科举人心如先生墓志铭》,据注“录自墓志铭拓本”;同时还附录有任承允“代作”的《王心如先生行述》(录自《桐自生斋文集》卷六),有关叙述与此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信无疑。按照本集卷首李鼎文先生《读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一文中的现成换算,即为公元1822年11月14日至1905年7月13日。此集《提要》虽然已有著录,但这些资料却还未及利用,原来的生年也只是大致推测,现在则连同卒年均可据此予以修订。又《清人别集总目》也曾著录王权并此集(见第1册第49页),但生卒年及两篇传记目录均付阙如,因此同样应当予以补充。
附带关于谢质卿。此集卷四诗歌有《寿陕安兵备道蔚青谢公(质卿)六十》一题凡三首,据下一题《挽陈星楼刺史(作枢)》推测作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秋冬之际(卷十一有《诰授中宪大夫知府衔商州直隶州知州陈君权厝志》,记载陈作枢谢世时间甚悉)。现在即定本年谢质卿(蔚青其字)满“六十”岁,则由此逆推,其生年当为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寿辰在十月杪”(本题第三首第六句原注)。《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著录谢质卿均缺生卒年及仕履(分别见卷四十五,中册第1483页;第3册第2299页),现在至少可以补出生年,并可知其曾官陕安兵备道,享年在六十岁以上。
又关于李光谦。此集卷十五有《云南镇雄州知州李公夫妇合葬墓志铭》,记载李光谦“卒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某日,年五十有四”。按“咸丰五年”乙卯农历“十二月”,公元已入1856年;但古人依农历计虚龄,因此其生年仍当为嘉庆七年壬戌(1802)。《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李光谦均缺生卒年(分别见卷四十四,中册第1438页;第1册第780页),现在亦可据此予以补充。此外依照体例,《清人别集总目》还应当一并补注这篇墓志铭。
不过,此集有关内容,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无误。例如卷十七倒数第二篇据任其昌《敦素堂诗集》补入的《户部观政进士陇南书院主讲任士言先生墓表》,称任其昌(士言其字)“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癸未[十五日]午时,年七十有一”,据此推算其谢世在公元1901年1月5日,而生年依农历为道光十年庚寅(1830);但今人龚喜平先生《甘肃近代部分作家生平辨正及其他》一文(注:原载《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以及《近代五位甘肃作家述论》注十五(注:原载《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4月专辑。),曾征引任其昌长子任承允《桐自生斋文集》卷六《先考府君行述》,考证任其昌“生于道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寿七十”,亦即公元1831年10月23日至1901年1月11日,这就与上引墓表不同。而如果仅就此二者进行比较,那么自然任承允的记载更为可信。《清史列传》卷七十三任其昌传,于其生卒年即采任承允之说。《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著录任其昌(分别见卷四十九,中册第1664页;第1册第472页),对生卒年的处理也是如此,这应该是比较妥当的。唯其卒年的公历已入1901年,这一点似乎仍然忽略了(又有关任其昌的这三篇传记,前及《陇右近代诗钞》曾一并收入附录;任其昌在该书中入编第十家,其名下标注的卒年已换算为公元“一九○一”,但小传称其“得年七十有一”,则未能顾及农历。《清人别集总目》于三篇传记缺少行状一篇,亦可据此补足)。
四、李于锴(卷五十五,中册,第1944页)
李于锴,《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第1册第760页)均缺生卒年。按作者次子即李鼎文先生,曾校点整理有《李于锴遗稿辑存》,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据此集《校点说明》以及附录王树楠《味檗斋遗稿序》、刘尔炘《山东沂州府知府前翰林院庶吉士武威李叔坚传》(此传亦见《陇右近代诗钞》附录,李于锴入编该书第十六家,叔坚其字)等记载,李于锴生于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已入1863年,2月13日),卒于民国十二年农历五月初十日(公元1923年6月23日),享年以旧历计为六十二岁。这个生卒年并此集,《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可据以补充。
附带关于陈墉、陈世熔。此集正文第一部分《味檗斋文集》有《二陈传》,记载陈墉、陈世熔二人事迹。其中涉及陈墉的生卒年,据“同治二三年……墉年垂七十岁”,又同治“四年二月……不二年,墉死矣”云云推测,大致可定为嘉庆元年丙辰(1796)至同治五年丙寅(1866),享年以七十出头(七十一岁)计。由于目前《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著录陈墉都缺少生卒年(分别见卷三十七,中册第1100页;第2册第1249页),所以这个推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又此传提到陈世熔“卒……年八十七”,《提要》著录与此相合(见卷四十,中册第1214页),《清人别集总目》则计为七十八岁(见第2册第1270页),不知当以何者为是。前及《陇右近代诗钞》最末附录有陈世熔《寄李云章、王心如二生(并序)》组诗八首(王心如即前及王权,李云章为李于锴之父李铭汉,云章其字),可借以推测陈世熔的生年,但也不是十分确切。
此外《提要》著录郭楷(见卷三十五,中册第1011页),曾提到一种《梦香草堂诗稿》。上及李于锴《味檗斋文集》内,有一篇为郭楷该诗稿所撰的序,书名“香”字在标题及正文中均作“雪”。检今人王绍曾先生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见第2册第1854页),此字亦作“雪”,依据是近人徐世昌《书髓楼藏书目》。但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一百零九郭楷小传,却作“香”,猜想这便是《提要》的来源。而现在证以李于锴此序,则可推断“香”字很可能即系“雪”字之讹。
上及李于锴《二陈传》、《梦雪草堂诗稿序》,以及《二陈传》前一篇《潘挹奎传》等,还颇多涉及有关人物的科名仕履等生平资料。这些内容对目前《提要》特别是《清人别集总目》来说,也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可借以补充(潘挹奎:《提要》见卷三十九,中册第1181页;《清人别集总目》见第3册第2417页。郭楷:《清人别集总目》见第2册第1935页)。
本篇提到的张晋、邢澍、王权、李于锴等四家专集的点校本(均收入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陇右文献丛书》),以及《陇右近代诗钞》,若干相关论文的复印件,笔者都曾经得到过有关校点整理者和论文作者的惠赠,并且其中像《张康侯诗草》还有一式两部。当时的出发点,本来是提供给编纂《全清诗》使用的。然而《全清诗》却至今仍然未能正式开编,这些资料只能用于为《提要》等书做一些零星的补订;尽管这也是前期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但相对于正式编纂《全清诗》而言,毕竟是一种遗憾。而上文的许多内容,事实上本来也应当由这些校点整理者和论文作者直接来写最为合适,笔者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为转述而已,同时也借这种方式表达对有关同志的谢意(其中《陇右近代诗钞》一书所涉作家比较集中,拟另文专门探讨)。
此外从本文还可以明显看出,《提要》以及《清人别集总目》对这种今人现成的研究成果往往没有予以充分的利用,甚至还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由此回想起当初制定的《全清诗》工作方针,凡是已有经过今人校点整理的点校本清人诗集,都尽可能结合《全清诗》的体例要求,优先予以吸收利用,并且最好还应约请原校点整理者承担该家诗集的具体工作(称为“特约研究员”),这样有利于提高全书的质量。现在从《提要》以及《清人别集总目》的有关情况来看,更能够证明这个方针确实是正确的。即使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从事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最好也应当尽可能地将该领域的已有成果网罗净尽,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收稿日期]2003-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