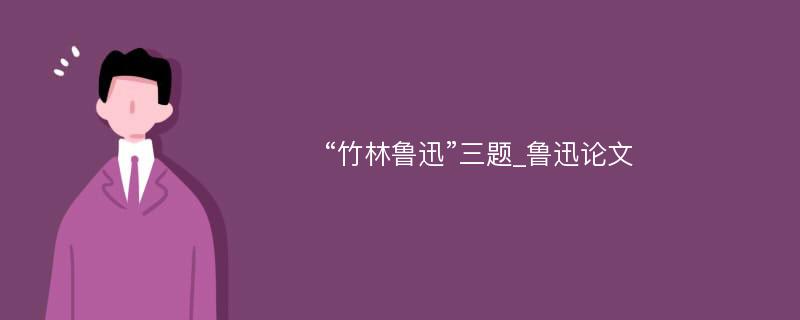
“竹内鲁迅”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竹内鲁迅”的“异质性”
“竹内鲁迅”从最初介绍到中国至今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仍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
中日上一代学者在八十年代初开展交流,并且合作将日本的鲁迅研究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都对“竹内鲁迅”这种“异质性”有着明确的认识。例如,一九八三年刘柏青先生访日之后,对日本的鲁迅研究做了详细介绍,他在高度评价“竹内鲁迅”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的开创意义的同时,又对“竹内鲁迅”表示出了极大的保留。这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了“竹内鲁迅”与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在鲁迅认识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他在介绍时,有意以竹内好之后的日本当代鲁迅研究来“淡化”这种差异:“‘竹内鲁迅’只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它的许多论点,都被后来的鲁迅论,克服了,修正了,超过了。所以,‘竹内鲁迅’的真价值,未必是表现在这些不大正确的学术观点上面,而是另有所在。”(《鲁迅与日本文学》,一九八五)交流了二十年后,伊藤虎丸先生的看法亦与当初没有什么不同。他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仍就竹内好的《鲁迅》指出,“从日中思想交流这一方面来讲,这本书同中国的鲁迅观、文学观的距离是最远的”。竹内好笔下的“鲁迅形象,即使只作为文学观本身的问题,不要说要和中国历来的鲁迅形象发生正面冲突,从一开始就很难找到对话的接点的”(《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新文学》第三辑“伊藤虎丸先生纪念小辑”,二○○五)。
因此,把“竹内鲁迅”导入到中国的鲁迅研究里来,从一开始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一九八六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竹内好《鲁迅》的中译本,可以看作“竹内鲁迅”本体直接进入中国的开端。只是印数太少了,据说只有两千册,就物理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资源,以至在后来的十五年间“竹内鲁迅”几乎没在中国鲁迅研究核心刊物乃至鲁迅学史当中留下痕迹。
笔者十分庆幸这二十几年间“竹内鲁迅”一直以澹然的“间接”方式存在,直至最近才出《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二○○五)这一译本,否则会因它的“异”而早被反掉。其实,这其间(尤其是近年)在中国看到的日本鲁迅研究,更多的倒是竹内以外的“鲁迅”。伊藤虎丸、北冈正子、木山英雄、丸山升、竹内实、片山智行、丸尾常喜、山田敬三、藤井省三等等的“鲁迅”都陆续被译介进来。对这些“鲁迅”进行整合将是有趣和有意义的题目,但那时可能会发现它们的初始点还是“竹内鲁迅”。这倒并不只意味着上述“鲁迅”都居“竹内鲁迅”之后,又都从不同的问题角度在延伸或修正着前者,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保持了与“竹内鲁迅”相一致的相对中国而言的“异质性”。
“异”者何也?个性也,主体精神也。“竹内鲁迅”本身实际早就回答了去年上海讨论会上的一个问题,即日本今后还会不会产生“竹内鲁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竹内鲁迅”作为一种“个”的存在,只能是唯一的,它最大的可能性是昭示给人们日本思想史当中的一种个性以及为保持这种个性,一个思想者在压制面前所付出的艰巨努力。当这种“竹内鲁迅”进入到中国鲁迅研究的话语中来的时候,也即意味着探寻个性即主体性的问题——至少,在“竹内鲁迅”对李长之的转述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的鲁迅研究在保持思想个性方面所曾经具有过的可能性。
“竹内鲁迅”的学术基础
那么,什么是“竹内鲁迅”呢?就其具体内涵而言,笔者同意山田敬三在《鲁迅的世界》(一九七七)一书中的意见,即指三本冠以“鲁迅”之名的著作,它们是《鲁迅》(日本评论社,一九四四年初版,一九四六年二版,创元社一九五二年版,河出书房一九五六版,未来社一九六一版)、《鲁迅》(即《世界文学指南·鲁迅》,世界评论社一九四八版,后改版改题为《鲁迅入门》,东洋书馆一九五三版)、《鲁迅杂记》(世界评论社一九四九版)。后两种在形式上为战后的作品,但竹内好的鲁迅论,原已在战争中写下的《鲁迅》当中集约性地表述出来,就是说,这三本当中的核心作品就是一九四四年的《鲁迅》。
如果还需要做一点补充的话,那么笔者以为,还应该加上竹内好本人对鲁迅文本的翻译。
就个人兴趣而言,笔者倒是希望有人来探讨一下竹内好在写作《鲁迅》时所借助的思想工具或者说“思考”工具。竹内好究竟借助了哪些思考工具(即知识)生成了他的“鲁迅”呢?在《鲁迅》(以下使用的文本均依照收在《近代的超克》内的《鲁迅》)中,中国读者最容易找到的恐怕是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不过,这个李长之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很陌生,很遥远了,虽是语言相通的国人,在读竹内好的《鲁迅》时,也未必是能借得上力的捷径。竹内好说“我买他的账”。他有时和李长之纠缠在一起说不清,有时竟能一口气引述两千多字以做“对象化”的处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长之在“竹内鲁迅”那里所衍射的思想活力以及实际发生的触媒作用。李长之倒是因竹内好在日本很成为“常识”,——但这已不是竹内好,而是要不要把李长之作为一种优秀的学术传统重新捡回来的问题了。
竹内好在北京留学期间正对女作家冈本鹿子的作品着迷,直到几年后动笔写《鲁迅》时还保留着对前者的“好得令人惊叹”(《北京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三九)的记忆。打一个很“土”的比方,就像过去“张大娘”在说别人的孩子时总爱说“这孩子就跟我们家二小子似的”一样,用来做比附的人和事总是最亲近和最熟悉的。在竹内好走进鲁迅时,冈本鹿子所扮演的角色就类似这样一个“二小子”。不,或许竹内对后者的沉溺与痴迷远非可以轻易出口的“二小子”可比。冈本鹿子“收拾”自己的“那些零零碎碎”“就是写小说”,而鲁迅的“收拾”,“不是写小说,而是‘不写’小说,或者说,在言辞不加修饰的意义上是‘写不出’小说”。就是说,竹内好对鲁迅“写不出”小说的这一断言,是借助冈本鹿子发出的。以笔者之管见,能像冈本鹿子那样把“爱的烦恼”写得那么美,那么惊心动魄的诗人和小说家还不多见。读了那些诗歌和小说,才会觉得竹内好把她用得恰到好处,或者说冈本鹿子帮助竹内好完成了对鲁迅一个侧面的阐释。只可惜冈本鹿子至今还没有一个中译本,因此,在中译本《鲁迅》里不论加上多长的注释,也无非等于告诉读者有这么个陌生人而已。真的,那么漂亮的作品怎么就没人译呢?
中野重治恐怕也是促成《鲁迅》写作的重要人物。中野重治之于竹内好的重要性,不下于他在日本文坛的重要意义以及给“转向”、“抵抗”所赋予的内涵。这倒不只因为后者在写作《鲁迅》时,“有些方法是从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上学来的”(《创元社文库版后记》,一九五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曾有鲁迅传的时候,中野重治就写了《鲁迅传》(一九三九),虽然还只是篇呼吁鲁迅传应该在日本被写出来的随笔而不是鲁迅传本身,但自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一九四一)起,日本的鲁迅传和传记文学却都是在这个随笔之后出现的,至于竹内好的《鲁迅》,恐怕有着另一层更深的关系,以至竹内好到死都会在所有鲁迅传记中最先想到这一篇(《日本的鲁迅翻译》,一九七五)。现在知道中野重治的人恐怕已经不多,先前也确曾有过若干介绍,那还是我们这个国度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学的时代。
最后是西田几多郎(Nida Kitaro,1870—1945)和芥川龙之介。关于后者,中译本有注释,而关于前者却没有注释。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再版自注中说:“由西田哲学借来的词汇随处可见,它们是来自当时读书倾向的影响,以今日之见,是思想贫乏的表现。”我在翻译时,由于相信了竹内好的话,没为西田几多郎做注,现在看来是一个缺憾。按笔者个人的读书感觉,所谓西田哲学的术语,在《鲁迅》中虽不一定“随处可见”,但一定出现在那些十分绕口却又精彩的段落里,如果只在“术语”层面,那么事情或许简单,但问题是在竹内好思想中执拗坚持的“鲁迅”、“中国”、“亚洲”这一视点当中是否也连接着西田哲学的根干部分,即在东洋精神的“自觉”基础上,积极导入西洋哲学,以探求东西思想的内在融和与统一。西田几多郎以东洋自觉之上的东西融和论,在明治以来的哲学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是日本一九一○至四十年代哲学思想的代表,故有“西田哲学”之称,所谓“京都学派”即指西田学派。据说,当年有许多东京的学生特意赶到京都来听“西田先生”的课,虽不知其中是否有竹内好,但由他的“读书倾向”也的确可窥知其影响之一斑了。
一九五一年在回答《群像》杂志的“我的文学源泉”的问卷时,竹内好在“你最尊敬”的日本作家和外国作家这两项里,分别填上了“芭蕉”和“鲁迅”。因此,在《鲁迅》里有“芭蕉”出现也毫不奇怪。芭蕉是竹内好喜爱并且读得很“透”的日本诗人,但这个诗人的心像(image)又当是来自芥川龙之介。后者是竹内好在二十岁到三十岁时爱读并且被“套”在其中的作家,直到后来他仍坚持认为芥川和鲁迅都是“美的使徒”(《芥川全集寄语》,一九五四),但早年最喜爱的却是芥川的“芭蕉论”(《关于芥川龙之介》,一九五四)。所谓“芭蕉论”,是指《芭蕉杂记》,这是芥川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写下的随笔(以下关于芥川的引用,均出自该篇杂记)。这篇杂记,不仅使竹内好读懂了芭蕉,也使他吃透了芥川处理诗人传记的手法,并且娴熟地运用到《鲁迅》当中。他自觉不自觉地把“芭蕉”照在“鲁迅”身上,并像芥川处理芭蕉那样来处理。所谓(论争之于鲁迅)“终生的余业”,所谓“撤下文台,即为废纸”,不仅是芭蕉的话,也是芥川表述芭蕉时所使用过的材料;在芥川看来,芭蕉的矛盾在于他的被“诗魔”的折磨(对诗歌的认真)和超然的出世态度,竹内把它表述在鲁迅身上就是“文学者”和“启蒙者”的矛盾;而且也正像芥川能够感受到“芭蕉不断的进步”一样,竹内好也在孙文和鲁迅身上看到“永远的革命者”;同样,芥川在芭蕉的“春雨蓬蒿旺,草径寂无声”的诗句里感知到了“百年春雨”,竹内好在鲁迅身上读到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全史”;而两者都使用的“鬼趣”一词,不论放在芭蕉还是放在鲁迅身上,都可谓道人之所未道……总之,在竹内好所能借助和运用的上述思考工具中,芭蕉和芥川处理芭蕉的方法被吸收得最为充分,也运用得最为有效。从前,刘柏青先生曾提醒笔者注意“竹内鲁迅”的“徘味”,现在终于有所悟,这“徘味”就是竹内好在把鲁迅“日本化”的过程中所加上去的“味道”,这一味道的制作,离不开芭蕉的俳句和芥川对芭蕉制作俳句的解说。还应该再附加一句,鲁迅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也和竹内好的这种出色的“日本化”处理大有关系。“国民作家”意味着鲁迅的被认同的程度,至少鲁迅在日本从未遭受过来自他母国的那种至今不绝的谩骂。
以上所涉及问题,虽然还不出工具论的范畴,但却足以说明竹内好在走近鲁迅之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素养以及有效的理论工具。竹内好此后的工作,就是与鲁迅相遇并投入其中去一搏了。
这“一搏”是什么?就是“竹内鲁迅”所应包含的最重要一点,即对鲁迅文本的翻译。
由中译本的统计来看,《鲁迅》一书的引用部分约占全书30%,其中对鲁迅的引用约占25%。在一九五二年创元版后记中,竹内好仍然认为如此大篇幅的引用,是他这本书的一个优点,“即使只捡那些引文来读,也会成为鲁迅文学的入门的”。后来,中日两国似都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以为不就是“引用”嘛!——不过,事情好像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这种“引用”与现在的不论从中文还是从日文《鲁迅全集》中的整段拿来25%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操作过程和内涵。
在日本,竹内好并不是鲁迅的第一个译者,也不是第一个研究者,在他动笔写作《鲁迅》时,日本早已有了一九三七年改造社出版的七卷本《大鲁迅全集》。但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鲁迅》中的“引用”均没使用现成的翻译,而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译过来的,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远远大于这个范围的对原文的重新阅读。竹内好所据中文版,当是一九三八年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他是在“啃”和“咀嚼”的基础上从事的翻译。日本近代非常看重自己的翻译,以至加藤周一认为,“明治的翻译主义”实现了西洋文化的“日本化”过程,同时也确保了日本文化的独立(NHK综合,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按照这种意见,竹内好通过翻译“消化”了鲁迅,实现了鲁迅的“日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和完成了自己对鲁迅的独特把握。对鲁迅文本的翻译可谓竹内好“终生的余业”。“所谓翻译,我相信是对原文的终极解释”。“我宁可相信,所谓好的翻译,是被最好的解释出来的东西,因而也是从自觉到翻译的界限的态度中产生出来的。”(《翻译时评》,一九四一)他终生都在向这种“解释”的极限挑战,一直译到死,共译(包括重译)了三百多篇,约占鲁迅文本四分之一强,但是直到最后仍对自己的“翻译”和翻译的“改译”不满意。“译者踏入作者本身当中,译出作者也没意识到的东西来,怕是真的罢。虽然是至难之业,但须以此为努力的目标”(《日本的鲁迅翻译》,一九七五),这是他临死前的话。
因此,《鲁迅》中“引用”的“鲁迅”,当然不再是中文原文,不过是在“终极解释”的意义上由竹内好变成的日语。这种“鲁迅语言”本身,实际上已转化为对鲁迅的阐释,于是,在被引用的“鲁迅”与引用者竹内好之间,便有了二者浑然一体的融合,“竹内鲁迅”由此而诞生。但是要注意,竹内好的“终极解释”容易被理解为“任意解释”,这是他的“鲁迅”遭受“学术”非议的主要原因;当消除这一误解之后,可以看到,竹内好在《鲁迅》中对鲁迅文本的大量翻译与导入,在确保他最大限度地“解释”鲁迅的同时,也使《鲁迅》一书因自觉遵守知识生产的内在规范(坚持鲁迅本身)而具有了高度的学术品位(开拓新型中国学)。《鲁迅》阐释的只是鲁迅而不是其他。
关于“奴隶的文学”
在《鲁迅》的“政治与文学”之章里,对鲁迅有着尤其多的引用,其中有想做“有系统的排列,但排不好”的连引,竟长达四页(第117—120页)。它们是鲁迅关于“奴隶”的言说,从而也可看做竹内好对这些言说的最早注意与采集。竹内好自称《鲁迅》是他的“笔记”,至少就此而言是恰当的。书中并没对那些看似杂乱的连引做任何编排和文意上的说明,却由竹内好转化的“鲁迅”言论本身做了最好的阐释。可以说,这是鲁迅价值的一个发现,也是一次巨大的精神能量的蓄积。后来,这一能量由“竹内鲁迅”开始,几乎衍射到了竹内好所有关于“文学”和“近代”的言论当中,至少通过中译本文集《何谓近代》这一篇也能强烈地感受到。
简单地说,竹内好通过自己独特的认知作业,从鲁迅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的“主奴循环论”中抽取出一个命题,即“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同”在何处?同在不具备能够自觉到自己之为奴的精神主体性。因为这种相同,所以奴隶的“解放”,也就不过是主奴秩序的颠倒,是同一循环结构内的角色对换。于是,历史只是“没有年代”的循环往复(“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从而不存在以个体的精神独立为支撑的真正的“发展”,即“第三样时代”的到来。笔者以为,这一发现,实在是“竹内鲁迅”的一大独特贡献。鲁迅的“革命”,不在于主奴关系的颠倒,而在于“主”与“奴”之外的“人”——主体精神——的确立。
竹内好的工作,将鲁迅的这一精神资源有效地注入到战后日本的思想和文学中,并释放为巨大的能量。举一个例子,战后不久,在大江健三郎还处在文学起步阶段,他便有幸与竹内好相遇了,那是竹内好的“伴随着会令人误读为绝望的愤怒,却又由刚直的逻辑和纤细的言语表述出来的评论”。在竹内好所给予的种种具有“深刻唤醒意义”的教示中,“特别是读了《奴隶的文学》这篇文章,我就像被击了一样。而且,从这篇文章中所获得的东西,伴随着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所做工作的日积月累,更加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问题,变得愈发沉重。虽然将来也绕不过这个问题,但通过自己写的小说而能推翻这个言词之日,如果认为是可以到来的话,那么将会在何时呢?也就是说,‘奴隶的文学’的问题,构成了我去思考竹内好与鲁迅的基本纲要”(《通过竹内好=鲁迅》,一九八○)。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这第三个题目将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因为在竹内好对鲁迅关于“奴隶”言说的发掘和阐释上,恰恰显露了他的界限。不,应该说,这种界限并不表现在他对鲁迅价值的发掘本身,而是表现在他把鲁迅作为与日本的“近代”绝对对立的价值,从而摆在与日本近代完全割裂的位置上。
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竹内好有着非常矛盾的说法,他先前认为“鲁迅从日本文学中吸收了很多东西”(《鲁迅与日本文学》,一九四八),晚年则说鲁迅留学时代“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鲁迅文集》第一卷解说,一九七六)。有这种矛盾也并不奇怪,因为先前说的“有关”,主要是借助周作人的回忆,后来否认“干系”,也与后来不再看重周作人有关,更何况“竹内鲁迅”的体系本身便很排斥一个与明治日本有关的鲁迅。也就是说,他最终还是否定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联系。因此鲁迅关于“奴隶”的言说也就更不在话下,在竹内好看来,那完全是鲁迅本身的独创价值所在。
日本的下一代学者在继承竹内好的前提下,实际都不约而同地对竹内好的关系否定说提出质疑,如竹内好的“正统追随者”伊藤虎丸的工作起点,就是在日本明治文学当中“试图搜寻至少可能存在的与‘鲁迅型’共通的接受近代的模式”(《鲁迅与日本人》,一九八三)。这一代学者(又如松永正义、北冈正子、中岛长文等)的努力以及所发现的越来越多的鲁迅与明治文学的“共通”,事实上已经推翻了竹内好“无干系”的假说。笔者也愿意在同一个方向上思考问题,想要知道鲁迅到底都读了哪些日本书。
关于日本,关于鲁迅的留学,周作人作为同样过来人,早年谈得较多,后来就少谈或者竟不谈了。比如说“丘浅次郎”罢,周作人说鲁迅学会日语的最大意义是读懂了他,但竹内好似乎到晚年才实际扫过他一眼,但除了“呈新味横溢之观”(《近代日本思想大系》,一九七四)一句外,未置一词。伊藤虎丸虽试图寻找日本明治的“鲁迅型”,但遇到丘浅次郎时,也把他排到与“鲁迅型”对立的非鲁迅型的行列去了。
鲁迅没有排斥丘浅次郎,而是贪婪地默默吸收了他[这是笔者关于近年所作的研究课题的结论。可参见《鲁迅与丘浅次郎(上、下)》(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87/2003、88/2004)]。令竹内好抽取出“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这一命题的鲁迅关于“奴隶与奴隶主”关系的言说,基本上是来自丘浅次郎。两者之间,已经不是“共同的时代教养”或“氛围”所表述的那种暧昧模糊,无法捕捉的关系,而是实打实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鲁迅读透了后者并将其化为自己的一块坚硬的思想基石。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对丘浅次郎的漏看,固然是“竹内鲁迅”界限的有力例证之一,但新的可能性也由这界限孕育而生。由此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鲁迅并不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近代”之外,他也是整个东亚近代知性链条上的一个“索子”,例如,如果说丘浅次郎的学说提出了“中间物”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使鲁迅为自己在“古今”和“东西”这两个维度上确立了位置,而这一位置又正是东亚“近代”整体所处的场域。
就鲁迅与明治日本知识共有的关系而言,也不妨把日本的近代看作是附着在中国近代身上的影子,了解日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去捕捉自己的影子,而在于重新了解中国近代本身。中国的近代到底是怎样一种近代呢?笔者期待着从鲁迅那里获得答案。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芭蕉论文; 文学论文; 李长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