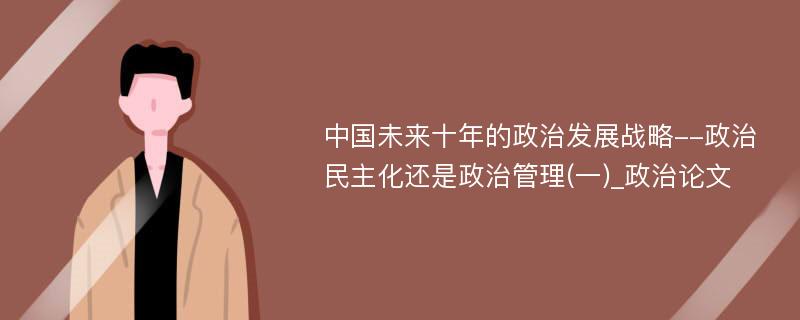
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政治民主化还是政治行政化(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政论文,政治论文,年中论文,策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模式:政治行政化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学者金耀基对“政治行政化”有精辟论述。根据香港的经验,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精英吸纳,即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决策结构;二是决策咨询,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广泛咨询公众意见。由于社会精英被吸纳到行政决策结构中,结果在行政体系之外,少有与这个体系站在对抗立场的政治人。而决策咨询使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金耀基认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积极的“非政治化”。
改革时代的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纳入行政体系,主动地制定有利于精英的政策,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不断开辟民意渠道,不但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同时也对大众的呼声做出适度回应。通过精英吸纳、政策倾斜、决策咨询,政府主动地满足精英的要求。这样一来,社会精英无须诉诸政治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要求。于是,他们或是出于自愿,或是出于无奈,而放弃了政治权利诉求,虽然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由于他们分散无力,因此即使心怀不满也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政府也就化解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中国的政治行政化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政治行政化还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改革”。自土地实行经济改革,自主地建设意识形态、并使之与权威主义政体相适应,这一切为中国赢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对于中共来说,“精英吸纳”、“咨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这些概念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对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统治策略却并不陌生,而且运用自如。其实,在中国,“行政支配社会”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从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工农大众实行“群众路线”,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对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精英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其力量不可忽视。而大众则收回了政治忠诚,对政府充满了怀疑甚至怨恨。于是,政治整合问题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治行政化”应运而生。
政治行政化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经验显示,这种“满足强者,剥夺弱者”的体制具有充分的弹性或适应能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不断满足新的强者,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它可以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其实,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特权。“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公民的需求作出恰当的“回应”并对其“负责”。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对民意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通过在决策机构中吸收社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地进行咨询,逐步放松对大众传媒和结社的限制,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和满足。为了维护稳定,统治者也必须对大众的要求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实际上,对中国大陆来说,公民的抗议、批评、组织、示威、游说决策者的权利和自由,也许比多党制、定期选举还重要。
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策略
根据亚洲、南美、南欧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很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群体联盟格局。这是因为,现存的权威主义政权的稳定性较高,近期内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动摇它的根基。而且,即使现政权崩溃了,新政体也难以脱离现有结构,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主义政治、精英联盟以及对大众的掠夺,还会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意味着,近期内,政治民主化是行不通的。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必须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大判断”是我们寻找未来政治发展策略的出发点。
简而言之,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基本策略应该是继续推行政治行政化。在群体关系方面,限制精英的掠夺,维护大众的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推行社会自由化,建设社会合作主义体制。
在未来十年内,精英联盟需要继续保持,但必须进行调整,精英的权益应该受到限制,而大众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这意味着,在分配财富蛋糕时,应该向大众适当倾斜。
当然,这种调整势必会损害精英的利益,从而威胁现存的精英联盟。一个敌视精英的政府是难以为继的,一个逼得大众铤而走险的政府也是难以为继的。这就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复杂而微妙的平衡的能力。
现实是,精英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又太少,他们不但不去维护这个给予他们过多关爱的社会,反而在疯狂地挖它的墙角。大众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代价而所获甚微。我们不敢奢望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是大众应该享有最起码的权利。我们不敢奢望精英们良心发现,但是期望他们具备最起码的智商,为了持续的掠夺而有所节制。把兔子都吃光了的狐狸只有死路一条。精英们只有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持续的稳定。而且,我们对精英的要求还不止于此。精英不能满足于“精明的自私自利”,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精英必须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必须成为受大众尊敬的群体。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如今,在中国,大众对精英没有尊敬和信任,只有猜忌、鄙视、仇恨。只有负责任的精英,才能赢得尊敬。在一个好社会中,精英要有责任,大众要有权利。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并非全然是坏事。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示范压力,没有来自内部的大众的反抗,没有威胁到政治稳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在一个行政支配社会的国度里,在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在精英贪得无厌而又毫无责任感的情况下,走向公平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大众将沦入无底深渊,赢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无法改变。
从制度方面来看,结构性冲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统之中。为此,必须改革政治系统。在权威主义框架内,政治民主化行不通,只能从社会自由化方面寻找改革的突破口。社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开放新闻和结社禁区。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提高社会监督政府的能力,有助于遏制政治腐败,也给大众带来组织起来的机会,提高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遏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因此控制了腐败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经济风险。所以,社会自由化有助于解决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问题。
那么,大众如何组织?又如何规范政府与有组织的大众的关系?我认为,合作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制度框架。
在合作主义框架中,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这些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作为对决策参与权的回报,它们要协助政府实施共同制定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主动约束自己的成员遵守协议。
合作主义分为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两大类。国家合作主义始终与寡头统治联系在一起,其特征是:有限度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民参与,统治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相对不发达的工业经济。在实行国家合作主义的国家里,因政府特许而得以存在的利益组织发挥着政府和经济生产者之间的媒介作用,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限制或控制生产者团体的独立活动。国家合作主义可以加强劳动纪律和管理,同时使相对低效和落后的工业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国际竞争的损害。
社会合作主义是与议会、政党和选举等正式民主制度并存的一种政治过程和制度。它的基础是职能代表制,即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垄断组织被政府允许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这种商讨过程通常是在正式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外,作为对政府给予的这种特权地位的回报,利益组织则保证其成员服从利益组织与政府共同制定的政策条款。与国家合作主义不同,社会合作主义产生于某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利益集团对社会代表性的垄断程度获得了高度发展。这些利益组织不但高度集中,而且有能力对那些违反集体协议条款的成员实行有效的制裁。
为什么中国应该选择合作主义体制?根据在于第一,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第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在近期内建立一种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职能社团结构。第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已经为行政机构与社团的联系建立了制度上的保证。第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不平衡,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国家来说,多元主义体制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