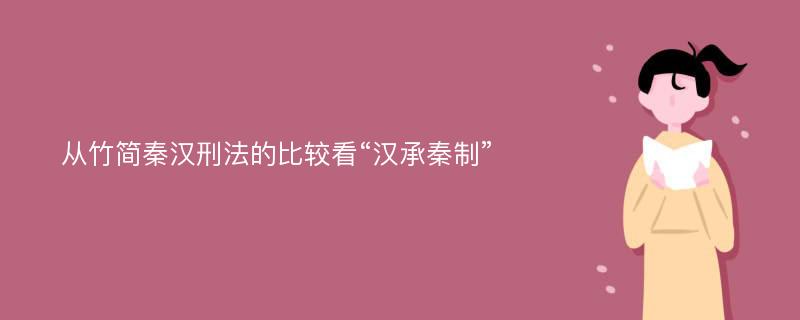
杨玛丽[1]2004年在《从竹简秦汉刑法的比较看“汉承秦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律,尤其是刑法,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重视。关于秦汉法律的关系,从史籍记载看,早有“汉承秦制”之说。但是由于秦律和汉律久已亡佚,因而使人们对汉初法律承袭秦法的具体情况缺乏准确的把握。 近年来大量秦汉法律简的出土弥补了秦汉法制史研究中文献不足的缺憾。本文以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刑法资料为主,结合相关历史文献,通过对比,对汉初刑法承袭秦法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研究。 论文通过对秦与汉初刑法中盗律、贼律、告律、捕律、亡律及有关官吏法的对比,认为汉初刑法不仅在部分律文上直接承袭秦刑法,而且对盗窃、杀人、不孝、诬告及逃亡等犯罪的处罚原则与秦刑法呈现出一致性。 论文通过秦与汉初刑罚的比较,指出秦与汉初基本的刑罚种类相同,主要有:死刑、肉刑与徒刑、迁刑、赎刑、赀(罚金)刑、连坐等。刑罚适用原则上也呈现“汉承秦制”的明显特点。通过秦与汉初刑事责任能力的对比,指出汉初刑法总体上是承袭秦法的,也有局部的改造和发展。 论文在对比的基础上,对“秦亡汉兴”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秦与汉初政治思想的不同是导致“秦亡汉兴”的最主要原因。
张娜[2]2016年在《秦汉法制因革探微》文中研究指明“汉承秦制”从汉代人提出开始,基本成为学界通说。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秦汉出土法律资料的不断发现与公布,为进一步澄清秦汉法制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将秦汉法律进行比较研究也开始为学者提倡与关注。本文主要利用出土秦汉《田律》、《金布律》、《关市律》、《盗律》、《亡律》、《告律》等相关法律资料,对秦汉相关法制的因革进行了细致探究,力图了解秦汉法制因革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与影响。论文主体主要由六章构成,现分述如下。第一章主要对秦汉《田律》因革进行探讨。涉及了生态保护规定,田、道管理制度,名田制度,赋税制度等内容。汉律在这些方面上对秦律都有所继承。同时在田地规划制度上略有调整,道路管理制度有所加强,赋税有一定减轻,体现了汉律的变革。第二章主要从秦汉贾市管理法制与租税制度两方面,对秦汉贾市法制因革进行探讨。通过研究发现汉律在贾市安全制度、交易制度,官府交易制度,租税制度方面基本都继承了秦律,但也有些新发展。反映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态势。第叁章主要对秦汉盗罪法制因革进行探讨。涉及了吏盗,“与盗同法”,主守盗罪,春秋决狱,群盗,盗杀伤人,劫人,盗墓,盗神御物,投书,盗启门户等法制问题。经过研究可知盗罪法制方面,汉律除了继承秦律部分法制外,总体上较秦律更加严厉。说明了汉初政权初建,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仍较混乱,汉政府因此加强了对包括官吏在内的各种盗罪的打击力度。第四章主要对秦汉亡罪法制因革进行探讨。本章将逃亡大致分为嫌犯逃亡,刑徒逃亡,奴婢逃亡,妻亡,普通百姓的邦亡、阑亡、将阳亡等类型,并逐一进行研究。同时就秦汉律对逃亡行为的控制制度也作了分析。研究发现汉律在逃亡法制方面也多有继承秦律,但同时也有变革。汉同秦一样都非常重视人口管理,不过汉初承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流亡现象较为严重。针对这种现状,汉初政府加强了对逃亡者的处罚,同时也鼓励逃亡者“自出”。此外汉初还制定了令无名数者限期登记的新法令。这些都是汉律变革的表现。第五章主要对秦汉告诉法制因革进行探讨。本章从秦汉四种基本告诉形式,自告制度,亲属间告制,告不审罪,诬告罪,以及奖励举告制度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在告诉法制上,汉律因承秦律的同时,在以上各方面基本都有变化之处。如自告制度不断成熟,亲属间告制呈现收缩趋势,诬告罪惩罚加重等。第六章主要对秦汉法制因革的原因与影响,秦汉法制因革与汉初无为而治的关系,秦汉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汉初在继承秦律的大框架下,又不乏渐进式的改革。汉中后期的法制则开始与秦及汉初律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因革特点是由统治思想,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现实,汉代统治者对秦亡教训的总结,秦法制本身的完善,时代变迁等原因造成的。而汉对秦法制的因承也巩固了秦汉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基础地位,并对后世法制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汉初总体上会倾向以无为而治为统治原则,但不能将其绝对化看待,认为汉初在法制上必然是约法省禁的,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出土法律文献可以印证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澄清传世文献中的不明之处,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相互补充。因此在法制史研究中,二者要兼顾,不能偏废。
叶露[3]2016年在《官法权衡:秦汉惩治官吏犯罪异同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秦汉之别是研究秦汉史方向一个崭新的视角,尤其从官吏犯罪的角度去体现两朝政治文化的区别。本文主要将官吏犯罪问题分为政治、行政和经济(以官吏盗罪问题为例)叁大类,将其惩罚结果做一比较,在比较惩治犯罪异同的同时,还加入了官吏特权的内容进行比较。通过对秦汉惩治官吏犯罪异同的比较,可以看出,秦汉政府都严厉打击官吏犯罪,但相比秦代的依律执行,汉代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最终结果影响很大。具体表现为:在政治犯罪的处罚上,秦依法治罪,汉同罪异罚;在行政犯罪的处罚上,秦律重数,汉律轻数,秦律重"法理",汉律重"情理";在经济犯罪的处罚上,秦律重于汉律。另外,秦汉官贵都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特权,而汉代官贵所获得的政府优待、特权地位,相比秦代轻滥。总之,秦重法治,汉重官治。本文以秦汉简牍和传世文献为研究主体,并搜集散见在其他学者的着作中的有关材料,分类对比,分别概括总结,得以从惩治官吏犯罪的不同这一角度,论证秦汉政治文化之别。
赵婷[4]2016年在《历代文学中萧何形象阐释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萧何是西汉一代开国贤相,他拥护刘邦起义,在楚汉战争中振抚巴、蜀、关中,保证战争人员和物资供应。同时,萧何眼光独到,为汉朝寻找到了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韩信。他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他的功劳仍然位冠群臣。汉朝建立之后,萧何仍然兢兢业业,更立社稷,制定律令,使战乱中的国家逐步走向正轨。萧何形象首先出现在《史记》中,随着《史记》的不断传播和接受,萧何形象的接受类型也日渐丰富和立体。本文以历代文学作品为载体,通过对诗歌、戏剧、变文、话本、小说等文学题材中萧何形象阐释和接受类型进行分析,研究萧何形象的阐释和接受在不同朝代和不同文学样式中的特点。共分为叁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研究史籍中的萧何形象。《史记》中关于萧何形象的记载是后世文学作品中萧何形象阐释和接受的源头。《史记》用精炼的语言,刻画了功勋卓着、眼光独到的开国贤相萧何的形象。同时,司马迁又秉持着“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录了汉高祖对功臣萧何既信任倚重又疑心提防,突出了两人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塑造了一个战战兢兢,明哲保身的萧何形象。《汉书》记载西汉初期的历史时,对《史记》多有承袭,是对《史记》的第一次深层次地接受。《汉书》对萧何的记载较《史记》更为详实,在《史记》的基础上丰富了萧何施行仁政的形象,拓展了“治世谋臣”的新的形象接受类型。第二章为第二部分,对历代作品中萧何形象阐释与接受状况进行总体概述,通过纵向分析与比较,概括出萧何形象在不同朝代中的接受特点和异同。唐代以前描写萧何形象的文学作品很少,只有4首诗歌提到了萧何事迹,这些诗歌基本上还是围绕史籍中的萧何形象进行阐释。汉朝时就出现了颂扬萧何制定律令的民歌。西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中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萧何的诸多功勋,塑造了一个功臣形象。继陆机之后做出突破的是隋朝李密,他慨叹于汉初功臣能够顺应时势,建功立业,在诗歌中塑造了一个乘势而为的萧何形象。唐代和宋代是萧何形象接受的高峰期,其间涌现出了大量描写萧何的作品。唐代作品中塑造的萧何形象类型增加至10类,并且对类型的阐释也更加丰富。唐代文人对萧何“一代贤臣”的形象接受程度最广,出现了接受主题,同时出现了“否定营建未央宫”“功不如四皓”等反面形象。宋代文学注重议论,在萧何形象的阐释和接受中,萧何与韩信的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形成了“举荐贤才”与“刻薄寡恩”并存的形象。元明清时期,对萧何形象的描写有所减少。在元明清文学中,萧何的负面形象被刻画得更加具体。元代出现了“杀戮功臣”“懦弱屈从”两种新的负面形象类型,明代文学中出现了两条关于“刀笔吏”形象的记载,认为萧何出身刀笔吏,无法与儒生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文人对萧何“转运粮饷”的形象接受程度非常广,形成了突出而鲜明的接受主题。第叁、第四两章为第叁部分,运用文体学研究方法,对诗歌、变文、戏剧、话本、小说等不同文学样式中的萧何形象进行研究。在诗歌这一题材中,萧何形象的最广泛的接受主题是“开国名相”,其次是“慧眼识人”。在诗歌中出现了正反两方面的萧何形象,但正面形象的接受程度要远超过负面形象。在变文中描写萧何形象的有唐代变文一部:《捉季布传文一卷》。戏曲四部:《追韩信》《千金记》《圯桥进履》《赚蒯通》等。变文和戏剧由于文体特点的限制,塑造出的萧何形象较为单一,或者举荐贤才,或者匡扶汉室,或者杀戮功臣,一部作品塑造的形象只专注于一个方面,人物形象不够饱满。而《西汉演义》中塑造了一个既功勋卓着,举贤任能,但同时又薄情寡恩,杀戮功臣的萧何形象,将正反两方面形象融为一体,充满张力。
参考文献:
[1]. 从竹简秦汉刑法的比较看“汉承秦制”[D]. 杨玛丽. 西北大学. 2004
[2]. 秦汉法制因革探微[D]. 张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3]. 官法权衡:秦汉惩治官吏犯罪异同的研究[D]. 叶露. 浙江大学. 2016
[4]. 历代文学中萧何形象阐释与接受研究[D]. 赵婷. 陕西理工学院.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