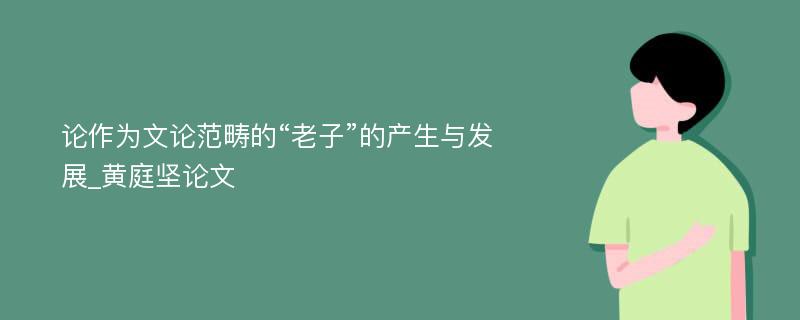
论“老”作为文论范畴的发生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范畴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筋骨,其出现和发展是为了阐释、总结和指导不断变化的文学活动,具有“系乎时序”的特点。作为文论范畴的“老”,出现于唐、盛行于宋而深化于明清,其发展脉络构成了批评史研究的一条线索。
“老”,最早见于殷代卜辞,本为老年,和“孝”、“长”、“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注:《说文解字》:“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凡老之属皆属老。”“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考,老也,从老省”。“长,久远也。从兀,从匕。”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老、考本为一字,后分为二,孝字为老人扶子或子以头承老人之手而行走状,“长”像老人披长发拄杖而行状。孝字后来引申为父考之意,长字引申出长官等意,孝字引申出孝顺父母,成为美德的通称,发展为孝道的观念。《乡饮酒义》:“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很好地概括了它们的关系。)。由于“孝”是中国第一位的伦理道德观念,从周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开始强调对长辈的尊重,“老”进入伦理层面,并具有了哲学意义,由《诗经》中的“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发展到了“上老老而民兴孝”(《礼记大学》)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老人历事多,经验足,因而“老”又引申为做事成熟老练。中国古代文论受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特点的影响,“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辞》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注: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937年8月第1卷第4期。《谈艺录》补订本中提到此处:“余尝作文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宜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古代文论这种人、文合一的特点从理论上为“老”进入批评领域提供了依据,文学自身的发展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一
“老”作为文论范畴在批评史上的正式出现,始于杜甫。他在《戏为六绝句》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指出:“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敬赠郑谏议十韵》;“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奉汉中王手札》;“枚乘文章老,河间礼乐存”。显然,“老”是杜甫对文学某一特点的理论概括。本文首先探讨的问题是,“老”作为文论范畴为什么始于唐,在这个时期出现具有何种意义。
由质趋文,是隋唐以前诗歌发展的基本轨迹。汉诗浑然天成,文中有质,质中有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解放,自我与审美意识觉醒,原本混沌一体的心物关系发生变化,自然与内心作为审美对象被发现,文学的独立性与价值得以确立,抒情性得到加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有意识地追求辞藻之美。虽瞻而不俳,华而不弱,然文与质已经相离。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就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特点的总结。建安之后,诗歌历经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新体诗和宫体诗等诸多变化,逐渐摆脱政治、道德观念束缚,抒发情感自由无忌,追求辞藻声色之美。这一发展趋势至晋宋,诗歌己文盛质衰,至齐梁则达到极致,文盛质灭,“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啐语》)。仅就齐梁诗歌而言,它纠正晋宋诗酷不入情的弊病,强调吟咏性情,创新艺术形式与技巧,是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宫体诗轻艳浮靡,被视为亡国之音,使它长期得不到准确评价。杜甫以“老”作评的庾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黜雕尚朴,“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庾开府集笺注》)。
庾信“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同上),在文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才高学博,少年得志,与其父庾肩吾俱为萧纲文学团体的核心成员,参与和改变了当时的文学风尚(注:《周书·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为左卫率;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侯景之乱打破了梁朝的太平景象,出使被羁、转为仕周、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使庾信由“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结客少年场行》)沦为“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拟连珠》二十二)。变故让庾信失去的不仅是亲人,还有玄学信仰和高门世族的文化优越感。他从变故中得到的也不仅是痛苦、尴尬与失落,还有反思求索、融贯南北文化、超越自我的机会。庾信最终超越了个人的不幸,以博大宽厚的胸怀,运用萧梁时期积累的艺术技巧,继承魏晋言志抒怀的传统,接受北周素朴务实文化的影响,“穷南北之胜”(倪璠《庾子山集注·注释庾集题辞》),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体,以丽语写悲哀,创作出了情感深沉诚挚、境界辽阔悲远的作品。和曹植相比,同是文质兼被,曹诗爽健明朗,感情强烈,气势与辞采双胜,是意气风发者的奔放之词,庾信作品则苍凉雄丽,深沉内敛,情性与声色合一,是饱经沧桑者“无穷孤愤,倾吐而出,工拙都忘”(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的心声写照。对于庾信后期作品这种苍远浑厚、波澜纵横的特点,杜甫一言以蔽之曰“老成”(注:对于杜甫关于“庾信文章老更成”之说,后人基本赞同,但也有例外。金王若虚《滹南集》卷三四就认为:“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称如此,且讥诮嗤点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
“老”体现的是庾信晚期作品对齐梁绮靡诗风的纠正与突破,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在杜甫之前,评者对庾信是毁多誉少。隋末大儒王通《中说·事君篇》认为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初唐几部关涉庾信传记的史书,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都对庾信持否定态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甚至直斥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对于这种现象,明代张溥认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实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庾子山集题辞》)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南朝浮艳文风积弊过深,深受其影响的隋与初唐诗歌要健康发展,批判不能不矫枉过正。隋文帝力主“屏黜轻浮,遏止华伪”(《隋书·李谔传》),唐太宗反对“无益劝诫”的“浮华”文体(吴兢《贞观政要》卷七),陈子昂高标风骨兴寄,都有纠偏救弊的目的。庾信历来被目为六朝诗歌的代表,受到批判在所难免。只有到了盛唐,诗歌完全摆脱绮靡诗风的不良影响,在扬弃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形成兴象玲珑、风神超迈的特点之后,六朝诗歌才可能得到客观评价,庾信的价值也才可能受到重视。
杜甫能够突出庾信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敏锐地捕捉到其作品“老”的特点,绝非偶然。杜甫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兴趣,“最善评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而且,在六朝众多诗人中,无论是国破家亡的经历,饱受战乱之苦与生活艰辛的身世,还是以丽语写悲哀等创作特点,庾信都与之最为接近。杜甫创作还直接受到庾信影响。黄庭坚:“杜之诗法出于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陈师道《后山诗话》引)冯班亦云:“庾子山诗,太白得其清新,杜公得其纵横。”(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一引)。
虽然如此,“老”作为文论范畴在唐代还处在萌芽阶段,文献中只有零星提及。如王仲舒《崔处士集序》:“帝唐绥之士,年未壮,其文老成者,曰博陵崔秀文。峻亮而坚,刚贞而和,止立而毅,其行也不迩声利,其文也文质相制,才气相发,于古人立意中,往往振起风雅。”(《全唐文》卷五四五)“老”苍凉悲远,虽有内在的气势与内敛的激情,与盛唐热烈奔放、超凡脱俗的时代精神还是不相适宜的。盛唐诗歌奇情新拔,天然壮丽,“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老健”仅是众体之一种。盛唐之后社会衰败,诗人心绪彷徨,“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张扬创作个性,把诗歌的触角伸向包括心灵在内的各个方面,但诗歌总的趋势是“稍厌精华,渐趋淡净”(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工于形似,平淡内敛、靖雅婉丽。其间虽也出现了“老”的作品,但不成气候,不是主流。
二
宋金元时期为“老”的发展阶段,明清为成熟阶段。由于“老”在不同时期发展状况不同,彼此又存在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因此这部分先叙“老”之纵向发展,然后就其中涉及到的问题集中阐释。
“老”作为文论范畴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表现之一是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有力地总结了当时的创作活动(注:“老”在宋代及以后还广泛运用于书法、绘画等艺术批评领域。书法方面如米芾《书史》:“濮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一样连成卷,字老而逸,暮年书也”;王世贞指出:“坡笔以老取妍,谷笔以妍取老,虽侧卧小异,其品格固已相当。”(《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六)绘画方面如韩拙《山水纯全集》:“苟从巧密而缠缚,诈伪老笔,本非自然,此谓论笔墨格法气韵之病”。)。表现之二是作为生命力很强的范畴,在发展中不断与其他字组合,构成新的词汇。如“老笔”、“格老”、“老健”、“老苍”、“老洁”、“老辣”、“老重”、“清老”、“老淡”、“坚老”、“稳老”等,扩大了外延和内涵。“老”在宋代的发展也有其必然性。它和宋诗对理趣与平淡美的追求,陶渊明在宋代文名达到极盛等现象同步,都是共同的时代精神和文学风尚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宋代社会动荡,诗人趋于淡泊自守,文化上沿袭中晚唐,思想观念复杂多元。就诗歌自身而言,经过汉魏六朝长期的发展和唐代的鼎盛,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主情转向主意,由重写境转向重写心,由浪漫理想转为贴近日常生活,由崇尚风骨兴寄转而追求理趣、平淡。在这种追求与创作中,宋诗逐渐形成了以筋骨思理见长的特点,“淡”受到空前地崇尚。诗作开千古平淡之宗的陶渊明在唐代还颇受非议,李白有“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之句,杜甫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之三)之讥,在宋代则受到梅尧臣、苏轼等人的极力推崇,文名盛极。“老”和“淡”有颇多关联与相似之处,如苏轼《与二郎侄书》:“凡文字,少小时须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苏轼佚文汇编》卷四)此时也受到宋人的关注和自觉追求。如僧人惠洪:“句法欲者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冷斋夜话》卷四),徐绩:“子美骨格老,太白文采奇”(《节孝先生文集》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诗辨》),后人多以苏、黄为宋诗代表。苏诗飞机生动,恣逸富健,有老健之气而少熔炼之工、浑厚之致,在“老”的发展中不如黄庭坚突出。黄庭坚在诗文中屡屡提及“老”:
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忆邢停夫》)
儿中兀老苍,趣造甚奇异。《次韵答邢停夫》)
谁能与作赤挽板,老笔犹堪寿百年。(《题刘氏所藏展于虔感应观音二首》)
二三子舍幼志,然后能近老成人,力学然后切问,问学之功有加,然后乐闻过,然后执书册而见古人。(《洪氏四甥字序》)
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答洪驹父书》)
对于黄诗,宋人也已开始以“老”作评。如普闻《诗论》:“鲁直长于律诗,老健超迈”。不过和“淡”在宋代已有成热理论相比,“老”此时仍处于发展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它基本还停留于作家作品的批评,细碎表面,没有成型稳定的理论。
金代社会动荡,历时也短,“老”在此期间的发展不甚明显,元代相对突出一些。这主要体现在方回的批评之中。以“老”评诗,尤其是以“老”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可以看作方回《瀛奎律髓》的一个特点。如卷十二评陈师道《秋怀示黄预》“冥冥尘外趣,稍稍眼中稀”两句“非老笔不能(注:方回评选,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评黄庭坚《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更唤雨鸠归”句,“后学却合点检,必老成而后用此例可也”(卷十七)。当然方回也并未局限于江西诗派,如评刘禹锡“诗老辣,不可以妆点并观”(卷四七《题招隐寺》评)。对于方回的批评,后人尤其是清人持有异议,此处从略,留于后面详解。
“老”作为文论范畴在明代进入了成熟时期,出现了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表现之一是杨慎从风格理论对杜甫“老成”说进行阐释。他在《升庵诗话》卷九中指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在此之前,对“老成”也有研究,如《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二认为:“老成者,以年则老,以德则成也。文章而老更成,则练历之多,为无敌矣。故公诗又曰‘波澜独老成’也。”相较而言,杨慎之说更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更大。表现之二是出现了蕴涵丰富的“老境”概念。王世贞《艺苑卮言》:“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七)虽然在此之前它已在历代诗歌中多次出现,但直到明代才得以理论提升。
在清代“老”得到进一步系统和深化。以往有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得到了理论阐释,变得具体、明晰、稳定。如《御选唐宋诗醇》卷十四评杜甫《病马》:“直书见意,无复营构,此为老境”。纪昀亦加以阐释:“浅语却极自然,熟语却不陈腐,此为老境。”(《瀛奎律髓》汇评本卷二一《雪作》评)此外,薛雪《一瓢诗话》:“诗文要通体稳称,乃为老到”。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一“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纪昀:“似乎易而极深稳,斯为老笔。”(汇评本卷二十《感梅忆王立之》)同时,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的非常具有概括力的概念,如“浑老”。“浑老”是冲淡中有雄浑,雄浑中有冲淡,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此概念在清代运用较广,如纪昀评张籍《西楼望月》“意境甚别,而未能浑老深厚”(汇评本卷二二)等。
上述两种进步固然重要,有意识地从“老”这个角度来分析文学现象,评价唐宋诗之差异,才是“老”在清代最大的发展。这一富有价值的工作是由纪昀来完成的。连同前面未曾阐释的问题,集中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老”与作者年龄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出现最早,可以说杜甫提出“老成”说就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是老而更成,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积累越多作品也就越成熟。如宋孙奕《示儿编》卷十有“老而诗工”一条(注:“老而诗工”:“客有曰:诗人之工于诗,初不必以少壮、老成较优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后诗,涪翁到黔南后诗,比兴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伟,大篇豪而古。如少陵到夔州诗,昌黎在潮阳后诗,愈见光焰也。不然少游何以谓元和圣德诗于韩文为下,与《淮西碑》如出两手,盖其少作也。”);刘克庄《赵孟侒诗题跋》:“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清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一也认为:“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意见。如清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六:“观余少时所作及今年诸诗,少时专力致工,今不及也。凡所谓文章老成者,格局或老,才思定减。杜子美则不然,子美本无才思故也。学问则老定胜少,少时可笑处殊多。”王说是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而言,纪昀则是从客观来讲,“老手亦有变而颓唐者”(汇评本卷二《晚出左掖》评),认为“老”与年龄没有必然联系,作品不一定越老越佳。
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对杜甫不同时期作品的评价上。将作品特点和杜甫的年龄阅历联系起来的做法始于黄庭坚。他在《与王复观》第一书中提出:“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律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方回发扬了这一观点,《瀛奎律髓》卷十评价杜甫《春远》:“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在卷十一《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中又指出:“老杜在长安,犹是中年,其诗大概富丽,至晚年则尤高古奇瘦也。”这种观点在杜甫研究中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学者如朱熹、胡应麟、田雯、袁枚等持有异议,认为杜甫晚年诗并不一定好,朱熹说:“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朱子语类》卷一四○)胡应麟则认为:“老杜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诗薮》续编卷下)。纪昀对杜甫中年时期的创作最为肯定和赞赏。在评《登兖州城楼》时认为:“此工部少年之作,句句谨严。中年以后,神明变化,不可方物矣。”(汇评本卷一)针对方回“愈老愈剥落”和晚年诗“高古奇瘦”的说法,纪昀指出“杜诗佳处卷卷有之,若综其大凡,则晚岁语多颓唐,精华自在中年耳”;“中年不止富丽,晚年亦不以奇瘦为高,此论皆似高而不确”。对于他反对晚年诗更佳的理由,纪昀在《多病执热怀李尚书》的点评中解释:“此杜公颓唐之尤者,以为老境,则失之”(汇评本卷十一),评《七言》“(方回)所选少陵七言六首,多颓唐之作。盖宋人以此种为老境耳”(汇评本卷十)。在这个问题上纪昀没有具体展开,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纪昀从“老境”与颓唐的关系等入手,突破将“老”和年龄联系的局限,是有一定价值的。
二是“老”与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一方面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体现出了对“老”自觉的追求,文献中亦不乏称宋诗“老”的记载,一方面当代一些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就宋诗对老境美的追求予以彰显,言之凿凿。实际上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一则理论与创作实际之间存在差距,宋人追求“老”与是否具有是两回事;二则随着诗歌认识的逐渐深入,后世可能发展出相左意见。仅以一个时期的文献定论而忽视其他,必然易致粗疏片面之失。
宋诗以杜为宗。杜诗体调正而正中有变,规模大且大而能化,“变则标奇越险,不主故常;化则神动天随,从心所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是以“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宋人另辟蹊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沧浪诗话·诗辨》)。这样在创作中就必然面临着法度与自由关系的处理问题。苏轼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书吴道子画后》),黄庭坚持同样态度,但在取向与作法上两人存在不同。“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黄庭坚《赠商子勉四首》),陶诗古朴天然难以力致,杜诗却有规矩可循。苏轼喜陶而黄庭坚宗杜,在如何由法度而自由的问题上苏轼还比较空泛,黄庭坚考虑的就比较具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等,就是他对布局、句法、用典等提出的要求,是他“领略古法生新奇”(《次韵子瞻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理论的具体化。黄庭坚的诗歌也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风格,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王侯”,打破常规,出以拗峭,读之铿锵有力,有兀傲奇恣之美。遗憾的是,江西后人学黄多注意具体法度而忽略了其诗学中重“活”的一面。黄庭坚诗歌尚因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雄健太过而生涩险怪,其末流后学生硬板刻的弊端更为突出。吕本中讲“活法”,注重流美圆转的风格,试图救弊。但从他“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等观点来看,他还是侧重在法度方面。方回为宋之遗老,江西诗派后殿,他为江西诗派开出的药方还是法度,意图通过句眼、响字等创作手段,达到“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的效果。后者是他总结出的杜诗的特点,认为“为此等诗者,非真积力久不能到野,学诗者以此为准”(汇评本卷二三《狂夫》评)。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陆机《文赋》)。唐诗怀珠玉而辉媚,宋诗则舍辉媚而求珠玉。后者长处在剥落皮毛见精髓,短处则在变而不正、大而不化,珠玉不得转成粗野死寂。而粗野就是失去法度的老健,死寂即平淡丧失生气与活力。
对此,明人已经提出批评。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指出“宋人似苍老而疏卤”(《大复集》卷三二)。清人的研究更为深入。如纪昀一方面肯定江西诗派一些作品具有“老”的特点,如评吕居仁《夜坐》“瘦硬而浑老,‘江西’诗之最佳者”(汇评本卷十五),同时又对宋诗整体是否具有“老”的特点提出了反对意见。《瀛奎律髓刊误序》:“虚谷乃以生硬为高格,以枯槁为老境,以鄙俚粗率为雅音”。评梅圣俞《闲居》:“以枯寂为平淡,以琐屑为清新,以楂牙为老健,此虚谷一生病根”(汇评本卷二三)。这与由其任总编纂官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方回《瀛奎律髓》的评价——“其说以生硬为健笔,以粗豪为老境,以炼字为句眼,颇不谐于中声”相为呼应。对于方回看重的响字、句眼,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序》中指出:“虚谷主响之说,未尝不是,然究是末路工夫,酝酿深厚,而性情真至,兴象玲珑,则自然涌出,有不求响而自响者。”方回的观点对纠正江西诗派末流的弊病虽不无益处,但失于细碎皮相,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纪昀此说可谓击中要害。
方回处于宋末元初,要解决的是江西诗派如何发展的问题。纪昀则是在清乾嘉时期,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总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诗歌的发展认识更为全面,视角更为开阔,所受的局限性也更小,对于宋诗的批评较之方回更为公允客观。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纪昀以宗唐存宋为立场,在评苏轼《答任师中次韵》一诗时指出:“语亦清健,或以为盛唐极则,作家老境,则非也”(注:曾枣庄主编《苏诗匯评》卷八,第262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直接将代表了最高水准的“盛唐极则”和“作家老境”相提并论,因此在评论宋诗时有以唐诗为准绳的倾向。至于现代学者方孝岳认为,“到了纪昀自己作这个《刊误》,就大事吹求,简直把他骂得无地自容,处处皆含成见;他所刊误的,自然也有些地方可以补救方回的,但实在不及方回之精辟独到”(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0页。),这可视为一家之言,在学术研究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此外,前面内容已清楚地表明,任何朝代都有具备“老”的特点的作品,并非宋代一朝的专利。诚如钱钟书《谈艺录》所说;“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因此在理解其“一生之中,少年力气发扬,遂为唐诗,晚节思虑深远,乃染宋调”时,不可局限于表面之意。若只将“老”与宋诗联系起来,那就与作者的本意背道而驰了。
三
在简述了“老”作为文论范畴的发生与发展之后,结合各个时代的创作与观点,大概可以总结出“老”的基本内涵。
“老”是一种平和自然、气势纵横的风格。杨慎以“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阐释“老成”,方东树以“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释老,都抓住了“老”中和多种风格的特点,但也都忽视了“凌云健笔意纵横”,没有认识到气势与活力是“老”成其为“老”的关键。苍凉悲远是“老”,雄浑冲淡是“老”,平易自然也是“老”。“老”并无定式,关键在于平和中有气势,有力度。“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之所荡。气才绝,即腐败恶臭不可近,诗文亦然。”(方东树《昭昧詹言》)。老和死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生气。没有了奔放的气势,“老”就是死寂,就是枯槁。气势纵横而不出以平和自然,是雄健,是粗豪,但不会是“老”。所以“老”又可以看作是平和自然与气势奔放之间的平衡状态。就像“清”易“薄”、“艳”易“俗”,“老”一旦在“平和”与“气势”之间失去平衡,就转为“颓唐”、“老气横秋”,容易“浊”、“鄙”、“浅”、“率”。当然这些并非“老”自身应有之义。
“老”是一种直抒见意、不加雕琢而深稳妥帖的创作特点。纪昀评杜甫《中夜》:“一气写出,不雕不琢,而自然老辣。”(汇评本卷十五)杜甫《九日》:“一气呵成,毫无雕饰,自是老手。”(汇评本卷十六)具体来说,就是创作中要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用乎其所不得不用,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做到恰到好处。《昭昧詹言》卷五:“凡前面正面后面,按部就班,无一乱者,所以为老成深重。”虽然仅就结构布局而言,诗歌创作的其他方面如字词使用、命意选题等等,无不如此。作为创作特点的“老”,不仅要保持法度与自由的平衡关系,还要注意构成诗歌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做到“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字词句粗疏浅易不是“老”,佳句层出而语脉横隔不是“老”,太费安排不是“老”,“波澜阔而句律疏”(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自然也不是“老”。
“老”还是作家作品体现出的不工自工、至法无法的水平和境界。创作“太抵始于法,而终于以无法为法;始于用巧,而终于以不巧为巧”(纪昀《唐人试律说序》,镜烟堂十种本)。作家在熟练掌握规划、技巧之后,在创作上就有可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作品不烦绳削而自合,无用法之迹,而法自行乎其中。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并非只存在诗歌批评领域。石涛就说过:“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石涛画语录》)。“看似容易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要达到“老”的水平和境界,作家必须苦习“熔炼”功。一方面作者自身要炼气炼神。纪昀《唐人试律说序》:“气不炼,则雕镂工丽,仅为土偶之衣冠;神不炼,则意言并尽,兴象不远,虽不失尺寸,犹凡笔也。”炼气炼神就是要寝食古人,培养根柢,熔炼诗材,同时陶熔意境,炼气归神。另一方面就是创作中要炼字炼句炼意。范温:“世俗所谓东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诗眼》)。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不同,实际上炼气与炼神、自我修炼与炼字炼句都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其结果都果得神明变化、自在流行之妙。
界定了基本内涵,“老”与其他范畴自然也就区别开了。以联系较密的“淡”为例。“淡”与“老”有交叉之处,都平和不张扬,都需要一定锻炼方能具备。但是二者又不同,“淡”强调的是平和下有厚度,有隽永的韵味,“老”强调的则是平和下有省略,有奔放的气势和强大的力量。“淡”有一种理想和清高的色彩在内,可能会被视为审美理想来追求,“老”则直接融入在现实与创作之中,是否被作为审美理想都不影响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目标,其涵盖面和包容性都远远大于前者。
令人遗憾的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老”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中国的辞典中差不多已经找不到“浑老”、“老笔”、“老境”等词语了。而现实是,“老”作为一种风格,一种境界,仍大量存在于文学与生活之中,比如老舍的作品。因此,加强对“老”这一类文论范畴的研究,并将其和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
标签:黄庭坚论文; 诗歌论文; 诗薮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杜甫论文; 瀛奎律髓论文; 昭昧詹言论文; 纪晓岚论文; 庾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