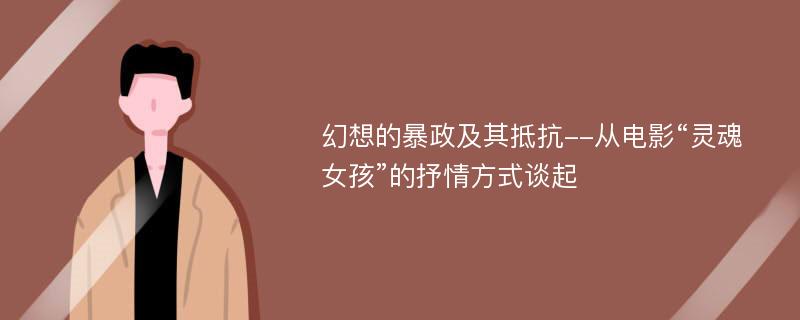
幻象的暴虐及其抵抗——从电影《香魂女》的抒情方式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象论文,抒情论文,方式论文,电影论文,香魂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讨论是很有影响的。阿多诺把现代艺术的风格概括为抒情化。他认为,抒情性的文学艺术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现象,是对普遍异化状态的一种主体性的反抗。现代艺术的主体化特征,决定了它在现实文化成规面前的软弱无力。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来说,阿多诺的结论显然无法包容两个基本的文化事实:(1)中国的抒情艺术传统源远流长,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的特有现象;(2)当代中国艺术的抒情方式不是主体性情感的简单抒发,而是对象性存在的诗意升华,它的基本目的不是情感的真实性,而是灵魂拯救的可能性。因此,研究和说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表征机制及其特殊性,并为其作出准确的理论定位,就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王国维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努力,他提出的“境界说”可以看作是敏感的美学对与现代化过程相伴生的异化现象的理论回应。王国维激赏“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境界,事实上是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崩溃的一种美学表达。在“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现实情境中,王国维找不到重建文化平衡的支点以及出路。按照叔本华和王国维的理论,在人欲横流的历史情境中,内收欲望似乎是唯一可能的抵抗。这其实只是从受难者的立场来看问题,如果我们从对象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也就可以看到另外的希望和可能性。
拉康说过,爱情是正在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标志。两个人的世界也可以是一个宇宙,它的丰富多彩根源于人的欲望与欲望的对象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欲望的表达是需要媒介的,这种媒介又必然地受到文化机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爱情故事可以成为个人欲望、现实关系和文化机制相叠合的凝结点,对它的分析也就可以达到对现实的一种剖析。
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是欲望实现的外在尺度。在现代化社会,财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主要标志。劳动把个体的欲望对象化为物质性的财富,欲望的这种转换一方面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并且进一步唤醒了主体中潜在的欲望和需要;另一方面,这种“解放”往往反而使人成为自己的囚徒,从而包含着十分浓郁的悲剧意味。在主体的需要方面,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情欲上升为主导性的心理动因。作为欲望得以对象化的一种方式,情欲也有它自己的逻辑和轨道,不能用劳动的方式和原则来代替。可悲的是,许多幼稚的人们用物质财富的规律和逻辑来处理爱情以及情欲的对象化,把不该混淆的东西混淆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以及欲望的交流就重新沉入到历史的深渊中去。在历史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盲目性的历史条件下,责任感和良知怎样才能获得它的现实基础呢?这是现实向理论提出的严峻问题。
先看一个具体的例证。在电影《香魂女》中,环环的悲剧性命运浸染着非常浓重的文化阴影。表面上看,环环的悲剧起因于一群孩子的天真游戏,这说起来很荒唐,但却是“现实”的事实。儿童的游戏以能指和所指的互不关联为前提,虽然游戏本身是对成人世界的摹仿,但是欲望的混沌和朦胧状态保证着这种摹仿的天真和完整。不幸的是,天真的游戏在无意之中却囚住了处于观看位置的欲望主体。傻墩子被孩子们的游戏所吸引,并产生了摹仿的要求。外在的形象把墩子内在世界中弥散着的、混沌状态的欲望具象化了。欲望一旦聚焦在一个具体的对象上,不仅会立即产生把欲望加以实现的要求,而且产生出特有的激情和力量。在这里,主体和对象的关系不仅是颠倒的和错位的,而且还是单向度的。墩子深陷在幼稚无能的状态之中,无法把想象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区别开来,即固执地要求把想象性的东西对象化和现实化。这显然是一种自恋性的关系,欲望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很容易由于无法交流而转化为伤害性和破坏性的关系。环环作为一个主体,她的主体世界是丰富的,而且有能力把自己的欲望对象化从而建立起与别人的深刻交流关系。现实方面环环却处在拉康称之为“镜象阶段”的状态中,由于她在物质财富方面的软弱无力从而深陷在历史难题的沼泽之中。
自恋是一种特殊的人格,它是个体无法在日常生活轨道中把欲望加以对象化的结果。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之间的断裂,极易把欲望反弹到破坏性表达的轨道上去。在电影《香魂女》中,墩子的激情从一开始就是盲目的和非交流性的。这种激情被孩子们的游戏所点燃,在环环的具体形象上聚焦,并且通过社会性仪式(娶媳妇)而得到实现。社会性仪式用强制性力量把两个不同的主体捆在一起,但是想象中的交流并没有实现。墩子的欲望表达碰到了一种如水般平静的拒绝,这是人在被剥夺了一切反抗权力之后的最后的抵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有力的抵抗。环环没有踏上用破坏和反抗来对抗不合理现实的轨道,她把欲望的投射,指向爱情世界之外的其他领域。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不仅他人的欲望是一种神秘的异在性力量,而且自己的欲望也往往是难以理解和控制的,欲望的对象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其他个体的伤害。叔本华仅仅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认为,只有欲望的死亡,才能解决现实的冲突。其实,在实践性的关系中,欲望的表达始终应该是丰富的和双向的,只是在物质主义原则支配一切的文化中,才能通过排斥、擦掉异向性来强化欲望投射的一维性关系。这种一维性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就是把欲望的投射对象看作是没有欲望的“物”。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在他的重要著作《暴力与献祭》中指出,人皆有欲望,但永远无法如愿以偿。人总是羡慕别人,对别人进行模仿。对欲望的模仿是人类一切冲突的根源;有欲望就有暴力,因而所有类型的文化都是由欲望和模仿和暴力制造的牺牲品而得以巩固。社会需要它的成员为之牺牲,因而就有了宗教的自愿献身精神。只是因为有了宗教的献祭与牺牲,社会才得以维持和巩固①。在电影《香魂女》中,香二嫂借助于物质财富的力量来解决人自身的现实难题,用外在的仪式来缝合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之间背道而驰的距离。为此,美丽的环环被奉献到傻墩子成年礼的祭坛上。当人的丰富世界枯萎为简单的物质性力量,而物质性力量又成为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原则和尺度时,人的世界也就衰败了。对于受压迫的弱小者来说,在物质财富和文化机制都成为异在性力量而且又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抵抗的依托似乎只能来自于人的内在世界。
在远古神话时代的祭神仪式中,巨大的凝聚力来自文化符号在能指方面的无限性和在意义方面的绝对性。这种无限性和权威性把人们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分离开来,同时又把人们的欲望投射对象凝聚在一个无限远的共同点上,以此来实现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世俗性仪式中,仪式的基本功能不是日常生活条件的疏离、颠倒和隔绝,而是日常生活规则的神圣化,它强化着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在这里,仪式的强制性力量也就变成了对受压迫者的暴力了。在《香魂女》中,孩子们对成人世界的摹仿是一种疏离性的摹仿,并不要求现实化,然而墩子对儿童游戏的摹伤则强烈地要求具体实现。幻想在文化中获得了它的形式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幻象也就获得了向现实转化的力量。当一种幻象以交流方面的彻底绝望为动力时,欲望的奔突也就必然夹着暴虐和恐怖。“……娶媳妇、过日子、点灯、说话、吹灯、睡觉……”在婚礼的仪式上,墩子念着孩子们做游戏的顺口溜,手中高举起环环的内衣向喝喜酒的人们炫耀,从人们普遍的震惊和同情的表情中,我们看到了某种苍白和不合理的东西。
同情和悲哀是大浩劫已经发生的标志。然而,在现实中,对受难者的同情和悲悯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现实关系的结构中,环环被一种神圣的力量隔离开来,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的权力和可能性。在自己的欲望表达渠道被堵塞之后,环环似乎只剩下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在现实和文化提供的轨道上完成主体的再生产,或者在与现实的冲突中自我撕裂。
在影片中,环环走上了与这两条道路都不相同的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背靠着香魂淀的静谧,环环用眼泪为自己举行了新生的仪式。在蒙受了剥夺、背叛、肉体的打击和精神上绝望的痛苦之后,环环可贵地保持着自己的完整性,向外投射的欲望转化为内在而宁静的灵魂之光,使她的形象渗透出一种特有的气韵。
近景。灰冷的月光。环环走下台阶。镜头凝固不动,似乎传达出现实的冷酷和文化的压抑。我们先看到环环的腿、腰,最后才是那垂着黑昏眼睑的大眼睛。影象是破碎的。中景。环环转过身去,攀上到屋顶去的楼梯,镜头随之移动,环环的背影完整而有力。这一组转过身去的影象后来又重复了一次,那是环环昔日的恋人金海从省城里回来的时候。白天,色彩明亮而丰富。环环正面对着香魂淀绣花(一种审美乌托邦投射?)看见金海回来并拿出礼物,环环进屋拿出一个红脸盆,走下台阶。影像仍然被分割。转过身去,攀上楼梯,环环的身体获得了自己的完整性。这两组镜头除了色彩上的某种相反以外,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第二次转过身去完全是环环主动的选择。在随后香二嫂攀上屋顶与环环交谈时,也是环环主动地摘下了象征着两人交流障碍的屏障。
环环成熟了,这种成熟显然是一种早熟。在痛苦和绝望的深渊中,环环挣破了现实关系所规定着的欲望对象化的轨道。她懂得了,人不能为自己的欲望而活。这不仅是因为,在现实生活条件下,欲望决不可能得到真正而全面的满足,而且还因为,在现实的文化轨道中,欲望的对象化只能带来对投射对象的伤害。历史已经证明,人的拯救不是欲望的放任和张扬,也不是欲望的凝敛或欲望的自我毁灭所能达到的。人的拯救只能是,在身体的、具体性的存在中重新找到人与对象的合理关系,也就是说,找到人作为人的真正的、完整性的存在。在贫乏、不公正、人欲横流的现实情境中,这种真理性的光辉的确非常稀薄,但它毕竟存在,就象遥远的星辰,平静地发出光辉,远远地昭示着我们。
关于欲望和灵魂真理性的关系,米·福柯写道:灵魂只有在同真理保持一种双重联系的情况下,才能战胜欲望,这双重联系,一是灵魂同欲望本身的联系,二是灵魂同欲望目标即真理之间的联系”②。在现实的文化结构中,这种双重联系分裂为相互分离的两个维度,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是主体性、个体性、欲望恶的维度,另一个是客体性、群体性、受难、终极价值的维度。艺术形象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把这两种相互分离、彼此对立的维度整合起来,缝合了个体欲望与欲望对象之间的距离。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来说,用直接反抗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和对立,不管强调的是哪个方面,都必然把分裂和对立推向极端。也许,确立统一的现实基础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真正建造志实现这两个维度相统一的新的人类身体,以及表达欲望的新的文化机制。面临现实的巨大压力和毁灭性的打击,抵抗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只有跳出了既有文化所规定的欲望表达轨道,抵抗才是建设性的,改造身体的工程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肉体的拥有等于一无所有,同样,肉体的反抗也只能是无效的反抗。因为对不公正的反抗会导致另一种意义的不公正。在超越现实关系这个意义上,虽然美和审美可以成为截断这种恶性循环的一种有力工具,但是我们也看到,审美幻象作为欲望和终极价值之间对立深渊的填充物,也可能转化为人类虚饰自己和压迫他人的一种工具。当审美幻象成为对弱小者压迫的一种力量时,对美以及审美仪式世俗化转折的再思考也就不容拖延了。我以为,这种再思考必然地要以对日常生活和批判性考察为前提。只有在对日常生活状态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的真正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说明个体欲望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艺术是我们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方式,它既是使我们能够转过身来凝视日常生活状态的透镜,也是远远地昭示着我们的一团光明。艺术形象是人类创造的非常特殊的对象物,它把人的苦难和绝望对象化为和谐的形式,从而产生出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转换是人仍然有能力把握住破碎的生活,保持着内在凝聚力的证明。它使我们在历史的重压之下保持住信心,并为未来的生活和文化建设而努力。在后现代文化条件下,肉体已经成为废墟,美学决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成为一门“感性学”,它更应该思考灵魂的拯救及其现实的基础。
注释:
①参见《近年来法国哲学关注的几个方面》载《法国研究》1988年第1期。
②米·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