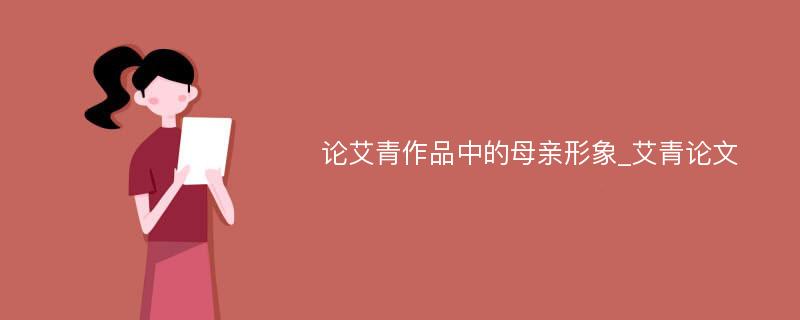
论艾青笔下的母亲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下论文,母亲论文,形象论文,艾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5-0087-05
作为地之子的“人”,在艾青的艺术世界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梳理、归纳并研究艾青人物诗的艺术经验,对于当下中国新诗的写作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也是对当代诗坛泰斗——艾青诞辰百周年的最好纪念。
艾青的人物诗可分成男性与女性两大系列。在女性系列里,艾青用抒情诗塑造了不少母亲形象:有诗人的乳母大堰河,有在马槽旁生下圣子耶稣的圣母玛丽亚,有饱受法西斯战争苦难的《补衣妇》,有在街头为失去两个儿子而《哭泣的老妇》,还有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游击队员的杨大妈(《藏枪记》),以及诗人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位有神圣母性的《年轻的母亲》等。这些母亲形象,既具有人类母亲的共性,也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活遭遇和个性特点。她们几乎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者,但“不幸”的特点各有不同:大堰河的不幸主要是贫穷、劳苦和受尽凌侮,她没日没夜地做着没完没了的繁重的家务和农事劳动,她的酒醉的丈夫平时还经常打骂她;她的死也是那样的凄惨:“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大堰河的不幸似乎在延续:“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大儿做了土匪,/第三个死在炮火的烟里,/第二,第四,第五/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里过着日子”。这怎能让她那“紫色的灵魂”安宁!那位被野蛮的战争逐出家园的补衣妇,只好在风沙扑面的路旁,给路过的行人缝补衣服,以获得一点可怜的报酬,为了能抢得一二个顾客,她已顾不得那哭泣的孩子,让他的可怜的眼“瞪着空了的篮子”。那个在玛拉可夫街头哭诉的法兰西母亲,她的不幸是法西斯战争夺去了她心爱的两个儿子的生命,她已在街头哭泣了一个星期,“眼泪已淹没了她的理性/痛苦已把她的心烧成癫狂”。诗人用满含深情的语言来描写这位不幸的法兰西母亲哭诉时的情景:“她的手抖动在头上/像两条被风摇撼的枯枝/撕裂的衣襟挂在肩上/破烂里露出了干瘪的乳房/她的眼睛流着混浊的眼泪/把她的脸越洗越脏”。正是这样一位被痛苦夺去了理智的母亲,一刻不停地向行人们诉说着自己的不平,控诉着法西斯匪徒们为了发财而制造战争、残害无数年轻生命的罪行。杨大妈是位革命的母亲,她也因帮儿藏枪被关进监狱,受尽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敌人先用“老虎凳”来逼迫杨大妈招供:“她的头发结在柱子上,/麻绳捆住了她的膝盖,/又搬来一叠砖,/把她的脚跟抬起来——”,酷刑的折磨并没有使杨大妈屈服,因为她已识破敌人的诡计:“先逼她交出枪支,/再逼她交出儿子”,她也已认定,她的儿子是好儿子,和那些年轻的英雄汉一起,打岗楼、杀汉奸,从敌人手里夺来枪,又用这枪去打敌人。汉奸特务们见杨大妈硬是不招,就给她加刑:“她的脚骨快断了,/她的眼睛发黑了,/无论他们问什么话,/她都回答说:‘不知道。’”强盗们见硬的不行就用软的,“解开绳索请她坐”,那个比蛇还毒的周老大对她说:“你的儿子当土匪,/都是吃了你的奶。”杨大妈仰起头、瞪着大眼对他说:“谁家的孩子,还不都是吃了奶才长大的?”杨大妈面对疯狂的敌人,她抱定一个信念“留下儿子留下枪,/再和她们拼一场,”“只要留得儿子在,/一定会报仇雪恨。”在杨大妈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品质,但诗人并没有将她拔得很高,她对革命的忠诚来源于她的亲情:一个母亲对亲生儿子的一种本能的爱与保护意识。因此,杨大妈这个革命的母亲形象是真实可信也是感人至深的。
艾青的母亲诗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结构——母与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显著特点便是“母子情深”。这一方面是由母与子的天然的依存关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习得的精神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观念所决定的。血缘亲情与人伦道德是母爱的基本内核,而伦理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对于土地、人民、种族和祖国的爱。所以,艾青笔下的母亲形象既有源于血缘亲情本能的母爱,又有那种植根于土地和人民的崇高的民族之爱。她们爱自己的儿子,甘愿为他们承受各种苦难与打击,甚至连生命也在所不惜,是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儿子都是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们的行为也是爱国行为。那位法兰西母亲之所以要为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两个儿子痛哭,是因为“他们都是我用奶养大的”,“都是我的心,我的爱情”和“我全部的安慰”;还因为“他们不醉酒、不赌博,不嫖妓女”,“不吵架,不惹是非”,“勤快地工作,节俭地过活”,更因为“他们爱祖国像爱他们的母亲/他们爱土地一如他们的生命/假如法兰西真的闯进了敌人/他们自然会被义愤送到前线”。那位革命母亲杨大妈之所以甘愿为儿子受尽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屈,也是由于她“知道儿子做事为了穷人”,而革命就是“穷苦的人心连心,/团结起来闹斗争,/赶走日本狗强盗,/消灭汉奸顽固军”。还有我们的国母宋庆龄之所以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之所以被诗人赞誉为“女性中的先知者”、“正义的化身”、智慧与光明的象征,也是由于她“和斗争中的人民一同斗争/和前进中的人民一同前进”,她从民族的灾难中觉醒,她和背叛革命的人决裂,她与人民一起抗击日寇的入侵,“她充满人道和友爱的心/抚慰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她“向呻吟在病榻上的母亲伸出手/向为饥饿而哭泣的儿童伸出手”,“她支持一切反侵略战争/为胜利的人民保卫和平”,总之,她是人民的母亲,人民也就是她的儿子。
从杨大妈、宋庆龄到那位法兰西母亲,她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她们的不幸也都与她们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她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博大无私的母爱,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并由这种本能的母爱升华为对祖国对民族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爱。我想,正是这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的爱维系着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而其中最具生命活力、最撼人心魄的就是那神圣的母爱,因为母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性的爱”。[1]所谓“生产性的爱”,即是说人类的爱是与劳作和责任紧密相联的,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圣经的《约拿书》。书中说,约拿根据神的旨意,向尼尼微人宣示神谕,并使他们改恶从善,于是神给约拿培植了一颗用来遮太阳的大树,约拿为此而感到些许的安慰,但不久神又让大树死了,约拿万分沮丧,并愤激地向神抱怨,神对他说:“你关怀一下葫芦吧,你既没有为它而劳作,也没有促它生长;它在一夜之间萌生,又在一夜之间腐烂。”神接着向约拿解释说,爱的本质是为某物“劳作”,“使它生长”,爱与劳作是不可分割的。你爱你为之付出辛劳的东西,你为你所爱的东西而辛劳。也就是说,爱的本质是关切与责任心。而母爱就是这种关切和责任心最生动的体现。婴儿诞生时,母亲的躯体为婴孩而“劳作”,婴孩诞生后,母爱继续致力于哺育她。母爱并不以孩子长大后会爱母亲为前提条件,她是无条件的,仅仅依据孩子的恳求和母亲的反映。所以母爱成为艺术和宗教中爱的最高形式的象征是毫不奇怪的。艾青不可能从理性上来认识弗洛姆提出的“生产性的爱”,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体认了这种爱,并把这种“生产性的母爱”,描写得如此生动形象,如此感人肺腑:“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大堰河对“我”虽没有十月怀胎与生产之苦,但却有五年的哺育之辛劳,“我”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她对“我”的爱超过了她对自己儿子的爱,即使在“我”回家之后,她仍深爱着她的乳儿:“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冻米的糖,/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在梦里,她吃了她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大堰河对乳儿的爱,既是神圣母爱的自然流露,也是与她哺育乳儿的劳作分不开的,因为这种哺育劳作的过程,从本源上说是一种生命转移的过程,如果没有母爱的生命能量的投入,新的生命就不可能形成,即使形成了也无法生存与成长,母爱之所以神圣,就在于它既是孕育新的生命的摇篮,又是新生命得以成长的保障,母亲会将她生命的全部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她的孩子们,而这种奉献是不期望有任何酬报的,如果说有酬报的话,那就是看到新的生命的诞生和成长,看到自己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因为这是人类超越死亡最现实最有效的形式,或许人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潜意识中是确实普遍存在着的,诗人艾青则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激活并有效地传达了这种生命的隐秘,致使其笔下的母爱形象被描写得如此动人如此深刻。具有大堰河美质的母亲形象还有许多。你看那被战争逐出家园的母亲,为了孩子的生存,她在沙土飞扬的路边“无声地给人缝补”;你看那位法兰西母亲,她为两个儿子的死竟站立在街头哭泣了一个星期;即使那些没有经受过苦难的《年轻的母亲》,也有一双最美丽的“母性的眼睛”,那神情有着不可侵犯的庄严。
母亲深爱她的儿子,儿子们又以同样的爱回报给他们的母亲,这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母与子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的诗人与大堰河之间并没有这种血缘亲情的联系,而只是哺育与被哺育、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如果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阶级,正像诗人所说:“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大堰河啊,我的保姆。”没有了血缘的亲情,那么乳儿对乳母的爱似乎只是对养育之恩的回报?诗人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诗中反复渲染这种养育之恩:“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监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呈给你吻过我的唇,/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呈给大地上的一切,/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们,/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应该说,诗人对大堰河的爱是深厚而博大的,其中有养育之恩,有对乳母不幸命运的同情,更有对所有像乳母一样不幸的母亲们的深深同情,在这种同情里既有阶级的意识,也有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正是这诸种情感的交织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忍不住要问,艾青与大堰河之间并没有血缘亲情,为何又如此母子情深呢?难道这仅仅是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没有其他的更为独特的心理原因吗?有的。从他们俩的生活与情感经历看,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都是被遗弃的不幸者:大堰河从小就被卖到畈田蒋,做了蒋忠丕的童养媳,她终日劳作,仍免不了遭受欺凌,好容易熬到十六岁,与蒋忠丕成了亲,之后又为他生养了三个儿子,但贫穷使她得不到丈夫的爱,在丈夫生病去世后,她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小艾青虽然出生在地主的家庭,但因为难产,也因为算命先生的一句“克父母”,也就决定了他的被遗弃的命运,本来他是应该被“除掉的”,后来算命先生告诉他的父母,用“舍”的方法可以破除这“犯克”的命运,于是他就被送到了正需要用养育乳儿而养育她的家的大堰河的家里,两个不幸的被遗弃者,就这样在命运的支使下走到了一起,她在养育他的五年里不仅获得了生活的来源,而且还从小生命的成长里获得了某种安慰,而小艾青则在她的怀抱里获得了神圣的母爱,留下终生难忘的“童年记忆”。二是他们都有一种赎罪心理,因为他们都曾经“犯过罪”,他们曾联手扼杀了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小生命。艾青在1942年儿童节写了一篇《赎罪的话》的文章,开头两节写道:“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自从听了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那里夺来的。这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2]这件事虽然是艾青长大后才知道的,但那种深深的愧疚感则伴随了他一生,命运似乎要让他以一生的坎坷来赎掉这个“夺命”的罪孽。艾青有这种“犯罪感”和赎罪心理,那么对于亲手“杀死”自己骨肉的大堰河来说,其内心又将是怎样一种状态呢?她即使有一千一万个溺死自己女儿的理由,她的内心也是绝对难以平静的,她的罪恶感绝对不会比艾青轻些。最近,传记作家吴洪浩先生,在他的新著《不灭的诗魂·艾青》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对大堰河溺死女儿的情景作了合乎母亲心理的想象与描写,现摘引一段,以飨读者:
昏黄的小油灯一闪一闪,夜静极了……
大叶荷放下孩子,轻轻下了床。她往床前的尿桶里倒了大半桶冰冷的水,抬起一双颤抖的手,把女儿从床上抱过来,弯下腰去,左手托着孩子的头,右手托着孩子的腿,咬紧牙关,紧闭着满是泪水的眼,将孩子的头朝下倒了过来,对着尿桶的口放了进去,由于她的手颤抖的厉害,孩子的头碰到了尿桶的边上,大叶荷全身颤抖起来。只听孩子轻轻“哇——”了一声,尿桶里“咕噜——”冒了一个泡,便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昏黄的小油灯停止了跳动,那只有黄豆粒大小的黄色灯火,像是送给那幼小灵魂的一朵小花,一朵带泪的用血染成的小花。[3]
大堰河终于凭这种残忍的忠心,换得了养育小艾青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取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痛苦啊!而唯一能减轻这种痛苦的方法,便是将对女儿的爱转移到乳儿的身上,也只有这样,她才会赎去那份深重的罪孽。正是由这样一种心理的驱动,使大堰河以胜过爱自己亲生儿子百倍的爱心去爱她的乳儿,这虽不是一种自觉行为,但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潜意识驱动。所以,我认为诗人与他的乳母的那份特殊的“母子深情”,与他们这种潜藏于无意识深处的被遗弃感和赎罪感,是有某种深层的内在联系的。
那么,大堰河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大堰河”是怎样把艾青推向世界诗坛的呢?对此,有学者借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说艾青的产生与德国大诗人歌德有某种相似之处,因荣格说过一句有悖常理但却十分精辟的话:“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4]143荣格认为,诗人的作品往往会超越诗人自己,这就像孩子超越母亲一样,创作过程也具有母性的特征,“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无意识深处,或者不如说来源于母性的王国。每当创造力占据优势,人的生命就受无意识的统治和影响而违背主观愿望,意识到的自我就被一股内心的潜流所席卷,成为正在发生的心理事件的束手无策的旁观者。创作过程的心理活动便成为诗人命运的推动者,同时也决定着诗人精神的发展。”[4]142在此,荣格非常强调“集体无意识”与“原型”对作家的制约作用,当创作主体触及并投入到这条无意识的河流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顺着它的流向往前流去。歌德在创作《浮士德》时就曾“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的某些东西”,并受到这种代代相传的德意志原型的驱动,不由自主地创造了浮士德。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浮士德”就是德意志灵魂的象征。与此相似的是,艾青创造的“大堰河”,也触及了中国灵魂的某些“原型”——勤劳善良、忍耐坚韧、温驯仁爱等,我们也可以说艾青也是在中华原型“大堰河”的推动下,走向中国和世界诗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得出类似于荣格对歌德的阐释:“不是艾青创作了《大堰河》,而是大堰河创造了艾青。”[5]不管这种类比性的研究有多么地生硬甚至是附会,但却给艾青研究引入了一个较深的心理层次,是极具启示性的。
同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究“大堰河”的奥蕴,但每个研究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譬如有人借用现代精神分析学说,对艾青早年痛失亲生父母之爱的“童年记忆”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艾青童年那种“失乐园”般的创伤是他日后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因素。[6]因为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已经证明,作家艺术家的童年生活对其日后的世界会构成或隐或显的情意结,对创作之维起着持续而重要的支配作用,甚至会沉淀为个人化的原始意象与创作母题。美好欢乐的童年生活可能会给作家的艺术天地染上一层怀旧的情绪基调,以抗衡浑浊的世俗世界,或化生为纯净素朴的风格。这足以影响他一生的创作。面对苦难,常人也许会像祥林嫂那样絮絮叨叨,或者轻易地让岁月之河淹没而忘却;但一个感觉敏锐的诗人,却会把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创伤转化为创作冲动的酵母,发酵成苍凉沉郁的生命意识。艾青像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一样,童年时代的心理创伤给他播下了寂寞的种子,在寂寞开化的时节,他开始了长长的“孤独的漂泊”与“自由地流浪”的生涯。先是“从美术中寻求安慰”,继而远离故乡四处求学,失去现实家庭的伦理悲哀在这里演化为精神家园的失落和放逐,所有的努力是让这颗寂寞孤独的灵魂获得一个安然恬静的精神居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精神居所并没有在他刻意追求的美术中获得,而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地狱之门外徘徊之际,他重又投进了“大堰河”那温暖的怀抱,走进了诗的殿堂——他的精神家园。如果说童年时代大堰河给诗人以肉体的生命,那么成人后她又给了诗人精神生命;然而这位给予诗人整个生命的母亲,不仅仅是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而是人类母亲的神像。当然,她的头上没有西方圣母的神灵光环,但她的质朴、她的平凡、她的无私却正是我们古老民族所具有的美德,因此,我们可以说她就是我们民族的圣母。在此,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诗人创作时把保姆的真名“大叶荷”记写成“大堰河”,后来诗人承认是记忆错误,因为“大叶荷”与“大堰河”在上海话里几乎是一样的,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误写”。也曾有读者有过类似的“误读”,但遭到诗人断然否定。从对诗歌意象的阐释角度看,诗人的自我纠正只是创作意图的呈现,而非意义的确指。在许多伟大的文本世界里,正是这种创造性的“误读”大大拓展了它的意义空间。因此,母亲以“河”称呼,实在是诗人潜意识里对生命之源的眷恋与渴念,“河”从来就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与象征。耶稣曾对来井边汲水的撒玛丽亚妇人说:“我喝这水,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活水,要在他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涌流不息,直到永生。”在诗人的灵魂里,不就是流淌着乳母“大堰河”赋予的生命之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