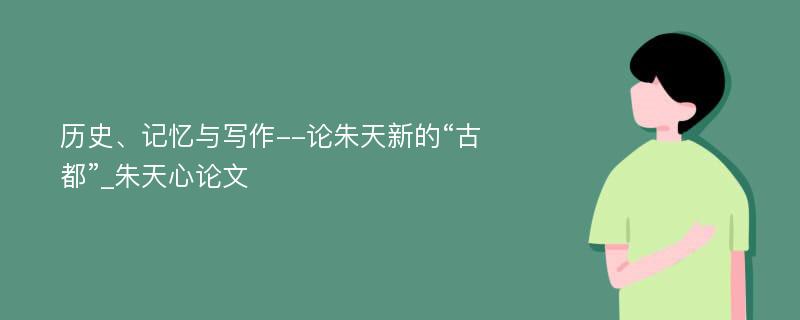
历史、记忆与书写——论朱天心《古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都论文,天心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根本没时间疗伤,我们抢夺铅笔和橡皮擦做武器,相互厮杀。 ——朱天心《看不见的城市》① 一、前言 身为台湾外省第二代的作家朱天心,长久以来透过文字的笔耕,寻找外省族群在台湾的定位问题,在外省族群与本土族群混融的社会情境中,朱天心不断地透过书写探讨了台湾认同议题。在朱天心的书写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作者在文字中所透显的历史危机感②,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文开始,朱天心即以夹叙夹议的语调道出这一群年轻生命,在经历成长,脱离眷村的大观园之后,面对起伏不定的社会情境以及生活、心灵的转变过程。作者年轻的兄弟姊妹们,在这座父祖的栖身之岛上,仅一时之间,生活空间已经被粗暴的褫夺,随时可能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因此除了选择流浪到下一个异乡,似乎也别无出路。 朱天心敏锐地意识到岛内这股吊诡的氛围,不再认命的隐藏于闺阁之中,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为那一群被岛国放逐的兄弟姊妹们发声,试图在被毁坏的土地上寻找历史的记忆,同时给予被污名化的外省族群新的记录与诠释。③究竟朱天心在担忧什么?面对历史处境的骤变,在外省族群逐渐被标签化成为与本省族群对立的存在之际,这一群外省族群面临了极大的生态转换,政权的转变使得这些原本居于优势处境的群体,由中心的主导地位流放至边缘,所有已经建构的记忆随着城市的瞬变面临被解构的危机,不确定性的膨胀以及记忆的松动,加上绝对性的消失,个人能够掌握的只剩书写。 透过书写,在自我记忆的寻访之旅中,通过空间的置换,《古都》欲停滞时间流动的企图相当明显,究竟作家在与时间的角力过程中想重建什么?当记忆中具体的事物一再地破坏崩解之后,对于集体失忆恐慌的朱天心,依随着主角个人经验以及记忆的寻访历程,欲在《古都》中重建一座桃花源。本文所欲解决的问题也从《古都》中所显露的“危机意识”中出发,进而探索朱天心对于历史、记忆的质疑与追寻,以及透过其特殊的夹叙夹议口吻中,所建构出来的《古都》意涵。④朱天心如何从“他者”的边缘身份进入“本土意识”高涨的发言场域,进一步为自己的所在辩护?从京都到台北,从过往到现在,面对朱天心巧妙的时空变换,透过历史、记忆的书写,在拼贴的图像中,或者可以探询到作家所欲揭露的失落与追寻。 二、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历史记忆与历史失忆显然已成为近来的热门话题,当权者利用权力之便不断地改变历史论述,从而使得历史的确定性一再地受到质疑,历史究竟是主观抑或是客观?⑤实际上,这些争论的重点在于“呈现”的问题上,究竟以视点(即事件)为主,或是以观者(即人)来决定历史,仍是见仁见智的悬案。在《古都》中,叙事者不断地发出对历史解释的嘲讽,在政治正确的修正下,台湾历史的溯源运动成为叙事者嘲弄的对象,一句:“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质疑所谓的大历史,也透露出颠覆大叙述的决心,小说中的自我对话俨然成为其抵抗现实破坏的最终策略,在自我记忆的重构过程中,对于集体的记忆与失忆有其特殊的观察与质疑。《古都》一文中对于历史记忆的追索,对集体记忆的存疑以及对于身份认同的敏感,都让这篇跳接在故乡与异乡、过去与现在的小说充满了张力,在探究《古都》的书写之前,小说中存而未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必须先予厘清,才能进一步深入小说中浓厚的记忆、伤逝与怀旧氛围。 1.何谓历史?叙事者在小说开头质问:“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作者未曾言明的疑问是:那么谁的记忆才算数?是过往灌输皇民精神的日本政府,或是灌输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祖国河山的国民政府?还是夹着“爱台湾”的本土论述以及政治威权的政府记忆?历史中充满了吊诡的变动性,究竟是原住民的经验为真,还是历史记载的年表事件为真?当叙事者面对建构记忆的实体逐一瓦解的时刻,以七个“那时候……”急切的召唤当时的天空、树木、泪水、思想、音乐等时空背景,欲借着熟悉的披头四、Don McLean的歌声与熟悉的气味以及曾经滋长繁茂的各类树木花草,如马齿苋、马樱丹、射干、长春花、芍药、牡丹以及南洋杉、罗汉松等来确认记忆印证曾经生存过的历史。然而,记忆是可靠的吗?朱天心说道: 随着工商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许多“没有回忆”的新商区新建物只会愈多、愈快,而相对的,一些充满了记忆和因此必然伴随而来年岁沧桑的市街、街屋……将会消逝的同样快和最重要的,不能复返。……一个反复被洗清的记忆、集体仿佛得了失忆症的人、地区、国家“主体意识”、“本土意识”从何而生?不动辄轻易被擅自填充内容做为工具才怪?⑥ 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变化与都会生活中,朱天心透视了所谓“历史”不过是一种被用来填充集体意识的工具,仅是当权者耍弄民众的一种包装罢了,作者强调的是“记忆的变动性”,为了不让记忆被擅自的填充,朱天心采取了以其琐屑私密的个人感官经验抵抗集体记忆的重新灌输。透过文字,作家重建自我的记忆,为了因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脉动,因而书写过往,在时空的错置拼贴下,淡水河可等同于长江,淡水也可视同旧金山,虽然谁也没见过长江与旧金山,然而这个图腾式的景物意象却深烙在“你”的记忆中,成为日后回溯时索骥的图像。 《古都》中透过叙事者——“你”,揭露了族群对立的荒谬性。“你”的父亲族谱为外省族群,而母亲则隶属于本省族群,强调对立的绝对论者们,无法定位的正是像叙事者这种本省与外省的合流血脉,正因为定位与认同的危机使得叙事者——“你”,悟出自己所处的尴尬位置。历史告知了岛国族群混杂的悠久渊源,然而,在国家机器的操弄下,这种混杂性透过执政者的操刀逐渐分出优劣,集体意识也依照政治版图的划分重新定义,叙事者的存在不断地提醒这种粗暴分类的吊诡与荒谬。“你”的本岛记忆来自母系亲族,在受过日本教育的外公、外婆身上汲取“本土”的味道,外公远处出诊及北上开帝大医学专科同学会的身影,与外婆一起所享受的“金刚糖球”或“腌芭乐”的味道以及火车廊站下的小敢仔店的记忆皆属于五六十年代,人物图像则停留于日据时期至战后初期时的身影,外公呼唤外婆“ネエサン”的殖民话语与搓汤圆,做蚁粄扫墓的记忆层层重叠,却没有丝毫扞格的输入自身历史记忆的深处。然而,随着父系外省身份的突显与自身的成长,“你”的自我异化日渐严重,甚至于躲入边缘,跟着同样来自异乡的同胞在角落窥伺这座逐渐充斥敌意的小岛,在存在的危机意识作祟下,做着往异乡高飞的梦想: 你们仰着头,蓝色洁净的天空趁着勉强斑黄的温带秋叶,看久了不知置身何处,就可以编织将来要去哪里哪里、大多是天涯海角之地的梦想,舍祖宗秋墓、族党团圆、隔重洋渡险、篡处于天尽海飞之地的哪里只是一直被指摘的你这种父辈四九年来台的族群。⑦ 身为1949年来台族群之后辈,在岛国的快速变化之下,处于被驱逐的忧患困境中,竟忘了自己血液中所混融的本土身份,“你”以幽默又悲伤的口吻说道: 因为害怕吃沾了死人气的蚁粄就不上坟,因为逃上坟就要求在上元节前回父母家……好些年后,成了忘记自己原先也是有坟可上的人。(207页) 这类矛盾的情绪与处境成为整篇小说的基调,深刻地讽刺了以历史溯源论定“外来”与“本土”的论述。实际上这些论者所强调的“历史”,并非仅是纯粹发生于过去的事实,最重要的是他们透过论述,模塑了社会记忆,借由探索“过去”召唤现实人群,经由文献、口头传述、庆典仪式以及形象化之纪念物品传输,凝聚人群的记忆,借着集体的回忆行为,加强人群的凝聚力,同时也强化了人群的排他性。台湾本土论述利用历史溯源去建立其言说的合法性,朱天心对于这种言论的反论因应策略便是不断地召唤自身的私记忆部分,企图以此对抗本土论述的论述霸权。因此,历史并不一定是对“历史现实”的记忆,而是一种想象,经由群体创造“过去”,然而,其中却包含了复杂的对历史事件的选取、修正与遗落。⑧正因为历史充满变动性,因此集体记忆的形成,其背后经常有更复杂的权力支配以及人事的主宰因素,所谓的历史解释充满了人为的操纵,朱天心借着《古都》明言了“历史”的吊诡与虚幻。然而,就连身为作家的朱天心或者也未察觉,自身捍卫的过往记忆的荣光,同时也是国民党外省政权的文化霸权时期,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作为岛上一份子的台湾人民,陷入的未尝不是如朱天心笔下的失落以及害怕被质疑的立场,不论是何种论述,由于立场的转换,其捍卫的部分也会各有所别,不论是国民党政权或是民进党,在历史的解释权上都掺进过多的意识形态,透过《古都》的探索,值得深思的不仅是外省族群的忧患处境问题,更是台湾如何容纳各种可能记忆的问题。 2.寻找认同:集体意识的荒谬。何处是叙事者——“你”可以栖身之所?处在一种被排拒在外却又不知何去何从的“异乡客”情境中,只有无尽的彷徨,既受不到岛国中占据优势地位之“在地人”的接纳,又不见容于所谓的“故乡”——神州,仿若迷了路的武陵人,忘路之远近,遍寻不到昔日的桃花源。究竟基于何种原因,让这位在岛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中年女子老有远行之意,面对生长的故土毫不依恋,甚至于必须时常将其幻想成异乡,方能勉强过日,最大的因素应是认同感的失落,在民族造神的运动中,“你”原先信仰的记忆突然在一夜之间被抹杀修改,甚至于“你”从小熟悉的民族救星,一夕之间也成为民族罪人,背负了强占宝岛的罪名,成为众所矢的标靶,一直以为是存在的事件,肯定的事实,突然间在眼前瓦解。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过多的不确定性动摇了所有的认同,在失落了认同感之后,最熟悉的岛屿也转瞬间成了陌生的地域,因此“你”必须远行,寻找曾经根深蒂固的认同依归,“你”说道: 你简直不明白为什么打那时候起就从不停止的老有远意、老想远行、远走高飞,……你从未试图整理过这种感觉,你也不敢对任何人说,尤其在这动不动老有人要检查你们爱不爱这里,甚至要你们不喜欢这里的就要走快走的时候。(169页) “你”不敢分析自己老是有远行之意的真正动机,甚至于避免剖析自己为何无法安心待在小岛上,最大原因在于害怕面对失落的认同感。就在政府大肆提倡爱乡土、爱人民的口号中,“你”在精神上对这座岛屿却渐行疏离,因为在爱乡爱土的集体意识的包装之下,熟悉的事物正逐渐崩解,面对政治上的转换情境以及都会化的环境变迁,迷路的武陵人——“你”,在寻找认同感的背后,却仅见国家集体意识所塑造的认同幻象,以及整个岛屿上的社会记忆重塑,透过各种身份认同的讨论会议,过去的记忆重新被修正,并依靠群体的力量重建过去,成为群众的集体记忆。⑨“你”嘲讽着: 要走快走,或滚回哪哪哪,仿佛你们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赖脸不去似的。…… 有那样一个地方吗?(169-170页) 叙事者——“你”嘲弄集体记忆的扭曲,对于执政者这种组构扭曲的集体意识之营造,以自我拆解的行文书写作为策略,揭露当权者所塑造的集体意识之荒谬。当权者有意的制造对立,以民族主义来制造省籍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有鉴于此,“你”以轻松的口吻回忆年轻时,为了买PX中所流出的真正的Levis牛仔裤而进入晴光市场——一个外国货品的集散之地。在其中见识到了充满异国风情的圣诞布丁、加了奇怪香料的面包,以及牛油、果酱、红茶、巧克力等代表异民族的象征,然而,当初仅仅发誓如果赚了钱一定要到这里买个够,而奇怪的是,这些完全无关于民族主义,到了年底,又面临了与日本断交的国际危机,年轻的“你”,突然一股爱国心沸腾,不仅捐出一颗巧克力糖的钱,并且发动捐血写血书,即使如此,日治时代所留下的仓库建筑仍是“你”喜爱流连之所,而且在路上见到白肤高鼻的人继续的以鸦片战争后的强势姿态抄着自己的女同胞,并搔得她怪叫连连时也并没有任何冲突之感,信仰与生活互不干扰的持续下去,没有过度的政治渲染,以及过多的情绪反应。 这种行之有年,将信仰与生活二分的生命态度,在政权汰换之后却产生极大的改变,“民族”“乡土”突然在城市中沸腾,检验信仰成为新生活的中心,自以为爱乡土的一群急着以本土的尺牍丈量这群外来客的爱国强度,甚至于将之塑造成不愿根留于岛国的族群,随时有悖离岛国奔向父祖之乡怀抱的可能。然而,正如“你”所控诉的,这群扭造重组历史的一群,真的以为这些外来族群有一个最终的归处吗?这里不仅仅是叙事者——“你”的疑问,同时也是朱天心这位外省第二代的疑惑:真的有那样的地方吗?一个不再质疑身份地方真的存在吗?朱天心从边缘观察中,指出执政者对于集体意识营造的荒谬。 《古都》中一再地以新旧政权对于集体意识的组构作为对比,叙事者——“你”先是以回忆的方式记叙了求学时代的政府,在十月三十一日(即蒋公诞辰)当天,总是优先开放给他们这些坐落于“总统府”附近的学校参观庆贺,当时的“你”抱持着欢跃的心情,以孙女似的天真无邪态度行礼祝寿,礼毕还可得到一颗寿桃。“你”在二十年后回想起当时的情境,才恍然大悟: 二十年后国际新闻报导里你看到为金日成衷心祝寿祈福的那些装不来的人民的笑靥,才恍然并感叹不已。(214页) “你”在二十年后面对政治生态的转变,对于学生时期所受到的集体收编,以及在威权统治下的思想重组有一种新的体悟,“你”记得当时总有几人不为统治者的爱国教育所感动洗脑,成长之后的“你”,还暗自羡慕这群人同样在十几岁的年纪已经如此具有判断力,让他们在日后的启蒙成长和独立人格的养成上,省了好大的一段冤枉路,然而,时移事往,曾几何时,这群在当时具有鲜明崇高独特判断力量的同学们,有的在二十年后政治正确的选择下,以政客的嘴脸说服“你”支持某政党之候选人,有的则是放弃了学生时代的独立主张,认真地考虑是否应教官之约加入国民党,并在回国之后马上加入政府机关,“你”突然间顿悟,所谓崇高独立的人格,在政治的权力操纵之下已经完全泯灭。“你”突然对于这些同学陌生了起来,不禁想到:“——她们这些当年不肯领寿桃的,在想什么?”透过“你”的记忆,新旧政权之间的权力运作,以及对于集体记忆的重构以及型塑其实并无两样,当年抵制威权厌恶当权者的人,后来却是最先向当权靠拢的一群。 戳破政治认同的荒谬,“你”又进一步探讨所谓的“在地化”以及“本土化”的虚谬,当执政者一再地以历史溯源论想还原台湾的远古记忆,进一步抹消所有外来政权统治的合理性之际,“你”想起了蒋经国时代所大量启用台籍人士的用意,原来是企图塑造一种落地生根的悠久历史感,两边都是人为塑造的虚幻意象。然而,那群因反抗集权政府而去国三十年的异议人士,一群爱乡土的本土论者们在时移事易一旦掌权之后,却照样在他们口口声声热爱的土地上兴建高污染的重工业,所作所为与他们所急切批判甚至于推翻的外来政权一样,“你”洞悉了这一切,在寻求认同破灭的同时,也意识了集体意识营造的荒谬性,于是老想远走高飞,《古都》确切地道出岛国在国家机器操纵下的悲哀,“你”无奈地诉说: 当这块土地没有了无可取代的东西能够黏住人民时,人民只能无可奈何而非心甘情愿的留下……新的统治者一定察觉到这一点了吧,难怪把社区主义高喊入云,希望借此人民能够不看佛面(国家机器、统治者)看僧面(乡土、同胞),后者的政治正确性哪儿有人敢挑战,你何曾见过无所不批判的反对党敢对土地人民有过任何微词。(199页) 本文充分展露了朱天心“论文式”写作的风格,在作者的议论中,也可窥知对政治以及城市变动怀着极大不满的作者,为何经常在书写中透露浓重的“衰老”意味,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对于现实生活变动的种种无奈与无力。⑩ 三、记忆考古——重建一座城市 朱天心欲借由《古都》追寻“原乡”记忆,然而透过书写,作者也不停的质疑,所谓的“原乡”在何处?叙事者——“你”化身为迷路的武陵人,在旅程中不停地追逐一切可能的记忆。此外,叙事者——“你”也企图以自我的经验记忆对抗社会集体记忆的灌输,以小我抵抗中心论述,建构私人的记忆史。本文欲借由叙事者——“你”对两座古都的寻访之旅,深入朱天心在书写《古都》所明显透露建构一座记忆城市的企图。 1.消失的“原乡”。《古都》一文中,企图寻找一处可供栖息之所,然而叙事者——“你”同时也自我设问,当真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吗?“你”在两座古城中寻找原乡的图像,但是,对这位既应有本岛原乡与神州原乡者“你”而言,这两处原乡在经过时间的荏苒以及都会场景的变动下,身为外省第二代的“你”对于属于父亲这一代的家国记忆相当模糊,叙事者“你”对父亲的家国记忆仅是透过虚弱的口述建构,对于遥远的家国,除了少了土地上的真实碰触外,实际上,对于所谓“故乡”的风俗习惯及人情世事也是断裂的,因此,“故乡”与“他乡”基本上呈现一种吊诡的关系。“你”被灌输的原乡是从未进入记忆中的地域,仅在地理课本中可以找到的地方,一处名叫“故乡”的符号,并不具任何代表性,就这点而言,所谓的“故乡”实际上仅是一处“他乡”。所有的原乡记忆显得相当的飘渺而不切实际,身为外来族群第二代的悲哀也正在此,因此,这群在眷村成长的共同体,在长成之后不是选择回到父祖魂牵梦萦的“故乡”,而是选择另一个异乡,或是美国,或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总之是一个接一个的流浪之旅,如叙事者——“你”一心挂念的好友:A与“你”有着同样的遭遇,同属没有原乡记忆的一类,所以A选择流放至美国,在美国进行台湾研究,起码在一处比台湾更像异乡的地方,还有一处叫台湾的想象原乡可供追忆。“你”其实能够同理A的逃避,然而,却也不免还是要问: 你不知道A在想什么,二十年没回过台湾,研究的却是台湾……(171页) “你”其实知道A为什么不回台湾的原因,只是潜意识中对于复杂的认同感到疲惫,因此只能对A的行为提出疑惑。于是乎,外省第一代带着永恒的乡愁回味过往(11),而第二代则带着虚无的乡愁逃遁异乡,第一代失落的是“原乡”,第二代则是面临原乡的消失。 《古都》中的“你”带着永恒的乡愁,欲寻求父祖之乡的记忆却面临记忆架空的窘境,仅能追溯的本岛的原乡记忆又面临解构的命运。“你”在中年怀旧的情感之下流露出对集体失忆的恐慌,以及对“原乡”追逐的企望,“你”在日渐边缘化的处境中,面对的是历史痕迹逐年消逝的台北城,构筑“你”原乡记忆的台北古都,正被逐步地拆解,于是“你”面临了时移事往的哀伤以及恐惧归乡的尴尬,因此“你”选择了异乡——京都作为原乡的图像,以对抗逐渐瓦解的台北城记忆,在这同时“你”也面对了自身华年不再的忧虑,于是对过往产生了浓烈的乡愁。(12)“你”对于一切的改变感到不安与愤怒,在对台北做一次巡视之旅后,“你”遗落了更多,五岁时对剑潭的记忆,第一次去宛如嘉年华广场的动物园儿童乐园,所感受到满天都是五彩气球、吹泡泡和音乐的欢乐气氛,被专门接待国宾的中国宫殿式饭店所取代,这个欢乐情境一直到二十年后“你”旅行开锣,在观光巴士上观看塞车的市集街头,才似曾相识地找到昔日的欢乐宴飨,对此:“你脸贴在窗玻璃上,留恋不已。”此外,捷运车站破坏的天际线,也毁掉了“你”十七岁对天空的记忆,对于丑怪至极的捷运车站,只存无限的惊骇。而十七岁时走过百遍的明治桥被一座新桥压着等待拆毁,桥上的桐灯则早被放在三峡的祖师庙中,连历史悠久的枫香都被砍毁,为此,“你”质疑着: 批评以往是外来政权的新统治者人马已执政四年,所作所为与外来政权一样,只打算暂时落脚随时走人似的,不然他们何以去掉那两排在你们所有现存的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枫香呢?(177页) 面对年轻记忆不断的流逝瓦解,“你”的焦虑日渐加深,《古都》中凸显了今昔的对比,呈线出过去与现代的冲突,“你”在现在中找寻过去,并借回忆敷衍现实,在时空错置中,“你”不断借由记忆重建过去,追逐年轻的故乡景象,如到城北郊区追溯年轻时所居住的眷村究竟在何处?当“你”发现过去的家可能已经成为某便利商店前的花坛,以及童年疯野的大山,如今仅剩残留的小山巅时,“你”清楚地知道:“消逝了的不只这些……”,消逝的是“你”在年轻岁月所建构的“原乡记忆”。现实考古的失落,让“你”不禁忧虑起下一代——“你”的女儿的记忆该是如何形成的呢?属于下一代的原乡会是什么?当“你”已经迷失于大楼林立的都会丛林之际,又该如何明确地告诉女儿“记忆”的可靠性呢?因为记忆失落的“你”已经找不到明确的例证交代你们曾经生活过的生命轨迹: 你简直无法告诉女儿你们曾经在这城市生活过的痕迹,你住过的村子、你的埋狗之地、你练舞的舞蹈社、充满了无限记忆的那些一票两片的郊区电影院们、你和她爸爸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你和好友最喜欢去的咖啡馆、你学生时常出没的书店、你们刚结婚时租赁的新家……甚至才不久前,女儿先后念过的两家幼稚园(园址易主频频,目前是“鹅之乡小吃店”),都不存在了……(181页) 于是“你”愤怒又忧伤地说道:“这一切,一定和进步有势不两立的关系吗?”“你”对于城市的过度开发以及完全不保留历史生活痕迹的粗暴行为,深感痛心,于是,你不再随意地进行记忆的考古之旅,害怕会发现一年到头住满了麻雀与绿绣眼的老槭树会在一夕之间消失,同时也害怕曾经熟拈的街道会在一夕之间变得全然陌生,“你”怀着恐惧,不愿意去和人回忆过往,也不愿意去记住新的东西,害怕又将种下一场流逝的开端,如同迷路的武陵人,找不到回乡之路。带着对岛国的失忆,“你”流浪至京都,甚至于每在失落了某些记忆之后,你也选择了京都这座古都作为避难之所,原因无他,而是在这座古都之中,记忆的变动性极小,除了四季的变化之外,每一户人家都是记忆中的样子,感同其情的和女儿在这里建构属于你们的记忆与原乡。于是“你”说: 是这样吧,在死之前,若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一点点记忆,你还可以选择去哪里……你,会选择这里吧,因为,因为唯有在你曾经留下点点滴滴生活痕迹的地方,所有与你有关的都在着,那不一定它们就会一直一直那样在下去,那么你的即将不在的意义,不就被稀释掉了吗?(195页) “你”选择异乡的古都作为最后葬身之所,主要原因在于这座城市保存了“你”生活的痕迹,而岛国上的那座古都,则每天消抹人们生活的痕迹,就此而言,在一个不愿保留人们生活痕迹之所,不就等于生活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中,“你”的原乡记忆在这样的城市中已经成为一缕孤魂,飘荡在被解构的建筑中。 2.建构桃花源——个人记忆的展衍。叙事者——“你”以青春岁月的流转过程来建构记忆,化身为人类学家重新探险台北城,并以个人记忆抵抗被肢解的破碎的记忆图像。“你”年轻的记忆透过殖民时期的地理表记:如总督府、文武町、本町、宫ノ下、明治桥等旧地重游,逆转了时空,重现年轻时的荣光与欢愉,在都会化的台北城中捡拾被城市遗忘、丟弃的垃圾,透过万花筒式的拼贴图像,重现其原乡记忆,试图重构青春时期的桃花源,并进一步地以此与掌权者进行对话,朱天心曾经说道:“觊觎并抢夺历史解释权,当然绝非台湾独有的现象,但我正逢此时此际,便不能不、不自量力的加入这场争夺,或谦卑的说,捍卫个人记忆”(13),因此,作家选取了以叙事者——“你”的记忆重构之旅这种私人经验记忆的小论述,对抗强大国家机器所强调的集体意识大论述。 叙事者——“你”心所神往的是如《稗海纪游》中的蛮荒台湾,是任何论述皆未被泛政治化时期的岛国,这种神往同时也是对千变万化却留不住任何记忆的台北城之反动。“你”在《古都》之中,对于因时间的流动而日渐消弭的生活痕迹充满极大的反感,因此,朱天心透过叙事者——“你”追溯之旅,利用种种空间的建构置换了历史时间的流动,甚至于停止历史前进,将时间倒返而回到过去,建构消失的桃花源,于是“你”以拼贴的空间意象构筑一座新城市。 “你”先是在异乡的京都中撷取一些不变的图景,包括了一个小吃茶店的午茶、旅馆供应的宇治绿茶袋,或是白川南通平行四条的街景,以及白川的水流景致,这些植柳与垂樱以及遮阳的垂帘让“你”想起江南,这座江南景象其实也仅是“你”想象中的记忆,其实,“你”并未真的到过江南,又如那些已经承担百年历史的清水坂、三年坂、二年坂的石坂路,以及清水寺、八坂神社、円山公园、百年老垂樱、南禅寺、东福寺、东本愿寺、二条城野野宫永远在那儿,这座古城百年不变,连“你”的记忆都未曾变化,甚至于整座城市的气味也都充满了熟悉感,这也正是京都之所以能安抚惊惧不已的“你”之处吧。带着熟悉的记忆,不再等待A的会合,“你”毅然决然的以伪装的观光客身份,重返海岛。 手持殖民地时期的老地图,以全然陌生化的身份按图索骥重构青春记忆,将历史时间变逆成为空间架构,于是你见到的岛国计程车司机不复你在岛国时记忆中的跋扈专横,而是旅游书中所描述具有笑颜、亲切特质的岛民,在一种陌生的角度观看的岛国,少了主观情绪反应之后,熟悉的新光大楼展望台成了异乡的摩天大楼,而丑陋的高速公路以及降落机场的航机们具有异国风情般的别有风味,“你”按图寻访每个青春时期曾经驻足流连之所,包括台湾神社、第二高等女学校、幸町教会、台湾总督府研究所、外公念的帝大医学专门部、帝大附属医院、赤十字本部、景福门、东门町、台湾总督府官邸,这些“你”高中时代经常流连晃荡之处,另外还有铁道ホテル的原址,让“你”想起此处的电扶梯口正是你年轻时候每个月得来排长龙办公车月票之处,此外,表町的后藤民政长官纪念博物馆也是“你”年轻时代的足迹之处,接着“你”仍旧依顺个人记忆的主导,继续走访荣町、新高堂书店以及怀缅隔壁“三六九”新蒸松糕的发酵香味,在个人记忆的展衍下,台湾银行、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总督府图书馆、淡水馆一一的跟着记忆重现,在殖民地图的索引下,逝去的青春图像又再度重现。于是线性的历史时间被拆解,以断裂的、块状的空间存在,于是历史时间转变成为地理图像。 叙事者——“你”任由感官知觉主宰一切,坐在曾被“你”视为丑恶象征的捷运上,幻想着过去平房时代的回归,想象着大片蓝色天空的覆盖,因此心中充塞了一股旷远之意,“你”以私密的选择性视野,建构记忆,于是一座1970年代的城市终于在这种访寻之间诞生。它也许像一座深秋时节某地中海植满橄榄树的小岛,又或许是“你”年轻时想象中的江南图景,其间,承载着你流逝的花样年华。这是朱天心在书写上的策略,透过“你”的记忆重构,与二十年后成长的“你”的愿望遥相呼应,“你”老想远离又无法远离的海岛,经过陌生化的处理,达到“你”在阳光炫目时候躲在空调凉爽的室内所幻想的异乡国度的想象,并且替这位迷路的武陵人——“你”找到心灵的安栖之处。 “你”在面对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破坏时,只好开始进行记忆考古之旅,走着熟悉的巷道,也许是罗斯福路一银背后的晋江街一四五号,也许是浦城街二二巷一号和七号,也可能是中山北路一段八三巷三十弄五条通华懋饭店的对门,又许是长安路二四九号,在这些城市的废墟中吸吮过去养料。朱天心透过反复的涂写,以其深植于心的历史图像来检验台北的政治文化,在过多的失望中,作家找到了以“你”的记忆敷衍来对抗被洗刷、重组扭曲的家国意识,同时在自我记忆的型塑过程中,对于这个毁多于留的城市发出沉重的喟叹。(14)朱天心悲伤的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话诉说着: 即使我是那种想在记忆中区别两种城市的人,还是只能谈论其中一座,因为对另一座城市的回忆,由于没有字词来相配,已经遗失了。(15) 悲哀的是没有字词相配的那座城市竟然是自己所处的海岛,而另一座具备鲜明印象的古城,则位于他乡。 朱天心道出了“认同感”相当吊诡的一面,最熟悉的台北城的生活的痕迹已被抹消破坏,如今仿若未识,俨然成为一座陌生的城市。而远地的古都——京都,千百年如一日,尽管有着人事的变动,然而却依然找得到“你”或是生活在其间的每个人的生活痕迹与熟悉位置,所以作家仅能喟叹:大概,那个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记忆的东西都已先你而死了。“你”反复的重述:如果连死后都可以预期活人世界的模样,那是多么让人放心的事啊!于是作家透过叙事者——“你”的传输,将青春历程填充在京都的场景中,作家的历史记忆也透过京都地理空间的召唤重新建构被拆解的台北城。“你”在《古都》中嘲讽地说:“不是只有冰冷不染尘埃保存良好的古迹就足矣……(201页)”除了这些古迹的保存外,曾经记录人民生活的树木、建筑也应该是保存的对象,没有人文的古迹,仅仅是废墟一座罢了,一座无法让人参与的古城,是没有办法留住人心的,“你”在小说最后以大哭告结,其中充满了对那群自称爱乡土的在地人最大的质疑与控诉。“你”所建构的桃花源是一座挪移异乡场景填充自己经验记忆的虚幻之所,叙事者——“你”在对时间、记忆与历史不断的反思过程中,最终的期待应是能够走出想象,活在具有人文而不再变动或是充满审视意涵的祥和之都吧。 四、来自边缘的声音——期待对话 朱天心将对政治处境的不安以及对历史记忆的怀疑,透过中外文典、流行资讯、《台湾通史序》、《桃花源记》以及川端康成的《古都》的互文,营造出“陌生化”的审美效果。(16)透过“陌生化”的过程,将这些旧的素材纳进创作中,可以激发并刺激新的思考。朱天心运用多重文本营造出《古都》中的二元性,包括台北与京都的对照,今昔的对比,以及主角——“你”和A与川端康成《古都》中的千重子与苗子的互文,呈现出一种交错的效果。 由于作者对于现实生活产生的孤离感,迫使着《古都》中充斥着对话的想望。朱天心以极私密、呓语式的内心独白,反映出都会人眼中密密迭迭的生活空间,并且运用了回忆、想象的话语技巧建构作者眼中的大都会。作者以第二人称“你”作为叙述的主轴,而“你”的开放性指涉则相当的多元,一方面可视为是叙述者的自我对话,另一方面则也可视为是作者在召唤读者的参与,历史记忆的变动强化作者召唤读者参与辩证思维的决心,《古都》叙述结构,采取的策略是多元的对话方式,主要是由“你”这位叙述者担任了心理分析的陈述角色,目的在于唤起记忆。小说一开始,便以I.V.Foscarini的话语: 我在圣马可广场,看到天使飞翔的特技,摩尔人跳舞,但没有你,亲爱的,我孤独难耐。 此段引文道出了作者召唤读者参与的企求,这种你、我难分的呓语式口吻也构成了小说的叙述主体,“你”的使用营造了一种互为渗透的情境,读者透过对“你”的召唤,得以进入作者的思维中,参与作者的创作过程。(17)《古都》中的“你”既是读者自身,亦是所有你、我、她的共同指称,《古都》的意义也正是在于提供一位“想象的倾听者”,以娓娓道来的耐心以及时空错接的技巧释放读者与作者的内心世界,进一步深入探究在这城市中彼此常见的“疏离感”从何而起?此外,充斥于《古都》中的文学与人名,如川端康成的小说《古都》、Candida、The 5th Dimension、Don McLean、Black & White的歌曲、D.H.劳伦斯、百花历、《桃花源记》、台湾府志、梭罗、莱特、佛洛斯特,各式涵括历代文献、殖民记载、地方县志、哲思小语等中外的知识范畴,全都被援用进《古都》之中,和正文营造出“互文”的对话效果,也呈现了多元性的对话策略,此种“百科全书”式的敘述模式,也呼应了知识爆炸的现代都会中的美学要求,并且以错置的方式充斥于《古都》之中,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面和作者的叙述争辩或同理,一面则接受作者的知识刺激,在经历了知识之旅之后,面对知识丰沛的作者,读者不得不以戒慎恐惧的心灵仔细思考作者的提问,由此也达到作者欲与读者对话的效果。(18) 《古都》透过各种文本的召唤,营造出一种文本历史化的现象,这也可视为朱天心在捍卫个人记忆的一种策略,台湾通史序中的描写充实了文本“史”的方面知识,而《桃花源记》的援用则造成了对比的效果,密集的桃花源之文本,营造出一种紧凑的美学效果,制造了悬疑的氛围,武陵人找不到桃花源仅能在迷失的街头放声恸哭,而桃花源在哪里?竟然远在遥远的异乡——日本。朱天心在其小说中,不断地透过各种文本的指涉来控诉台北的毁坏。此外,作者更以川端康成《古都》中的千重子与苗子来暗涉主角——“你”与A。A与“你”的记忆形成了互补作用,A与“你”在《古都》呈现视觉交换的具体效果,文中“你”,穿梭于四十岁、二十岁以及十七岁之间,小说中的“你”透过对A的回忆描摹召唤了青春记忆,分别多年以后,“你”与A相约在异乡的古都见面,而“你”像是经历一场私密的回溯仪式般的支开了女儿与丈夫单独前往,而“你”在古都中最担心的是A与“你”之间在岁月流转下所面临的改变,现实的“你”因为生过小孩以及年龄的增长,身上开始出现令“你”嫌恶的气味,在各种不安下,“你”选择回到岛国,在刻意陌生化的观光客身份的掩饰下,重温了“你”与A昔日甜蜜亲昵的过往,在“你”的回忆中不仅召唤“你”的年轻记忆,同时也召唤青春时期的A,小说中并援用了川端康成《古都》中的段落,以《古都》文中不知是“千重子化身的苗子”还是“苗子化身的千重子”暗指“你”与A,此外并利用文本的互涉对照了京都与台北,并在记忆的断缺之处相互融合解释。A成了“你”的化身,而“你”与A俨然是被撷取的两个空间的影像。(19)朱天心捕捉了两个空间影像,以交错的方式不断地重现对照,也营造了对话的效果,A是“你”青春时期的表征,也是记忆青春的第一镜头,“你”与A在彼此的惦念、与躲藏中扮演了对方的镜像,A是“你”的化身,而“你”也是A的化身,在回忆中重演了暧昧的青春记忆,其实,流浪在外冒险的A满足了“你”屈身小岛的抑郁以及无休止的远游想象,而栖身小岛的“你”同时也是远放在外的A终极乡愁的怀想对象,A与“你”仿佛孪生姊妹般的相互迢望补足自身的缺憾,A与“你”在少年的青春中记录了一座城市,“你”透过青春记忆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建造,但在同时却也记录一座城市的毁败。 朱天心运用了记忆重建历史并记录了两个城市,一个台北,一个京都。制造了对比的效果,然而在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作者透过文本的爬梳却也重新建构了一座城市,属于青春与梦想的“原乡”。 五、结语 朱天心的小说的意韵在于疏离中透着一种热切,透过各种知识的填充表现出冷静的文字效果,然而其间却隐藏着作家积极的想望,尤其是《古都》一文中所触及的尖锐话题与情感,小说中包含的历史张力极具深意,透过历史、记忆来讨论朱天心的《古都》书写,不仅进一步深入外省第二代的内心世界,透过书写所展露的焦虑与忧伤,都清楚地道出作家纠葛复杂的心境。在历史与身份认同的找寻过程中,《古都》中的叙事者“你”透过时空的错置,说明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在这座海岛寻求身份认同的吊诡,即使现实生活中的“你”是一位迷路的武陵人,是一缕寻找不到乌托邦的茫然幽魂,但是透过记忆的重塑,“你”坚持每个的记忆的有效性,因此得以在想象中召唤青春的桃花源。在朱天心的书写中,作家以各式的文本与对话要求读者的参与,同时与年轻的自己对话;充分展露了后现代叙事的跳接手法,也打破了传统以线性时间发展的不可逆的书写模式,在跳跃的空间中开展了新的陈述话语,并且有效的以空间的图像推展逆转时间的流逝,于是“你”、A、台北与京都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互文系统,《古都》也在复杂的多元指涉中被不断地解读讨论着。 注释: ①⑥(13)(15)见《近代の日本と台湾报告集》,27页,日本社会文学会主办,2001年12月15、16日。 ②从《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到《我记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以迄《古都》可以清楚地看见朱天心笔致的转变轨迹,从浪漫幻想的小说经营转而正视现实与政治,正如黄锦树所言,是一种“从大观园到咖啡馆”的书写改变,而这期间,朱天心的历史危机感的加深正是其书写模式转变的极大动因。参见黄锦树《从大观园到咖啡馆——阅读/书写朱天心》,收于《古都》,235—282页,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版。 ③胡衍南提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篇小说的客观价值在于:“算是一个历史的‘纪录’与‘诠释’吧,特别是在大伙的‘记忆’正逐渐被现实侵蚀、而有遗忘可能的此刻。”全文参见胡衍南:《舍弃原乡乡愁的两个模式——谈朱天心、张大春的小说创作》,载《台湾文学观察杂志》1993年第7期。 ④王德威称朱天心在小说中夹叙夹议的议论口吻为“论文体”,即作者在叙事内容与对象中经常以后设口吻进行叙述与理论论述。见王德威:《老灵魂前世今生——朱天心小说》,收于《古都》,10页,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版。 ⑤历史的客观论者注重“视点”,认为一种过去历史的事实早就存在并已被完整存封在史料中,只要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态度,不主观,无偏见,便能够将之释放出来,客观派史学主要在将“过去”框住,不允许任何人以自身的角度改变框架,从这点出发,历史的真实、可靠仿佛有了凭借,如此,历史方使人放心。然而,历史相对论者则不以为然,他们批判所谓的“客观”,并将强调的重心放在“视者”的身上,宣称一切的历史皆来自于视者。然而,不论是客观派史学抑或相对派史学,都引来争议。详见李纪祥:《时间历史敘述——史学传统与历史理论再思》,31—38页,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版。 ⑦朱天心:《古都》,213页,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版。本文所援引之《古都》原文,盖以此版为主,以下引用皆不另作注解,仅标明页次。 ⑧有关于台湾与中国的复杂历史认同问题,参见王明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失忆》,载《历史月刊》105期,35—40页,1996年10月5日。 ⑨关于集体意识的形成与认同,详见王明珂:《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载《当代》91期,6—17页,1993年11月1日。 ⑩张颂圣归纳朱天心的小说书写中所透露“衰老”气息的肇因为:“旧的生活方式和痕迹在眼前快速消逝,未曾经历战乱和贫穷的新人类贸然登场,当前主流论述颟顸政客对解严前文化积淀的全盘否定”,解释了朱天心书写中特有的无奈感。参见张颂圣:《绝望的反射——评朱天心〈古都〉》,见《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214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梅家玲在研究眷村文学时提出:“眷村第一代居民原来自大江南北,南腔北调的方言,加上风味各异的饮食习惯,交错出地域上的‘广度’;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的共同战争记忆,则延展出时间上的‘深度’。……整个眷区,是‘家’的延扩,也是‘国’的缩影,强固的‘共同体’情感,遂于焉凝塑。此时,‘国’自然是原应笼括秋海棠版图的中华民国;真正的‘家’乡,则总在‘还是要回去’的遥远海峡彼岸。”见梅家玲:《八、九○年代眷村小说(家)的家国想像与书写政治》,收于陈义芝主编:《台湾现代小说史综论》,388—389页,台北:联经出版1998年版。 (12)王德威提出:“‘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即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见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250页,台北:麦田出版1993年初版。 (14)王德威说道:“正因为朱及她的人物意识到大历史的了无理性,他(她)们对生活的细节,对记忆的缝隙,愈发变本加厉的摩挲思辨。”见《老灵魂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说》,收于《古都》,12页,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版。 (16)所谓的陌生化也就是使人们本来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把大家司空见惯的事物置于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来考察,这样引发人们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参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76页,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7)唐小兵:《〈古都〉·废墟·桃花源外》,收于刘继蕙、周英雄编《书写台湾——文学史、后殖民与后现代》,391—401页,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版。 (18)(19)骆以军认为透过朱天心这种知识堆砌的书写模式使得:“阅读中可以在层层遮覆的叙事陷阱中猜疑、耽溺、一种极度夸大极度华丽后的怅然之感,一种对庞大资讯崇敬并虚无的复杂情感。”见骆以军:《记忆之书》,收于《古都》,36、41页,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