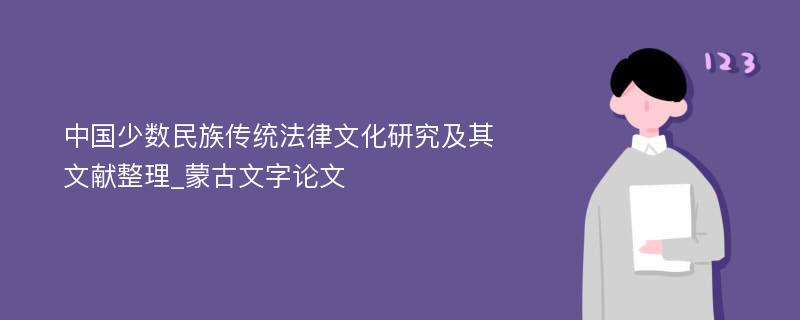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的研究及其文献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文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文献论文,民族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2)01-073-0009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是古化的还是近代的各个民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各具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宛如一颗颗明珠,构成了祖国传统法律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与整理这份宝贵遗产,古为今用,一直是法学界、史学界、民族学界不断探索并力求实现的目标。本文谨对迄今为止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法律文献、以及对其所作汇编和整理情况作一简要的论述。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其先民就开始制定刑律。《尚书·吕刑》中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爱始淫为劓、刵、椽、黥。”该记载表明苗族的先民早就使用肉刑,并参与了中国早期法律的制定。兴起于战国末期,兴盛于秦汉时代的匈奴,是中国历史上北部草原游牧民族中第一个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代表,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从父权制确定以来,单于的职位和权力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继。下有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级官职,也是由一些显贵氏族或家族世袭。匈奴有自己较为完整的国家政权机构,分为三个部分:单于庭、左贤王庭、右贤王庭,分别管辖匈奴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匈奴有刑律,由辅政的骨都侯主断狱讼。“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满十月,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北魏时期,历朝皇帝都很注意法制建设。自道武拓拔珪时修订律令,后六代皇帝八次修律。特别是孝文帝时期的法律修订与改革,规模较大,效果显著,最值得称道。他“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先后两次修律,是为《北魏律》。孝文帝配合政治上的革故鼎新,改变过去法律中繁复严酷的条文,从简从轻,把“恕死徙边”作为定制,改诛连之法,废止某些野蛮刑讯,并“遣囚赴耕”。他还整顿司法机构,惩办枉法官吏。魏孝文帝的法制改革既承袭了汉、魏、晋律的传统,又依据民族政权发展的需要作了权变,以期补偏救弊,呈现出“综合比较,取精用宏”的特点。北魏律典溶入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法律精髓,对后世法律的制订和实施影响很大。
公元六至八世纪,突厥民族在金山南麓、漠北高原曾两度建立突厥汗国。在汗国内,可汗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下设由贵族世袭的叶护等凡二十八等各种官吏。汗国还有相应的刑罚、税收制度。七世纪初,回鹘兴起于漠北,中期以菩萨为最高军事首领。“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内部齐肃”。由此可见回鹘早期法律之一斑。八世纪中叶建立了强大的回鹘汗国。历回鹘十五世可汗中,有十一世接受唐封号,但仍设置自己的政权机构,行使自己的法律,沿袭自己的习惯。作为薛延陀属部之一的黠戛斯于九世纪中期国势强盛,设有君主(阿热)和官宰,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其文字语言,与回鹘正同。法最严,临阵桡、奉使不称、妄议国若盗者皆断首;子为盗,以首著父颈,非死不脱。”七世纪末,在我国东北牡丹江上游,建立了以靺鞨族为主体民族的渤海王朝。渤海国延续二百余年,“为东海盛国”,有着比较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它接受唐朝册封,并且“一准乎礼”,建立起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和法律道德规范。其政治机构中,可毒夫(又称圣王、基下)是主宰一切的国家首脑,下设三省六部。在忠、仁、义、智、礼、信六部中,礼部相当于唐的刑部,掌管法律、刑狱、审复等,是王国的最高法律机构。
地处西北边疆塔里木盆地南端的于阗、鄯善国,虽皆先后臣属于汉、魏、晋、北魏王朝,但亦建立了整套的国家机器和较为系统的法律制度。据出土的法卢文书记载,鄯善国王代表着法律,集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刑罚种类比较简单,较少死刑,又因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为发展贸易,法律对交换、贸易加以保护。
公元七世纪,吐蕃在我国西南部兴起,其首领松赞干布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藩王朝。当时吐蕃已有较为系统的成文法,用创制不久的吐蕃文字行文发令,并制订了六种大法。墀松德赞时期又修订完善法规,有所谓《九双木简》、《真智五木简》、《三审判木简》及《流动木简》等法律。根据仅见的片断文献记载,可知吐蕃法律也是比较完善的,具有诸法合体特征。吐蕃法律保护等级森严的贵族统治制度,刑罚严酷,刑网密布,往往轻罪重罚。其中还保留有某些原始社会的残余,如部落会盟、同态复仇以及类似神判的习惯法。八世纪,在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地区,乌蛮、白蛮等民族建立了南诏政权。南诏以唐朝的行政机构为参照,并部分采借吐蕃的法律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及其政治法律制度。国王为南诏,下有内阁首领称为清平官,还有军事高级将领大军将等。其下有相当于唐朝六部六曹,其中刑曹主管司法刑律。又设断事曹长,主管缉拿推鞫盗贼。后六曹改为九爽,其中管理刑罚的称为“罚爽”。
十世纪初,契丹族在我国的北部兴起,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王朝,并用创制的契丹文字制定了成文法,以北方民族的习惯法吸收汉律而制成《决狱法》,并设置夷离毕以决狱讼。太宗时因其境内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同而设置北、南两套官制。北面官制为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而设,南面官制为治汉人州、县而设。辽代前期法律不仅“同罪异论者盖多”,在民族待遇上也有很大差别,契丹人和汉人犯法处罚轻重不同,且刑法严苛。十世纪中后期,辽朝修订法律,改弦更张,逐渐趋于宽平,调整了民族关系,改变了契丹人同罪异论的特权,更加趋同汉律,后以辽兴宗重熙五年(一零三六年)所订《重熙新定条例》为基础,屡经重订增补。
西夏于宋代称强西北,与宋及辽、金成鼎足之势。其统治民族党项人早期“俗尚武力,无法令”,北迁后,社会发展很快。其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案上常置法律书,可见当时已有成文法。党项族内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元昊在全国仿中原制度,设十六司,分理六曹,其中有刑部,为审刑司。西夏中后期法律更为完善。仁宗天盛年间(公元一一四九至一一六九年)修订律令,制成《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这是一部诸法合体的法典,目录外共二十章。它既吸收了唐、宋法的重要内容,又有自己独特的体例,并且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在行政法方面,将行政机构设置、职官定员,官吏升迁黜免都载入法典;在军法方面内容具体、丰富;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有关畜牧方面的律条规定颇为明细;诉讼程序是官府接到呈诉状后,将犯人押解到狱中,如审讯时不招供,予以严刑拷打,使其认罪服法。这部重要法典以西夏文刻印。但夏亡后,已久不传于世,二十世纪初才出土于古城遗址。这是保存至今的、最古的一部少数民族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律令》之后又编成了《新法》一书。神宗时有《光定猪年新法》的编纂。
十一世纪初,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完颜部发展较快。由于女真族原无成文法,“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部落联盟首领石鲁曾改革女真旧俗,为制定法律,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二十世纪初,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确立了新的法制。金初法制保留有氏族社会某些平等原则,刑赎并行。以后多次修律,如熙宗皇统年间,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制,参辽、宋法,成《皇统制》,此为金朝的第一部法典,亦是其统一法制之肇始。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章宗时注重法典修订,制成《泰和律》,是为金朝是完备之法典。金朝法律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同时具有其民族特点。如辽代刑法有杖、徒、流、死四刑。金因地理条件所限,无法流放边地,便只有杖、徒、死三刑。但女真人打伤与杀死汉人、契丹人无罪,而汉人对女真人稍有触犯,便处死刑。金律不仅行于当时,也影响于后世,在少数民族法制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居住在我国西南边疆的傣族,随着社会的发展,于十二世纪由首领叭真统一各部建立孟泐政权,受中央王朝封号。为维护封建领主地位,制定了封建法典。用老傣文保存下来的《芒莱法典》是十三至十四世纪制定的。这一法典及其他法律如等级法规、民刑法规、地方公约、罚款和赎罪规定等在西双版纳地区长期保持法律效力。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了漠北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颁布了“札撒”(法度)、军断刑狱、词讼和掌管户口,征收财赋,后逐渐形成成文法。至世祖忽必烈时期,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忽必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使国家机构日臻完善,中书之下设六部中,其中设刑部掌管刑狱,另设宣政院掌管释教和吐蕃事宜。元初曾沿用金律,世祖时始编法典,成《至元新格》,后世又多次修订,都起到法典作用,但未能达到完整系统。元初蒙古的断事官依旧保留,执掌蒙古、色目、汉人词讼,后只处理蒙古事。蒙古统治者把全国各地各族分为蒙古人、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在法律上有许多对四等人不平等的律条,如汉人殴死蒙古人处死,而蒙古人殴死汉人只断罚出征。元朝的民族政策前后有所变化,有的政策在团结、融合其他民族、特别是色目人上层集团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大部退至长城以北,明王朝与蒙古封建主开始长期对峙,为维护蒙古封建领主的统治,解决内外种种矛盾和纠纷,保证佛教的崇高地位,一些蒙古族大封建主或单独、或联合制定了一些重要法典。其中主要有十六世纪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掩答汗主持制定的《俺答汗法典》,明朝后期漠北喀尔蒙古领主所订《白桦法典》,明末清初喀尔喀和卫拉特封建领主们会盟时制订的有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卫拉特法典》有一百二十一条,其中有政治、宗教、社会、家庭、婚姻、放牧、狩猎、战争、财产等方面的法律。他们对犯罪多用的经济处罚,不强调刑罚。这些法典不仅是研究蒙古族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十六至十七世纪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问题的极其难得的文献资料。
十七世纪初,居住东北的女真人进一步发展壮大,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女真各部的统一政权后金,在法律设置方面渐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随着罪名和刑名的发展,刑法原则逐渐充实和明确。其中也反映出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如满族汉族同罪异罚、满人可议功减罪等。此外还保留有某些原始民族制的残余。后来他们仿明朝设立包括刑部在内的六部,《大明会典》成为他们处理政事的主要依据。满族入关后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大体沿用《明律》,掺合满汉条例而成。后又多次修律,乾隆时期颁行《大清律例》。清朝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政策,但维护满族优越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逐渐削弱,对少数民族司法管理相对加强。清朝设立了专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理藩院,还制订了维护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单行法律《蒙古律》、《番律》、《回律》等,认可了盛行于南方山地许多民族地区的“苗例”,从而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管理。
据上所知,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源远流长,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法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各民族法律的多样性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亦即说,这些少数民族法制带有明显的民族、地方特点,反映出各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形态、政治组织、管理手段、文化习俗等。有的随着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变异性,有的则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法律和中原王朝法有密切关系,往往互相影响和吸收,多有明显的内在发展联系。在我国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在法制建设上都曾起过重要作用。所谓中国法系,不仅包括中原王朝法律,也应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法律在内。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汉族和少数民族交往的增加,少数民族参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意识的加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与地位越发显著。
二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少数民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独龙、怒、傈僳、德昂、阿昌、佤、景颇、拉祜、纳西、基诺、黎、布朗、鄂伦春、赫哲等十五个民族或这些民族的部分,原始社会色彩颇为浓厚。大、小凉山的彝族处于奴隶社会。西藏的藏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处于农奴社会。壮、布依、侗、苗、瑶、土家、畲、白、回、维吾尔、蒙古、满等三十多个民族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由于各族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不少民族仍然保留着与本民族社会形态相应的法律或习惯。这些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特征的传统法律形式和内容。各民族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法律并存,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下仅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几个民族的传统法律作一简单介绍。
居住在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依靠长期形成的习惯来管理社会。他们从生产资料占有、劳动组织、猎物分配到财产继承,从婚姻、丧葬到宗教、禁忌、血族复仇,从氏族到个体家庭,都有一套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对违反习惯的成员,一般由氏族长、家长进行说服教育,重者则受棍刑乃至绞刑。后来有些案件如盗马、杀人等,逐渐交官方处理,但仍有很多问题在氏族内按传统习惯处理。这种官方加氏族内部处理问题的情况,是与鄂伦春族社会处于过渡状态的村社制度阶段相适应的。
生活在云南西北部的独龙族,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地保留有父系氏族和处于解体阶段的由氏族内近亲成员组成的家庭公社。在贡山地区,独龙族的习惯法主要是处理时有发生、处理较轻的男女通奸和极少发生、处理较重的盗窃问题。处理时或由当事人和解或由老人调解;间或用神断,如倘若被告不承认则捞油锅以决胜败。但他们有时也向土司衙门告状。居住在高黎贡山西部的独龙族则与此不同。在大家庭里,除个人首饰及武器外,一切财产皆为公有。贫富差别小,有互相帮助的习惯。则于绝少偷窃现象,也就没有保护私有权的习惯法。内部少交换,契约关系少,借贷无利息。个人和村寨间的纠纷械斗,双方死亡人数相等则人命相抵,如一方多死了人,另一方则要赔偿命金,命金由全村人平摊。
在云南省西南地区的位祜族,大部分处于不发达的封建地主经济或封建领主经济阶段,部分还残存着大家庭公社组织。这些地区有明确的村寨界线,村寨有较强的凝聚力,是一个紧密的集体。成员间能团结互助,村社公共劳动由各户轮流担任。村社有寨规,是各成员必须遵守的习惯法。每逢过年要开村社大会,称为“迪卡节达”,成年男女都可参加,全村吃一顿团结饭,选举新的村社头人。按原始民主习惯,村社成员有选举权,也有罢免权。会上还要定出寨规,如不准吸鸦片、不准娶妾重婚、不准偷盗、不准懒惰等。同时还对违反寨规者订出若干处罚条款。这种习惯法形式带有原始民主色彩,但头人已经有了管理村社事务、处理案件的权力。
与拉祜族交错或毗邻而居的佤族,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尚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形态,其习惯法为“阿佤理”。佤族各村寨都有世袭或选举出来的头人,其条件是能说会道,生活经验丰富,善于调解纠纷,作战英勇或是打猎英雄、家境富裕者。数小寨组成大寨,涉及全大寨的事和处理重大纠纷,头人不能专断,要由全寨群众商议决定。头人(窝朗)的职责之一是召集会议、调解纠纷、执行决断。巫师(魔巴)是解释习惯法的权威人物。抄家是佤族习惯法中强有力的手段,用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与佤族类似,近代的景颇族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农村公社残余,头人、山官管辖一个农村公社。它是由若干村寨组成,每一村寨还有头人协助山官管理事务。景颇族的习惯法收“通德拉”,“通德拉”就是山官及头人维持社会秩序、处理公社各项事宜与纠纷所依据的法律。他们的习惯法往往与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具有很大的约束力。
在典型的凉山彝族社会中,虽然没有出现国家这样的政权组织。但是,作为民族机关的家支却起着政权的作用,维护着其统治秩序,家支头人作为奴隶主代表行使职权。彝族奴隶社会长期适用习惯法,彝语称“节威”(制度之意)。所有的人被严格地分为四个等级,即兹莫、诺合、阿加、呷西,习惯法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高低,维护奴隶主的等级特权和对所属奴隶的剥削压迫,保障兹莫、诺合的尊严和人身不受侵犯,保障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凉山彝族的有些地区还没有司法机关和监狱。
聚居在中国西财边陲的傣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历史阶段,长期使用本民族的习惯法。“刑名无律,不知鞭挞,轻罪则罚,重罪则死”,“其刑法三条,杀人者死,犯奸者死,偷盗者全部处死,为贼者一村处死”。二十世纪,首领叭真统一各部建立勐泐政权,随后的历史代宣慰司和勐级土司为维护封建领主地位,颁布了一系列封建法典,如西双版纳傣族的《民族法规》、《礼仪规程》和《孟连宣抚司法规》等。这些法规体系完备,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关于财产所有权、债权方面,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规定,也有犯罪和刑罚及诉讼方面的规定。其中以《民刑法规》最为典型。
在苗族地区,基本上是按宗支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叫“立鼓为社”。各鼓社均有自己的民主议事制度,根据古理和传统习惯制定规约。这就是发展到后来的“议榔”制度。“议榔”在湘西称“合款”,在云南叫“丛会”,黔东南称“议榔”。榔规款约就是苗族的习惯法。苗族的习惯法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过去都是口头传诵榔规,民国前后则用汉字记载于石碑、木牌上,立于寨旁路口,然后杀一头牛或猪。牛拴在坪地中央,人们围在四周,寨老念毕“议榔词”后,把牛杀掉,每户分一块肉,表示牢记榔规。他们饮血酒盟誓,表示由衷遵守。对习惯法的称谓,各地也不尽相同。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苗族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事宜的“发财岩”,专门管治偷盗事宜的“禁盗岩”,专管婚姻纠纷的“女男岩”。从江县孔明乡则称刻有习惯法条款的石碑为“民法”。广西苗族通过“埋岩会议”,一般是把一块平整的石碑的三分之一埋入土中,碑上刻有大家商定和必须遵守的条规。违反者要受到处分,如罚款、戴高帽游街、活埋等。明清时期,苗疆各民族的习惯法经过长期的演化,逐渐丰富起来,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苗例”。“苗例”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程度等各个方面。经过中央王朝的认可,“苗例”在苗疆地区长期适用。
侗族虽然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阶段,却仍然存在原始社会的明显痕迹。例如,他们仍普遍存在村社会议制的残余——款。侗族的习惯法源本为“约法款”。约法款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款条,而款条又分别表现为“款碑条”和“款词条”两种形式。款碑是早期款组织起款时树立的一种特定石碑。这种石碑一般都立于款坪中,日后的讲款仪式和执法仪式都会在此碑前进行。款碑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早期的款碑不刻文字,汉字传入该地区后,才以汉字刻入。款词条是侗族习惯法的主要形式。原始的款词条由款首聚众共商,款首当众发布并付诸实施。它是一种立石为碑的盟诅要约,故有人称之为“石头法”。这种石头法最初较为简单,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表达形式。由于当时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无法将有关条款用文字记录下来,不利于款众掌握。款首们为了便于款众记忆及在发布时使款众兴奋,于是采取词话形式,把约法编成歌词,日夜吟唱,世代相传。后来,这些款词被侗族文人用汉字记录音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成了侗族习惯法的主要成文法。近年来,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均已整理出版流传于当地的约法款词。其中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马安寨老款师陈永彰保存有一部款书手抄本。该书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对款规款约的记载较全,其中约法规有十八条,共七百五十六句。
与苗、侗等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传统法律文化相似的是广西瑶族。过去中央王朝或在这里建立土司制度或直接设立州、县进行统治。但在瑶族内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统治势力尚未渗入的边远山区,还存在具有原始残余形态的瑶老制、石牌制等。瑶老的产生或经过民主选举,或自然形成,或由神判决定。有关生产、祭祀、民事纠纷、刑事判决、抵御外来侵略、滋扰等,都由民主讨论决定。大家订出共同行动的约法,由瑶老负责执行。有的地区把共同议定的公约条文,刻在石板上,或书写在木板、纸上,竖立或贴在集会的地方,要求全寨民众共同遵守,是为石牌制。涉及整个大瑶山村寨利益时,要召开总石牌会议,共同商讨、决策,随着大瑶山瑶族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近代中华民国政府的势力不断深入,政府强化县、乡组织形式以便于统治,石牌制原始民主色彩逐步减弱。
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在近代已经有一部分进入比较发达的地主经济。他们以当时政府的保甲制度结合原有的伯克(乡、镇)、于孜巴什(村长)、阿克沙卡尔(乡老)统治制度对维吾尔族人民进行统治。此外,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和“宗教法庭”也起着社会控制的核心作用。他们的宗教法庭大多设于乡里的集市,本身是宗教统治的权力机关,但又与保甲政权血肉相连。设有卡孜(法官)、艾兰木(审判员)、热依斯(检查员)、毛拉(文书)等。法庭的职责是维护伊斯兰教教义、处理婚姻纠纷、财产继承有土地买卖问题,并有关押人三至五天的权力。卡孜(法官)、艾兰木(审判员)由县政府任命。有的维吾尔族地区地主经济初步发展,还保留有落后的封建庄园制度。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和加(封建统治者)庄园成了“化外”之地,政府和庄园内的依附农民不发生直接关系,行政事务均与和加管家交涉办理,民刑案件也由和加自行处理。和加们为了便于统治,还规定了各种礼法,对违反礼法者要加以惩戒。
藏族分布地区广大,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在四川、云南部分经过改土归流的地区,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在县之下设乡、保、甲,乡保、甲长由藏族头人充任,政府为巩固和扩大在藏区的统治,采取“以教辅政”的政策,勾结上层喇嘛,管理包括诉讼等行政事务。在土司统治地区,各土司有一套司法机构,寺庙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施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各地一般无成文法,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但习惯上也有较为固定的司法范围。少数地区有成文法,如德格土司的“法律十三条”,毛垭土司的“十三条禁令”等。其法律维护农奴主封建所有制。凡抗拒土司、拒服差役、抗纳贡赋、拖欠债务者都要受到严厉惩处。不同等级的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比如头人和喇嘛的命价至少比农奴高出两倍以上,土司和上层喇嘛的命价则更高。农奴主的司法手段野蛮残暴,他们设有室狱、水狱,牧区有穴狱、墓狱,刑罚中仅肉刑就有鞭笞、吊打、截手、割鼻、挖眼、剁脚、抽脚筋等。一般案件由村长处理,较大案件由头人或土司审理。西藏地方封建政权由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两部分构成。噶厦下设协尔帮勒空,专门管理刑事案件,西藏地方政府使用沿用了数百年的法典。法典维护农奴制度,保护农奴主阶级利益,根据法典规定,可“按其情节不同,或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还有很多酷刑,未列在法典之内。政府的司法官员在处理案件时,公开收贿赂,任意颠倒是非,专横跋扈,因此冤狱比比皆是。此外,藏族地区也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神判制度。
总的来看,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异彩纷呈,历史悠久,许多民族的法律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间社会经济、文化互相交往不断加深,他们的传统法律也有趋同特征。
三
与各少数民族丰富而别具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相对应的,是他们有着极其丰富的法律文献资料。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献资料,大多散见于以其本民族文字或汉文记载下来的文献资料里。其中有古籍文献,也有当代的文献;有较为系统、完整的法典和法规,也有零散的习惯法和司法文书资料;有成文的文献,也有口碑资料。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内容广泛,种类繁多,卷帙浩繁。从内容上看,包括历史、政治、哲学、思想、法律、军事、天文、地理、语言文字、生产技术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从形式上区分,主要有文字记载的和口头流传的两大类。其中文字记载的又包括用各种民族文字(含民族古文字)和汉文记载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一些古代少数民族和现代少数民族的先民曾分别使用过法卢文、于阗文、焉者——龟滋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这些民族古文字的古籍也很丰富,如契丹文的《萧孝忠拇指》,女贞文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大金得胜陀颂》、西夏文的《天盛年新定律令》、《音同》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常重视整理和出版民族古籍的工作,专门设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办公室,组织人力物力,整理出版了或正在陆续整理编辑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古籍,发表了大量民族古籍研究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整理出版各种文字的民族古籍近一千种,其中蒙古文的一百三十余种,藏文的一百六十余种,维吾尔文的二十余种,彝文的五十余种,朝鲜文的二十余种,哈萨克文的十余种。北京民族文化宫复制出版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和英文、日文、梵文的民族文献五百余种,三十余万册。许多口头流传的古籍已经记录下来或者进行了录音。在已经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种,有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和史书。历史方面的有满族的《满文老档》、《八旗通志》,蒙古族的《蒙古秘史》、《黄金秘史》、《大黄册》、《蒙古源流》,藏族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巴协》、《红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彝族的《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傣族的《孟连宣抚史》、《西双版纳历代编年史》,回族的《回族和中国伊朗伊斯兰古籍资料汇编》,哈萨克族的《乌古斯汗传》,锡伯族的《亚奇纳》,白族的《词记山花》、《白古通记》,纳西族的《东巴经》等。文学方面的有闻名世界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萨格尔》、《江格尔》、《玛纳斯》。这三部史诗均已成书,并有几种文字的译本。仅《格萨尔》藏文本就出版了六十二部,发行量达三百多万册。还有彝族的《阿诗玛》,哈尼族的《木地米地》,苗族的《仰阿沙》,维吾族的《福乐智慧》,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壮族的《今是山房吟草》,朝鲜族的《春香传》、傣族的《俄并与桑洛》,瑶族的《评皇券牒》等。
少数民族的口碑文献,即口头流传、世代承袭下来的文化遗产,数量十分丰富。如侗族的《创世歌》、哈尼族的《创世史诗》,土家族的《摆手歌》,黎族的《祖先歌》,畲族的《高皇歌》,景颇族的《凤凰田》,水族的《古歌》,赫哲族的《伊玛堪》等,内容有神话故事、民族历史、民族起源、民族迁徙、民族交往等。上述由国家组织的种种文化抢救和搜集工作,尽管没有专门就习惯法一项进行研究,但里面包含了大量有关于此的内容和资料。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年,中国政府组织广大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针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田野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包括民族来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现象在内的社会历史状况。据不完全统计,记录的各种资料有三百四十多种,二千九百多万字,整理的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有一百多种,一千五百多万字。此外,还拍摄了一批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的科学记录影片和图片,搜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物。在此基础上,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七年,国家民委先后组织中央和地方民族研究人员和民族工作者三千多人,进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共编写出版三百九十八本,九千多万字。在这些简史、简志中,或多或少地都涉及到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或方面。
同时,中国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亦予充分尊重和重视,组织对各民族的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保护和研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中国各级政府以及文化艺术部门组织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专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工作调查,抢救、搜集、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投入巨资,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深入民间采风,搜集整理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乐曲继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等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从县(旗)到地区(自治州)、市,再到省、自治区,级级选送。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编十卷,共编纂三百卷,全部出齐约四百五十册,总计约四点五亿字,正在分卷陆续出版。
在对少数民族的传统历史与文化资料综合发掘与整理的同时,一些学者和机构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专题性调查与研究,比较集中地收集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资料。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工作日渐趋强。较为著名的学者及其作品有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云南民族古籍从丛书》之一、《瑶族文库》之一,云南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杨锡光、杨锡、吴志德整理译释的《侗款》(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之一,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出版),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之一,广西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周润年与喜饶尼玛译注、索朗班觉校的《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刀永明、刀建民、薛贤的《孟连宣抚司法规》(云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广西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黔西南州志办编的《黔西南布依族乡规民约碑》(内部刊印)、张济民主编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苏联E·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的《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一至七章)》,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罗致平编译的《一九四零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西北组一九七七年内部刊印)、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刘尧汉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等。
长期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为人们所忽视,有关方面的论述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近期(一九七八年)以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及这门兼跨民族史学和法学领域的学科,使这块“不毛之地”渐得开垦。其中藏族,蒙古族(包括卫拉特蒙古)、哈萨克族等民族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还有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一部少数民族法典——《西夏天盛律令》进行深入探讨,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满族法制史的研究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从努尔哈赤肇造基业起,满族由习惯法过度到成文法的过程,以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法律思想、立法路线、各项法律的制定和审判制度等等,不仅揭示了满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建立饶有特色的“参酌汉金”的法制历史实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满族入关取代明朝、统治中国不是偶然的。另一个是阐述了满族入关、君临天下后清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立法原则、法律形式、司法管辖以及具有民族特点的审判方式等问题,特别是论述了《理藩院则例》、《回例》、《番例》等法典的丰富内容(注: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十年[J].民族研究,1998,(5).)。另外,关于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著作和也不断问世。范宏贵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出版)、师蒂的《神话与法制》(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高其才的《中国习惯法论》、夏之乾的《神判》(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邓敏文的《神判论》(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宋兆麟的《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杨怀英、赵勇山等的《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法律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杨怀英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徐中起、张锡盛、张小辉主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出版)等。至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论文则更是数量很多,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此外,许多研究民族的著作也往往有包含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
四
尽管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宏富、特征各异,足以对说明法理学等法律科学中的许多重大和根本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迄今为止,在如何收集、整理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的法律文献方面仍有许多空白点与巨大的潜力。一些口承的法律法规需要记录和整理,许多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法律法规需要翻译和整理,不少散落、遗失在民间的少数民族法律法规需要收集与整理。此外,在国内尚无一本将这些弥足珍贵的法律文化资料汇编出来的著作。所有这些,都需要学术界的不断努力与合作来完成。
收稿日期:2001-10-8
标签:蒙古文字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习惯法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