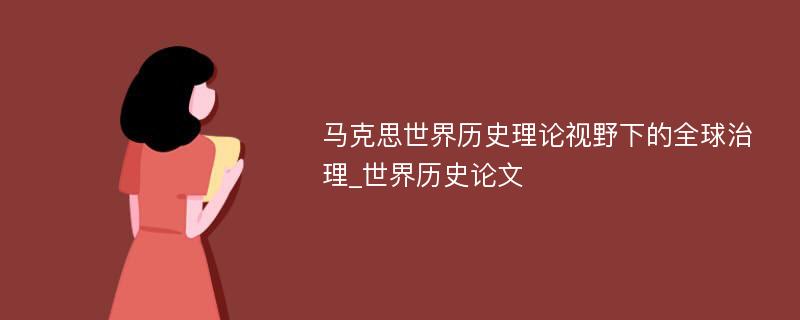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全球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野论文,世界历史论文,理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2-10-09]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1-0031-19
一 引言
世界历史理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在古希腊时期,世界历史观念就已经在众多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萌芽。素有“历史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中就展示了一种朴素的世界历史观念。到中世纪,奥古斯丁(St.Augustine)等著名神学家将人们引向了另一种世界历史观念之中,他们借上帝之身超越了民族历史观念的狭隘性而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并确立了历史进步观念、上帝目的论和历史时空观念。①后来,但丁(Dante Alighieri)则将世界历史视为人类自身智力与潜能的发展过程,把中世纪颠倒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摆正过来,把神意的世界历史观念还原为人类本身的创造活动,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此后,世界历史观念又历经了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哲学提升”、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的“文明化的进化”、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人道主义世界历史范式的确立以及黑格尔(George Wilhelm Hegel)把世界历史归结为“世界精神”②的漫长过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变革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一次厘清了“世界历史”这一概念,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特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其空间内涵不包括16世纪前各民族、国家、地区相对隔绝、彼此孤立而尚未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④马克思抛弃了中世纪把神置于人之上的世界历史观念,批判了理性主义把世界历史视为自由意识的进展过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吸收了包括但丁在内的人本主义世界历史观念,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科学的重构。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多部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用这一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认为人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实质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⑤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生产使用价值的特殊劳动开拓世界历史,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才能真正开拓世界历史。而劳动从特殊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过程正是劳动的异化过程,也是资本形成的过程。资本在直接生产的过程中无止境地、盲目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使它必然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历史界限而开辟广阔的市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⑥马克思还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⑦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而且也使物化的社会关系成为束缚个人的枷锁。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不是为了个人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它才成为这样的产品,因而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诚然是表面的形式;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⑧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怎样开拓世界历史,而且也揭示了资本是怎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世界性控制的。这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全球治理。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全球治理的思想跟“世界历史”理论一样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但是,当今在探讨全球治理的思想源头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不得不提起的。
二 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与全球治理的源起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人们一般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一背景下而兴起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初学术界对“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界定。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后,为了解决国家间面临的安全困境,或者为了拓展疆土、扩充影响力而形成相应规则(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跨国家的治理开始出现。最早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推向学术领域的是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他虽然很少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但他从全球的视角来考察全球生活,并在这个层面上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术语。他认为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⑨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在其颇有影响的《全球大变革》一书中也谈到:“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⑩中国学术界引入“全球治理”的术语比较晚,但也都是基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试图建立全球性秩序而探讨全球治理的内涵。俞可平可以说是最早把“全球治理”的概念引入中国学术界的。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1)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解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内涵。
假若全球治理确实主要是指对国际秩序的追求而忽略其价值取向问题的话,那么全球治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出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即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被全球性的世界历史所取代的状况下就已经出现了。或者说,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是全球治理的前提。只不过当时的全球治理更多的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管理。既然全球治理是规则、秩序的跨国界影响,那么首先必须要有跨国界的关系的出现。没有这种关系就不可能有调节这种关系的规则和秩序。开启这种跨国界关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开始真正进入了世界联系和交往的时期。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两百多年间,人类才把被海洋隔开的各大陆,被沙漠、高山隔开的各文明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打破了世界联系和交往的闭塞性,使分散发展的区域民族史逐步转变为整体发展的世界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12)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也指出:“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13)不过,仅仅是地理大发现还不足以开启跨国家的关系,真正开启这种跨国界关系的是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占有,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资本的本性驱使着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从一国、一个民族内部拓展到整个世界。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大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率,因此,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4)起初这种联系是非常简单的、松散的,但后来随着资本运动的加速以及社会分工从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建立的这种联系逐渐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系。这种以资本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联系”就是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机制。
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资本主义“联系”为什么需要治理?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治理这一概念,但他在揭示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的过程中看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客观上要求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的治理。当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对此形成自觉,但资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充当着对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治理的一种“自觉”的工具。众所周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们的生产力水平不一样所决定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卷入“文明史”中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5)生产力发达的资产阶级往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则只能从属于前者。那些“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则只好听命于前两者的使唤和奴役。结果,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层级关系,或者说是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关系。资产阶级只知道无限占有剩余价值,并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全球治理结构。但是,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纽带是非常清楚这种全球治理结构的,并且在维系这种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生产力水平在资产阶级内部是严重不平衡的,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难以克服,这个矛盾首先在一国内部发生,但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落后国家的扩展和资产阶级对外的殖民掠夺,这个矛盾也迅速蔓延到所有“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于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制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16)因此,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就是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治理。然而,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的治理是无效的。这种无效治理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为转嫁危机而举行的大规模对外战争。
三 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及其实现方式
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但是,资本要真正充当治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一,世界历史进程是资本控制之下的一个进程。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遍及全球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其三,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客观上对全球治理产生了需求,同时资产阶级自身也对全球治理产生需求。
首先,世界历史进程是否是资本控制下的一个进程?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又是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开创的重要标志。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外化与实现,世界精神决定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付诸实施”。(17)但是,马克思却把人的发展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质与核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8)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和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民族性的限制,并“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而发展起来。(19)结果,“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20)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同时也把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从一国扩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覆盖的全球,进而使资本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实际控制者。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遍及全球并形成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就指出:“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只是一种不断超出自己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21)资本就是在满足这种欲望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为了这个目的,“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22)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一方面客观上充当了为世界历史进程创造物质基础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必须“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3)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所到之处,用资本的利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并迅速地不断消除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世界在经济、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24)
但是,这个“整体”实际上是存在着尖锐矛盾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必然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种矛盾的最终出路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掠夺世界市场的战争。从这一角度来看,资产阶级只是充当了开创世界历史不自觉的主体。但是,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进行全球治理,特别是要遏制资产阶级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另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地提升,但社会生产的无序化、无政府状态反过来对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产生了阻碍作用。其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次性的经济危机,而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使资本生产得以继续下去,资产阶级主观上也对全球治理产生了需求。
有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之后,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资本进行全球治理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虽然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但它是这一历史进程不自觉的工具。然而,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却充当了全球治理自觉的工具。资产阶级用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并由此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绝非是要把自己淹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而是通过这个进程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包括“把人的尊严都变成了交换价值”,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5)这样,资本就可以在它所开创的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
其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通过资本卷入到资本的“文明”之中。资产阶级首先在一国范围内把落后民族、落后的阶级纳入到资本化的进程之中,“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26)然后,资产阶级把一切资本化并非仅仅限于在一国范围之内,而是把它的资本化过程推向全世界。资产阶级将资本化推向全球的过程首先是借助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借助于便利的交通和新航路的开辟;其次借助于资产阶级价格低廉的商品。前者使资本走出了欧洲、走向了世界,后者则使资本在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落地生根,并且用有悖人性的方式征服了“野蛮人”。这样,资产阶级就“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27)在这个世界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8)简言之,在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中,一切都从属于资本。
再次,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资本。资本的力量使“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中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行各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29)一句话,资本摧毁了封建社会的一切藩篱并借助于新航路和新的航海技术而走向了世界。而与新航路的开辟相伴随的是资本通过血与火的殖民掠夺进行的疯狂的原始积累。新航路开辟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便开始以武力掠夺和商业贸易双重手段,将美洲、亚洲、非洲等变成了资本的殖民地。马克思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在迫使其他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采用殖民掠夺手段更甚于贸易手段。他指出:“在整个18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3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殖民掠夺的手段使资本的作用降低了,相反更表明资本的“迫使”作用更加增强了。因为一般的贸易仅仅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和资本对其他民族的自然征服,但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是无法满足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的无限欲望强烈要求资本的发展要有一个巨大的加速度。资本发展的这个加速度来自于哪里?只能来自于武力掠夺。也就是说,殖民掠夺是为资本的加速增值服务的,是为资本能够更快地“迫使”一切民族接受资本的支配服务的。不仅殖民掠夺是这样,包括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也是为了使资本增值获得这样的加速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31)由此可见,世界市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化,而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则使资本在加速度中实现了对世界市场和一切民族的控制。
最后,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要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但为了剩余价值而寻求一种畸形的秩序,资本正是借用这种畸形的秩序来进行全球治理的。毫无疑问,人类要追求一种理想的秩序,但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秩序呢?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他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指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糕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32)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判“理想秩序”的标准,即“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判”。(33)马克思主义的秩序观也认为,秩序必须确保是“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34)在资本把野蛮民族卷入之前,原来的社会原本是有一个秩序的。正如恩格斯在评述氏族内部的组织特点时所说:“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35)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产生了这样一种需求: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作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划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36)这里的“一般条件”所指的就是秩序。然而,当资本迫使一切民族进入资本化进程之后,无论是一国内部的秩序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秩序都是资本建立起来并为资本的增值服务的。在这样的秩序之下,不仅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被雇佣和被奴役的无产阶级最后只剩下把自己出卖给哪一个资本家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有。因此,这样一个畸形的全球治理秩序注定是不稳定、不安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7)
四 以资本为工具的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
国内治理机制是有价值目标的。俞可平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善治”的价值取向,并从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十个方面揭示了“善治”的价值构成。(38)同样,全球治理机制也是有价值取向的。在这一方面,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进行了非常有益的研究。他们不仅认为全球治理机制是有价值的,而且还从规范的角度阐述了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公共标准。他们认为,“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使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以互利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的准则和信息。它们能减少交易成本,创造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展示可信度的机会,克服背叛承诺问题,同时提供包括原则性的、和平解决冲突方法在内的公共产品”。(39)而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公共标准,他们提出了关于合法性的三种独立的标准,包括国家同意、民主国家的一致同意以及全球性民主。他们还认为,在价值目标的保证之下,全球治理机制能提供并维护国家无法供给的收益,这会进一步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40)托尼·麦克格鲁(Tony McGrew)认为,限制了人们更高水平的全球社会正义和人类安全,就是“扭曲的全球治理”。(41)因此,人权和民主就是作为支撑全球治理的价值大厦的核心价值。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蔡拓认为,“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42)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本身就是民主、正义、平等等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一种再现。尽管即便是在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这也不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客观上要求全球治理的过程要体现民主、正义与平等。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价值目标,这也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秩序。任剑涛认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制约全球治理观念导向的作用”,不过,“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所显现的实际状态来看,全球治理价值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各民族-国家自有渊源的文化价值基础上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也就相应地成为支持或瓦解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43)
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也有价值取向,但它体现的是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4)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以资本为工具的全球治理的非道德取向。资本要实行全球治理,首先是把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是单个的资本家和单个的工人,而是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表面上看,工人是自由的,即出卖给哪个资本家由工人自己决定,但资本家一旦雇佣了工人即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家就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从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的劳动资料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厂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隙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45)因此,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46)资本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目的是使资本获得最大的增值。
其次,资本实现全球治理的非道德取向还在于资本的殖民掠夺。通过圈地运动,西欧资产阶级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使原来的自由农转变为雇佣工人,于是自由农被资本化了。但是,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并不到此结束,而是为了资本迅速增大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47)为了这一目的,西欧资产阶级开辟了一条殖民增殖的血腥之路:残杀土著居民、在非洲与美洲之间贩卖黑人、在爪哇推行盗人制度等。所以说,西欧殖民主义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景”。(48)
再次,资产阶级所谓的“公共信用制度”实际上是资本全球治理非道德价值取向的有力证据。资本不仅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核心纽带,而且也是不同资本家(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的核心纽带。那么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的关系靠什么来调节呢?首先靠的是工业资本,工业资本借助于新技术和新航路而进行殖民掠夺并最终建立起工业资本霸权。工业资本因“美洲金矿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而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49)殖民制度又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工业上的霸权带来了商业上的霸权。因此调节不同地域的资本关系的工具很快被商业资本所取代。但是,商业资本最初并不能离开工业资本而独立存在,为此它还必须创造出新的条件来支撑其独立的存在。这种工具就是公共信用制度。在这一制度体系中,首先是国债,国债实际上调节着资产阶级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债发行人凭着等同于相同金额的公债券掠夺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财富,从而使自己大发横财;同时,以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银行,“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50)简言之,就是要把国民彻底榨干为止。随着国债制度产生的是国际信用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隐藏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累源泉,而且还是强化资本的国际殖民掠夺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本在国际间的相互借贷,实力弱小的资本因获得这种借贷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从而也就可以实施更残忍的殖民掠夺。也因为这种借贷,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贩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51)从国际资本借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仍然可以看到资本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取向,而且也看到了西方大国兴衰的一般历史过程。
不过,资本的野蛮性并不否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52)资本简单的概念之所以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因为资本内在地要求自然(nature)变成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自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53)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就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替代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54)具体而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至少表现为:其一,资本扫清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局部调整和改变。其二,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资本的最主要目的和直接动机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内在目的的外化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55)甚至可以这样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56)因此,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三,资本客观上为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改变资本原始积累时那种血淋淋的野蛮做法创造条件,从而有能力给资本的统治披上正义性的外衣。例如,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不断地缩减必要劳动时间、极大地增加剩余时间,这同时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社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扩展了人类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57)
但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全球治理是一种道德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驱使雇佣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这种本性也决定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讲“社会道德”。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度,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8)换言之,资本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取向注定了这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是脆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五 马克思对全球善治的追求
国内政治中客观上存在着所谓的善治,也就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的善治要体现正义,而正义应该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有这样的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9)那么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全球善治?如果存在,它究竟是什么内容呢?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善治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现实。马克思认为,理想中的全球善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前文述及,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是全球治理兴起的前提。没有世界历史进程,没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跨国界关系,也就没有所谓的全球治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物的观点,而且也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60)也就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全球的视野中来思考的。单个人的发展、单个国家中的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跟世界上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1)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是全人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目标。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置于全球治理的视野中来考量,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具体体现。
但在资本主义时代,首先是资本使劳动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62)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一首田园诗,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动却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63)结果,劳动非但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反而成了禁锢人性的枷锁和异化人类的罪魁,因此,“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64)资本不仅使劳动异化,而且也通过使劳动异化而导致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65)在这种异化劳动状态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66)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确切地说——在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只能是一种奢望,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事实上,马克思正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全球善治的理想来追求的。
首先,马克思对消除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方法没有别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就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本的前提保障。马克思指出:“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67)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68)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必须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69)只有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铲除导致劳动异化的土壤,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其次,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全球善治,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联合的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70)因为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弱小的,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力量就更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1)简而言之,单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资本的支配。这也充分表明,“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的论断。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72)在马克思看来,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存过程。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指的是摆脱了民族地域局限性的、与整个世界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具有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的现实个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个人思想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解放的过程。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的,马克思指出,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必须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最后,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在这一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性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一阶段,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不过,从第一阶段经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都要经历血与火的斗争。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73)在这一阶段,人类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实现个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条件就是“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创造)的能力”。(74)到那时,社会成员才能彻底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5)
六 结论
把全球治理视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是把全球治理当做基于民主、平等、正义等普遍认同的普遍价值基础上的一个秩序建构过程,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共同合作,通过订立各类国际制度,在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最终使国际社会接近秩序的过程”。(76)但是,这种层面上的全球治理是狭义的全球治理。狭义的全球治理,主要是指对全球秩序的追求,并通过这一秩序避免全球性问题的泛滥。从这一角度来看,狭义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就是“全球共同治理”。因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的协同行动。广义的全球治理是伴随着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以及由此产生了跨国界、跨民族的关系而出现的。资本所开创的广义全球治理虽然也追求全球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全球协同行动的结果,而是资本作为一种特定力量强加的,其目的是追求资本这种“特定力量”的利益最大化。当今所说的全球治理即全球共同治理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疏离,也就是全球共同治理既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资源贫困状态,也存在着价值上的严重亏空。(77)即便如此,这种全球共同治理是建立在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基石上的,而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后而兴起的全球治理则是为谋取最大的剩余价值服务的,因此,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是一种基于非道德价值取向的畸形秩序。这种畸形秩序注定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而且,在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78)当今的全球治理的机制是脆弱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但相比之下,资本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更为脆弱,因为资本把世界带入文明之中,但资本的全球治理却是反文明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善治是不存在的。相反,全球善治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不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中,而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工具、手段和目标上的严重缺陷,马克思没有把全球善治的价值目标放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框架之中,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全球治理模式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这种全球治理模式中,人的全面发展将得以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将真正实现全球善治。马克思深知,资本作为全球治理的手段和工具,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治理,相反它会带来全球性的危机,不仅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由于资本的掠夺还会产生危及人类生存和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资源性危机等。从这些情况来看,当今所说的全球治理被认为是伴随着全球问题而兴起的,实际上是延续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任何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都是全球治理革命的对象。因此,马克思一直在努力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寻找实行全球治理的新的工具、手段乃至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当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全球治理的工具仍然是临时性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性的。只有当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胜利,“自由人联合体”取代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后,全球善治才得以实现。因此,在“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模式建立之前,任何全球治理的模式都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即便它在某些领域内取得一定的效果,那也只是既有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暂时性妥协。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文中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7页。
②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归结为精神的领域,表示“精神”的意识是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④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第11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200页。
⑨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⑩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1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3)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278页。
(1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3-17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32)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3页。
(33)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38)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3-24页。
(39)艾伦·布坎南、罗伯特·基欧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30页。
(40)艾伦·布坎南、罗伯特·基欧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34页。
(41)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42)蔡拓、吴娟:《试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35页。
(43)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页。
(4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45)《资本论》第1卷,第660页。
(46)《资本论》第1卷,第666-667页。
(47)《资本论》第1卷,第864页。
(48)《资本论》第1卷,第861-862页。
(49)《资本论》第1卷,第860-861页。
(50)《资本论》第1卷,第865页。
(51)《资本论》第1卷,第86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53)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第1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6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90页。
(59)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162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
(76)苏长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页。
(77)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6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殖民主义血腥的烙印。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市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