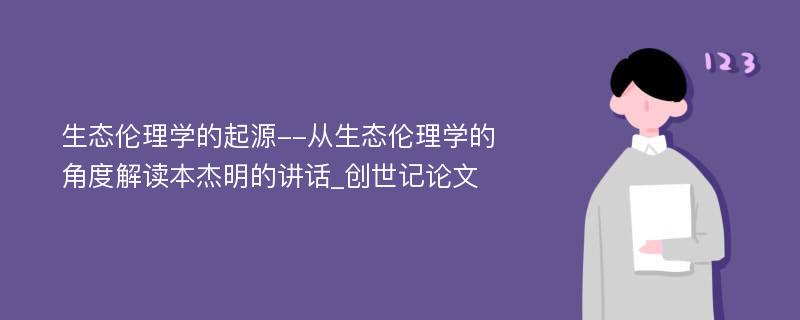
一个生态伦理主义者的《创世记》:从生态伦理视角阐释本雅明的语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生态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者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早期形而上学代表作“论自然语言和人的语言”,可谓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原发种子”之作。因为作为他思想特征的“两面神”(“Janus-faced”)面貌在这早期文本中已开始形成,即,他一方面通过从卡巴拉神秘主义传统解读《创世记》来阐释弥赛亚救赎的启示,另一方面却建构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世记》”(Andrew Benjamin 157)。也就是说,他对《创世记》的解读既有些神学色彩,更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这种两面性的结合并不是随意杂合,而是他的刻意追求,直至发展为他公开把犹太教对神启的阐释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结合而产生的独到的理论视角。借此他把现代性中科学用于战争杀戮、用于毁掉自然等而取得的所谓“进步”叫做“地狱”,呼吁截止这样的时代,而开始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纪元。他把这个新纪元叫做弥赛亚的时代,即被救赎的时代。
阿多诺把本雅明这个独特的视角叫做“否定的神学”或“逆反的神学”(qtd.in Buck-Morss 140),不仅深受其影响,更将此影响出色地体现在他的著述中。当汉娜·阿伦特称阿多诺是本雅明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弟子”时(Illuminations 2),她指的正是这种影响与传承。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的对启蒙理性、亦即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经典之作《启蒙辩证法》中,他们将“否定的神学”精神贯穿在了整个批判中。在“否定”的层面,他们如本雅明一样激进地批判工具理性、科学主义至上、人的绝对主体性及其同一性思维,揭批了所有这些观念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新的神话,而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神学”的层面,他们当然不再有卡巴拉色彩,但他们开宗明义便提出“一个完全启蒙的世界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性胜利”(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 4),并以此作为认识前提而展开批判,这已经是在呼吁对以操作、征服、改造、赢利为特征的工具理性范式的截止,因此也就隐含着对以模仿、审美、敬畏、关爱为特征的感悟范式的倡导,借此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地点须从完全形而之下的物质实践层面(工具和功利性质的领域)向同时关注形而之上的参悟和体验层面转向的迫切必要性。
本雅明的早期神学—形而上学之所以能够启发这种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就在于,他在早期语言论中就通过对《创世记》的重新阐释,而描绘了一个天地人合一的共同体,以伊甸园中不同的语言层次为象征演绎了一个美好和谐的生态伦理秩序,使之与“堕落”以后的世界,即现代性,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他在早期所描绘的这样一种秩序就是他在最后的理论遗言“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要回归的“本原”,用他所借用的卡尔·克劳斯悖论般的语言来说,这个“本原就是目标”(Illuminations 263),即,这本原才是“超验无家可归”(Lukacs 61)的现代人可建构和谐家园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雅明在早期语言论中就通过对《创世记》的独到阐释而建构了一个“生态伦理主义者的《创世记》”,而他则可以说是一个“生态伦理”这个术语产生之前的生态伦理主义者。而这种思想范式虽然使他生前出版著作时备受挫折,却给他带来巨大的“身后荣誉”(Illuminations 2),因为这视角正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超前洞见。
在本雅明版本的《创世记》中,人类的堕落并不是由于女人或欲望所诱导的原罪而导致,而是归咎于一种“篡位”或一次“变乱”,这便是,“生命之树”的主导地位被“知识之树”取而代之,由此原初的宇宙秩序被打乱了。因为“生命之树”的统治“代表着上帝的纯粹、完整的权威性,上帝的生命弥散在世界万物中,一切生灵与作为其本原的上帝息息相通。世界中没有邪恶的杂质成分,没有阻塞和窒息生命的‘空壳’,没有死亡、没有禁锢”(328-29),①而“知识之树”的统治则意味着判断与抽象的产生,导致了一个以善与恶的对立为原型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打破了天人合一的本原状态。
本原世界的完整与合一就在于它是上帝完成他的创造之后“看到一切都很好(善),并给予祝福”(323)的世界,在他的“一切都很好(善)”的造物中不存在“恶”;“善恶对立”是知识之果所教导出来的虚构,是与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道”(Word)和真理相对立的判断和知识,它标志着人“道”(human words)的诞生。这是本雅明从犹太教的卡巴拉阐释学中继承下来的奥义,但是却把它转变成一种隐喻,用于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在本雅明看来,人“道”,即人的语言、人的法则、主体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与自然、与世界分裂开来。随着人类理性的进化和征服自然的文明进程的发展,人与万物血脉相连的生命纽带被斩断,人外在于自然,自然变成了对象、材料、资源,被指涉、利用、操作,自然不再有自己的质量、自己的语言,而只是数量和物质。由此产生了人在对待自然时的种种“蠢行”。本雅明把这些“蠢行”叫做“堕落”(329)。“堕落”在此被注入了文化哲学的含义。按照这一含义:人类被逐出天堂,进入历史,因此“他命中注定要用自己的血汗从土地中获得生计”(Andrew Benjamin 160),自然从此后被人类主体对象化、物化,成为被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启蒙理性把这一切叫做“进步”,而本雅明却“逆历史潮流而动”(Illuminations 259),不承认这是“进步”,而称之为“灾难”或“浩劫”(catastrophe)。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原罪”就是打破了卡巴拉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器皿”(苏勒姆252,266),而开启了以波德莱尔所说的“破碎性、瞬间性、偶然性”(Baudelaire 13)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历史的所谓不断进步必然只是一场不断堆积“废墟”的风暴,朝着与天堂相反的方向吹去,使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用卢卡奇的话说,这便是,现代性在其源头上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罪过的语境,一个开始了物化或对象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于人与自然异化过程中的主观片面的知识与判断遮挡了客观总体的真理与方向。
本雅明在他的语言论中把这种“无法控制的历史堕落”(Andrew Benjamin 161)叫做“语言的堕落”。在此,语言是一个神学或哲学概念,代表着一种世界观。在本雅明看来,堕落以后的语言状态表现为索绪尔所界定的那个封闭、共时、平面的符号体系,他称之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语言观”(324)。在这种体系制约下的语言与世界是分裂的,两者只有任意、人为的关系。语言并不能传达事物的本质,而只是任意地指涉事物,语言作为一种人类主体之间约定俗成的规则,被用来抽象、统括、归化和收编世界。起支配作用的是体系和规则本身,其他都被当作无生命的东西,被演绎和操作;言说的也只有体系和规则,世界则被消声;体系和法则把一个多维度、多样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派生出来的抽象对象。语言的这种操作性同时意味着它的工具性,即语言用于交流关于物的有用信息,而不是传达物的本质、在场和生命,这在本雅明看来不啻一种缩影,正反映了世界整体性的破碎,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性的胜利和对物的独断统治”(328-329)。
与此相对立,原初的语言,即天堂中的语言,或人未堕落前的语言,则是一个大宇宙观意义上的语言,即,在那时,万物都有语言或都是语言、都自我表达。因此语言被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上帝的语言,即单数大写的道(Word),它浓缩着世界的整体性,从这一整体中生发出世界万物,因此万物都是道的载体,都是以生命和质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道,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传达着、述说着道的精神实质,因此都是神启(revelation)意义上的语言。本雅明称这种表现为自然万物的语言为本体语言。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人的语言,在人类未堕落之前,人的语言也就是亚当的命名语言。根据本雅明所阐释的《创世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来替他管理这个世界,他在完成了创造世界的任务以后,就把他创造世界的语言传给了人类,但是免去了这种语言的创造性,只留下了它的认知性和接受性。这种语言角色的分派内含一种伦理的戒律,它规定了人类的本分就是参悟和领会宇宙真理、万物之道,借此来调整自我在世界中的定位,而不是充当上帝,染指生命、天地、生物种类的创造与毁灭等非本分的事务。在伊甸园中,上帝示意每种动物走上前来,由亚当命名,受到了命名的动物各个表现出无比的幸福,表明名毫无遗漏地再现了物的本质,可以说亚当的命名也就是纯认知、纯接受、纯称谓,他不仅能从万物中认识和接受宇宙之道,并且能够用名来加以表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本雅明说“亚当不仅是人类之父,也是哲学之父”(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37)。
在这种语言秩序中,自然语言向人传达自我,人的语言则通过传达自然语言而向上帝传达自我,即通过感悟世界而向上帝表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所在。人在这个传达的总体中充当着一个传令兵或信使的角色,而自然语言就是“每一个哨兵用自己的语言传给下一个哨兵的口令,口令的意义就是哨兵的语言本身”(332)。也就是说,语言直接连着本质,语言一旦命名,就有意义的在场。语言就是一种介质,显现真理,因此也就是昭示或神启。这种内在统一的传达,本雅明又称之为翻译。在巴别计划之前,即人的主体性无限膨胀之前,翻译不是徒劳的横向转换而是有效的纵向传达,“每一种较高层次的语言都是对较低层次的语言的翻译,直到在最终的清晰中,上帝的道得以展示出来,这就是这个由语言所构成的运动的统一性”(332)。
这种语言的统一性实际上也就是世界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但这只有在人与世界保持着一种模仿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中,才能自然而和谐地存在,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关系中,人与自然才是平等的。对这种平等关系,本雅明在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的著作中,仍用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词汇加以描绘。他认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全在于万物对人类保有一种“光晕”。所谓“光晕”,本雅明最初在他的“摄影小史”中的界定与他的语言论密切相关,即事物的“一种奇特的时空交织,一种独有的、无论离得多近都总是带有距离感的表象或外观”(Walter Benjamin,“Lit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518)。作为具体体现,本雅明把它描绘为人参悟自然时所感到的一种氛围:“夏日午后休息,对着天尽头的山峦或头顶上播撒树荫的枝条凝神追思,直至这个凝思的时刻与之所观照的事物的物象融为一体——这就可谓吸纳了山峦或枝条的光晕”(Walter Benjamin,“Lit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518-519)。
由此可见,事物的光晕首先在于事物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存在,即,它不是人的投射、建构或复制,而是有自己的身份;而当事物处于这种自我存在状态时,它也就还没有成为人的材料,还没有被人类的技术所渗透,这时事物与人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具有相互尊重的距离感,事物向人显现的是自己永远略带神秘色彩的外观或形象,两者的关系正如作为两个主体的人眼中的你我。对此,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意象”一文中说:“对光晕的体验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将人际间普遍的关系传播到人与无生命、或与自然之物之间,那个我们在看或感到我们在看他的人,也回眸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事物的光晕意味着赋予它以回眸看我们的能力”(Walter Benjamin,“On Some Motifs in Boudelaire”338)。
这便导出了光晕产生的最重要前提,即人必须能够承认物的自我存在,并能够在一个审美距离之外凝思参悟、模仿移情、直至达到忘我。由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可变成诗的源泉。诗人正是能够赋予自然之物以回眸能力的人,而被如此唤醒的自然目光又总是给诗人以梦想,并使其通过追忆“被怀旧的泪水所朦胧的往昔”(Walter Benjamin,“On Some Motifs in Boudelaire”338)而永远追逐这个梦想。这个梦想的原型就是在机器没有介入自然之前,人对世界万物的虔敬和人生体验的完整性。哈贝马斯用通俗的表达把这总结为,只有当人类把自然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把自然视作鲜活的、言说的生命,而不是被动、沉默的物质,人类才能倾听和接受自然的语言,才能避免凝视和被凝视、主体和他者的关系,而建立平等、模仿、对话的关系。②这是一种无论离得多近总是有距离的敬畏感,但是有悖论意味的却是,这种距离和敬畏却带来真正的亲近,带来人与世界和睦共处的生存状态,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伦理关系。
在本雅明版本的《创世记》中,人类堕落的标志就是这种关系的破裂。原初的和谐被打破以后,人类语言不再内在于原初那个纵向的总体中,而是自我为营,从专有名词,即命名的语言,变成了一个符号体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结构中构造空中楼阁,因此不再具有传达性、不再能够命名,而只能交流关于世界的信息。语言一旦与世界丧失了直接沟通的能力,必然变成任意指涉,话语不再直接与意义相关联,而是与主体性同义。指涉就是同化、归化、统括、收编,是绝对的权力,而被指涉就是被对象化、物化、非质量化、成为被操作的客体。这种堕落所带来的是人与世界的分裂和异化,人的模仿能力衰退,诗性消失,而世界则在人类如此改变的视野中失去了光晕、失去了神圣,变成可被占有、掠夺、利用的纯粹的材料。结果,自然丧失了其生动与活跃,表现为沉默与悲哀;因为已经与本质失去了联系的人类,再也看不到自然本真的面貌,听不到自然无声的语言,那个内在的传达链已经断掉。人一旦不再能够命名,而只能指涉,那么在人的视野中,一切都变成了符号,其意义永远不会立即在场,而总是在寻找等价物来实现自我。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事物的价值完全被其交换价值所替代。因此在本雅明看来,人的堕落也将自然一起拖着走了下坡路,而人类本身则从此后在一种无止境的追求效用性的劳作中轮回。这表现为,在现代商品化社会中,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人们不断开发新产品,新颖的时尚不断替代过时的时尚,但这种新颖并不是真正的新颖,而不过是同一性的永久复归。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所谓的“新”其实是一种走不出来的轮回,即宿命。本雅明不仅把这种状态叫做神话,即一种走不出来的魔幻般的束缚,更把它叫做灾难。因为在他看来,“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无节制)地发生,这本身就是灾难”(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 473)。而现代性,在他看来,正在走向以这种以没完没了的灾难为标志的地狱。
本雅明想做一个救赎天使,拯救如此毁败的世界,但是在现代性进步大潮的裹挟中,他如此势单力薄,无可奈何。他在最后的“理论遗言”——“历史哲学论纲”中,以“新天使”为隐喻,给后人留下一幅在当下这全球现代化时代越发耐人寻味的哲学寓言画:
克利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表现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碎片,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它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龙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断壁残垣则拔地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Illuminations 259)
在本雅明看来,人类离开了天堂中和谐完整的生存状态,进入历史。历史以进步为动力,然而一旦单纯的技术进步远离和谐完整的生存理念,它所留给世界的只能是一堆堆的废墟和残垣断壁。他作为意欲拯救历史的天使,面对两种鲜明的反差:远观越来越遥远的天堂,近看不断堆积的文明废墟。他想打断历史盲目的进程,恢复生机与完整,然而进步的大势却是一股与传统和本原逆向的巨大力量,裹挟着他。他单枪匹马、无能为力,然而他没有迷失方向,他始终面对远去的家园,背对忧患的未来,因为他始终认为“本原才是目标”(Illuminations 263)。
这幅构思于他自杀前夕的寓言画,充满了绝望与悲壮,但也正如马尔库塞借用本雅明自己的原话对本雅明的赞扬所言:“正是由于那些不抱希望的人们,才给我们带来希望”(马尔库塞216)。我们的理解是,正是忧患意识,让我们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在还不是太晚的时候,挽救自然,挽救世界,挽救人类自己。
注释:
①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Walter Benjamin,“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Reflections:Essays,Aphorisms,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Trans.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Jovanovich,Inc.,1978)314-32.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See Jürgen Habermas,"Walter Benjamin:Consciousness-Raising or Rescuing Critique," On Walter Benjamin:Critical Essays and Recollections,ed.Gary Smith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8)9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