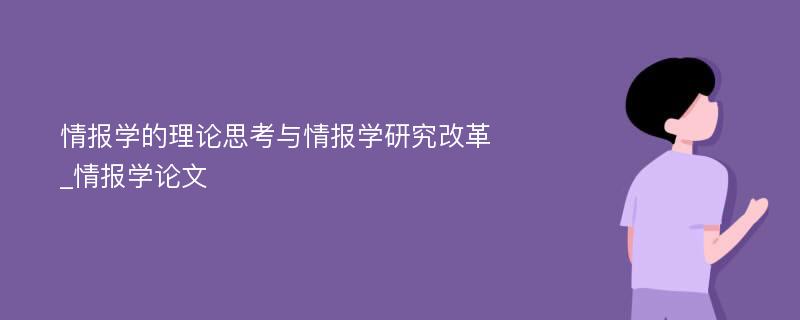
情报学理论思维与情报学研究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情报论文,思维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静审视情报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在情报学理论构建上,明显存在“品性”不足的缺陷。情报学研究的肤浅性论证、技术性移植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表面的繁荣与深层的贫困构成当前情报学研究的一大实然景观[1]。不可否认,情报学研究一直受制于其他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地。由此,有责任感的研究者不免质问:情报学理论研究上到底前进了多少?对情报学又进行了多大程度上的发展和完善?情报学如何为情报利用提供智力支撑?又如何为克服情报(或知识)利用障碍提供理论支援?尤其是情报学遭遇质疑,身份认同存在危机的时候,情报学如何建构一个坚实的自我?如何挣脱他者的殖民或被边缘化?如此等等的反思不一而足。而“情报学理论思维”的提出就是“直面问题本身”,使情报学摆脱理论“尊称”之憾的研究使然,也是其获得内在的发展动力[2],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与重建学科尊严的应然选择。情报学发展表明,情报学要想摆脱当前尴尬的处境,得到真正发展,也应当诉诸情报学理论思维,因为理论思维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3]。从某种意义上说,认真反思情报学理论思维,就是关怀与重建情报学的未来与希望。
1 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内涵
思维是人类所独有的,它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种认识过程或认识能力。相对于经验思维来说,理论思维是对理论形态的一种理性思维。因此从学理来讲,情报学理论思维就是从情报学概念的辩证表达出发,对情报学理论形态展开的思维,它以情报学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矛盾运动深刻揭示情报学理论和情报活动的内在本质与逻辑规律。这一规定性是情报学理论自身具有的辩证属性及其发展进程规律决定的,也是进行情报学研究的客观要求。情报学理论自身的特性要求不断指向理论的根本,对其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性反思,以真正情报学的方式进行情报学研究,用情报学理论思维进行情报学思考,对情报活动进行反思,进而改进或变革情报活动方式。情报学理论思维的使命在于反思、批判、探索、改进、建设、超越,最终旨在走向理论的澄明之境,真正为克服情报(或知识)利用障碍服务。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特性应是思想性、批判性、创新性、理想性。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解决人类利用情报(知识)障碍为取向;以一定的知识系统为依据;以情报活动为思考之源;用情报学概念、范畴、术语研究情报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当前采用较严谨、科学、辩证的情报学概念、术语、范畴等来阐述情报学问题的元情报学研究就是一种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很好运用或表达。
2 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缺失与情报学研究的反思
2.1 发展检视
情报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受到诘难,质疑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甚至质疑其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以往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一方面承认情报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情报活动的目的,后者说明情报活动的途径、手段与障碍;另一方面,又宣称情报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而不再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的治理[4]。然而情报学发展至今,不但没有比较一致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且连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也没有形成,更不用说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独特表达或彰显。
回望情报学的历史进程和审视情报学的现实命运,情报学似乎成了一个矛盾综合体。无论作为科学的情报学、理论的情报学,还是作为学科的情报学都在一片质疑声中艰难前行[5]。
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主流》中共列出了11个学科,其中没有情报学的一席之地。20世纪整个70年代,世界各国的情报学研究者就曾对情报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美国著名信息工业研究所的马赫卢博认为,不存在这样一门独立的情报科学,情报科学是众多学科的总称。他在《情报研究:学科间交流》一书中,把40多个学科统称为情报科学[6]。谢拉和克列夫兰在1977年针对这些讨论作了如下尖酸而刻薄的评论:“在一页接一页关于什么是情报学基础的讨论中筛选……哲学上高谈阔论的优势,显露出我们正在试图靠说教把情报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接受”[7]。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还不完善,致使其还处于一种“失落”状态[8]。
已故情报学家王崇德教授在回顾情报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时指出:“一门可以称为学科的科学(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居然达到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9]。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情报学由来已久的前科学阶段或次等学科地位至今没有多大改变,情报学仍旧面临系列的困境和危机[10]。为何情报学的生存境遇如此尴尬?为何情报学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自我”的位置?如何使情报学自我的存在成为可能?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积极面对并去努力反思的发展性问题。
审视我国情报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引进”成为我国情报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殊景观,我国情报学的发展更多的是移植、借鉴了国外情报学的概念、范畴、体系,而唯独缺少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与研究,拿来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无意识行为。此外,不加批判地“移植”与“应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所研究和探讨的问题都可还原为哲学、图书馆学、文献学、行为科学、认知学以及社会学问题等,这使其自身独特的对象域(形式对象)反而被遮蔽了,学科地位、身份、发展、命运等也自然出现了诸多的危机,如学科成熟度不高、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情报学总是给人一种不成熟、难自立之感。而一门学科的成熟,在于掌握了一种独特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即理论思维。仔细检验当今的情报学研究成果,贫困性发展的时代性特征凸显,思想淡出,影响力小,原创性不足。对世界情报学理论,我们几乎无甚贡献(老祖宗的著作除外),甚至甘愿接受殖民化的侵袭;对情报学,我们几乎无甚建树,只有从其他学科拿来的份,而几乎喊不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对情报活动,虽心向往,但远未发挥重要影响力。
诚然,对国外情报学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对我国情报学的发展与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随之出现的问题是许多研究者在本土的语境下却沦为“他者”的传声器,其他学科对情报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思想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更多的情报学研究概念混乱、范畴模糊、术语庞杂,不仅缺少了情报学自身的反思与加工,而且失去了情报学研究自醒的自我意识。以至于到目前,依然未能建立起情报学科的自信,划定自身特有的解释领域。
2.2 问题反思
反思我国情报学的现状、生存方式与发展水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情报学研究困境凸显,如话语的依附性、思维方式的贫困、方法论的缺乏等。有国外学者指出:“它或胡乱地拼凑或直接套搬别的学科的理论,严重缺乏自我的逻辑定位及独立的观念或思想。各个学科理论都在情报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将情报学分割、肢解。而许多情报学研究者似乎也不怎么关注自己的‘领地’及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并自觉或不自觉致力于情报学的分化及‘引进’工作。他们不尊重情报学话语,甚至以别的学科逻辑为基准为情报学定位、寻找归宿与合法化依据”[1]。情报学研究对情报活动所作的描述、解释、证明、预测越来越少,用外来的理论诠释情报活动,用既定的理论程式去裁定情报活动。而这使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重要的生存根基与逻辑品格,也严重地制约了情报学发展的进度、方向和速度。从当前情报学研究现状来看,情报学理论的建构更多充斥着一定的随意性——主要是研究者缺乏情报学理论思维。
边缘的地位与尴尬的处境,使我国情报学发展出现了“三多三少”的必然结果,多移植、少创造;多直觉、少批判;多借鉴,少超越。为什么情报学研究困惑重生?为什么在其他各门社会科学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情报学理论仍步履蹒跚,落在后面,情报学理论似乎还是不能把握自己的发展状态?为什么情报学理论方面的论争总会出现实际上是前提性条件发生分歧的现象,以致论争各方在论争之前,总要构筑自己的堡垒,作出自己的界定?当然,其间不少情报学者也对情报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持久的争论至今仍未能有一个明晰的回应。1987年在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思维、新观点、新方法研讨会上有学者就发出了“加强情报学自我意识的思考”的呐喊,指出“理论要上天”的声音[11]。此可谓是中国情报学发展的时代之声。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情报学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是理论还没有从情报活动实际中抽象、概括出来的问题。其表现有三:一是特别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概括不够;二是情报学理论缺乏独立个性,体现情报活动自身规律、反映情报活动特殊矛盾的理论不多见;三是作为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理论学科的情报学哲学,也缺乏思维深度,要么就是现象的罗列、列举,要么就是照搬别人的理论”[12]。那么,怎样提升情报学的理论高度?如何体现情报学理论的独特个性品质?又如何生成真正属于情报学自己的理论思维呢?
3 情报学理论思维与情报学研究变革
当然,造成我国情报学研究发展困境的原因是众多因素的合成,但笔者以为当前情报学研究要想实现困境下的突围,必须诉诸情报学理论思维,其乃情报学研究出现新景象、新面貌的重要选择或支点。客观地说,导致情报学理论思维缺失的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也有内部因素的缺位,特别是情报学理论思维缺乏很大的自明性。
由此,重建情报学学科认同,提升情报学理论品性,拓展情报学在当前学术语境中的理论发展空间,探寻高度的理论自觉,必是一项充满艰辛与理论挑战的重大任务,它需要情报学者多方面的理论素质,理论视野、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等。每一个情报学者不必回避也无法回避,因为这是时代赋予的情报学使命。
3.1 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关怀
情报学理论思维是一种向“未知之地”的旅行,因此,必须运用理论思维的力量来关照当下情报学的现实,以超越的眼光思考情报学的未来发展,才能突破当今普遍流行的思维模式,把眼光投向更为高远的时空,以保持一种理智的诚实,一种谦逊的态度面对我们所研究的情报活动世界.面对我们所申明的情报学知识,面对我们的情报活动现实,面对我们所坚持的情报学主张。问题是如何探寻其应然的发展之路、怎样去完成“颠覆”性的思维转向。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面对如此多的诘难与“不满”,众多情报学研究者从不同维度予以了必要的问题关怀,旨在“拯救”情报学的命运,变革其生存方式,从而构建起有自己独特概念、表述方式、思维方式等的研究时空,建立自己的思维路径,形成自己独立的思维品格,实现从思维向智慧的提升,赢得学术的尊严。美国情报学者巴克兰等人指出:“情报学理论研究者缺乏‘史’的意识,而史则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每一位研究者的思维和认识,都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所以研究者应学习情报学史知识,进行研究要有‘史’的意识”[13]。因为情报学理论研究者要想清楚自己所处的情形,明了自己的出发点,就不能离开对情报活动历史的考察和人类情报学思想发展历史的总体把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有一些思维敏锐、洞察深刻的学者站在情报学发展的前沿,在探讨情报学自主与开放[14]、寻求情报学独立[15]、多元的个性品质[16]、变革情报学研究的方法论[17]、关注情报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对话[18]等方面进行了时代性的应答。这些“变革”的实现离不开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关怀。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没有情报学理论思维,情报学研究的变革必然是有限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
3.2 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回归
科学史上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理论思维对于揭露原有理论体系的逻辑矛盾,对于揭露原有理论与概念的缺陷或局限性,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认识和评价原有科学理论,对于原有科学概念或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对于建构新理论、创立新知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情报学理论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变革也催生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回归。
国外学者认为:情报学是理论体系,但没有独立的逻辑、体系、术语等;情报现象太复杂,因变量很多,不可测、不可控的因素很多,故需重建情报学理论思维;从学科发展的维度来看,情报学也从没有提升到一个高位,而其变革必然催生着情报学理论思维;情报学的科学定位及其成熟需要情报学理论思维,尤其是对情报及其情报活动的本质是什么、情报学的归属等问题的认识与深化[19-21]。
那情报学何以获得作为独立学科的尊严?何以成为一门具有实践价值,为人们所信、所用的学问?笔者以为: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回归,情报学的发展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才能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重建学科的尊严,才能还其一个应然的学科身份。情报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理性活动,它对情报学者的理论思维具有较高的要求。只有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情报学者才能真正地认识情报学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情报学问题[21]。马克思也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为真正的情报活动是具有理论气质的,而理论气质的魅力离不开理论思维的不断提升。
3.3 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实践主体
寻找情报学发展的合理路径,寻求其安身立命之根,为其存在进行正当的辩护。这是情报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情报学者沉重的责任。因为,学者的使命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在此意义上,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入场”,需要情报学者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在一个发展与超越的制高点上来关照情报学问题。情报学理论思维应内蕴一种思想性、革命性,其应成为情报学研究者应有的一种研究品性。
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重建情报学理论思维是情报学变革方向与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也是情报学者自醒的一种表现和义不容辞的时代重任,是“理论创新”的时代语境下情报学者的一种必要的回应与根本性诉求。挣脱依附性的生存处境,谋求自主的发展空间,是支撑情报学者前进的不竭动力,然担负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无疑是情报学者。情报学来自哪里?又到哪里去?这是任何一个情报学者无法回避也不必回避的时代性问题。而唯有直面问题本身,情报学才有资格获得生存,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相信,情报学理论思维的重建将使情报学获得新鲜的血液与发展的动力,也是情报学走向成熟的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