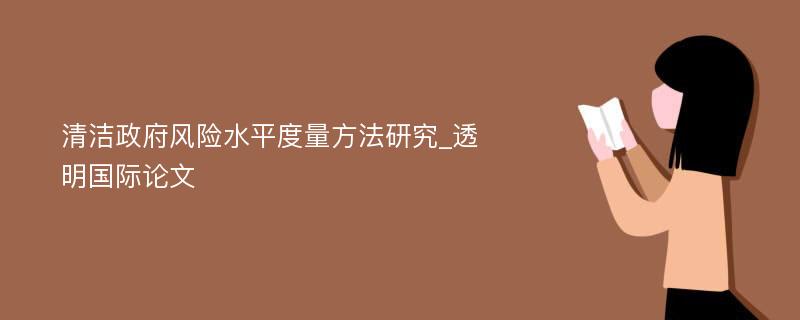
廉政风险水平测量方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平论文,风险论文,测量方法论文,廉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13)01-0006-06
经过几年的推广,廉政风险管理已经传播到中国很多地区、部门和单位。廉政风险管理对于促进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何科学、定量地评价廉政风险水平却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科学测量廉政风险水平是决定廉政风险管理科学化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廉政风险水平的实践评价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廉政风险管理由北京市崇文区②于2007年首创,在得到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肯定后,迅速在中国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推广开来。廉政风险管理实践从一开始就把风险管理(查找风险、制定风险防控措施等)、质量管理中的PDCA循环③等引入其中,使廉政风险管理成为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也带有不少的科学化成分。鉴于科学、量化评定廉政风险等级(或水平)对于廉政风险管理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文章主要介绍和讨论廉政风险管理实践中的一些相关做法。
崇文区的首创实践把廉政风险划分为思想道德风险、制度机制风险、岗位职责风险三类并查找风险点。崇文区还提出了查找三类风险的风险点的依据。如查找制度机制风险点主要依据本单位承担的业务工作,重点是涉及人财物管理、行政审批、行政执法、重大工程招投标等方面的情况,并按照具体工作、工作程序和工作职能等查找可能存在的问题。[1]
在查找到风险点之后就需评定或确定廉政风险等级④。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关于“评定风险等级”的具体意见是:根据权力的重要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及危害程度等因素,按照“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评定,并经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对不同等级的廉政风险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⑤北京市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意见》中提出的确定廉政风险等级的办法与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意见类似。所不同的是,该意见希望能够“实现廉政风险点动态管理”。[2]刘淇[3]在北京市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讲到了查找风险点和确定风险等级的办法和要求。他指出,要找准权力运行风险点,认真查找每个部门、单位、岗位在权力行使、制度机制、思想道德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点,并依据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行使的频率、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及危害程度,对查找的廉政风险点评定风险等级,实行风险等级管理;要突出重点对象,把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人事权、执法权、司法权、审批权、监管权的领导干部以及人、财、物管理等关键岗位作为重点对象,切实规范领导干部的用权行为。
崇文区以及后来的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实践廉政风险管理过程中,在查找风险点和评定风险等级上有一些很好的做法,如走群众路线。他们广泛发动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和职工全部主动查找风险,参与风险管理。这些实际做法,使廉政风险管理成为推动群众性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各地、各部门实际开展的廉政风险管理实践中,所使用的廉政风险等级评价方法都差不多,文章中统称为“实践评价方法”,其中以北京市的做法最具代表性。采取的方法或评价依据主要有两种:一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二是腐败案件发生的情况。
实践评价方法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三个风险等级的划分是一种定性评价的方法,而不是定量的评价方法;二是所获得的风险评价结果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并不代表实际发生了的、真实的风险水平。
从交通系统和“一把手”方面能更清楚地看出实践评价方法的这两个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无论是从近些年来全国交通系统官员、“一把手”腐败案件发生情况,还是基于权力等的制度分析,都可以得出交通系统、“一把手”是廉政风险点,而且风险等级应该是最高的。但是,是不是全国的交通系统,所有的“一把手”都是这样呢?实际的廉政风险水平到底是怎样呢?真的都是高的吗?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在河北省交通厅厅长焦彦龙的领导下,笔者曾对河北交通系统作过一个深入的案例研究,在交通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实质性的创新,至少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实现了河北交通系统的廉洁。廉洁“一把手”的实例也能够找出不少。但是,实践评价方法不加区分地都给河北交通系统和那些廉洁的“一把手”贴上一个永恒不变的标签:廉政高风险点。依照实践评价方法,廉政风险管理将成为不可改进的,这和廉政风险管理在过程上的持续改进主张是矛盾的,北京市希望的对廉政风险点实行“动态管理”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实践评价方法还带有另外一些严重缺陷。其中,最为严重是使用腐败案件来评价廉政风险的做法,该做法必然导致测量上的系统误差且误差水平难以估计,结果就是测不准,同时还把反腐败部门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些特点和缺陷表明,实际评价方法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比理论上的科学性问题更严重的是其制约着廉政风险管理实践的深入开展。廉政风险管理的一个核心思路和基本途径就是引入质量管理的PDCA循环,通过持续地改进不断降低廉政风险水平,直至把廉政风险降低到计划所设定的理想水平之下,由此取得反腐败的成功。PDCA循环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计划(plan),计划环节的一项关键任务是要设定廉政风险管理(或质量管理)的终极目标和阶段目标。没有定量的、准确的、实际的、真实的廉政风险水平测量,计划目标就不能设定,计划环节就不能完成。没有计划环节所设定的管理目标,整个廉政风险管理过程(或PDCA循环)就失去了基础或起点。同样,由于没有廉政风险水平的科学测量,PDCA循环中的检查(check)环节也没法做,检查环节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或行动,action)也就无从谈起。总之,由于缺乏科学的廉政风险水平测量,PDCA过程根本就不可能完整地引入廉政风险管理实践,希望它循环起来或持续改进就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考察北京市丰台区首创以及后来各地、各部门的廉政风险管理实践,都存在着低水平重复、不可持续的情况。究其原凶,关键就是还没有解决廉政风险水平的科学测量问题。
综上所述,科学的廉政风险水平评价方法不应该只是基于分析,而主要应该是基于实际的测量,测量出实际的、真实的、具体的、准确的廉政风险水平。该风险水平应当是定量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廉政风险管理真正走向科学。
本质上,廉政风险水平也就是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在研究和试图测量的腐败程度(level of corruption or degree of corruption)。理论和实务界已经开发出一些腐败程度的测量方法。如果能够测量出一个地方、一个行业或一类职位,在一定时期的腐败程度,这就是真实发生着的廉政风险水平。定期地比较该腐败程度的变化,将可以准确地评价廉政风险管理的实际进展和成效。
二、传统的两大测量方法及其优缺点分析
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腐败程度的测量,即要测量出腐败的真实水平。但是,直接测量腐败的真实水平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传统的测量方法可以划分为两大流派,即基于被查处的腐败案件的客观测量法和基于民意调查的主观测量法。
(一)客观测量法
基于被查处的腐败案件的客观测量法也被称为硬数据(hard data)测量法,是最直观、最古老的一种方法。各国民众很自然地根据本国执法部门、司法机构当期查处的腐败案件的数量、涉案官员的级别、涉案的金额等来评价本国的腐败程度。如果说此方法也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基于腐败案件。一个行为是不是腐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争议。查处的腐败案件是以一国的法律、法规为标准,又经过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因此,争议是比较少的。换言之,基于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评价腐败程度,数据是可信的。
但该方法的一些严重缺陷也源于基于腐败案件,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该方法的测量结果存在系统误差。⑥腐败是一种秘密犯罪,信息不对称与发现难是这种犯罪的主要特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及时查处出所有的腐败案件。这也就是说,查处出来的腐败案件水平永远低于真实的腐败水平,而且很难估计两者之间的误差。第二,以腐败案件测量腐败水平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反腐败机构查处的腐败案件越多,应该意味着“产出”越大,但却证明了腐败越严重的“结果”。透明国际在1996年有关CPI指数方法的说明文件中,也指出了基于腐败案件数据的客观测量法的此种缺陷。⑦因此,如果真以腐败案件来测量腐败程度,将会误导反腐败工作,使反腐败机构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腐败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各级政治和政府官员的理性选择是尽量少查处腐败案件。也就是说,查处腐败案件的工作会受到很多人为的干预,这将使测量腐败程度的系统误差更大,而且难以估计误差大小。因为这些原因,这个方法已经基本上被理论界所抛弃,转而寻找其他测量思路和方法,而主观测量法就是新发展出来的方法。
(二)主观测量法
最具代表性的主观测量法是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腐败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国内习惯翻译为国家清廉指数。该指数的数据来源种类较多,但大多是基于民意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因此CPI也被称为是“民意中的民意”(poll of polls),很多调查数据都是基于被调查者个人的总体的、抽象的对于腐败程度的主观看法。⑧正因为如此,该指数被称为主观指数或印象指数。主观调查法可以克服硬数据法的一些缺陷,如可以克服系统误差和测量悖论,这是其优点。但缺点也是严重的,如其测量结果和真实腐败水平之间的误差可能是很大的,逻辑上难以估计误差的具体水平。用社会科学测量方法上的术语,就是该测量方法的信度(reliability)比较差,甚至难以通过起码的信度标准。
美国著名的腐败研究专家Michael Johnston比较肯定CPI的信度,其根据正是CPI编制者提供的该指数各源数据之间的较高的相关性。⑨其实这种表面上较高的相关性是靠不住的,CPI的源数据采用的都是主观测量法,其缺陷原因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是完全可能的。透明国际制作 CPI的特殊方法也能说明该类方法在信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透明国际在制作某年的CPI指数时,总是同时使用同一个数据源(最近三年的调查数据)。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CPI分数的剧烈波动,使历年CPI分数更平滑一些,从而避免给人不可靠的印象。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为了掩盖主观测量法在信度方面的缺陷。人们凭经验就可以对主观测量法的信度缺陷做出评判。影响人们主观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腐败案件查处,特别是腐败大要案查处情况以及媒体对于腐败案件的报道的影响。在腐败大要案发现和查处前后,同一个人在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的评价就完全可能大相径庭,这将带来严重的信度问题。总之,使用主观测量法来测量腐败程度也是不准确的。
上述分析表明,已有的两大测量方法虽然都有一些优点,但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都不能准确地测量实际的腐败程度。
三、行为测量法及其在廉政风险水平测量中的应用
腐败的真实水平是不是真的就不能直接测量呢?也不能如此绝对。国际社会在实践中最新引入的一些方法可以看做是一种近似的直接测量方法。从逻辑上来看,腐败行为也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尽管腐败是一种秘密交易,局外人和局内人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是,第一,腐败行为确实是真实的行为,而非抽象的概念;第二,腐败分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任何腐败行为总有人知道。不仅从事腐败交易行为的当事人拥有完全的信息,腐败分子的身边人也可能知悉其腐败行为信息。
这类试图直接测量腐败真实水平的新方法被称为第三类方法,它们是基于行为,严格地说是基于人们在生活中的真实经历(experience),因此,也被称为行为测量法。该方法的逻辑基础是被抽样出来的受访者可能是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医生、教师、工程师、普通公民等。他们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腐败行为是拥有完全信息的,对自己从可靠途径如从家人那里获得的腐败行为信息也是比较可靠的。
行为测量法或第三类方法的优点就是很好地克服了前两大方法的缺点。部分被受访者所知悉的腐败行为或许没有被及时作为腐败案件查处出来,甚至永远得不到调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把这些信息提供出来。而且只要是真实的经历,而不是总体印象,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就能得到保证。香港实际测量结果的稳定性就是该测量法信度较好的一个证明。⑩总之,该行为测量法既可以克服客观测量法的系统误差,也可以克服主观测量方法的信度不佳的问题。由于能够近似地测量到实际的腐败程度,因此,它还可以避免客观测量法带来的逻辑悖论问题。
实际上,行为测量法已经在一些最新的测量实践中采用了。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中国香港和透明国际全球腐败趋势指数调查。
最早在实践中引入行为测量法的是中国香港。廉政公署自1992年以来就委托一家专业调查研究公司,逐年对香港的反腐败工作成效进行调查。以2010年为例,调查在15~64岁居港人士中抽样访问了1570人,于2010年10月13日至11月30日进行。调查问卷中有两类题目很重要。其一是“你或你亲友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有否遇过贪污情况?”香港多年普法以及早期的针对性调查表明,香港居民对于什么是腐败犯罪有准确的认知。2007年—2010年的调查中,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2.3%,2.6%,2.5%和3.6%。其二是关于腐败态度的调查,即是否容忍“香港贪污”。0为“完全不可以容忍”,10为“完全可以容忍”。2010年调查的平均分数分别是1.3。(11)
透明国际组织近些年来开始发布一个新的指数,即全球腐败趋势指数(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GCR)。该指数的原始数据是一个大规模的跨国民意调查。2010年的GCR在全球86个国家调查了超过91500人,调查实施时间是6月1日至9月30日。GCR调查问卷中有一道和香港调查类似的题目:在过去12个月中,你或你的家人向下列机构行贿过吗?(12)列入调查的组织或部门包括教育系统、司法部门、医疗服务、警察和公共服务等。亚太地区行贿水平很高的国家有柬埔寨(84%)、印度(54%)和越南(44%)等,中等或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有新加坡(9%)、中国香港(5%)、中国大陆(9%)和中国台湾(7%)。需要说明的是,该调查题目所覆盖的并非全部腐败行为,也不是所有行贿,而只是行贿中的小贿赂(petty bribery)部分而已。(13)
为什么对于部分腐败的调查所获得的比例比对于完全腐败的调查所获得的比例还要高呢?是不是行为调查也不可靠呢?以中国香港为例,香港2010年调查的比例是3.6%,而透明国际调查的比例则是5%。即使存在误差也不应该有如此之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调查所针对的总体(population)不同。透明国际的调查总体是成年人(general adult population),而香港则是15~64岁居港人士,包括非成年人。这就是说,香港调查的总体比较大。不同人群遇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未成年人遇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要小于成年人,普通大众遇到腐败的可能性要小于官员甚至商界管理人士等。
下文从理论角度集中讨论腐败程度的定义,行为测量方法及其测量到的结果与腐败程度测量之间的异同,腐败程度和廉政风险水平之间的异同等关键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腐败程度的定义问题。
尽管腐败程度在学术界早就是一个专门概念,在实践测量上也屡屡成为对象,但是,关于腐败程度的操作化(operational)定义却十分缺乏,这与腐败定义的汗牛充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传统的两大腐败测量方法只定义了腐败,没有定义腐败程度。操作化地定义腐败程度是测量腐败的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定义腐败。
近些年来,有个别专家提出了腐败程度的操作化定义。如美国Andrew Wedeman[5]提出的定义:实际腐败率(Actual Rate of Corruption,ARC):
ARC=Corrupt Officials/Total Officials(1)
如果国家甲的ARC是10%,而国家乙的ARC是3%,则可以肯定地说甲的腐败比乙严重。但这个定义还不够充分,还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补充修正。
一是腐败不应该只限于政府官员。众所周知,在当代社会,腐败可以发生在政府、企业以及多个社会领域。正因为如此,透明国际在2000年给出了新的腐败定义:滥用委托权力(entrusted power)谋取私利。在这个新的定义中,委托权力取代了传统腐败定义中的公共权力,这表明任何代理人(agent)都可能腐败,而不只是公共官员这一类特殊的代理人。鉴于此,ARC中的分母和分子就不只限于政府官员,而是所有可能腐败的人员数和实际腐败的人员数。中国香港的调查针对居住于香港的所有15~64岁的人士,而不论这个年龄段的人士是政府官员,商界人士还是其他的任何人士。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腐败,但并不是说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就不会腐败,只是可能性很小,可以忽略。
二是Wedeman给出的腐败程度定义只刻画了腐败行为的量,而忽视了腐败行为的质或情节因素。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同样是两个人的腐败,情节或危害完全可能有天壤之别。如陈水扁的腐败和一个普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所发生的小腐败在程度上绝对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程度的定义是复杂的,至少还需要刻画其“质”的方面。
到底如何来刻画腐败行为的质呢?廉政风险来源于风险管理。尽管风险的定义有很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Yates和Stone[6]于1992年提出的风险结构三因素模型。他们认为,风险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和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其实,Yates和Stone的模型只刻画了风险的两个因素,即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不确定性)和损失的大小。转化成一个操作化的定义即
R=p·C
(2)
式(2)中:R为风险(或风险程度,或统计意义上的风险损失),p为风险发生的概率,而C为风险造成的损失的大小。R,C和p分别相当于Yates和Stone三因素模型中的三个因素。
腐败行为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或概率特征,也必然会造成损失,因此,也可以把腐败行为看作是一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引入廉政建设领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Wedeman只定义了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即式(2)中的p。其没有定义的C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刻画腐败行为的“质”或情节的变量。所谓某个腐败行为的“质”或情节,可以被统一看成腐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或成本。之所以说陈水扁的腐败在情节上比一个普通警察来得严重,主要是因为指陈水扁的腐败造成的损失要比一个普通警察的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当然,腐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要比一般自然或经济社会风险的损失复杂,一些腐败损失是可以量化和测量的,而另一些腐败损失则很难量化和测量。例如:陈水扁贪污了很多金钱,并把大量不义之财转移到海外,使台湾社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部分损失是可以量化和测量的;但他的腐败还严重地损害了台湾民众对于民主和法治的信任,损害了台湾政府的公信力,这些政治和诚信损失尽管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进行测量,但很难像经济损失那样被量化。
上述分析表明,可以把风险定义套用到腐败定义上来,如建筑工程领域的腐败。假定政府在某年里有100项公共工程,发生腐败的概率是10%,平均来看,每起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是50万元。总的损失就是500万元。总的损失就是建筑工程领域腐败的程度(R),腐败概率是10%(p),损失的大小是100×50万元(C)。发生在其他领域的腐败也都适用风险定义。如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腐败,医疗系统中的腐败等。其实,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总体腐败程度也可以使用这个定义来描述,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发生在各领域的腐败加总(∑)。
借鉴于风险定义的腐败程度定义比Wedeman的定义更全面和充分,但对于腐败行为损失的测量将更加困难。因此,迄今为止的测量实践以及下文有关实际测量的讨论还局限于腐败发生概率(p)的测量,即Wedeman定义的实际腐败率。尽管这样做只刻画了腐败行为的“量”,但只要能测量准确,也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第二,行为测量法及其测量到的结果与腐败程度测量的关系问题。
Wedeman给出的腐败程度定义ACR很简单,但很难直接测量到,因为很难知道腐败人员的真实数字。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办法测量ACR。一个近似的直接测量办法就是行为测量法,正如中国香港和透明国际GCB所做的那样。类似于ACR是实际腐败率,可以把中国香港和透明国际测量得到的比例称为“腐败接触率”(Encountering Rate of Corruption,ERC)——即有多大比例的人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实际生活中能够真的接触到腐败行为。实际腐败率和腐败接触率之间应该存在着强因果关系。只有真实存在腐败行为,人们才有可能接触得到,而且腐败越多,人们接触到的可能性就越大。定量地来看,如果ACR是0,即人群中没有腐败行为,则 ERC也是0;如果ACR是100%,即人群中所有人都有腐败行为,则不论如何抽样调查,ERC也是100%。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任何的腐败程度上,实际腐败率都严格地等于腐败接触率。二者在量上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严格的统计证明,或者通过可能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但可以说,以腐败接触率来度量实际腐败率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测量腐败接触率来获得实际腐败率。这就解决了通过传统方法难以直接测量实际腐败率的问题。
第三,关于腐败程度和廉政风险水平的关系问题。
廉政风险水平主要关注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而腐败程度,特别是ACR是具体描述这种可能性的一个量化指标。以当期的ACR来反映这个时期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突变。即使有突变,也需要一段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腐败程度和廉政风险水平是一样的。
借鉴透明国际组织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最新测量实践,并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廉政风险管理实践中的廉政风险水平的科学、定量测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腐败程度测评,通过逐年比较来评估廉政风险管理的实际进展和成效。
第二,借鉴透明国际和中国香港的重要实践,采取基于行为的测评方法。借鉴他们的经验,开发中国版本的行为测评问卷,主要测评被调查人的经历,同时也需纳入针对态度的调查。
第三,建议主要调查题目、总体与抽样方法以及调查时间都尽量与香港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与香港的调查进行横向比较。如果可以把香港当作一个标杆(benchmark),这种横向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要。
第四,通过细化的调查题目(item)设计,实现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岗位之间进行比较。这样不仅有利于确定工作的重点,有利于对全局工作的指导,也有利于评价和指导不同地区和领域的工作。
第五,鉴于腐败行为的复杂性,不仅需要从频度或范围角度去评判,也需要从情节或性质角度去评判。透明国际和中国香港的测评实践都只关注前者,可以在后者进行一些创新,这在操作上并不复杂,增加相应的调查题目就可以做到。
注释:
①在中国的反腐败创新实践中,多使用的概念是“廉政风险防控”、“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或“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相对于第一个概念,后两者中的“防控”、“防范”和“管理”更有重复或累赘的问题。其实,使用“廉政风险管理”更为简明,既表明其源于风险管理,又区别于一般的风险管理,含义和“廉政风险防控”等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文章中统一使用“廉政风险管理”概念。
②在后来的北京市行政区划改革中,崇文区已和原东城区合并,组成新的东城区。
③质量管理中的PDCA循环由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W Edwards Deming,1900—1993)首先提出,PDCA分别是管理过程模型中四个环节的英文单词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ion(处理)的首字母。
④实践部门所使用的“廉政风险等级”和文章中使用的“廉政风险水平”是一个概念。廉政风险水平并没有被严格定义。廉政风险管理源于一般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可以根据风险管理中的风险定义来定义廉政风险。在风险管理中,风险(risk)通常是指一个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所带来的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概率)的大小。也就是说,刻画风险的大小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损失,一个是概率。廉政风险水平中的风险当然同时关注损失和概率两个要素,但更关注概率大小,因此,笔者把廉政风险水平定义为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的大小。
⑤详见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中纪发[2011]42号,指导意见第6条。
⑥透明国际在国家清廉指数(CPI)调查方法说明中,认为硬数据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效度(validity),严格地说,不是效度问题,而是系统误差问题。详见透明国际1996年以来有关CPI指数方法的说明文件,透明国际的网站为www.transparency.org。
⑦Instead of acknowledging this,“objective” data would“punish”such a country with a bad score.详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1996,网址为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previous_cpi,其实,在逻辑上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⑧比如说,CPI指数的一些数据源的调查问题是这样的:IMD asks respondents to assess whether“bribing and corruption prevail or do not prevail in the economy.” WEF asks in it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in your industry,how commonly would you estimate that firms make undocumented extra payments or bribes connected with import and export permits,public utilities and contracts,business licenses,tax payments,loan applications.influencing of laws and policies,and getting favorable judicial decisions.”详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PI Framework Document 2002,网址为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previous_cpi.
⑨详见Michael Johnston的The new corruption rankings:Implications for analysis and reform,Prepared for Research Committee 24,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Quebec City,Canada,August 2,2000。
⑩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2010年“腐败接触率”和前几年有稍大一些的变化,是因为2010年的调查题目做了调整。
(11)详见2010年廉政公署民意调查报告摘要,香港廉政公署网站为 http://www.icac.org.hk/tc/useful_information/sd/sd/index.html.
(12)原题目是In the past 12 months have you or anyone in your household paid a bribe in any form to each of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organizations?
(13)详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标签:透明国际论文; 廉政风险论文; 廉政论文; 风险评价论文; 系统评价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科学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