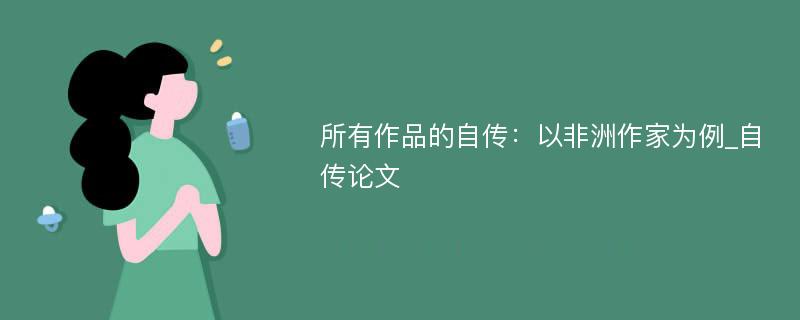
“一切作品皆自传”——非洲作家自传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传论文,非洲论文,个案论文,作家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有自传都讲故事,一切作品皆自传。”① 熟悉库切的人清楚,这不是库切的说话方式。可是,他讲了,而且还把这句话放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颇有几分盖棺论定的意味。说话一贯模棱两可的库切为什么说出这样决断的话,难道他要为自己的这部书——《重弹录》——辩护?
普通读者不读《重弹录》,一般学者也不会去碰它。库切的小说行情看涨,这是事实。相比之下,《重弹录》的读者却不多,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需要“辩护”。为什么?
这跟书的内容有关。《重弹录》收录了库切的25篇文章,长的达40多页,短的只有寥寥数页。文章跨度20年,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有贝克特、卡夫卡、戈迪默等作家评论,也有句法研究问题,还有牛顿、橄榄球、审查制度、广告里欲望的三角结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么庞杂的东西,库切却通通把它们视为“自传文本”。② 难道真是说“一切作品皆自传”?
一
正是因为一切作品不全是自传,库切才说“一切作品皆自传”。此自传,非彼自传也。显然,库切知道,他写的那些文章不是自传,所以才有此说。那么,自传的彼此之分,何以在《重弹录》里合二为一呢?
细看《重弹录》,我们发现,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文只有一篇——1984年写的“追忆德克萨斯”,而且也只有短短4页。从文类上说,有些文章归类起来比较麻烦。不过,根据文章内容和发表刊物,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划为五类:自述(1篇)、演讲(1篇)、随笔(2篇)、书评(5篇)、论文(16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文章不是自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文本”。说《重弹录》是自传,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然而,库切好像又没错。不但如此,他的合作者、文集的编辑大卫·安特微也说,这是一部“作家的智力自传”。③ 更有甚者,评论者居然说,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自传”。④ 事实和数据证明, 《重弹录》不是自传,可作者、编者和评者偏偏异口同声,个个咬定自传不放。要解释这个有些奇特的现象,我们不妨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文类的并置效应。
《重弹录》的第一个并置是作者与编者的并置。文章的作者是库切,安特微负责选编工作。可是,这样的安排并没有改变文章的性质。文章是论文,它们就还是论文,是书评,仍然是书评,不能因为编者的出现,文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
让文章性质发生变化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工作。身为作者,库切写了“作者的话”,置于一书之首,与之并列的是“编者导言”,长达13页。“编者导言”和“作者的话”,一长一短,表面上看没有多大呼应,实际上都在尽力给文章定性。库切写“作者的话”,惜墨如金,短之又短。他先说书的缘起,次讲文的增删,再谈增删问题,最后鸣谢,惯例性质十分明显,根本不像戈迪默所言,他具有“像云雀一样翱翔的想象力”。⑤ 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作者的话”里,库切却声称,这些文章将被视为“自传文本”的一部分。
细活当然需要编者来干。“编者导言”洋洋洒洒,涉及的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我们把它加以归结的话,三部分的轮廓还是相当明显的。第一部分画龙点睛,说出全书标题的真义所在。《重弹录》不是老调重弹,而是温故知新,通过回顾,探讨未知。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重弹录》这个标题揭示了库切作品的特征——反思性自我意识。“在此,反思性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经过库切学问的滋养,自我意识被用来理解各种状况——语言状况、形式状况、历史状况和政治状况。它被用来驾驭当代南非的小说写作。”⑥ 问题的关键是,“反思性”与“自我意识”都跟自传有关,是自传的重要特征,但它们还不是自传的定义性特征。关于自传,法国学者乐热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回顾性的散文叙述,由真人书写,讲述他本人的存在,关注的焦点是他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他的人格故事。”⑦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因为库切的作品具有“反思性”和“自我意识”,就断定《重弹录》是“自传文本”。这个部分不长,可是编者安特微一而再、再而三前后四次都在变相地给《重弹录》定性——这本书是“作家的智力自传”。口风跟库切如出一辙,显然,作者编者在搞“统一战线”。
“编者导言”的第二部分很快就露出了马脚。不错,这里面有一些传记成分,如库切的写作背景和创作师承,但我们发现,这些只是一带而过,不是第二部分的重点。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了库切的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了《幽暗之地》(1974年)、《内陆深处》 (1977年)、 《等待野蛮人》 (1980年)、 《麦可·K的生平与时代》 (1983年)、《福》(1986年)、《黑铁时代》(1990年)等六部小说里所体现的学术取向,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知识对库切的具体影响。这也是“编者导言”的主要内容,因为导言的第三部分只是一个简短的结论。我们不禁要问,作者和编者“共谋”,抽象定性,而具体内容与实际定性“谋而不合”,甚至南辕北辙,难道说《重弹录》不是“此自传”,而是“彼自传”,抽象泛指意义上的自传?
可见,无论是“作者的话”,还是“编者导言”,作为文类,它们是序言。按序言体例,既然作者和编者都声称《重弹录》是“自传”,他们完全有可能把序言写成自序传或他序传,大量添加不可或缺的自传事实和传记事实。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失去了一次机会,没能让序言与文章发生文类的并置效应,从而改变全书的性质。
二
至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出,《重弹录》收录的24篇旧文不是自传,歧义不大。“作者的话”与“编者导言”并列,没能点铁成金,把这些文章作者的底细和盘托出,使之自传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断定《重弹录》就不是“自传文本”。原因在于,虽然作者和编者在前言里工夫没有做到家,但是他们两人还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在《重弹录》里。库切是谈话者,安特微充当访问者,他们两人花了两年时间做了9次访谈录,内容约占全书五分之一,可谓下足了力气。
问题的前提是,访谈录也算传记文学;这些访谈录还是催化剂,让那24篇文章改变性质,发生化学反应,从严肃刻板的论文变为充满“个人生活”的“自传文本”。
相对而言,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访谈录是谈话录的一种,谈话录是传记文学,有史可鉴。著名的个案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麦德温编的《拜伦谈话录》、瓦雷里的《对话录》和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等,所以,《传记文学百科全书》这样界说:“谈话录、对话录和燕谈录可以定义为谈话类传记,常常是文学传记。”⑧ 具体到《重弹录》,我们还是应该一分为二,文章归文章,访谈归访谈。它们之所以能够合二为一,是因为文类的并置所产生的效应,我把它称之为文类的并置效应。这个效应体现在《重弹录》里相当突出。看一下该书的扉页,还有它的版权页,我们发现,这两处都赫然印着副标题——“文章与访谈”。细读目录,不难看出,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而每个部分的文章之前都冠以一篇访谈。正是因为访谈与文章并置,它们虽然不能改变文章的性质,但是它们改变了文章的语境,而这个语境恰恰是一种“自我语境”——即讲述“个人生活”和“人格故事”的语境。其结果,文章的性质虽然无法改变,但这些文章通过访谈,来龙去脉充满着“个人生活”,从而被自传化了。
让我们举些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句法”研究构成一个独立的部分,共有三篇文章组成。一篇讲英语里的被动修辞,另一篇研究作为修辞手法的无主句,第三篇探讨牛顿与一种透明的科学语言之理想。读一读这三篇文章,我们不难了解库切的学术兴趣,特别是他作为修辞学者的见解。也就是说,这三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库切的研究成果,但没有看到库切作为学者的自我,更没有看到库切作为学者的自我与库切作为小说家的自我之间的关联。自传往往把自我寓言化,自我的寓言化是自传的核心问题。多年之后做访谈时,库切被问及上述问题,他的回答就是纯粹“个人生活”的自述了:1979年休假,“我”一边埋头写小说,一边恶补语言学的课;“我”先到德州,后到加州伯克利;“我”写完了小说《等待野蛮人》,三篇论文也完成了草稿;“我”所用的理论模式也许已经过时,但论文的要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教养——我那相当不错的实证主义的乐观精神。”⑨ 自我的底牌一一摊开,我们不但看到了库切的论文,还看到了论文背后的自我,特别是他给自我所赋予的意义——“实证主义的乐观精神”。三篇文章是论文,没有自传色彩,但库切运用访谈,大量铺设自我语境,论文大有被“收编”之势,变为自我成长历程里的精神产品,仿佛成了自传的一部分。这就是文类并置所起的效应。
自然,问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既然谈话中提到了小说,既然库切又是以小说闻名于世的,何不顺水推舟问问小说创作与语言研究的密切关系。库切的回答难免让人失望:“我必须坦白,《野蛮人》与我1979所做的语言学工作之间,我看不出直接的关联。我们应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写的有些东西是为了游戏、放松、消遣,专业之外意义不大。也许,除此之外,这还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自我事实,我花时间(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搞研究,好让我逃离这个巨大的世界,还有它的烦恼。”⑩库切善于直面真理,更善于直面自我,那个有时让人难堪失望的自我。在此,库切有意向我们展示他负面的“人格故事”。这也是他两部回忆录里最拿手、最诱人的部分。(11)
库切并不总是让人失望。他也讲自己小说技巧的主要特征,如《等待野蛮人》的核心是环境,《麦可·K的生平与时代》以叙述节奏为主打,《福》这部小说则以声音为主脑等等。此外,他还谈小说家的自我和如何挑战自我,特别提到当他写《等待野蛮人》需要描写他没有见过的地貌时,自我挑战的意味就更大。可见,这些访谈录不仅勾勒了《重弹录》里文章背后的个人经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揭示了两个不同身份的库切——作为学者的库切和作为小说家的库切。身份建构是自传艺术的升华。因此,访谈录展示了库切的不同身份,进一步把文章自传化了。访谈与文章并置所产生的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三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访谈录——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类并置。
问题是,库切不喜欢访谈录,为什么还要做访谈录?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实际上相当复杂。库切罗列了几条他憎恨访谈的理由,听起来不无道理。首先,库切认为,访谈十之八九是跟完全的陌生人交流,而这些陌生人往往假借访谈之名越界,侵入私人空间。这是他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其次,访问者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缺乏职业素养,有些访问者甚至连起码的兴趣和好奇也没有,所以,他们的问题低级无知,就不足为奇了。(12)再次,访问者的控制欲令他望而生畏。本来一篇好好的访谈,有问有答,观点各异,风格多样,可是访问者硬是插上一手,编、审、剪、补,把一篇好端端的东西弄成一个思想单一的独白,让人哭笑不得。(13)
访谈录的问题不小,但问题一律都出在访者身上,谈者无罪。这似乎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库切已经意识到谈者的问题。在一篇访谈里,库切指出,谈话录里的谈者也需要警惕,因为他总被授予一种特权——一种对自己文本所拥有的话语特权,那让人不安。(14) 库切深知访谈录的诸多问题,除了《重弹录》里的访谈外,他还做过一些访谈,原因何在?(15) 库切本人的解释是,他选择对话,选择访谈,是想“绕过我本人独白的死胡同”。(16) 这是不是真实的原因呢?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谈话录的几个要素:
既是对话,重要的条件是双方的地位和关系要对应,平等相待。既不认为自己比对方高明而大发教训,又不认为对方比自己高明而处处请示。最好是商量,同意不同意都可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发言的一方管不着人家,不像严师训劣徒,可以打手心。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也不能使我读他们的小说就和他们一样想。我得出来的和接受到的恐怕和他们想教育我的不 大一样。对话不是同样的回声。(17)
这里,金克木把对话的条件、原则和性质都一一点明。对话的条件是“平等相待”,对话的原则是“商量”,对话的性质是不要有“同样的回声”。事实上,金克木所谈的对话是对话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的对话在现实里几近空中楼阁,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很难举出这类对话录的名著。而我们看到的谈话录名著,无论是《论语》,还是《歌德谈话录》,大多是师徒或半师徒关系。为什么这种不平等的谈话反而容易产生杰作?原因可能不少,但有两点至为关键。一是反差造成的。大师与门徒之间,年龄不同,经验有别,学识迥异,成就悬殊,一作幼稚状,一作宗师态,一问一答,醍醐灌顶,反差一大,戏剧性就强,容易达到淋漓尽致之功效。二是叛逆心理。门徒即叛徒,貌似恭敬的背后不免藏有犹大之心。此外,多年师徒成兄弟,他们要打破沙锅,把大师的那点老底问透。这颇能迎合读者的心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上述种种,《重弹录》庶几近之。库切讨厌访谈,但也做访谈,原因是要绕开“独白的死胡同”。这是他说的原因,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新书发布的市场运作等。深层的原因是,访谈录是一种特殊的文类并置——访者的别传与谈者的自传之并置。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库切对访谈录既恨也做。恨,是因为访者多半陌生,无知,又好控制,不具备“同情之理解”,没有做别传的起码资格。做,是因为库切的访者有一个特点:他们基本上是他的研究者,研读既久,了解就透,常常别具慧眼。而库切自己又比较自觉,不时提防着谈者的老毛病——对自己的文本“擅自越位”。两项结合,访谈就容易达到金克木所说的境界:“平等相待”, “商量”,让对话发出并非“同样的回声”。为什么能达到并非同样的回声效果?访者用问题来做别传,别具一格;谈者以回答来口述自传,自成一体。一问一答,和而不同,这就是谈话录的并置效应。潜意识里,库切是喜欢并置的。他的作品《幽暗之地》、《福》、《彼得堡的大师》等,甚至他获诺贝尔奖的演说词——“He and His Man”,(18) 都表明他的并置性思维特征。而用别传与自传的并置来创造一种特色自传,正是库切梦寐以求的事。在《重弹录》的结尾,库切先用他,后用我来替自己立传。当他离我越来越近时,库切写道:
[A]utre biography shades back into autobiography.(19)
钱锺书说“自传就是别传”,(20) 库切却说别传自传如影随形。别传自传的关系如此微妙,难怪库切会大而化之地说:“一切作品皆自传。”这话提醒我们,《重弹录》是自传性作品,自传性作品就是自传吗?(21)
注释:
①②③⑥⑨⑩(13)(16)(19) J.M.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ed.David Attwell(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391,vii,2,3,141,142,64-65,19,394页。有趣的是,许渊冲教授也用法英合壁的autre biography来译“自传就是别传”里的“别传”,以压头韵,可谓神来之笔,灵犀点通。参见Xu Yuan Zhong,Vanished Springs(Beijing:Panda Books,1998),40页。
④ Ann Irvine,“Review of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Library Journal (June 1,1992),p.124.
⑤ Nadine Gordimer,“The Idea of Gardening”,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1.1 (February 2,1984),p.3.
⑦ Philippe Lejeune, On Autobiography,ed.Paul John Eakin,trans.Katherine Lea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p.4.
⑧ Alexander Smith,“Conversations,Dialogues,and Table Talk”,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 :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 ed. Margaretta Jolly (Chicago &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2001),p.231.
(11) J.M.Coetzee,Boyhood :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 (London:Vintage,1998),pp.122-123 ; Youth (London:Vintage,2003),p.97.
(12) 参见J.M.Coetzee,Stranger Shores:Essays 1986-1999 (London:Vintage,2002),299页。关于访谈录的遭遇及其给作家的屈辱,可参见Doris Lessing,Walking in the Shade(London:Flamingo,1998),100-101页。
(14) Tony Morphet,“Two Interviews with J.M.Coetzee,1983 and198T”,TriQuarterly 69 (Spring-Summer,1987),pp.454-464.
(15) Richard Began,“An Interview with J. M. Coetze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3.3 (Fall 1992),pp.419-431 ; Jean Sevry,“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 Commonwealth Essays and Studies 9.1 (Autumn 1986),pp. 1-7; Andre Viola,“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 Commonwealth Essays and Studies 14.2 (Spring 1992),pp.6-7; World Literature Today,“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0.1 (Winter 1996),pp.107-111.
(17) 金克木:《金克木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52-253页。
(18) J.M.Coetzee,“He and His Man”,PMLA 119.3(May 2004),PP.547-552.
(20)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4页。
(21) James Olney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p.250-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