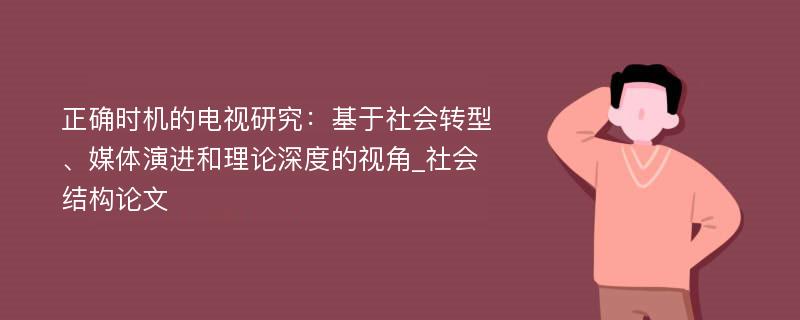
电视研究正当时:基于社会转型、媒介演进和理论纵深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深论文,媒介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理论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直面“尴尬的繁荣”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任何面向分支的研究,皆强调“贴地飞行”:第一,任何研究都需要“接地气”,“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①,不能脱离具体而动态的社会—历史情境,只在观念世界里打转。第二,任何研究也需要与经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获取超越性的理性反思和审慎预判。因为再细致的调研也难免“见树不见林”,或许只能在实务层面有些启示,正如米尔斯提醒我们的:“相信小范围的细节研究不管得到什么结果,都有助于启发我们解决或阐明结构意义的问题是一种愚蠢的念头。”②
若从“贴地飞行”的视角观照我国的电视研究,不难发现有两种流行的误读:第一,学界与业界“同仇敌忾”。前者旨在为后者背书,没有深刻的问题意识,狭隘地看待电视生产及其传播情境,不重视前因后果的复杂和关联,只关注“此地此刻”的现象和所谓“前沿”,“已知与未知的界限并非以研究活动的自主性逻辑来设定”③。于是,当电视受到新媒体冲击时,业者的焦虑不经过滤地成为了学者的焦虑,电视研究也被莫名地渲染上一层“明日黄花”似的底色,学者们忙不迭地思考着诸如“电视是否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电视如何通过新媒体复活”等问题。第二,学界与业界“形同陌路”。前者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永远只落在观念世界,电视作为电视研究理应重视的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却只是躯壳和附庸。学者擅长“在天上画地图”,由此,虽然相关研究日趋完善,但在本质上,知识生产的价值却日趋虚无。这也就难怪,业者们戏谑电视研究为“性感学”(主观性、客观性、美感、时代感……)。
或是“同仇敌忾”,或是“形同陌路”,由误读走向误写。近年来,在中国的电视研究领域,我们看到不少“左右为难”的理论文本,它们带给学界一种“尴尬的繁荣”:数量可观、质量堪忧。更为不妙的是:因为问题意识模糊和逻辑起点重复,电视研究的理路日渐局促而狭窄。
怎么看?又怎么办?身为这一领域的后辈,近年来,我的确看到周遭前辈或同辈(也包括我自己)在四处借力:或是搭上新媒体发展的“快车”,或是寻了西方先进或中国传统理论“做伴”……这种倚重外部性经验和观念资源的方式,不是没用,但久而久之,依然有“隔靴搔痒”之嫌。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转入电视研究的内部思考问题。诚然,这种转向尚不成熟,但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直面“尴尬的繁荣”。甚至,正是聚焦于内部性经验和观念资源,让我欣喜地发现:电视研究正当时。这里从社会转型、媒介演进和理论纵深三个方面,提供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可能。
社会转型:从宏观到微观的议题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通俗地讲,不只是“求新”“求强”,而是“求变”。诚然,当新兴事物出现、稳态事物变强之时,与之相关的思考和研究往往涌现。比如,中国电视研究的发展,就与中国电视的兴起和走强密不可分。但是,“新”和“强”并非思考和研究的本质,统摄“新”“旧”“强”“弱”等的“变”方为问题和逻辑的圭臬。于是,哪怕在中国电视被认为变“旧”变“弱”的今天,中国电视研究也不该有危机感,因为我们依然可见“变”之现象。反过来说,如果电视研究只考虑课题经费、热议程度等功利性因素,一味“求新”“求强”的话,它必然南辕北辙于“求变”的研究本质,同时自戕于学术合法性。事实上,若是真正“求变”于电视研究领域,会看到“新”“旧”“强”“弱”等在不同层面和程度呈现出多元的图谱。而且,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电视研究的多元图谱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具体体现为从宏观到微观的鲜活议题。
(一)结构性的社会议题
从宏观层面来看,转型中国的结构性变迁,从顶层设计到边缘突破,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无论大小成败,都在影响着国家、社会和每一位民众。电视,作为提供大众视听产品的媒介组织,它既受到结构性变迁的影响,也影响着结构性变迁——此间的互相建构(影响与被影响),制造了一个多元的议题空间。
比如,当前热门的若干类型节目,《非诚勿扰》、《养生堂》、《非你莫属》、婆媳题材剧等,如果单个分析,各有千秋,但易停留在业务层面,且难辨偶然因素。若从结构性视角出发,电视研究就该这样思考问题:四类节目,对应着相亲、养生、求职和家庭关系四种需求;四种需求,背后是阶层(流动板结化的社会更强调“门当户对”)、医疗(“看病难、看病贵”逼人DIY养生)、就业(“找工作”成为社会性难题)和代际关系(独生子女一代婚后与长辈的微妙关系)四个议题;而四个议题,都是转型中国社会变革的热点和敏感点。因此,在结构性层面,节目的热门,与满足社会需求有很大的关系;热门的节目,也通过民众的收看改变着社会观念和行为。
在电视研究领域,可深入探讨的结构性社会议题还有很多,而且,它们本身处于变动之中,就学者而言,实乃利好。此外,虽然“社会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④,但从较新视角切入的电视研究,也将拓展这一老话题的讨论空间。
(二)媒介组织的体制和机制
从中观层面来看,电视台与制作公司作为一种生产和传播文化产品的社会组织,只要存在一天,体制和机制因素就一定在发挥着作用。并且,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都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
通俗地讲,体制因素“自上而下”,而机制因素“自下而上”影响着电视组织及其生产活动。正是因为社会与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从电视研究的视角,我们可以关注相关体制哪里出现弹性、哪里仍有局限性,相关机制哪里开始升级、哪里依旧保守。特别是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组织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于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电视组织特别是中国电视组织,当前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
在此,以近期的两个行业现象为例简单说明。一是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摒弃简单的价值判断,在媒介组织层面,我们就可以从体制与机制、政策与对策的关联视角切入剖析其中的局限性和能动性。二是西方模式广泛引入中国,在表象性的节目呈现及收视效果之外,电视研究还可以探讨西方模式对中国电视生产流程和团队建设的现实再造,以及对于中国电视体制的长远影响。
而且,媒介组织体制和机制的相关议题将电视台与制作公司视为“一种文化产业领域的存在与运作形态”⑤,由此,与之相关的电视研究也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等国家层面的思考和精神⑥勾联了起来。
(三)作为行动者的业者和观众
虽然社会结构和媒介体制等宏观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生产的走势,也对电视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从微观层面来看,“虽然结构制约个人,但个人的能动性既维持着社会结构又改变着它”⑦,于是,社会个体在其行动中体现出的能动性,同样也是不该忽视的重点。在电视研究领域,行动者既有作为生产传播主体的电视业者,也有作为接受信息一方的电视观众,“一传一受”都是行动。而在社会转型期,电视业者、观众及其行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革,其中的许多问题尚待我们深挖细究。
比如,“电视民工”这一提法虽是玩笑,但在其背后可以反映什么样的行业生态?在这种生态下,业者的职业心态是什么?在这种心态下,业者的行为模式与过往及西方同业有什么不同?在这种行为模式中,业者之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是什么?又如何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体(合作单位、拍摄对象等)发生关系……这些有质感、有细节的故事,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应该会是有价值的经验性素材。
再比如,有本名为《电视》的中国当代小说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与电视朝夕相伴。在很大程度上,她比我们的情人更亲近,比我们的父母更恒远。我们以为遥控着电视,不过是遥控着一面通向世界的窗口。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们是被那面窗口在遥控着。”⑧可见,在目前常见的收视率、“量化受众”观念之外,观众研究这一块还有相当宽广、尚待发掘的“质化受众”研究空间:怎样“朝夕相伴”?为什么“亲近”?为什么“恒远”?到底是“遥控”还是“被遥控”?
媒介演进: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这是中国电视学者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选择上的通病,事实上,也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界的通病。“追新”本无过,但是,“忘本”的“追新”却是一种狭隘功利的思维方式。对于具体的研究项目而言,“追新”或许能让项目在建制内成立,但却远离了研究的本质。
我们要明白,任何事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面对时间长河,任何武断设立新旧标准的尝试只会徒劳无功于“抽刀断水水更流”罢了。于是,电视研究的展开和推进,必须将特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放入媒介演进的社会—历史坐标中。电视,也曾作为新媒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由“作为新媒体”变成“面对新媒体”。那么,目前的电视研究是否已将电视成长和成熟的历史爬梳清晰?是否能全面地比较“作为新媒体”和“面对新媒体”的电视传播?
在我看来,上述两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答。这里仅从我国电视的演进过程出发,在历史的和比较的两种视角中找寻若干可能有助于解答的思路和做法。
(一)1958年以来的中国电视史
在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整体高度,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等专业图书⑨以及每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已经在并继续在铺陈中国电视的事实进程。另如胡智锋关于中国电视创新的时期特征“三品”论——中国节目创新经历了从以“宣传品”为主导到以“作品”为主导,再到以“产品”为主导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从对多种传媒艺术样式的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探索,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特征和艺术特征;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进行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效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拥有较大的创新空间⑩——也就中国电视生产领域的内在规律和走势做出颇具解释力的阐述。
对学术前辈们在宏观层面的理论贡献除了借鉴和享用之外,当前的电视研究在历史思考层面并非无事可做:第一,中观和微观的电视史叙事。比如,中国广电监管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某种类型节目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某一电视机构的组织发展、某一电视业者的个人职业发展(生命史)等问题,都可以有三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第二,电视史料的搜集和整合。1958年以来,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节目万万千,但真正被找出并进入研究视野的却没有万万千。借由数字化技术,当下理应建构、拓展节目影像素材的研究数据库;还有就是,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电视文献和影像素材更有待搜集和考证。第三,“走进”故纸堆、旧影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走出”。“走出”之后,或能夯实当前中国电视研究的基础和厚度,助力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以及启发中国电视实务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
(二)作为新媒体和面对新媒体
如今,新媒体、全媒体、媒介融合的话语和实践甚嚣尘上,以至于“在学术界里有许多人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旧媒体终将被新媒体所取代,因而已经没有研究旧媒体的现实意义了,‘新媒体研究一窝蜂’的热潮随即出现。如此这般的旧媒体研究无用论与新媒体研究热,在中国、日本和欧美都非常普遍。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每个时代都曾出现新媒体,都曾出现类似的现象和论争。”(11)
在我看来,当下的电视研究如果仅仅思考“面对新媒体”的现象、问题,那么,最后难免遭遇“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尴尬。诚然,“面对新媒体”的理路不是不可取,但它仅就不同媒体在同一时期的现象、问题进行讨论,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就同一媒体在不同时期的现象、问题进行讨论。两面合一,这种真正意义上“融合的比较视角”才是恰切的、完整的。由此,在“作为新媒体”的电视和“面对新媒体”的电视之间进行比较,考察不同时期的社会情境、职业认同和生产机制等话题,或许能够得出更丰富、更有启示的观点和结论。
“融合的比较视角”除了在“作为”和“面对”之间进行关联分析,还需要结合技术和制度因素去挖掘本质,比如所谓“新旧媒体”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新旧论”,那么,若在制度层面书写“新旧论”,会有什么样的景象?是否有一些新问题、新解释的浮现?技术更新,是否一定带来制度的更新?制度更新,是否一定推动技术的更新?中国电视,是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相关研究的优良领域。
理论纵深:可能的观念和方法论
社会的转型、媒介的演进,给予中国电视研究更大的空间和潜力。前文从两个方面就一些拓展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诚然,提出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为了更好更深入地作答,我们还需要观念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武装”——这就是本节所谓的“理论纵深”部分。
(一)转型社会学的启示
“面对中国的转型社会,要把握与‘经济奇迹’并立的‘体制奇迹’,就必须形成转型社会学的独特的问题意识,构造出‘转型问题’并加以研究。”(12)虽然,前述为社会学者所言,但对于身处转型中国的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么,中国电视研究如何受启于转型社会学,并与之对话呢?第一要思考的是:中国电视为何转型?关于社会变迁的文献告诉我们,可以从技术、意识形态、竞争、冲突、政治、经济、全球化和结构性压力(13)等多个维度切入,分析转型的不同维度、不同原因的中国电视,是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相关研究的优质及其彼此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影响比重。第二要思考的是:中国电视如何转型?它和社会变迁的主要模式——进化、扩散、涵化、革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官僚化(14)——的关系是什么?转型社会学和社会变迁理论给中国电视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观念架构,解放了其略显窄化的理论视野和理路(但绝非意味着“转型电视学”“电视变迁理论”等“戴帽理论”的成立)。不过,转型中国的画卷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其间具体的社会情境、个体及其活动曼妙多元,如何探究?
这就涉及到究竟哪种方法更有解释力的问题。“如果说定量方法对于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夷平,社会运作高度制度化、规划化的西方发达社会来说,的确常常是更适用的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质性研究方法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就具有三方面的特殊性,体现在: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以及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15)——笔者赞同此观点,认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6),即质性研究方法的充分使用,对于当下中国电视研究的推进和深化大有裨益。
(二)新文化史的借鉴
媒介实践的演进,相应带来的是媒介历史的书写。前文所述“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概言之:一是在“宏大叙事”之下重视中观和微观的探索,二是强调脉络的和多元的思考。那么,如何在这两种视角下夯实电视研究的经验和逻辑积累?在我看来,新文化史的路数或许是可以借鉴的,因为它让历史更细腻、贴地、有质感,“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特殊的生存策略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性。相对于将重大历史事件放在某一目的论体系中去寻求因果解释的现代史学来说,新文化史感兴趣的是事件的具体过程,要根据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其特殊意义。”(17)
必须要说明,我对新文化史的认识并不深,只读过少数几本书籍(18)。但就在这几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经常会想:电视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电视的历史,是否也可以这样书写?日常化的电视生产和电视业者的日常生活,是否对我们理解过往的行业发展有所助益?多元的视角和包容的脉络,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推进今后的电视研究?起码累积更多的历史和经验素材?
的确,在电视领域,严肃的学术研究罕见同类作品。不过,大众化的电视产品,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倒是出现了多部具有新文化史意味的影像文本,比如关于电视剧与社会变迁的《电视往事》,关于“春晚”与民众生活的《春晚》以及关于电视文艺与时代发展的《绽放的力量》等。所以,我们何妨在学术研究领域尝试一下呢?
结语:“成长,待长成”的电视研究
综上,本文从社会转型、媒介演进和理论纵深三个方面,对中国电视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做出了一种探索性检视。所谓“正当时”,自是意味着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可妄自尊大,“审慎的乐观”或许是一个较好的描述。所谓“审慎”,是因为中国电视研究仍旧“待长成”,对于电视实践的指导能力,以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话能力,都还需加强;所谓“乐观”,是因为中国电视研究一直在“成长”,我们的研究对象依然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着,我们的研究背景——转型中国持续提供了多元动态的社会—历史情境,我们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且融合了多个学科和方向——身为其中一员,至少我觉得,可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层出不穷,而问题及问题意识,方为研究活动最本质的“源头活水”,不是吗?
当然,上文讨论的三个方面,带有相当浓郁的个人学术训练和兴趣之痕迹,仅是一家之言,确有挂一漏万之嫌,也绝非盖棺定论。在此,若能引发电视研究同行的思考乃至共鸣,已是极好的事情了。
注释:
①潘忠党:《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总序。
②[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页。
③徐帆:《电视研究》,见童兵:《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④[英]洛佩兹、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⑤[澳]科特尔:《媒介组织与产制》,陈筠臻译,韦伯文化2009年版,第4页。
⑥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1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0/25/c_111123409.htm。
⑦[美]克罗图、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⑧庸人:《电视》,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⑨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11)卓南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传媒学术网2005年11月28日,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3229。
(12)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见李友梅等:《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3)(14)[美]瓦戈:《社会变迁》,王晓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1、67-92页。
(15)应星:《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9页。
(16)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7)姜进:《新文化史经典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
(18)比如[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英]布里格斯、伯克:《最新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络的时代》,李明颖、施盈廷、杨秀娟译,韦伯文化2006年版;[英]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