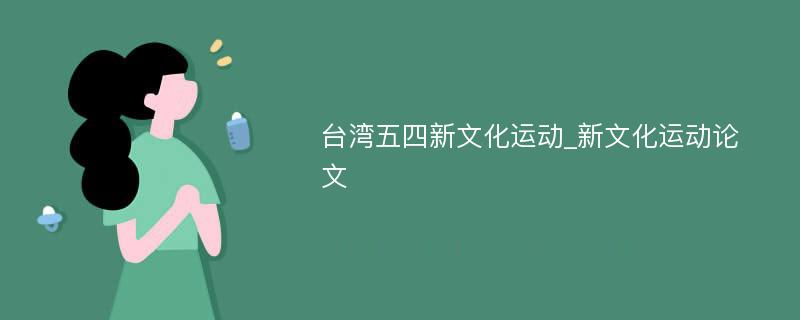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同声相应论文,同气相求论文,在台湾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5月4日,北京古都掀起了“五四”狂飚。不论当时及后世对此评价如何分歧,但它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的转折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五四”狂飚的威力所及,不仅席卷了中国大陆,而且也在台湾海峡激起了波涛。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五四”新思潮在台湾的传播和影响大体有两个渠道、三个时期。两个渠道,指日本渠道和大陆渠道;三个时期指日据时期、光复时期、解严后时期。
台湾留日学生有吸收新思潮的有利环境。“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不仅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义,与中国大陆留日青年共同组成了“声应会”(参阅林载爵:《五四与台湾新文化运动》,见《五四研究论文》,1979年5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而且通过办刊物、 写文章、组织巡回讲演等方式来表达这种共同的关怀和认同。作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主要是《台湾青年》和《台湾民报》。前者于1920年7月16日创刊于东京,发行18期后,于1922年4月1日改名为《台湾》, 1924年5月10日终刊。代表人物有台湾留日学生林呈禄、吴三连、 王敏川、刘明朝、蔡培火、甘文芳、陈端明、陈炘、 林伯殳等。 后者于1923年4月15日创刊于东京,1927年8月1日迁移台湾印行。 该刊与《台湾青年》的主要区别,是由“汉和兼写”改为以“平易的汉文”为写作工具,因而更具影响,更显威力。
大陆渠道当然是影响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主渠道。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为例,他直接影响的台湾青年就有张我军、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洪绍潭、林剑腾、吴文生、简锦铭、卢炳钦等20多人,其中张我军就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不仅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名文《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首先对台湾的旧文化抨击发难,引发了台湾文学界的“新旧文学论战”,而且创作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乱都之恋》、《买彩票》等论文、新诗、短篇小说,显示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尤为可贵的是,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评介了大量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台湾撒播了“五四”新文学的火种,其中包括鲁迅的《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 正传》,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冰心的小说《超人》,郭沫若的新诗《仰望》,郑振铎的新诗《墙角的创痕》,焦菊隐的新诗《我的祖国》等。
以时间划分,五四新思潮在台湾的影响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大约在1920年至1925年前后, 其高潮掀起于1923 年至1924年。由于台湾当时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民众的百分之八十都是佃农,在一小撮跟日本殖民者相勾结的大地主的阴影下过着三餐不继的赤贫生活,所以台湾文化启蒙运动虽以语文改革为突破口,但背后所隐藏的主要观念乃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真谛。对于在中国大陆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台湾新知识分子充满了崇仰之情。《台湾青年》创刊号的一篇文章说:“诸君!请看看中华民国青年们的纯洁理想——活泼的运动。他们一旦觉醒,便具有时代性的自觉,为了世界,为了国家,以浑身的热情奋斗,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羡慕的事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台湾新知识分子也表达了钦佩的心情。《台湾青年》创刊时,他们邀到了蔡元培的题字:“温故知新”。在《台湾民报》的创刊号上,陈逢源有诗云:“诘屈赘牙事可伤,革新旗鼓到文章。适之独秀驰名盛,报纸传来贵洛阳”(《祝〈台湾民报〉发刊》)。《台湾民报》创刊号转载胡适的戏剧作品《终身大事》时,编者“超今”(即黄朝琴)在“按语”中作了这样的介绍:“胡博士乃中华思想界的第一新人,他的令先君,前清的时代,曾到台湾做官。博士平时的著述,也常常念著台湾,所以和我们的缘份,算来实在不小,记者抄这篇,载上本报,不但介绍博士的名著给读者阅看,且对博士要表个极大的敬意。盼望其再到台湾同我们同胞谈谈心……”。台湾报刊还转载了陈独秀的重要论著《东西民权根本思想之差异》(《台湾》第四年第三号)、《敬告青年》(《台湾民报》第七号),以及其他诸如吴虞等人物的新思想。在这样的交流下,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便成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典范。
第二个时期是在台湾光复之后直至解严之前。这一阶段在台湾承传“五四”运动传统的第一人就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他首先主持了台湾编译馆的馆务,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流毒不遗余力。编译馆被撤消之后,他又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许寿裳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的运动,是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运动,而“台湾从前在日本统治时期可说是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没有独立自主之权,只有服从听命,绝对不许违抗”,现在重归祖国,亟宜培养民主精神。此外,许寿裳认为,日本的科学“都是追随欧美先进国之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现在台湾所需要提倡的不但是跟随先进国后面的那种科学,更要有独创的精神,迎头赶上,从事于研究那些尚未为人着手的问题,而建立前古所无的发明和发现。”除此而外,许寿裳认为在台湾还需要提倡大公无私的实践道德和增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情。他希望年富力强、精神纯洁的台湾青年能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继许寿裳之后,又有一批亲历过“五四”运动的学者、作者、文化人于1949年以后陆续来台。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回忆“五四”运动,从不同侧面帮助台湾的新生代增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1954年5月4日,刚从印度来到台北不久的罗家伦写了一篇《五四的真精神》,刊登于同日台北《中央日报》。他说:“当五四运动还在高潮的时候,我在北大朋友们合办风行一时的《每周评论》里,用‘毅’的笔名,写了一篇讲五四运动的意义的短文,就明白指出五四运动不单是专指五四那天发生的那件事,和曹、章、陆的罢免与巴黎和约的拒签,而当认为是新文化意识的觉醒、青年的觉醒、与广大民众的觉醒。不久当这运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又在《新潮》发表一篇1 万多字的长文,被上海《申报》等全文转载过的,名叫《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在对于这运动各方面检讨以后,主张大家要认定方向,分开向两个大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积极的研究学术,为新文化运动放一个建设性的异彩;一方面是深入民众为实际解除民众痛苦,增进民众福利而努力。”
1967年9月,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的《新潮》一书。他说:“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反对旧社会制度和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实更远了。”
1973年,78岁的林语堂在台湾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无所不变合集》,书中收录了他回忆蔡元培、周氏兄弟、胡适的专文。1977年,台湾德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林语堂的英文自传《八十自叙》,其中谈到“五四”时期他跟胡适的配合:“胡适在民国7年回到北平时, 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 他由意大利返国, 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mu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平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15与16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的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1989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林语堂之女林太乙撰写的《林语堂传》。书中说,这几篇谈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进经过的文章,是发表在一份英文报上,引起了胡适的注意。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 翻译家梁实秋也是“五四”运动参加者。 1979年4月26日,他在台北《联合报》发表了《我看五四》一文。 文章回忆说,“五四”运动发生时,他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正在清华学校读书。他曾跟同学们一道赴天安门集会,后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后来他还在前门外珠市口煤市街一带发表街头演说,甚至用旗竿打破了一辆汽车的玻璃。他概括说:“我所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约有数端:一个是爱国心的发扬。一切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国家高于一切。人应敬爱自己的国家,不可崇洋媚外。一个是个人自由精神的培养。既不肯盲从古人,亦不肯盲从今人,要善用自己的头脑。”
百岁老人苏雪林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早期女作家之一,迄今为止,各类著述多达三四十种。在台湾举行的一次“五四”座谈会上,她说:“五四是民国8年5月间爆发的,那时候我在安庆教小学,我并没有实际参加五四运动。而且,坦白说,我那时的思想还是保守的,一直到我到了北平以后,我的思想才有机会改变,才真正认识五四的精神和价值。再经过多少沧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赞成和肯定五四的。”
第三个时期是台湾实行解严政策至今。在前述第二个时期,虽然前有许寿裳先生的倡导,后有罗家伦等“五四”同时代人的介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独裁政策,凡二三十年代在大陆出版过作品的作家常常名入黑籍,“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左翼作家作品)一律以异端看待,因而“五四”运动的研究和“五四”进步作家作品的传播在台湾基本上属于禁区。国民党当局不仅对鲁迅作品和30年代进步作品实行“查、封、禁、堵”的扼杀政策,就连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也忠而获咎,对当局表示“大失望,大失望”。所以,台湾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学的断层期。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当局宣布解严之后,台湾学术界和文学界人士以炼石补天的精神致力于填补“五四”一代与当代台湾文学的断层。仅在1989年,台湾唐山出版社、谷风出版社和风云时代出版社就推出了三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不久,台北海风出版社从大陆引进版本,推出了一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赏析,其中也包括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一些以出版纯文学作品为主的出版社如洪范书店陆续出版了不少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台北春晖影业公司还派员到大陆,摄制了一整套介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电视片,收到了史料性与观赏性一致的艺术效果。
1989年,台湾著名文学杂志《联合文学》将第四卷第七期辟为“五四文学专卷”。马森在《前言》中指出:“五四”那一代的作者“最大的贡献是在精神上解脱了历史积累的僵化状态,在形式上为今日的中国文学做出了铺路的工作。没有他们那代人,很难想像我们今日的中国文学会是这样一种面目。”著名“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在同期发表的《怀人量史论五四文学》一文中认为,“五四主要思潮底背后,都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自我意识的认同和发扬,个人人格的觉醒和重视。当时青年学生和作家铮铮抗议,批判传统和现状,正是要争取自己做主人。70年来,受了五四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凡是能坚持这种精神的,多表现得风骨嶙峋。”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在同期发表的《五四三巨人》一文中极力推崇胡适、鲁迅、周作人。他说:“五四时期真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文化史上最有精神、最有生气、最有勇气说真话的一个时代。三人白话文写得极好,古书读得极多,最主要的,他们攻读西洋文学、思想真有悟会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古老的中国,加以全盘的批评,不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对那旧文化、旧社会、旧道德有所袒护。这点我觉得最了不起,也最令我心折。”研究台湾文学史的权威学者叶石涛也在同期发表了《五四与台湾新文学》一文。 他说:“民国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它所包含的活动层面很广泛;它不但是政治、文化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主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革新运动;特别是以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革命为其主要的一部分,给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带来内心性的、深化的觉醒。尽管当时的台湾在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下,但台湾的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和新生代知识分子,很迅速地接受了五四运动各层面的影响,在五四运动的思想革新的刺激下,展开了文化的革新运动……除五四运动的刺激和冲击之外,威尔逊的弱小民族自决论,以及日本大正民主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想也发挥了相辅相助的效用。所以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是变相的反日民族运动,其实是推翻殖民地统治获得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重要的一环……不可否认,没有五四就没有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五四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指针之一,这是可以确认的事实。”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主将张我军的真知灼见。“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并引之为典范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丰富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这原本是台湾学术界早已达成的共识。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台湾岛内“台独”舆论甚嚣尘上,台湾文坛出现了一种噪音。有些人无视历史,也无视现实,闭着眼睛说什么“台湾文学没有传统”、“台湾文学,是独立存在的,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也不是中国文学的边疆文学。台湾文学就是台湾文学。”他们甚至荒谬地把“五四”新文学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比喻为英国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文学和文化上的“台独”论者,充当的不过的政治上的“台独”势力的奴婢和附庸。我们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重温“五四”运动的光辉历史,不仅对于那些数典忘祖的文化上的“台独”论者是一种很好的教训,而且能帮助那些一时不明真相者分辨大是大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