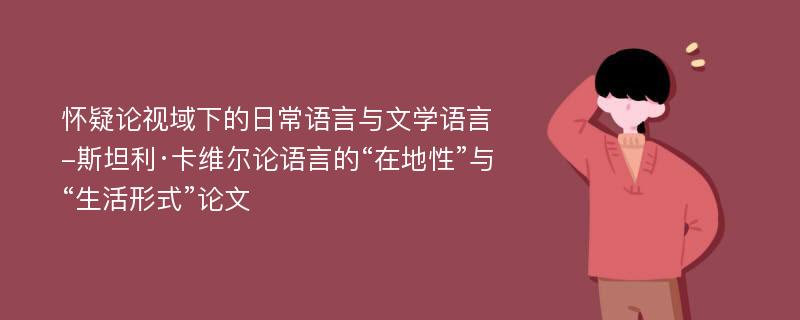
怀疑论视域下的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 ——斯坦利·卡维尔论语言的“在地性”与“生活形式”
林云柯
摘 要 :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下的“语言学模式”与“逻辑学模式”对于认识的“直观”基础存在着根本性争议。斯坦利·卡维尔在日常语言分析中通过对怀疑论视角的批判与吸纳,超越了两种模式的直接对立,并通过“在地性”“标准”(Criteria)与“一般对象”(generic object)等概念阐明了一种由先验的“生活形式”奠基的日常语言与日常理性。一方面指出了怀疑论的“乞题”本性,另一方面也主动地将怀疑论作为对外部权威的免疫因素吸纳进日常语言的原则当中,使得日常成为一种鲜明的自主性与革命性的理性范畴。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揭示出文学语言何以使得文学写作成为一种极致而决然的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反思活动。
关键词 :斯坦利·卡维尔;在地性;日常语言;实证怀疑论;“Criteria”;至善论
一、导言:“语言学转向”中的语言学与逻辑学模式
“语言学转向”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以往的文学理论视野中,这一转向主要是指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在另一同题的思想脉络上,约翰·塞尔1975年面世的《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标志着语言分析哲学开始介入文学研究。理查德·罗蒂选编的理论文集也以“语言学转向”为题,将诸多语言分析哲学划归为一种整体性的理论范式转向。后者对于“语言学转向”的理解倾向于关于逻辑实证的论述,表面上虽与前者同题,但又似乎彼此无涉。
DGIWG发布的成果分为文献和注册资料2种。文献包括地理空间信息类标准与专用实施标准、技术报告、产品规范、手册与指南、标准工作路线图(road map)和早期文献,其中,地理空间信息类标准与专用实施标准规定了军方地理空间信息的构成,技术报告是推进战略实施的一种申报机制,产品规范由各成员国根据DGIWG标准在多边合作协议下制定,手册与指南规定了标准与产品规范的实施方法,标准工作路线图规定了未来的标准化工作计划及相关的工作计划,早期文献即DGIWG不再维护的文献。DGIWG现行的测绘地理信息类标准、规范和指南见表1。
但事实上两者在同一主题下的交集既有正面的,也有潜在的。较为正面的交集发生在1935年和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争论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真正在法国思想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卡尔纳普所坚持的是基础语言的经验主义特征,并表达为可观察的断言,而这些断言所构成的陈述也是基础性的:“逻辑学,是一种数学,或是语言的句法,而语言被理解为规则的体系。”[注] 安托尼亚·苏莱:《1935年和1937年巴黎会议对维也纳学派的接受,或“纽拉特风格”》,米歇尔·比特博尔、让·伽永编:《法国认识论1830—1970》,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年,第31页。 而在纽拉特看来,一旦我们选择了以一种“逻辑语言”为“统一科学”奠基,就会使得科学实证变成一种“应用逻辑学”。这里最根本的矛盾在于,一种建构主义的数理逻辑思维将数学限制在了逻辑学的范畴中,这种由语言符号作为“统一科学”奠基的趋向是纽拉特以及法国认识论传统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数学的逻辑化意味着自康德以降的“纯粹数学”所带来的“先天直观”(空间与时间直观)的丧失[注]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3页。 。
在诗学理论中也能够找到两者交集的潜在证据。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指出,诗学不发现和派定“意义”,而是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由此,他反对“新批评”的解诗原则:“只有一首诗的文本和一部《牛津英语词典》,即可提供比一般读者稍许透彻、深刻的解说。”[注]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可见,在卡勒看来,诗学并不依赖任何“赋义”,也不是对某种先在意义的发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立场的论述中,卡勒首先提出,对于“语法”和“规则”的检验所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学家“心照不宣的知识参照”,即一种语言能力,而非逻辑上的实证能力[注]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51页。 。
可见,从直观之可能性的角度看,语言学模式意味着:什么落入了我的(语言)直观能力的范畴之内?而逻辑学模式则意味着:我们通过何种(语言)逻辑形式为我们的直观提供了可能。前者的立足点在于,语言承载了人类某种认识直接性的能力;而后者则力图建构使得认识能够更为清晰的语言表达形式,其代价就是对认识的直接性在相当大程度上的拒绝。在这种理解下,语言分析界掀起了一阵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视为与逻辑学模式一样的“先验策略”的思潮。这种理解即将康德的哲学贬低为一种不清晰的逻辑形式,也将罗素和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归入了“先验哲学家”的范畴[注] 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2.。而其之于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后果,则表现为日常语言哲学对于“先验”观念的抛弃,使得语言学模式迅速走向一种由语用学主导的“实用主义”范式,由此,语言学模式逐渐走向了相对主义。
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在《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中,他描述了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氛围。此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意义证实理论”(Verifiability Theory of Meaning),在这样一种理论下,所有自身不是纯粹逻辑形式的问题都被要求提供可观察到的证据才能判断真伪,如果不能被实证,则被当作“伪问题”抛弃。如此一来,形而上学、伦理、美学以及宗教问题就都被视为“无意义”(meaningless)的[注] Stanley Cavell,Themes Out of School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209-210.。卡维尔一方面认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暴力,而另一方面他也无意在过度的实用主义方向上将哲学变得“简单而琐碎”。他认为我们对于任何思想的批评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分析它们赖以产生的方式。这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的日常语言哲学不是为否定任何思想和事物的价值而存在的,而是要从日常语言而非哲学理论中挽回上面这些范畴的意义“直观”。这是卡维尔思想的基本目的及特质所在。
二、日常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对实证怀疑论的“乞题”批判
卡维尔早期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在其第一篇关于日常语言的文章中,卡维尔选择了当时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森·梅茨作为商榷的对象,后者不但是该流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少数在现代命题逻辑与斯多亚逻辑学之间展开古今对话的研究者。在《论日常语言的确证性》一文中,梅茨指出日常语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明确地界定其究竟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是“分析性”的还是“综合性”的。因此日常语言的确证性标准本身是模糊的[注] Benson Mates, On the Verification of Statements about Ordinary Language, Inquiry , vol.1, no.1, 1958, p.162.。
找到与产品有高契合度的知名人物帮助用户做消费决策,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实际体验产品。用户沉浸度越高,越容易对视频中介绍的物品感兴趣,这样也利于视频展示的产品销售。例如:爱开箱短视频节目。每期有一位开箱达人给大家介绍一款新奇的好物,说明自己的使用感受,满足用户好奇心。既保证视频高可看性又实现高转化率。
冷凝式节能器采用强化翅片换热管结构,翅片管外部走烟气,管内走水,同时冷凝式节能器本体结构紧凑,占用空间较小,安装位置可因地制宜。
梅茨选择的批评对象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吉尔伯特·赖尔。在《心的概念》中,赖尔区分了“事件”与“素质”,以及更具体的表述:“知道那个事实”和“知道怎样做”。后者在赖尔的日常语言观中等同于一种可以做某事的能力,这样的词汇通常被作为表示智力的形容词[注] 赖尔:《心的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页。 。赖尔选择了一类特殊的词汇来佐证这种“能力”,他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自愿”和“负责”。赖尔认为在这两个词引导的陈述中,虽然某一行为并没有发生,但是说话者的“能力”却得到了表达。比如“自愿”所暗示的意思是“本有能力不做”,而“负责”所暗示的则是“本有能力避免”。赖尔认为这种对于说话者能力的暗示,就是这两个词的“日常用法”[注] 赖尔:《心的概念》,第73页。 。
在卡维尔的理解中,日常语言不同于哲学性语言,它不是一种用于论证或者证明的“中介”,而是我们栖居其中的“生活形式”本身,这意味着日常语言之中用以做出判断的“标准”也不能仅仅是一种外部标准,否则就仍然无法逃开实证主义的指责。由此,卡维尔着重解析了维特根斯坦关于“Criteria”的概念。
梅茨的批判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于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质疑,即日常语言自身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一致性原则,而只是实用性的和相对性的。因此,对于日常语言的“原则”的申明是卡维尔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卡维尔反驳梅茨的立足点在于,同样词汇的“日常用法”实际上并不在于其“词义”是否一致,而需要首先明确日常表达所属的不同类型,只有明确了表达的类型,才能进一步分析语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卡维尔由此提供了两种日常语言的基本类型,用以区分奥斯汀与赖尔之间的分歧:
(1)有些陈述用以提供实例(instance),这些实例是关于在语言中我们在说“什么”:
“当我说了……我就不是说——” “当我们问……我们就不是在问——”
(2)而有些时候,这些实例有阐释性的成分附加,当我们提供实例的时候同时也就提供了对这一实例的阐释,而这样的陈述也会通过指涉第一种类型而被检验:
“当我说……我是指(暗示,说)——” “我不会说……除非是我指——”
卡维尔的分析实际上指出,奥斯汀和赖尔对于“自愿”的理解并非基于“词义”的一致性,而是代表了关于“自愿”的两个彼此独立又具有奠基关系的日常语言层次。奥斯汀的“用法”所显现的是这一词汇在某一语言中的应用“实例”,以卡维尔的转化来说,即“我们可以说‘自愿馈赠’”,在这一例子中“自愿馈赠”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它所提供的是关于“日常语言”的明见性层面,即在所有“通常情况”下,在“自愿”所标识的自发性当中,我们获得了“馈赠”的概念。而赖尔的用法则属于一个日常之中的“例外”层面,在这一层面中“自愿”或者“负责”这样的词汇的意思才被特别质询:“问一个孩子是否对打破窗户负责,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去问它是否为他按时完成作业负责,这是没有意义的。”[注] 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6.
在这个分析中,卡维尔指出实证主义者忽略的是,赖尔的层面只能由母语持有者提出,而奥斯汀的层面则属于非母语学习者。对于后者来说,语言最初被把握为诸多用法实例,而只有当这些用法实例被转入“母语”层次中,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这门语言,这也是语言学习中的自然倾向。卡维尔指出,一旦进入“母语层”,实证主义的某些质疑就成为“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即虚设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比如“他是否需要为按时完成作业负责”这类“反例”:“我们的满意、正确或者许可是否和自愿有关,这个问题在这里没有产生;但是这是由于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不会被拿出来质问,因此才没有什么可能出错的地方。”[注] 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 p. 7.因此,实证主义的“怀疑主义”没有意识到,其质疑的不是日常语言经验确证性的缺失,其成立的前提在于预设我们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的“在地性”(native)。赖尔的例子说明,只有能够直观到语言中的蕴意(implications)或者其中的“暗示”,才意味着在 “母语层”掌握了语言。这才是日常语言有效性的最终标准。
通过将“在地性”确立为日常语言的基本原则,卡维尔反向质疑了实证主义怀疑论的有效性,在对于日常语言及信念的质疑中,实证怀疑论所忽视的根本问题在于,无论何种质疑,最终都需要落实到相应的“母语层”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一个疑问能够被理解的潜在前提在于,它能够在这种“在地性”中被回答。因此,实证怀疑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总是倾向于提出以某种特定的“语言”无法回答的问题。卡维尔指出,实证主义的批判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让一个问题能够“有意义”(make sense),而“有意义”的依据并不在于经验确证,而在于其得以被提出的语言本身,否则它就是“不切题”的[注] 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 pp. 13-14.。
因此,卡维尔进一步指出,赖尔所例举的“蕴意”不但不是缺乏原则的,反而是日常语言原则性的核心所在。如果说奥斯汀的“实例”层面标识了作为语言学习主体对于一种语言得以运转的“自然状态”的识别(“自愿”即我朝向他人,而“负责”即我对他人的回应),那么赖尔的层面则提供了“必然性”层面,即“自愿”和“负责”的凸显标识了对于“自然状态”的偏离。而身处于同一种语言内的问答者能够直观地框定这种偏离的范畴和指向:“偏离”激发了我们判断的意向,而“在地性”则提供了我们能够做出判断的可能。从最日常的表达上来看,即对于处于同一“在地性”中的问答者来说,问者总是知道“我在问什么”,而回答者总是知道“他希望我提供哪一类的回答”,这就是我们对于“蕴义”与“暗示”的日常理解。
目前,中国已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向度。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中国社会取得了惊人的历史性进步。然而,在近几年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也萌发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安事件,其中,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征地拆迁引发的“钉子户抗争”即是近几年最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
我们总是感觉我们想要去提问,而总是忘记我们其实早就有答案了。(也可以说我们拥有所有能够给出一个答案的全部要素)苏格拉底告诫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形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就此提醒我们自己。所以,对于那些想要用日常语言言说的哲学家来说,他们也要知道: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何时——我们应当——说什么。[注] 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p. 20.
三、“实指定义(解释)”与语言习得:日常语言的伦理性奠基
对于卡维尔来说,理解一个问题也就意味着理解这个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同样,理解日常语言很大程度上就是去理解我们的语言学习过程。在日常语言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语言学习焦点一个集中在开篇关于“实指定义”的问题,另一个集中在“意义用法论”的理解上。虽然这两个问题看似非常基本,但实际上却在当时的研究者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比如乔治·皮切尔认为“意义即用法”实际上宣告了对于词语客观意义追述的不可能性,词语完全沉沦在用法之中,由此“实指”本身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行为[注] George Picher,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 NJ: Prentice Hall, 1964, p.252.。而唐纳德·古斯塔夫森则认为,“实指”承担了“this”这一“逻辑专名”的意义,没有“实指”则“一个(而非‘这个’)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意义的[注] Donald Gustafson,On Pitcher’s Account of Investigations § 43,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 vol. 28, no. 2 ,1967, pp. 253-254.。
心电图在心肌缺血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新定义对于以往的心电图诊断标准未加修改,但增加了部分内容。本次新定义认为心脏记忆是一种电重塑现象,在异常心室激动(如快速心律失常、起搏或频率相关传导异常)后可出现弥漫的T波倒置,强调在上述心律失常时如出现复极异常,应考虑电重塑的可能性(心脏记忆),此时不能仅将心电图变化作为心肌缺血的诊断依据,而应进一步结合患者的缺血症状、cTn的演变模式和其他影像学资料来帮助确定诊断。
卡维尔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接近古斯塔夫森。在《理性的主张》的相关段落中,卡维尔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我通过指向一只小猫并说“小猫”这个词,孩子跟着我重复了这个词。在整个场景中,我所希望的是将那只小猫和“小猫”这个词建立起对应关系,但这一场景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的微笑、抱着她、我鼓励她的语气等等,我并不能确定她是否理解了我的期望。直到有一天,又一只猫经过眼前,孩子又一次说“小猫”这个词,此时我似乎确定她至少成功地学到了我所教授的东西。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她微笑着看着一块毛皮说:“小猫”。我才发现她并没有真正学会我所要教的东西[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2.。
这就是语言学习初期“实指”定义的疑难所在,故而如皮切尔这样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无法在这一行为中获得确证性,因此它只是一种次要的语言学习方式。但是卡维尔指出,这种理解其实是误以为在语言学习中,学习者总是优先指向关于一个“外部对象”的确证性,而由于这种确证性无法达到,故而“实指”的作用就被降格甚至取消。但实际上在这一原初场景中,重要的是学习者已经开始试图进入与“我”共建语言“在地性”的工程当中。这意味着孩子并没有仅仅在一个“音位”的层面上理解“小猫”这个词,而是将其带入一系列能够得到教学者回应的意向当中:
她对毛皮也做所有这些行为,微笑,说着“小猫”这个词,并触摸它。可能这里发生的句法应该被转译成:“这个就像小猫一样”;“看这只好玩的小猫”;“柔软的事情总是好的不是么?”;“看阿,我还记得当我说‘小猫’这个词的时候你那么的高兴”;又或者是“我喜欢被爱抚”。[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172.
卡维尔实际上指出,语言学习并不是教学者将一个客观意义作为某种“物质”给予学习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日常语言的自然倾向中,学习者不可能只停留在奥斯汀的“实例”层面,“实指”教学所建立的是一种主体间的指向“共通性”,这意味着我们将开始学习(教授)“我们的语言”。而之所以我们在语言掌握的熟练阶段能够直观地把握赖尔层面的“蕴意”,也恰恰是由于语言中的“意义”并没有被一种“命名性”的“实指”所勘尽,否则在一种被客观对象勘尽的语言里,我们的想象、投射与判断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卡维尔指出皮切尔和实证怀疑论的问题实际上都在于没有理解我们在“实指”行为当中学到的究竟是什么。语言的“意义”而不是狭义的“词语的意义”才是“实指”所真实指向的东西,孩子的回应有其“意义”意味着他接受了我们通过“实指”给出的进入语言“在地性”的邀请。语言学习不是以词义或者事物开始的,而是始于我们亲近学习者,让我们之间相关的“生活形式”在语言、事物和人之间流转起来。而为了这种可能性,教授者就必须以身作则,从而让学习者能够跟从我们,这就是由“实指”所激发的语言的“意义”:“‘教’在这里意味着‘向他们显示我们是如何说的和如何做的’,并且‘接受他们是如何说和如何做的’等等;这远远比我们知道什么和我们能说什么重要得多。”[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178.
在此卡维尔同时回应了我们开篇提到的问题,语言尤其是日常语言确实存在着某一“先验”层面,而无论是康德式的“观念论”还是逻辑学的逻辑形式,都不必被理解为一种对于认识的特定辖制,它们实际上也都是为了抵御各自时代不同的怀疑主义而进行的语言“在地性”构建。对于康德来说是为了抵御笛卡尔、贝克莱与休谟问题,而对于罗素和弗雷格来说则是“心理主义”问题。较之其所抵御的怀疑主义来说,它们都是更具有“可理解性”和“可对话性”的。因此,怀疑主义的无效性在于异质的语言“在地性”之间的问答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在尚未进入对方“在地性”情况下的怀疑“僭越”,是怀疑主义的根本谬误所在。
在卡维尔看来,“先验”意味着在我们与特定的认识对象的关系之下,总有另一个能够脱离“知识秩序”关于生活世界之“普遍性”的奠基层面,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而对于日常语言来说,卡维尔指出其“先验”层面在于一种伦理性:日常语言的“相关性知识”实际上在于我们如何建立起一种日常信念,在于我们知道我们会对“彼此”的语言和行动负责。这也就是为什么奥斯汀和赖尔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都意识到“自愿”“负责”以及“承诺”和“命令”才是我们语言中的基本日常词汇。而在“实指”行为中所指向的对象,正如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一样,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的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对象的“物自身”,但是在伦理意向的运转当中,在我们的语言当中,这种“存在”总是能够被证成的:
一方面加强技术指导,由各市区派出技术人员赴乡镇村现场指导,搞好施工放样工作,抓好日常技术管理。另一方面,严格工程验收程序,制定《苏州市农村村庄河道疏浚整治实施管理办法》,要求全市各地建立起以镇为单位的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理档案制度,档案资料要达到“一图(村平面图)、一表(村河道情况表)、一合同(本次河道疏浚工程施工合同)、一像(施工前后的对比图像)、一账(本次河道疏浚工程实施财务账目)、一总(本次河道疏浚整治实施工作总结)”的“六个一”标准。对疏浚河道的验收,坚持整治一条验收一条,凡验收不合格的河道,明确整改,责任到人。
当你说“明天我来接你,我保证”,那么孩子就开始学会什么叫持续一段时间,以及什么叫作信任,而你所做的将显示这种信任是值得的。当你说“穿上你的毛衣”,则孩子就学会了命令及权威是什么,而如果颐指气使让你感到焦虑,那么权威者就是有所焦虑的,权威本身即是不安的。[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27.
四、日常语言与怀疑主义的共生性:“Criteria”及日常的“免疫”
梅茨强烈质疑这样一个未经显露的“事实”能够提供一种明确的语言用法,并且指出在日常语言哲学内部,关于“自愿”的日常用法也无法统一。他举出另一位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为例,在后者关于“自愿”的例子中,这一词汇仅仅用来区分主动行为和应激反应,比如我们可以说“自愿”加入军队和馈赠礼物,而像打嗝这样的行为则是“非自愿”的。由此梅茨指出,语言的日常用法并不能自发地形成一种一般性的认识论意义,而仍然需要放回可确证的经验命题当中给予考察[注] Benson Mates,On the Verification of Statements about Ordinary language, Inquiry , vol.1, no.1, 1958, p.170.。
首先,“Criteria”作为“标准”往往出现在“官方用法”当中,且往往与“Standard”纠缠在一起。在卡维尔看来,前者所关涉的判断是关于将对象归入哪一类型,而后者则是关于满足某一资格的相关程度。比如,一个医生不仅要根据自己在医学院学到的相关知识作为“Criteria”来判断病人所患疾病的类型,进而还要能够依据“Standard”来判断疾病的程度。又比如分数作为“Standard”来评价学习掌握的程度,如60分、75分、90分等,而“Criteria”用来判断学生的“及格”“良好”和“优秀”,后者被理解为从属于前者。而根据卡维尔的解读,维特根斯坦的“Criteria”的认识论地位是独立于“Standard”这一“外部标准”的。拥有一个关于某物如此这般的“Criteria”,即是说一个对象,当它在一个问题中被“Criteria”所判断,其所判断的是,它要么是在这一问题中所能够判断的事物,要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它就不能被识别。因此,并不是“Criteria”从属于“Standard”或者与之并行,而是“Criteria”在语言中奠基了我们判断行为的类别及其被识别的可能性。
由此卡维尔指出了第二个层面的区别,在官方的用法中,“Criteria”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评估序列,它总是被给予预先存在的候选对象,因此,“Criteria”总是使得这样的评估显得尽可能的理性、一致、融贯、非人为以及更少的随意性。也就是说,这样的“Criteria”是被我施于已知类别的对象的。但是在维特根斯坦处,“Criteria”是关于做出断言这件事情本身的:并不是以什么标准来评估一个已知的对象是否符合要求,而是以什么标准我才能说我获知了那个对象。比如一个人是否牙疼;他是否在读、思考、相信、希望;是否在自言自语,是否在注视某个形状或者颜色等等。这样的“对象”和概念都不是被预先归类的(unspecial):“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日常对象以及关于世界的诸概念本身。”[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14.
卡维尔举出一个例子,当一个人问“你穿这个衣服是自愿的么?”,我们的语言“在地性”让我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他‘一定是在说’(Must Mean)我的衣服是奇怪的。”而卡维尔指出,在这样一个回答中,起作用的不是经验实证,而是我何以能够得到意义所指的“必然性”(must)[注] 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pp. 9-10.。卡维尔实际上指出,日常语言的确证性并不在于某一特定词汇的意义或者用法,而在于如何在这种“必然”的理解中确证我们是否处于“我们的语言”当中,没有这个层面,实证怀疑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法被真正提出的:很基本的常识是,一个由对方指向提问方的指号“←”,其所表征的就是这一提问的“必要性”。日常语言的这一原则,才是哲学最本然的思辨状态:
卡维尔的分析仍然承接日常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即我们的日常认识和判断之所以可能,其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客观的外部标准或者对象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于一个判断为什么是有意义的。比如在日常理性中,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以分数为量化的程度标准不能真的对应“优秀”或者“不及格”,我们对一个学生某方面能力的“评估”可能完全不受制于这样的外部量化标准,而对此我总能够也必然要对我的判断给出“Criteria”。卡维尔指出,在“Criteria”的参与下,当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做出判断的时候,所发生的程式实际上不同于对于外部标准的诉诸:
这样的解读实际上就恢复了我们对于“判断”的日常信念,即判断总是一种自发性和自主性的行为。在卡维尔看来,维特根斯坦的“Criteria”所揭示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活动不断地保持我们自发性的永续性,这同时也就使得我们对于对象知识的识别不是一次性的或者盖棺定论的,而是在以日常语言为载体的永续的认识自发性之中不断地被充实或者说强化。这一过程就其实现来说,不必进行一种二元的辩证思维,而就是直接表现为我们对日常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我们是否充分地进入一种语言的“在地性”当中。因此不同于某种对于认识活动的终结性评估,“Criteria”所激发的是关乎“判断”这一概念的“生活形式”,即我们通过判断来理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同意”(agreement)、“接受”(accepted)以及“给出”(given),是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关于“判断”这一生活形式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的)的研究描述了如下三个主要的步骤:(1)我们发现我们正想要知道关于一个现象的某些知识,比如:疼痛,期望,知识,理解,产生一个看法……(2)我们将我们对这些现象所做出的陈述保留下来。(3)我们自问,是什么“Criteria”让我们能够言说我们所说的东西(并且还能够继续以这样的说法言说下去)。[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29.
花样游泳有单人、双人、团体等形式,都是只有女子能够参加。花样游泳起源于欧洲,1920年花样游泳创始人柯蒂斯将跳水和体操的动作混合一起表演,起初只作为两场游泳比赛之间的一种娱乐节目,后来逐渐融入舞蹈和音乐,成为一项优美的水上竞技项目。
4.4 药剂防治 发现园内有轻微病害后,选用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和70%甲基硫菌灵水分散粒剂800~1 000倍液交替喷施,可起到有效预防作用;当病害严重时,选用30%苯醚甲环唑悬浮剂4 000倍液和45%咪鲜胺水乳剂3 000~4 000倍液交替喷施,可有效治疗柿炭疽病。
5.1 农业防治 清除越冬病虫源,保持果园清洁;及时绑蔓、摘心和疏除副梢,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产量;加强水肥管理;深翻除草;应用抗性品种;适时套袋。
构成过腔的不同音乐材料,无意间为过腔构筑起了多种不同的结构样式,使得过腔充满了无穷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将过腔的结构与字腔本身固有的头、腹、尾腔的结构结合起来形成的字腔+(或 0)过腔①所谓“(或0)过腔”是说,不一定每个字腔都要带过腔,过腔的出现也根据艺术的需要。即使是0过腔,对每一个字腔来说,这个位置却是不可替代的。就像剧场中的座位,即使没人坐,但这个位置照样存在一样。这种结构,不仅是对传统曲牌音乐结构的重大突破,更是世所未见的、崭新的昆曲曲牌唱调的基本结构。
“Criteria”作为一些基质(突显、标明、特别说明),其寓于可能被做出的确定的判断之中(即一种非随意性);基于“Criteria”之上的同意就意味着使得“同意判断”这一行为成为可能。而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里,甚至看上去我们建立“Criteria”的可能都需要建立在一种先在的对于判断之同意的基础之上。[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30.
由此,卡维尔就将一种基于“对象”认识之确定性程度的怀疑主义彻底清除出了日常语言,但同时也将“怀疑主义”作为基因嵌入了日常理性之中。之所以日常语言的这一机制能够不受怀疑主义的困扰,恰恰是由于“Criteria”自身就是日常语言之中的怀疑主义基因,因为这一概念意味着我们的判断合法性实质上总是自发形成的,其目的性不指向任何客观性,而是指向理解与认同。想要通过怀疑论动摇日常语言的共同体,从日常理性原则上来说永远都是合法的——因为其本身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基础,本质上是主观的和自发寻求认同的行动;而从行动效果上来说,这种动摇又异常的困难——因为新的“Criteria”只能在寻求认同的行动中才能形成,这就意味着个体对于固有共同体的脱离只能以重建“另一种语言”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意味着一种彻底的自发的革命性。由此,日常语言自身内部的“怀疑主义”基因实际上比外部的怀疑主义要更为彻底,同时也更不容易被消弭。
因此,对于卡维尔来说,“Criteria”就是一剂怀疑主义的疫苗,使得日常语言的有机体具有免疫力,免于来自外部的怀疑主义的攻击:抵御外部怀疑主义的就是我们自身的“语言能力”。传统上,这种“能力”被理解为描述外部世界的能力,但在卡维尔的理解中,这种能力是关于我们学习语言、进入某一共同体的“能力”,而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超出已有语言,脱离并构建新的共同体以及“我们的世界”的可能性。而这就是卡维尔基于日常语言对于怀疑主义的最终处置,从这一层面说,日常语言对于道德、自由和权力的主张实际上要比传统哲学更为极致和绝对: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与之相关联,或者将他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而与之关联,而不是关于一个知晓者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知晓将其自身构建为确实的。[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45.
五、怀疑主义与文学语言:爱默生与梭罗作品中的“一般对象”
这样的对象呈现于认识论者,他不是在与他物的区别中识别它的,也不是将其视为具有特殊面貌的或者其他这类的对象。对他而言不如说是一种无法被识别为特定对象的东西,如果他能够感知到它,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一种通性(thatness)。对他来说,向他而来的是一个孤岛,一个周身空无的躯体,或是一块孑然一身的陆地。[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53.
(三)仅注重软件的操作和结果的分析,却忽视了对统计原理的深度分析和统计思想的逐步渗透,理论讲授不够立系统、深入和立体。
而从文学的“对象”角度考虑,则意味着摆脱“对象”在旧有实例中的具体“身份”,从而使之“一般化”,以等待被文学语言所生成的新的“生活形式”所纳入。卡维尔在对早期奥斯汀的认识论批评中论述了这一点。在《他者心灵》一文中,奥斯汀认为关于一个对象的认识确实性就是给出足以证明“我如何知道”的认识程序,亦即在特定的认识情境中,对象的确实存在就是我对于其“身份”在排他性层面的可能性勘尽:“我说这就足够了是指,对于它(有原因支持,并且关涉着当下的意向和认识目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层面来说是足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与可竞争的其他描述。”[注] J. L. Austin, Philosophy Passag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84.
卡维尔指出,奥斯汀认识程序的实质基础,实际上是认为我们对于外部对象的认识,都是对于“特定对象”(special object)的认识,由此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与外部事物及世界的认识关系是落入孤立的“例证”之中而非普遍的“概念”当中,而如何确定那些“例证”是可以被采用的,我们就仍然要寻求一个外部的权威标准[注]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 p. 52.。而与奥斯汀相对的传统认识论则是对于“一般对象”(generic object)的探寻:
卡维尔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一方面来自其日常语言思想,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来自他能够将其思想运用于文学、戏剧和电影的批评之中。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是以语言为理性基质,在其中界定对象与认识主体的日常存在方式,从而扭转了传统哲学中受制于主客两极的认识论疑难。而从他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来看,其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说明的是,文学语言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在于文学作者总是意图将自己置于原有语言“在地性”的边缘,好的作者由于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能够明确一种极致的反思,也就意味着进入一种“疏离”状态。
在对爱默生和梭罗的阐释中,卡维尔也践行了其基于日常语言对于认识主体与外部对象的这种理解。在“逆反的思想”中,卡维尔通过对爱默生“自我疏离”的阐释确立了一种道德“至善论”的可能。普通的道德或者追求一种个体的沉思与不受外界影响的“慎独”,或者完全以已有的公共标准为辖制,两者都不能在遵循规则中独立思考公共道德律令的合理性。一种“至善论”意味着个人的自由思考最终要为公共道德的改良做出贡献或者成为榜样。在卡维尔看来这是文学的重要性所在,文学就是要让我们与已知进行主动的断裂,并在这种断裂中思考与反思。卡维尔没有因为传统的维氏研究而规避“私人”这个概念,他实际上暗示维氏所否弃的是一种肤浅的私人性,这种私人性,正如他对奥斯汀的批判所显示的那样,位于一种不彻底的、自我辩护的层次上。文学写作恰恰是一种严肃的私人性,一种对私密性的忍耐。他引用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的话:
在卡维尔看来,奥斯汀在这一时期所真正忽略的问题是,“你如何知道”这个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你如何知道某物(存在在那、是什么、是否名副其实)”,而是“是什么让你能够做出这个判断”以及“什么让你认为这个判断是有意义的”,这是传统认识论关于“一般对象”所提出的问题的正确转化形式。正如卡维尔在“实指”问题中所阐述的,其表面上以“名实相符”为目的,但实际上却是通过伦理奠基的“曲行”而到达这一目的的。“实指”行为实际上就是将“特定对象”复归于“一般对象”,从而才能在教与学两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可寄居的“外部世界”。一种对于认识对象的本然判断没有这样的“一般对象”以及“外部世界”作为奠基,奥斯汀式的关于“特定对象”的认识是无法自然展开的,其展开只能依靠一种严格的指称行为,而这种行为恰恰是与维特根斯坦“Criteria”对立的外部权威的自我确证“标准”。
学者越是深邃地将自己投入到其最为私人的境遇之中,最为隐秘的预感之中,他就越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恰恰是最能够被接受的、最为公共的,也是最为普遍的真。[注] Stanley Cavell,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44.
卡维尔指出爱默生很多著名的句子都来自这种私人与公共之间极端的相反相成的勾连。他还引用了爱默生赋予私人生活的极端权重:
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应该寻求成为一个更为辉煌的君主制,对它的敌人更为冷酷,对自己的友邦更加友善与平和,它要追求这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国更甚。[注] Stanley Cavell,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 , p. 45.
卡维尔实际上通过爱默生这种极端的两极修辞说明了一个似乎已经被淡化了的常识,就是我们对文学作品总是要求一种“鲜明性”。正如皮浪主义所提出的“相反者等效”表现为日常语言的基本公式是“谁也不更”,它保有了对于私人感官的信任。这一公式潜在地把关于“现实—虚构”这一组对立之下的语言游戏涵盖于其中,因此在日常语言中常见这样的表达——“文学虚构比现实更真实”。在这样的表达中,“真实”通过“更”从“虚构—现实”这一组低级的对立中提升出来,“真实”由此成为一种判断“标准”,这种提升是由日常语言自身显现出来的。由此“私人性”才没有停留在维氏所说的“私人语言”层面,而被提升为一种由语言呈现出的“Criteria”,而我们不必问日常语言何以是公共的,而是认可由个人的日常语言所呈现的就是具有公共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需要呈现一种私人性的“鲜明”,它是一种让“一般对象”更清晰的意图。一种日常语言与公共生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中保留了一种无限回溯的、自我探究的可能,使得我们能在一种最为理想的层面上,通过最深刻的自我反省、沉思与劳作获得那些作为私人“一般对象”的公共性的种子。这种相反相成,在极端的趋向于断裂的张力中仍保持着连贯与建设性,这便是文学的“至善”所能够承担的任务。
卡维尔的文学“至善论”虽然以一种极端的爱默生式的修辞为引导,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综合性的策略。卡维尔在爱默生对私人性的强调中看到的,并非一种对于他者的拒斥,而是一种敢于面对他者的勇气。他指出爱默生的“自我疏离”实际上是对于羞耻的研究(investigation),在一种严肃私人性被泯灭的所谓“人类社会”当中,道德法实际上并不真的存在,因为严肃的私人视角的缺失使得我们无法在语言中获得探究我们“一般对象”的通道,这意味着我们羞于说“我认为”“我是”,即我们不敢于作为一个人类而存在[注] Stanley Cavell,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 , p. 47.。
“至善论”在爱默生处看起来只是一种精神的传达,而在梭罗处卡维尔则发掘了它的个人实践性。在《瓦尔登湖之义》中,卡维尔将《瓦尔登湖》视为一部基于写作的自我历练:
字词从远处向我们而来;它们于我们之前就已在此;我们从它们之中降生。获得它们的意义,也就是去接受它们自身状况的事实。去发现什么正在言说于我们,正如去发现我们正在言说什么,正如从它们的已言说之中发现那些精确的定位;去理解为什么在彼时彼地它们被如此说出。[注] Stanley Cavell, The Sense of Walden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64.
卡维尔更加注重的是对一种时空与历史感的呈现,比如在开篇处,他不断地将梭罗的处境与美国大陆最早的开拓者们的处境相比照:
(189)南亚瓦鳞苔Trocholejeunea sandvicensis(Gottsche)Mizt.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马俊改(2006);余夏君等(2018)
我们知道在那些凌冽的年月,新英格兰的先人们是如何用木头垒砌自己的居所。这样的民族的原初时间在《瓦尔登湖》中重演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当重做,而它的遥远又证明了重演的不可能性:探索并栖居于土地之上,把诸多疑问的种子播下,如此一劳永逸。[注] Stanley Cavell, The Sense of Walden , p.8.
如果说在爱默生处卡维尔提炼出的是一种共时性的私人与公共之间“一般对象”的探究与融合,那么在梭罗那里开启的就是历史与自然的视域。卡维尔通过对这两个作家的引用说明了在美国的经典作品中确实有其所蕴含着“一般对象”的“一般视域”。在卡维尔看来,文学作为语言与哲学最初的发生地,它本身就呈现出一种类似于瓦尔登湖式的自然状态。《瓦尔登湖》实际上聚集了很多浪漫主义的元素,这让它时而处于一种“超越性”的亢奋当中,但梭罗在这些元素聚集之时对其进行了一种“文学取消”(literary withdrawal),使其得以被揭示却又保持在“一般对象”的萌芽之中:
他对这种取消的描述是站在一种清教公理会(Puritan Congregationalists)的视角,这一视角属于教堂会众中的一员:一种可见的神圣。在这一视角之上,作者笔下的文字以及他自身的行动,它们的观众是全然的共同体,他们聚集于此。对于梭罗来说,最初也是最终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学会如何对他们言说,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的问题是,他要如何建立自己主张的权力。[注] Stanley Cavell, The Sense of Walden , p.11.
卡维尔的文学观可以说是一种由怀疑主义所催生的自然状态,文学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博物学,这也正是由杰弗里·S·克莱默所注疏的注疏本《瓦尔登湖》所呈现的状态。在注疏本中,他对于第一章“简朴生活”的注疏量就达到了四百个以上,它显示了在表面篇幅并不大的散文之下竟蕴藏着如此对的“对象”[注] 享利·戴维·梭罗著,杰弗里·S.克莱默注:《瓦尔登湖》,杜先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这样一种博物学,对于卡维尔来说既是关乎信仰的,也是关乎文学的,同时也是向批评开放的,而经典的完全意义需要在三个层面的融合上才能理解。尤其从文学的观点看,《瓦尔登湖》的作者:
被赋予另一个使命,即走向一种涵盖了创造的、来临的、判断的和救赎的理解形式;由此他需要对究竟有多少诗歌牵涉其中做出自由的裁定,并对道德的编码范围进行诊断;并且,广阔无垠的历史和一两个小规模的史诗也在其中保留了相应的空间。[注] Stanley Cavell, The Sense of Walden ,p.15.
本研究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分析亲子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集聚程度,并利用百度指数自定义时间段功能和地区筛选功能,统计2013—201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亲子游网络关注度,分析亲子游网络关注度的规模位序变化。
卡维尔通过怀疑主义所催生的文学观正是这样一种“视域融合”的文学观。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文学的“视域融合”不是诸多对于文学接受的融合,而是文学自身就是这样一种融合,它自身作为“信仰—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有待融合的层次,而在自身之中又包含了文本、道德与历史时空的融合。如果我们直接提出这样一种文学观,它会显得过于玄妙,而卡维尔则通过怀疑主义由日常语言将我们带到这一境界。
六、余论:卡维尔日常语言思想的影响
卡维尔作为一位全能型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拉塞尔·古德曼所言,他的思想兼容能力之强、兴趣范围之广在同辈人里无人能及[注] Russell B. Goodman(ed),Contending with Stanley Cavell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因此,在一篇论文中全面介绍和阐释卡维尔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是在何种批评领域,通过日常语言哲学分析揭示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这一方面是卡维尔所认为的文艺作品固有的潜在动机,另一方面也是他贯穿于其自身智识生涯始终的方法论诉求。本文旨在阐释与厘清卡维尔这一基础性思想的建构进程,而这一思想也在美国其他理论家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如前文所示,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意图通过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性的“共通感”模式作为一切认识论的奠基,由此哲学、文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就得以在这样一种日常的认识论范畴中连贯地展开,而非用其中一种语言范畴“外在的”施加给另一种语言范畴以某种解释。因此,卡维尔的思想不仅仅如其自身所示被应用于文学,更被广泛地运用于具体的政治以及宗教理论的研究当中,从而也是理解美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宗教精神问题的重要参考思想。安德鲁·诺里斯(Andrew Norris)的《成为我们所是:斯坦利·卡维尔作品中的政治与实践哲学》是对卡维尔著作中关于如何形成作为“生活世界”的人类共同体问题的提炼和阐释,从而将日常语言哲学的应用范畴拓展到政治学。由于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提供了理解主体性与他者关系的新视角,再加上卡维尔的电影批评著作都是以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为核心分析对象,他的理论也被认为要超越德里达的“友爱政治学”而更受到女性主义研究者的青睐。在《非主权自我,责任与他者性》一书中,罗西娜·卡尔茨(Rosine Kelz)将卡维尔与汉娜·阿伦特与朱迪斯·巴特勒进行比较,她着重比较了巴特勒和卡维尔对于主体性的不同看法,在前者看来主体性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历时性地建立起主体性的定义,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探寻个人是如何将自己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为主体的;而卡维尔则更强调主体向他者与共同体建构之可能的开放性,这意味着主体所承载的首先不是自身的定义,而是要成为能够主动接受和拒绝的主体,两者虽然论述的路径不同,但是最后都指向一种对于“未经选择的生活条件的抵抗”[注] Rosine Kelz, The Non -sovereign Self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ness :Hannah Arendt ,Judith Butler ,and Stanley Cavell on Mo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Agency ,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65.,而在《卡维尔、友谊和基督教神学》一书中,皮特·杜拉则将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上升到了与神学互相参照的高度,并认为卡维尔提供了一种对于神学的兼并式的日常视角(Annexation of Theology),他认为卡维尔所给出的视角不仅仅涉及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同时也关涉基督教中上帝与基督在现代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基督教通过求助于上帝而得到完全的最终的解决。而基督则意味着所需即在手,或是说是本然的(nowhere)……基督教教导我们要拒绝我们的有限性。而基督则向我们显示如何去接受它。”[注] Peter Dula, Cavell ,Companionship ,and Christian Theolog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63.
由此可见,卡维尔的思想为一些传统上已为我们所熟识的观念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解读,也开辟了更为切实的实践道路,即一种更为真切的“文学介入”。这种介入不是为政治介入而生的文学,而是文学及审美在一种对抗实证主义的事业中本身就作为一种“文学(政治)行动”而发挥作用。因此,卡维尔的思想也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思想语境中重新定义文学的实践性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9)01-007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14ZDB087)
作者简介 :林云柯,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天津 300071)。
DOI: 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1.008
责任编校:刘 云
标签:斯坦利·卡维尔论文; 在地性论文; 日常语言论文; 实证怀疑论论文; “Criteria”论文; 至善论论文; 南开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