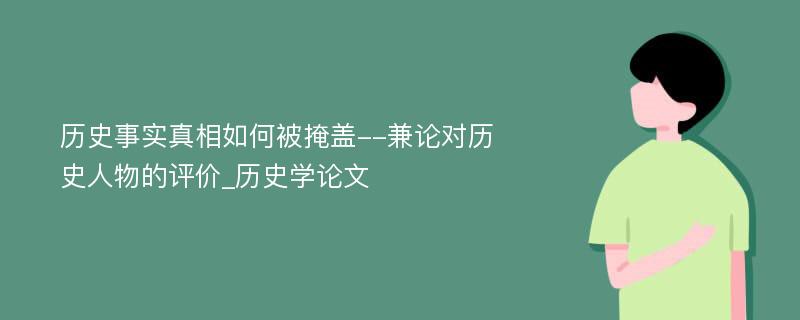
史实真相是如何被掩盖的——兼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历史人物论文,真相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说是历史学中的“老、大、难”问题,“老”、“大”两字,可以不必解释,说它“难”,那是因为一个适当的评价,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史实真相的把握;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评说标准是否合理,两者缺一不可。
澄清真相 谈何容易
通常,我们总是相信事实是可以说清楚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史实(诸如“昨晚邻家猫生子”之类)总是说得清的。评价可以不同,事实必须说清楚。一位历史学者如果对史实真相有所隐瞒、夸大、歪曲、甚至篡改,那就违反了学科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就该受到批评或谴责。不过,就历史学的现场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实在不少。
众所周知,历史中有许多史实真相说不清,是由材料的缺乏所造成,这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原因。然而,并非只有客观原因。西方历史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史实“说不清”的主观原因,比如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就“造成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因素”,列出了“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根本的哲学冲突”等原因[1]。其实,从根子上说,史实真相的“说不清”都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差异、或冲突所造成。人们能够理解因为史料的不充分而造成的说不清,却不太注意因“利益关系”的差异、对立而造成的对史实真相的隐瞒、歪曲和篡改。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斯堪的那维亚人究竟可曾对早期俄国历史做过什么贡献?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人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是大部分来自这些斯拉夫人,还是仍为纯粹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是先于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呢,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家后才来到此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按照政治——民族的路子来长篇大论地进行讨论的。只要政治上不卷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论据后面的偏见[2]。显然,因为涉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史实真相就不容易说得清。或许历史学家“心里明白”,但他只能缄口不言,或者有所隐瞒,甚至不得不有所歪曲和篡改。由此可见,史实真相之说得清或说不清,全看史实与我们的关系。过去的史实一旦直接或间接地与当下人们的利益得失扯上了关系,它就不容易说清。
自然科学的事实一般是中性的,社会历史学科中的事实则牵涉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已有所论述。[3]而且,有例可举。1923年10月,列宁曾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个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四、五种传记、年谱),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4]。因为涉及当年苏联领导人的利益问题,史实真相就不允许你把它说清。史学家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书中,也列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事例: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消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例,在中外的历史上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古奇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历史真相的,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5]。人们常说,“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倘若社会未能建立有效的“生存保障”而要求历史学者都像南史氏、董狐那样为秉笔直书而冒死以赴,这样的规范非常人所能做到。于是,通称的做法只能委屈史实,让真相保持沉默。
借用克罗齐的说法,历史编年处理的是“死的历史”,历史评价涉及的是“活的历史”,“活的历史”也就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联系、显示意义的历史,也就是最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相信史实真相总是可以说得清的,那是把历史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
“自我审视”与等待时机
下面所录的一段话,虽写于20多年前,但现在还很难说是已经过时。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不同。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如果与此有牵连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现代史),其内容、趋向,与现实中的主题精神相一致,那自然好。但历史上的主题内容,论证起来与现实中的主题不协调、有分歧是经常的。碰上这种情况时如何抉择呢?不必迟疑,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应首先尊重现实中的主题。这不是历史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论证历史问题的任务与现实中之斗争的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别。把进入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暂时放置不做,将来可做,后人可做。这与涂抹篡改者不同,无损于历史家的风格。这样做,是历史家与人民在现实中统一步调,保持一致,恰是表现其政治上的严肃性,同时也无害于历史科学[6]。
从学理上说,当一门学科的研究,在陈述其研究结果或者事实真相时,不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还要看一看它是不是与现实主题相协调、相一致。这种学科的研究状况很难使人把它与科学精神、科学品格相联系。然而,这种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中外的史学史上是普遍地存在,即许多历史学者会自觉或不直觉地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审视其与现实主题的关系,以便决定哪些是可以径情直遂、秉笔直书的;哪些是应该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的。然而,就破坏史实的真实性而言: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与涂抹、篡改,或许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历史学者的“自我审视”,造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种怪现象。比如,潘旭澜先生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一文中讲到的“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7],这原本是不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做什么考订发掘才能发现的问题。有关的史料不仅很多,而且也很容易获得。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却一直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是有意地粉饰掩盖。在这些研究领域里,研究者似乎不想去争什么历史事实的“发现权”或史实真相的“揭发权”,而是等待恰当的时机;不径情直遂,而是有所斟酌,甚至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结果,一些史实的真相,原先是说得清的;后来却又说不清了;现在则又要花些功夫去把它说清楚。一些涉及历史人物的理解、评说问题,常常是说得早不如说得巧。这里所谓的“巧”,意思是指说得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的一些新观点,有不少都属于这类情况。如果我们要追寻学科研究的“发明权”,那么,有些研究思路或角度,甚至有些具体的论述,早在20世纪的前期就已经提出了,80年代后的新观点,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新问题,仅仅是因现实主题的转换,恰逢其时、恰到好处的“旧话重提”。
恩格斯曾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8],这当然是史学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场中的历史学者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要求他毫无顾忌、径情直遂;另一方面,社会责任又要求他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避免与现实主题相背离。一旦他发现自己所揭示的史实真相与现实主题不协调,或者发现他的研究会影响或伤害他所服务的、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利益,大多数历史学者会采取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其结果便是史实真相的被掩盖。
学科规范 功效甚微
科学家的责任是说真话,历史学家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至今仍无有效的办法。《真理的社会史》一书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说真话,不是靠研究者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是靠学科内在的一整套行为规则[9]。其实,真正对自然科学家起到一些约束、规范或制约作用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规范,而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和严格推行。正是后者使得人们能够发现谁在违反规则,谁在篡改、伪造实验数据,谁是隐瞒或剔除不利证据的“科学骗子”。正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及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保证了自然科学家不太敢说假话。当然,科学中的不同门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体而言,规范的运作越正常、越严格,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越强,其对学者的约束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则越弱、越不明显。
由此来看历史学科,毫无疑问,历史学是一门有着自身的学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伊格尔斯在与海登·怀特争论“历史学是不是文学虚构”时就非常强调这一点[10]。只是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检视、识别、纠错的功能是较弱的,且常常未能正常运作、严格推行。仍以有关“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的讨论为例。“作伪的史料不能使用”,这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洪秀全的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穷奢极欲、妻妾成群等记载,都被弃之不用,这似乎符合学科研究的规范。“相反的史料不能回避”,这也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现今,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40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来看,潘旭澜先生的有关“洪秀全的真面目的”几点概括,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们的共识[11],有关洪秀全真面目的揭示,似乎正是依据这一条学科规范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原先被弃之不用的材料现今已是“历史真相的实录”而加以利用的这一转变,并不是靠学科规范自身的运作来实现的。
另外,叶书宗先生在《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讲到苏联史学界对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及其评价的经过,也可以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一个案例。有关布哈林的真实史料早已存在,“作者确曾查阅过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但他“却不根据事实来写历史”。直到20年后,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才得到了澄清和纠正。[12]但这时候的澄清和纠正也不是靠学科自身的发展(如史料的新发现)和学科规范的正确运作(学者依据学科规范的互相检视、纠错等)来实现的,而是俄罗斯的现实社会“允许、需要”这样的“澄清和纠正”。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运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变换,那么,这些学科规则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保证历史学的真实性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上述的3点讨论,都只是涉及到有关“史实真相”揭示上的困难,都还是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方面,“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侧方,则牵涉到我们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一旦进入到后一个领域,历史学所表现出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样多变、反复无常”特征似乎为其他学科所罕见。这构成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方面的困难。不过,这已经属于另一类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