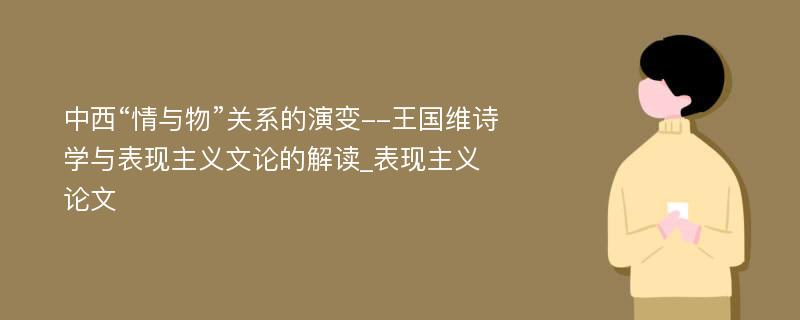
中西“情物”关系的演变——王国维诗学和表现主义文论的互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现主义论文,诗学论文,文论论文,中西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0X(2015)04-0084-03 王国维和西方表现主义在艺术本质上的一致性体现在两者对“真”的理解中,两者对主体创作文学的“真”就是让主体“真心实意”的观照事物,因此,要准确的判断两者是否是同一个“真”要回到中西方对“情”的理解中去把握。 1 西方文化视野中的“情物”关系 西方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与他们有史以来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作为一个以出海贸易为生的海边民族,冒险和探索是他们的本性,其骨子里就有探求事物本质的性格,主动性很强烈,主体的地位也在无形中得到赞赏和认同。西方的哲学对文学的审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哲学中最重视的就是理性,理性使得西方人尤其重视自身的价值。人的自由观念是不可限制的,因此将主客体的关系划分得特别清晰,客体永远处于低下的被动的角色,而主体的地位一直高高在上。德国文学家路德维希·鲁比纳在《时代回声》中说出了表现主义作家们共同的艺术观:“不要为艺术而艺术,而要为人而人。”[1] 主体至上的观念在西方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西方人对主体“情”的看法有些悲观,采取的是消极态度。他们认为,情感是在受罪,人因为有情感而产生欲望。这个世界是缺乏生机的,活力必须从外灌注。柏拉图认为,世界本身是“相”,这个“相”是现今世界的发源地,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人一旦有了情感的输入就离纯粹的“相”越来越远。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跟柏拉图的“相”是差不多的意思。对于他们而言,自然世界——就是“物”——只是处于客体的位置,是无价值、无意义的“质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他们强调人的地位,突出人的价值。但亚里士多德对客体也是有定义的:“凡是带有现实感的东西都能把事物带到我们面前。”所谓“现实感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物”。在此,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了关联,并且客体是被动的,必须被主体灌输情感。主体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康德在审美判断领域用审美活动打通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美学家们试图寻找主客体融合的方式,转变两者对立的局面。立普斯是移情论的杰出代表,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美学理论,他说:“审美欣赏的‘对象’是一个问题,审美欣赏的原因却是另一个问题。美的事物的感性形状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但也当然不是审美欣赏的原因。毋宁说,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或自我,也就是‘看到’‘对立的’对象而感到欢乐愉快的那个自我。”[2]“移情说”的基本观念就是客体是无情的,主体将主观感情“嫁接”或者是“转移”到客体上,使客体拥有主体的意识,仿佛客体有了生命。立普斯认为主体在客体中看到了自己,然后欣赏自己,从而产生美。在《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一书中他对“移情”做了这样的解释:“移情作用就是这里所确定的一种事实;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曾存在。”[3]立普斯提出的“移情说”虽然拉近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可他的理论中主体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情物关系”发展到20世纪初期,表现主义美学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先驱人克罗齐更是名噪一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交替时期,及以后至少二十五年时间,贝奈德托·克罗齐关于艺术是抒情的直觉的理论,在美学界居于统治地位。”[4]表现主义是继承康德美学之后以克罗齐和科林伍德为代表的美学流派,克罗齐在康德的理论基础上给予艺术自主更多更全面的解释。“克罗齐比现代其他美学家更强有力地总结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艺术思潮。他鲜明地标榜一种艺术哲学,即每件艺术作品是一个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现,因此是一种创造(只受它自己规律的支配),而不是一种模仿(受外在规律所支配)。”[5]这种极端的唯心主义思想是表现主义思想的基本倾向,决定了表现主义美学的本质,“艺术的直觉永远是抒情的直觉”。[6]克罗齐认为艺术的精神是个体精神,这种想象力的活动只是针对个人的意象,与事物外在粗糙的材料、颜色、气味等物理性质没有关系。克罗齐否认艺术中事物的物理特性,就在于他想要阐明艺术的不可模仿性。艺术创造的结果是个人意愿和受个人意愿影响的外物的结合。在论艺术和传达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艺术是“心灵的事实”,能传达的作品就不是艺术品,这个观点备受历来学者的指责。“传达活动同样包含着艺术家的想象活动,并且是艺术作品完成的必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传达活动比艺术家头脑中的想象活动更丰富更重要,因为只有被传达出来的东西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品。”[7]克罗齐最著名的美学论断“美即直觉”,是表现主义的核心命题。“直觉”二字继承于康德思想,并在康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康德认为“感性”一词是认知方面的意思,而在西方,“感性”一词除了认知以外,还有情感、情绪的含义。克罗齐就是在此让“情感”重新回归到“感性”之中。“克罗齐把美学的对象看作‘直觉事实’,把美学自身看作‘直觉认识的科学’。”[8]直觉事实就等于感性认识。那么,美是有情感的。“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9]。克罗齐对“情感”做了明确的定义:“情感,或灵魂状况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内容,而是用直觉范畴所看到的整个宇宙。”[9]P235情感是一直跟随着人的生活,心理对世界事物的任何感受都可以称之为情感。在克罗齐眼里,直觉就是表现,直觉产生的就是形象。表现主义作品表现的人的异化、人和社会的矛盾、人的压抑和烦闷等内容,就是直觉之后在感情逼迫需要下创作出来的,艺术手法的变形掩饰并不能否认激烈言语所透露出的真实。“情”和“物”的关系紧密联系。“‘美感经验为形象的直觉’是克罗齐的说法。我以为这个学说比较圆满,因为它同时兼顾到美感经验中我与物两方面。”[10] 2 中国传统文化观中的“情物”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自然当做神灵一样膜拜,天人合一成为人们的理想。古老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观念一直徘徊在文学审美研究的门口,情物关系也要符合这种“大一统”的思维。先秦时期,“情”作为和“志”对立的另一面,随之被赋予浅薄的“私情”上的理解,“情”是“志”的附属物。到汉代的时候,结束了先秦儒学“情”和“志”分离的状况,不像以前诗是遵守儒家规范“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条。汉代陆机写《文赋》的原因就是要解决文章“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这里的“意”指的就是情,“物”指的是文章描写的对象,包括自然风景和社会现象。这个时候“缘情”说被正式确立,情感得到了解放。刘勰主张心物交融,一方面“情以物兴”,另一方面“物以情观”。“情物相生”反射出来的意思:一是情感染物,二是物有了情态,并反射到诗人身上,加深诗人的情绪。刘勰的发展不仅在于他情物融合的理论,更在于他首先提出“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观点,指出感情的“联类不穷”。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由“言志”转向“缘情”,“缘情”说的气势盖过了“言志”说,创作方式上突破了儒家的礼数;书写内容从以大的政治教化为中心转变为写个人悲欢交际。此时对“情”的理解已经彻底摆脱了诗教的束缚,此后的“情物关系”也一直处于“情景交融”的状态中。唐宋时期,王昌龄提出“三境”说,最高的是“意境”,寄托了诗人更深刻的思想和生活哲理。司空图的“思与境偕”和周弼的“虚实”说都是在借鉴王昌龄的学说中从情物融合的关系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明清时期,王夫之认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在他的论述里,“情”和“景”是处处相伴相生的,有情处必有景,有景处则终有情。 王国维“境界”说的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达到了对情物关系理解上的高峰,“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他提出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境界说”和“写境”和“造境”的创作方式都是值得我们慢慢探究的美学理论。他的著作《人间词话》,虽然篇幅短小,但内容精深细微,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理论和西方美学理论的精华。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它借鉴了西方的审美经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点。他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里写道:“故经验之世界,乃外物之不入于吾人感性、悟性之形式中者,与物之自身异。”王国维已经从中国古代传统的由情到物的审美方式,转变到西方由主体向客体灌输情感的审美体验中去了。他在《人间词话》上卷六十一则写道:“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令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现实的“人”已经在王国维这里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诗人要登高望远,居高临下,发挥自己的主动权奴役外物。西方重主体轻客体的思想早已经深深嵌入王国维的美学体系。“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王国维认为‘情’始终是一个最活跃(能动)的‘原质’,由于它才沟通了‘主观’与‘客观’的根本关系,把主观能力的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11]主体的地位提高,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在此得到验证。 3 中西方“情物”关系的汇通 中西“情物关系”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从发展脉络来看,西方的主客体关系尤其注重对主体的阐释,主体的张扬成了他们共同所要表达的东西,而外物只是主体抒发感情的手段,没有任何活力;在中国,我们看重的是“情物合一”的过程,这和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谐”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情”必须寄托在“物”之中,“物”也会因为“情”而变得更加人化。窥看中西两种“情物”发展的细节之处,我们可以得知:尽管在探索情物关系的初期,彼此是从两条不同的线路出发,可最终还是不约而同地走在了情物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结局下。罗显克认为中西“情物关系”的不同在于西方的“情”是关于人的性格、生命和精神状态,而中国的“情”是指人的情感,主要是指个人的情感状态。然而,对于情的内涵问题,中国的“情”也并非只是人的感情这么简单。的确,我们就人的感情在诗词中的表现可轻而易举的举出很多例子来,但同时也可以发掘中国诗词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描写。例如,王国维最为欣赏的李煜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两词句,不难发现个人情感的细细碎语,也难以磨灭对人普遍生存境地的担忧。自然之物生死循环的不变法则,折射出人在遇到困境时难以自救的无奈。这里的“情”已经超出了个人情感,转向更高的普遍的人的精神状态上。同样的,西方的“情”也不都是在反映博大的全人类的性格上,对于个人的心境也作诸多描绘,“一种活泼的情感变成完全是一种鲜明的意象”“客观现实的再现变成了主观感情的表现”[12],个人的情感借助现实事物得到完美的呈现,作品即是作家自己的,投入情感的深浅也必定是作家自己的事。“每一位创造性艺术家自己使用的表现手段都是最好的,因为它能够最为恰当地表达出这位艺术家所强烈希望表达的东西。”“形式反映出每个艺术家的精神,打上了艺术家的个性烙印。”[13] 收稿日期:2015-05-21 修回日期:2015-06-08